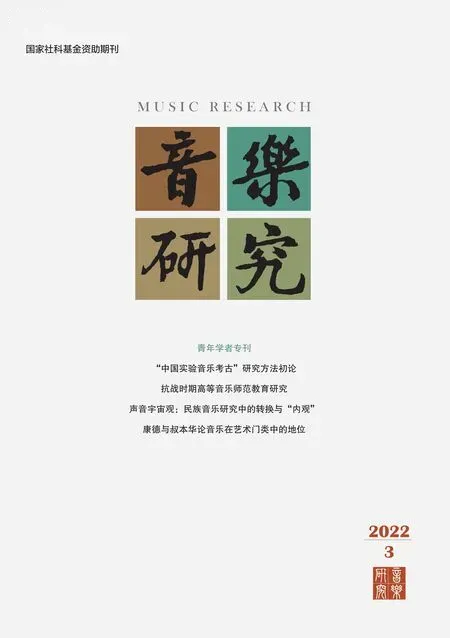阈境的幻视
——林瑞玲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理念及技法研究
文◎谢 天
一、林瑞玲的音乐作品
作为一位成果卓著的现代作曲家,林瑞玲的作品很早就引起了业界关注,并在美国、法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意大利及澳大利亚的许多著名音乐节上展演,曾获得多次国际作曲比赛大奖。
林瑞玲曾从自己40 多年来创作并发表的95 部各种体裁的现代音乐作品中,甄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创作成就的7 部器乐作品和5 部歌剧作品,来代表她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声音“符号”的理解,以及她的多元文化创作观念。
(一)现代歌剧作品
林瑞玲的5 部现代歌剧作品,不仅在题材内容方面体现了其多元文化的意识,在音乐表达方面更是突破文化的时空局限,任凭思绪驰骋于多元境界的典型表现。《俄瑞斯忒亚》(The Oresteia,1991——1993),是林瑞玲创作的第一部歌剧。这是一部为6 位歌唱家、11 位演奏家和舞者而作的7 幕现代歌剧,脚本主要改编自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同名戏剧三部曲。虽歌剧故事以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为蓝本,但作曲家所展现的情节内容和音乐风格,却是她对多元文化元素的理解、提炼与重组。第二部歌剧《月灵节》(Yuè Lìng Jié,1999——2000,又名Moon Spirit Feasting,即“月灵宴”),是她中国文化情怀的一次独特表达。第三部歌剧《航海者》(The Navigator,2007——2008),是一部“梦幻”歌剧(a “dream” opera),该作品意在探索激情的极限,以及在毁灭或创造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性。作曲家在这部歌剧的乐队配置中,加入了巴洛克竖琴、抒情中提琴、羽管键琴等独具风格的乐器,在音乐中又引入了“曾经激励她创作这部歌剧”的瓦格纳歌剧的一些新元素。第四部歌剧《树木编码》(Tree of Codes,2014——2016),是为女高音、男中音和16 位音乐家而作,表现了血统、记忆、遗忘、时间和启发等主题。第五部歌剧《天空之图》(Atlas of the Sky,2018),被称作是一部后现代“跨体裁的歌剧”(a genre-crossing work)①参见网页信息Liza Lim, Long Bio. 检索网址:https://lizalimcomposer.com/(2020 年5 月15 日)。:在舞台结构上部分是常规歌剧,部分是女高音演员们呈现的集体仪式,即由3 位打击乐手和群众演员共同表演的一部形式变幻莫测,表现“群体力量”的歌剧。
总体而言,林瑞玲创作的歌剧作品,在体裁形式上基本上都属于简约而复杂、感性而抽象的后现代风格,表演形式常为两到三人演唱,三到十几人的乐队伴奏,主题虽来源于不同文化传统,但却不是对传统的写实性呈现,而是从传统中抽离出用音乐的感性形式来传达其理性意念。所以,这些作品无论从题材的多样性还是从体裁的现代性上,应该是能代表林瑞玲创作思想和人文情怀的重要作品。并且,林瑞玲的歌剧作品从主题内容到音乐元素,都表现出她对跨文化“边界”的突破,以及对多文化复合元素的综合运用。这样的创作理念,以及通过音乐表达其文化价值的追求,在她的器乐及其他声乐作品中也有体现。
(二)器乐作品
林瑞玲自选的7 部“节点性”器乐(包含声乐元素)作品中,室内乐《人间欲望花园》(Garden of Earthly Desire,1988)是作曲家的开山之作,标题和创作灵感来源于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命运交织的城堡》(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1973)这部寓言文学作品,音乐表现的主要是意大利文化,但也包含了更加多样的含义,“仿佛嵌入了西方文化的数百年历史记忆”,所以在音乐结构上表现为“碎片化的、爆破式的所谓‘残骸’体结构”。②Lim Programme Notes: Information About My Compositions. July 27, 2011.检索网址:https://limprogrammenotes.wordpress.com/page/6/(2020 年5 月15 日)。可见,林瑞玲从其步入创作的初期,就开启了多元文化“混搭”和多样技法“拼接”的后现代作曲模式。
《不可视》(Invisibility,2009),是大提琴采用双弓演奏的一首独奏曲,作品主题是基于澳大利亚土著“存在美学”(aesthetics of presence)中的所谓“闪光”(shimmer)概念(既揭示又隐藏了神灵的存在)。作曲家解释,“不可视”这一作品标题,不是要表现声音的沉默,而是要表达一种不可视(听)但却潜在于内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在作品中是通过大提琴的物理结构,以及弓毛系法不同的两杆琴弓摩擦所产生的不同振动效果来表现的。③Lim Programme Notes: Information About My Compositions. August 2, 2011.检索网址:https://limprogrammenotes.wordpress.com/2011/08/(2020 年5 月15 日)。
《无形之舌》(Tongue of the Invisible,2010——2011),是为即兴钢琴演奏者、男中音和16 位乐手设计的一部“预置音乐”,主要表现对爱的广义理解,音乐中融入对神的崇拜、性欲的狂喜,以及对世俗与神圣、感官与超验的感悟等内容。音乐的“预置”,主要体现在使用系统的即兴创作设计与演奏员密切合作,即音乐采取预先创作的部分与现场即兴演奏的部分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让音乐的固定因素(作曲)与开放因素(即兴)展开对话。这样的“预置音乐”,对表达宗教的神秘性及其诗意的多解性和不确定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性的巫术》(Sex Magic,2019——2020),是一部“关于女性历史上神圣情色的作品”,以女祭司的占卜、预言,以及女权、身体、子宫、分娩等内容,表达一系列另类文化逻辑。作品采用了特殊的乐器组合形式,主要编制有:倍低音长笛(Contrabass flute)、现场电子乐器(Live electronics)和新发明的所谓“动能”打击乐器(Kinetic percussion);作品中倍低音长笛“扮演”着女祭司形象,成为神谕发声的通道。
除了7 部“节点性”器乐作品外,林瑞玲还有许多其他器乐/声乐作品也广受好评,同样体现了这位作曲家一贯坚持的题材“多元性”和技法“创新性”特点。比如,在以澳大利亚土著育伦古族(Yolngu)艺术为灵感的作品中,如《暗影下的幽光》(In the Shadow's Light,2004)、《闪光》(Shimmer,2005)、《梦景中发现的歌》(Songs Found in Dream,2005)、《胎 动》(The Quickening,2004——2005)、《闪光的歌》(Shimmer Songs,2006)、《赭色之弦》 (Ochred String,2008)等,都将“闪光”(Shimmer)④“闪光”(Shimmer),是澳大利亚育伦古族土著美学中具有核心价值的审美范畴。原指土著艺术图案中一种以点交错的阴影线条营造幻视的特殊美感,它不仅显现为物质的创造性转化,也被认为是先祖精神力量的象征,同时具有“揭示”和“遮蔽”的双重特征。这一土著美学概念,用多文化的特征性音乐元素加以表现。又如,在《航海者》(The Navigator,2008)、《世界之轴》(Axis Mundi,2012——2013),以及《灭绝事件与黎明的合唱》(Extinction Events and Dawn Chorus,2017)等作品中,作曲家又分别对人与动物、常态与超自然、当下与永恒之间的关系,进行“变移性”认知的音乐化处理,由而体现出一种无法预测且充满暗示的“知识转变”。⑤Tim Rutherford-Johnson. “Patterns of Shimmer: L iza Lim's Compositional Ethnog-Raphy.” Tempo, 65(2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9.
林瑞玲的许多作品,不仅得益于她对全球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域声音特征的敏锐感知,也源于她立足现实的开放性好奇和对不同声音“信号”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敏感领悟。她正是带着对跨文化的关注与思考,用音乐去审视和寻找多元文化的内在精神。因而在她的音乐表达逻辑中,他不在于对文化声音样式进行“廉价的模仿”,而是从其自身的“文化边界”立场或“中间位置”,用创新的作曲技法和微妙的听觉感受去阐释跨文化的艺术本质。
二、林瑞玲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理念
林瑞玲华裔血统与其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共同赋予了她东、西双重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似乎必然会使她在创作中借助于“复合文化”的优势,但实际上,她的艺术在提纯过程中,常常会超越两种文化的拥趸而升华为新生的艺术认知。
我的家庭背景是中国人,虽然我出生在澳大利亚,我是我们家第三代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我的第一语言是闽南语(汉语方言),在文莱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式教育下,我的闽南语很快被英语所取代……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是一个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截然相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人们常常会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地方”的关系,也经常会意识到自己的“移民”身份。当我从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继续探索我对“中国文化”的想法时,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把“中国”作为一个内部景观(Interior landscape)的象征,我自己也心存“边界”地旅行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内部景观之中,寻觅着新的发现。⑥Liza Lim.“ Critical Commentary & PhD Folio.”Thesis of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01, p.15.
从上面这段自述文字中,我们可大致领会到这位作曲家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内省,以及如何用音乐去表达中国文化的心理准备。林瑞玲明确以中国文化事象为创作依据的大型作品主要有两部:一部是表现“中国 仪 式 街 剧”(Chinese ritual street opera)题材的歌剧作品《月灵节》;另一部是以曾侯乙墓(及其出土乐器、兵器和殉葬乐伎等)及中国象征文化为创作意象的大型室内乐《沟通亡灵的明器》(Machine for Contacting the Dead,1999——2000)。
《月灵节》的歌剧脚本,由澳大利亚作家贝丝·雅普(Beth Yahp)编写,演员由3 位歌者和9 位演奏者共同担任,角色有月亮女神嫦娥、后羿、美猴王、西王母娘娘等神仙,也有僧人、巫师、小丑,以及看不见的“游魂野鬼”等。故事由中元节为饿鬼施食仪式、节日走街歌舞、嫦娥奔月、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及王母娘娘叙事等组成,是从阴间到人间再到天界神仙世界等一系列中国民间神话、节日民俗元素的拼接和混搭,剧情“充满了神秘、疯狂、混乱的气氛”⑦Lim Programme Notes.检索网址: https://limprogrammenotes.wordpress.com/(2020 年5 月15 日)。。这种把中国节日民俗、民间故事等元素“串烧”式拼接在一起的故事编排和音乐表现,看似荒唐不羁,迥异于中国人对自我文化的审美与认知,实则体现了这位华裔西方作曲家审视、体验和表达中国文化的一种不同于中国作曲家的另类表达。在《月灵节》中,由“混乱”而产生的荒诞性,主要还是出自于脚本的构思和主导。作曲家的表达逻辑,实则是站在东西文化的“中间位置”,重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一种新探索。这部歌剧并未采用将西洋乐队与中国二胡、日本筝等东方乐器进行简单融合的方式,而是在东、西两种异质乐器声音之间寻求某种样式上的“统一感”与“近亲性”。作品既没有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曲调,也没有选择中国民族式歌唱方法,而是将传统音乐观念、演奏者的音乐观念,以作曲家的超越性创作思维直接反映在作品当中,从此展开对新的“音世界”的探求。
《沟通亡灵的明器》,是林瑞玲受法国Ensemble Intercontemporain 现代乐团的委约,为配合2000 年11 月开始在巴黎“音乐博物馆”(Musée de la musique)举办的“中国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的演出,而创作的一部专题性作品,也是这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华裔女作曲家,以她不同于中国本土作曲家的独特视角来表现中国古老文化遗存的一部特殊作品。林瑞玲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
所有这些都为我的作品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启示意义的原始材料,在一种近乎歌剧感的场景中,设置出一个万千世界。这不禁让人想到考古学方面的问题,以及“地下建筑”(镜像的世界)、被禁声的“仪式性宫廷音乐”等映象;同时让人联想到被保存下来的这些乐器在其静默表面下已经消逝的声音;也让人认识到墓室中物体摆放的风水方向;还让人意识到嵌入这些乐器、器皿和铭文中的宗教文化体系;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那些和曾侯一起活生生地被殉葬的女人们的可怕命运————这一切都是非常具有暗示性的。陵墓的建造和内部物品的放置也让我感兴趣,它是一种来自彼岸的文化映射。这座陵墓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死界线的标志,它提供了一个让生者可以向祖先诉说的仪式中心,是作为一种与灵界(Spirit world)沟通的设备(Instrument)或“机器”(Machine)。⑧同注⑥,第68 页。
林瑞玲对这一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墓考古发现的观感与视角,与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音乐家显然大不相同。当我们把这一墓葬出土的“文物”看作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中国古代辉煌的音乐文化和高超的乐器制作技术(尤其是青铜编钟的冶炼和定律技术)的例证时,林瑞玲发现的却是一套具有戏剧性场景感的古代陵墓布局,是该“地下建筑”所反映的中国古代侯爵生前的一个“镜像世界”,是陵墓中宏大而精致的古代乐器所鸣响的辉煌仪式音乐,是这些被埋葬于地下而遭“禁声”的古老乐器两千多年来的静默守候。最终,她把所看到的这一陵墓奇观,定性为“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死界线的标志”“一个让生者可以向祖先诉说的仪式中心”“一种与灵界沟通的设备或机器”⑨同注⑥,第68 页。。这就是作曲家为什么将作品标题命名为Machine for Contacting the Dead的原因,也是笔者之所以将英文标题意译为《沟通亡灵的明器》⑩笔者之所以将其译作《沟通亡灵的明器》,主要是参考了作曲家本人在曲目介绍中引用的孔子的相关说法,即《礼记·檀弓下》所载:“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明器”一词在中国考古界主要是指随葬的实物仿制模型(而非实物本身),而该作品虽以中国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实物(古代武器、乐器等)为表现依据,但作品标题中的Machine 一词所指代的其实并非出土实物本身,而是指隐喻着精神力量的一种器物。故而,笔者此处将作品标题中的Machine 译作“明器”,也是本着作曲家本意所指,意为“神明之器物”。的原因。此外,用“Machine”作为作品标题中的主语,本身就说明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核心内容并不仅是曾侯乙陵墓及其墓葬器物的物象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从物象中抽离出来的一种引申含义。可以说,以具体的物象为创作灵感的来源,在音乐表现上却超越对具体对象的描述,表达从中抽象出来的理念感悟。这种看似理性却又化理性为感性体验的思想表达途径和音乐表现方式,正是林瑞玲在其大部分作品中一贯采取的适用于音乐(尤其是纯器乐)的表达方式。或许,这也是林瑞玲通过音乐来表达其哲理思想、情感感悟的,值得赞许的一种创作策略。因为,用音乐简单地模仿或“再现”某种具体的事物,本身就不是音乐所擅长的。
三、《沟通亡灵的明器》的创作策略及技法分析
(一)乐章结构及标题意向
将具体物象作为灵感来源或表达抽象思想的一种“媒介”,这种创作策略不仅表现在这部作品的总标题上,也是该作品五个乐章都遵循的一种表现方法(见表1)。

表1 《沟通亡灵的明器》五个乐章的标题
从《沟通亡灵的明器》总标题和各乐章分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些标题本身就部分地表达了作曲家林瑞玲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向。在这些推进个人体验、唤起物象内在“生命”的标题背后,是作曲家对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意志性捕捉与重新认知。可以看出,作品的布局与墓地内部的结构形态存在深层关联。
(二)乐队音响的结构布局
本文的主标题是“阈境的幻视”,其中的“阈境”一词,是指“犹如以门槛为界线的一个特定环境空间”⑪参见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0 页。。在《沟通亡灵的明器》中,笔者感受到的“阈境对立”,是作曲家林瑞玲借鉴几何透视法设计的虚实结合、错综复杂的音响空间对置。“幻视”(Vision),既指作曲家在创作时对彼岸文化象征性的理解视角,更是一种以传达音响能量为目的的特有感知,这正是作曲家内心听觉中反复追求的创造性转变。尽管这部作品对音响逻辑的想象原型,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钟、磬、丝、竹等中国古代乐器,但是作品的乐队编制仍是西洋乐器,其中没有用到任何具有显著音色要素的中国传统乐器,只是在三组打击乐器中汇集了多种中国与东南亚的锣类乐器。仅从乐队编制来看,也体现出作曲家对中国题材(尤其是以中国乐器、声音意识相关的中国题材)的“另类”创作理念。
(三)自性的音高结构表述特点
为了控制材料在听觉上的持续整体统一感与表述逻辑,“主要音”“轴心音”“单一音”等特定的技术观念,已成为现代音乐创作中具有精神内涵的主要方向之一。林瑞玲在这部作品中虽然寻求着跨文化的精神方向与时空体系,但是从她具体作曲技术的范畴中不难看出,其音高结构及旋法样式的生成,都关注着某种联结精神领域的方法:或是以复合层次的碎片化材料同步来探索超现实的情感世界,或是以乐器特殊演奏法中脉冲般的听觉效果来联系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的“闪光”美学。但笔者认为,这些个性突出的技术背后所隐藏的非理性经验根源,主要来自作曲家对自己谙熟的东南亚文化的审视与理解。这种对于文化属性与声音形态的感受方式,同样也会渗透进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音乐化表达中。
在音高结构的设计方面,林瑞玲将音高划分为几个活动区域,同类音级组合可以自由替换的音高控制手段。这立刻让笔者联想到艾尔诺·兰德卫(Ernö Lendvai)在分析巴托克作品时提及的“轴心体系”技法。在第二乐章“灵器(一)”中,核心音高的贯穿手段与弦乐器演奏法中的逻辑习惯(尤其是泛音的驻波性质)有着微妙且密不可分的联系————乐曲开始小节,在大提琴两组泛音滑奏的基础上(第一拍的♭b2——♮b2,第三拍最低弦♭A1上第5 泛音c1到第3 泛音♭e 的下滑),通过左手按弦压力的变化(按实第一拍中♮b2的四度人工泛音点♮e1),共同形成了两个相差小二度关系、以纯四度为框架的核心音程(♭B——♭E/♮B——♮E)。将其进行结合,还可生成为一组框架音程跨度为三全音的中心对称四音列(♭B——♮B——♭E——♮E)。这种音高关系,仿佛曾国徽记中两组分别以阳刻与阴刻为雕刻手法的龙,不仅内部互为倒影关系,且经过整体倒置(以四音组顶点音E 为轴心向上进行的整体音列倒影E——F——A——♭B),即可与原型构成一组首尾相称的收拢性链环;此外,这些中心音高在不断流动的泛音触发中,也被“拖拽”至不同八度的音域空间得以突出,犹如沿着一条“隐性音轴”螺旋地移动,并以不同形态贯穿在整部作品的发展思路中。这样的音高组织观念,与兰德卫的“轴心体系”虽不相同,但综合上述两种关于“轴”的独特含义,按笔者的理解可称之为“核心音轴技术”(见谱例1)。
“核心音轴”在横向音高组织中的生成原则与偏移策略,不仅与线条结构的张力相关,还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旋法特色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以回避传统和声概念为标准,在不协和的进行中有指向地处理音列组合的嵌套关系,同时在听觉中产生的时间倒错感(对小三度结构的破坏)也赋予了音响独特的平衡价值。
(四)音乐时间性的多向解释
1.序进与循环并存的时间结构
在《沟通亡灵的明器》音乐的时间叙述方式中,核心音轴的动机式分割与延伸、音响倾向的变化、特性材料在整段内的再现,以及各段之间以相同音高或音色来衔接的“鱼咬尾”式处理(呈持续体的音响状态),这些音乐结构的组织逻辑,显然是在时间的线性尺度中得以展现的。例如,在第一乐章“承载记忆的宫殿”中,第一乐句由低音木管、铜管与钢琴组成的如同重型武器般的低沉音响,与第三乐句(排练号B 开始)中穿插破坏听觉稳定的突变性材料(以两支短笛为核心),综合创造了一种时间感知模式上的先后关系。同样,在该段落主体动力性发展部分过后(排练号J 后开始材料回顾),第二乐器组中“钢筋”般的厚实低音交替(第148 小节),与其后两组木管在高音区间歇性爆发的能量运动,在其技法运用与声音效果方面,均与第一、三乐句中的音响推进逻辑相同;并且,这些材料更以“紧缩再现”的方式,增强了前后呼应的序进式结构模式中的张力,也使音乐可测量的时间构造发生了微妙的伸缩变化。
在笙含蓄而高雅的长气息演奏中,依靠连贯的呼吸变化来唤起一种隐藏的自律化节奏,是其音乐表述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声音的时间形状,也因此不同于日常均衡的线性结构,通过不断变化的材料循环将时间卷为螺旋的样态。根据林瑞玲本人的解释,笙作为“承载记忆的宫殿”中一件“超乐器”(Meta-instrument)的设计原型,它的音响状态与作品的配器方式息息相关。实际上,该段落内局部结构单位的组成关系,也恰好对应着笙声音流动中的循环性时间构造。尽管这可能是作曲家的无意而为,但从宏观的音响布局来看,在结构比例不平衡(带来差异)的小部分之间采用相同特征的音响节点来加以统合,这种处理无疑强化了整体音响发展中无始无终的时间感受(见谱例2)。

谱例2 Spiral structure of time with nodal points of each section, Mov.1, Memory Palace(螺旋形时间结构态及节点材料示意)
谱例2 是以单音或独奏音色为分割依据的结构示意图。这些节点的位置,都处于音响力量较为松弛的“离散型边界”,由于每个结构单位中的声音的气息运动都相对完整,因此,它们综合后所创造的时间感知模式也逐渐表现为在圆形上的多次循环。可以发现,除去转接至尾声的最后一次单音音响设计(第163 小节),整个段落内各结构单位的比例安排,呈现出以中央位置的第5 个节点(第93 小节)为轴心,依次向左右两端扩散的横向对称性设计。不同于作曲家克拉姆(George Crumb)作品中对于音乐参数的严格镜像对称控制,林瑞玲对这些分离的微观结构的音响处理则更加自由,从而使声音避免了由于算术的平衡(功能主义框架)而导致的死板和衰弱。这些局部结构通过时间相位产生的音响间离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出新的音乐空间形式,而是作为对之前部分进行“重读”的起点,在“限制与非限制”中赋予音乐不可预测的时间流动。
2.弹性速度推动的时间“换档”
速度作为音乐整体的第一要素,它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作曲家对于音响运动状态的考量,其自身所产生的弹性更赋予了声音“生”的本体(遵循了自然的物理规律)。此外,无论是西方音乐于理性逻辑基础上布局速度,还是中国板腔体音乐结构方式中的速度推进,其目的皆在于使声音获得戏剧性的张力和变化。由于现代音乐中对于诸多理性因素的破除,作曲家对速度感受的表达也更加丰富而细腻。

表2 第一乐章“承载记忆的宫殿”第31——61 小节速度布局
林瑞玲对这部作品的速度安排,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如她本人所述:
第一乐章中,三位打击乐手演奏的节奏性材料象征着音乐与时间空间的出入口。例如一个5 连音的特性节奏,它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一种戏剧化处理————将音乐材料转移至最高或最低的音域。在第43 小节中,5 连音的非均分结构转化为均分化节奏重复,这象征着一种“换档”:音乐的速度开始加快且叙述更加紧凑,原先的材料也进一步得以丰富展开……⑫同注⑥,第76 页。
在谱例3 中,第40、43 小节的两次“换挡”设计,显然阻断了线性时间的平稳延伸,作为一种“旁观性”的独立因素,它的突然介入促使音响在瞬息间达到了极高的空间密度(也是时间的凝缩)。然而,“换挡”的短促重音材料本应在反复中产生的结构动力,却总被更多气息悠长的和音材料所阻碍(或许源于“抛物线”的速度规律),从而将音响流动“追溯”到之前的氛围中。从这种意义来看,该部分时间流动的方式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重叠,这种难以衡量的时间构造也赋予了音乐随后无法预测的发展可能。

谱例3 Arrangement of tempo of Mov.1, Memory Palace, bars 31-61
结 语
与中国人对自我文化的审美与认知不同,林瑞玲携带着自己的华裔血统和西方文化身份闯进了广阔的世界多文化天地,以华裔身份观察世界,以世界眼光回视中华,用她娴熟的西方现代音乐技术手段,夹裹着古老而新奇的世界文化元素,以新的音乐感受和新的创作思维,表达着世界各地古老文化的重新认识。正如有人对她的评赞:“其作品似乎根植于一切传统,却又如同天外飞仙般无恃无凭。”⑬刘祥焜《不屈的思考者 不倦的实践者————林瑞玲音乐创作中的三个元问题》,《人民音乐》2018 年第7 期,第40 页。这的确是对这位“音乐诗仙”的一个诗意而又十分准确的评价。
林瑞玲作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起步创作的作曲家,她的创作轨迹似乎从未趋于平庸,其艺术主题、技术样式和声音品质,总能在敏锐丰富的感受中衍化出全新的艺术作品。大型室内乐队作品《沟通亡灵的明器》,是林瑞玲在关注中国美学艺术方面的代表作品,是解开林瑞玲音乐中这些微妙的跨文化转变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的一把钥匙。作曲家对她跨文化形式作品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源于其立足现实的开放性好奇与对不同声音“信号”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敏感和自觉。这种以艺术真实性为标志、对跨文化边界血统的审视与寻找声音本体生命的方向性实践,使林瑞玲的作品即使在表现中国主题时也并未追求纯粹的传统中国色彩(乐器、曲调等中国音乐要素),而是以她独特的“双视角”来观照本文化,将特定的传统文化现象转换为一种普适的精神感悟和情感体验,用西方的手段(西洋乐器和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表达出让西方人也能感受到的中国文化意韵。在这部中国题材的作品中,林瑞玲所采用的创作观念和技术手段,不仅代表了一种对于东方文化的“局外式”感悟,更体现出艺术家在个人创作道路中另辟蹊径、不甘平庸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