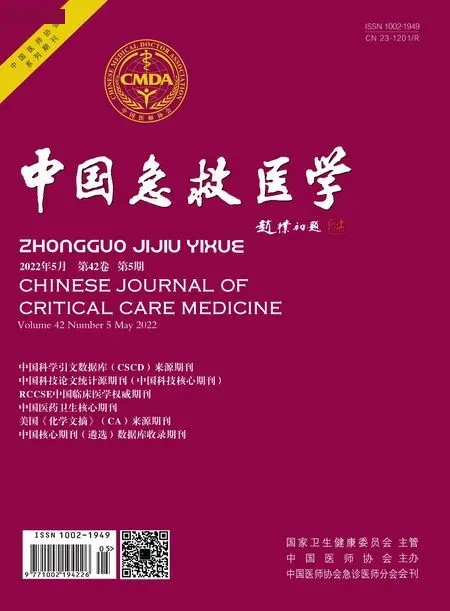胆碱能抗炎通路对脓毒性急性肾损伤的免疫调控机制
史晓翠, 李俊聪, 李文雄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是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脓毒症(sepsis)患者中一种常见而严重的并发症,特别是在老年患者中[1]。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ICU患者发生AKI最常见原因,占ICU中AKI病例的50%或更多,其中成人住院患者AKI病死率为14%~60%[2];AKI也增加了患者进展为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和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的风险[3]。脓毒性急性肾损伤(sepsis-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SAKI)是通过肾血流动力学改变、免疫细胞活化、炎症因子大量释放和内分泌失调等多种机制导致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损伤[4]。免疫细胞活化后产生的炎症反应是SAKI发生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但在针对SAKI的临床试验中抗炎治疗并不成功[5]。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通过胆碱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 CAP)发挥交互作用,即通过迷走神经的炎症反射通路,抑制炎性细胞释放细胞因子,从而阻止进一步的器官损伤,这种神经免疫交互作用有可能成为SAKI的治疗靶标[6]。本文将主要阐述CAP对SAKI的免疫调控机制。
1 CAP的组成与效应
随着近年来对CAP不断深入的研究,可将其作用机制简单概述如下:迷走神经传入纤维的活性受到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危险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以及针对其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刺激后,该信号通过大脑的孤束核和迷走神经背侧运动核激活迷走神经传出神经纤维,传出迷走神经(胆碱能神经)刺激脾交感神经(肾上腺素能神经)释放去甲基肾上腺素,去甲基肾上腺素与脾脏CD4+T细胞上的β2肾上腺素能受体(β2 adrenergic receptors, β2ARs)结合后引起乙酰胆碱(acetycholine, ACh)的释放。ACh与巨噬细胞上的α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icotinic acetycholine receptor, nAChR)结合可产生抗炎效应,抑制巨噬细胞及各种具有α7nAChR的免疫细胞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促炎因子[7]。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通讯可以调节免疫功能和炎症,CAP连接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通过ACh和迷走神经发挥抗炎作用[8]。 CAP是一种抗炎免疫调节通路,被认为是AKI的保护机制之一[9]。CAP主要由迷走神经、中枢M受体、脾脏和脾神经、CD4+T细胞和巨噬细胞、α7nAChR等组成。
1.1迷走神经 迷走神经副交感纤维起自迷走神经背侧核,终止于迷走神经丛的副交感神经节,发出的节后纤维分布于胸腹腔内器官,控制平滑肌、心肌和腺体的活动。迷走神经还可以调节促炎因子的生成[10]。迷走神经的传入支在感受炎症反应PAMPs、DAMPs以及针对其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刺激后,释放ACh,并与中枢神经系统的M受体结合,再通过传出支进行负反馈调节。机体的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单核细胞、树突细胞、内皮细胞等,虽不直接受到迷走神经的支配,但几乎都表达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作为主要的神经递质之一,传出支末端释放的ACh可与这些细胞上的α7nAChR受体结合,抑制其释放促炎因子[11]。对脓毒症小鼠左颈迷走神经进行5分钟电刺激,可以明显降低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并产生包括肾脏在内的器官保护作用[12]。相反,切断脓毒症小鼠迷走神经,可明显增加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和病死率[13]。
1.2中枢M受体 中枢M受体是一种毒蕈碱型胆碱受体,为G蛋白耦联受体家族的一员,弥散分布于节后胆碱能神经纤维所支配的效应器细胞膜上。研究[14]发现,给予极低量的中枢M受体激动剂,短时间内就可以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和炎症的发展。在注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的小鼠脓毒症模型中,注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加兰他敏(galantamine)后,加兰他敏通过迷走神经明显降低血清中TNF-α水平,起到器官保护作用;而注射中枢M型受体拮抗剂则阻断了加兰他敏降低血清炎症因子的作用。进一步研究[15]发现,加兰他敏不能降低α7nAChR基因敲除脓毒症小鼠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这些证据表明,中枢M型受体路径可激活α7nAChR,在控制机体CAP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参与这种调控的中枢性神经元回路机制仍不清楚。
1.3脾脏和脾神经 一旦细菌或细菌产物穿透最初的屏障并进入血液,下一道防线就是网状内皮系统。网状内皮系统包括脾、肝、肺和腹膜等器官或组织[16]。脾脏是网状内皮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CAP的最终反应器官。迷走神经通过其协同效应激活脾交感神经[12]。脾神经远端释放去甲基肾上腺素,并与脾淋巴细胞的β2ARs相结合,释放ACh,再与脾巨噬细胞的α7nAChR结合,从而抑制脾脏巨噬细胞释放TNF-α[17]。事实上,在去脾的动物中,迷走神经刺激(vagal nerve stimulation, VNS)并没有减少TNF-α的产生[6]。给SAKI小鼠注射右美托咪定(β2ARs激动剂)来激活胆碱能通路,发现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明显降低,AKI改善,而后进行的脾切除术则减弱了右美托咪定的抗炎、抗凋亡和肾脏保护作用[18]。在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IRI)小鼠造模前24小时应用VNS,可使肾脏免受IRI。进一步的脾切除小鼠实验和脾细胞过继转移实验[19]表明,脾细胞在VNS对肾脏IRI模型的肾保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在脓毒症模型中,GTS-21(α7nAChR激动剂)注射前的脾切除术减弱了单核细胞进入腹膜腔的募集,消除了GTS-21治疗的生存效益[20]。C1神经元位于延髓,支配迷走神经背侧运动核,对C1神经元进行脉冲波刺激,可减轻SAKI大鼠的肾脏损害。在切除脾的小鼠中,刺激中枢C1神经元没有产生肾脏保护作用,而注射预先与去甲基肾上腺素共同孵育的脾细胞后,其肾脏保护作用得以恢复[21]。由此得知,脾脏及脾神经在炎症的神经调控路径中起关键作用,并为SAKI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1.4巨噬细胞和CD4+T细胞 两种类型的免疫细胞在CAP中起关键作用。一种是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阳性的CD4+T细胞[22];另一种是表达α7nAChR的巨噬细胞[23]。CD4+T细胞和巨噬细胞是CAP激活后介导抗炎反应的关键细胞。小鼠实验证实了CD4+T细胞在CAP中的作用,VNS在野生型小鼠中产生抗炎反应,但在缺乏功能T细胞的裸鼠中不产生抗炎反应;将CD4+T淋巴细胞过继到裸鼠体内,VNS的抗炎作用迅速恢复[22]。α7nAChR阳性巨噬细胞在CAP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尼古丁和ACh等CAP激动剂能抑制LPS诱导的野生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释放TNF-α,而这在α7nAChR敲除小鼠的腹腔巨噬细胞中被消除[24]。这些结果表明,巨噬细胞上的α7nAChR对CAP具有重要作用。
1.5α7nAChR
nAChR是一个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大家族广泛分布于全身的神经元和非神经细胞。这些受体均为五个相互作用的亚基所组成的五聚体,α7nAChR是神经元型nAChR的一种亚型。α7nAChR蛋白是由5个α7亚单位构成的同源五聚体,5个亚单位环绕形成一个中心孔道。各亚单位接合处共有5个配体结合位点,配体与结合位点的相互作用可改变受体的功能状态。
尼古丁是一种α7nAChR特异性激动剂,可降低内毒素诱导SAKI小鼠的血清TNF-α,以及肾脏促炎因子水平[25]。Borovikova等[26]研究发现,ACh可抑制巨噬细胞释放促炎因子,但刺激a7nAChR基因敲除小鼠的迷走神经不能降低其血清TNF-α水平,因此,ACh的作用需由α7nAChR介导。与野生型脓毒症小鼠模型比较,α7nAChR基因敲除脓毒症小鼠血清、脾脏和肝脏中TNF-α水平均较高,表明CAP通过α7nAChR来抑制细胞因子的产生和调节炎症反应。有研究[21]显示,光刺激C1神经元对肾脏IRI小鼠具有肾保护作用,而这种保护作用在α7nAChR-/-小鼠中消失。
2 CAP对SAKI的免疫调控机制
CAP通过胆碱能神经及其神经递质、α7nAChR等来对抗炎症反应。在LPS诱导的SAKI模型中,可在小鼠肾组织中观察到大量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和肾组织凋亡蛋白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3等表达增加;激活α7nAChR介导的CAP,可以明显降低肾组织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上调抗凋亡蛋白B淋巴细胞瘤2(Bcl-2)的表达,减少肾脏细胞凋亡,从而发挥肾脏保护作用[27]。CAP减轻SAKI的主要免疫调控机制如下:
2.1阻断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活化 NF-κB的核易位是调节免疫细胞激活和促炎细胞因子表达的关键调控因子[28]。烟碱性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胆碱)呈浓度依赖性,增加NF-κB抑制因子的表达,抑制LPS激活的NF-κB通路,减少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释放TNF-α,间接抑制高迁移率族蛋白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 protein,HMGB1)的释放,以抑制炎症反应[25]。在脓毒症模型中,ACh 作用于巨噬细胞表面,α7nAChR 可以抑制 NF-κB 的核转位和激活非受体型酪氨酸蛋白激酶2(JAK2)-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TAT3)途径,影响多种细胞因子转录,抑制血浆炎性因子水平[29]。右美托咪定可通过激活α7nAChR-NF-κB信号通路,减轻LPS引起的肾损伤,而脾切除术阻断了NF-κB通路,减弱了右美托咪定的抗炎、抗凋亡和肾脏保护作用[19]。用胆碱、NF-κB抑制剂(Bay11)或蛋白酶体抑制剂(MG132)处理人肾细胞,可有效抑制LPS刺激后的炎症反应。在LPS诱导的SAKI期间,肾蛋白酶体活性是NF-κB介导炎症的主要调节剂,烟碱性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可抑制蛋白酶体活性和炎症,减轻LPS诱导的肾损伤[25]。
2.2抑制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合成与释放
CAP和促炎细胞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多种分子途径。激活α7nAChR、JAK2/STAT3通路,减少巨噬细胞迁移,减轻炎症反应[30]。α7nAChR的激活还可以作用于 Toll 样受体(TLR)介导的信号通路下游的负调控因子蛋白激酶,即白细胞介素-1 受体相关激酶 M(IRAK-M)[31],增强巨噬细胞基因和蛋白水平上的IRAK-M表达,导致TNF-α的产生减少,且沉默IRAK-M基因可明显逆转炎症[32]。IRAK-M广泛表达于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表面,通过阻止 IRAK1 和 IRAK2与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解离,它可以通过与TNF受体相关因子6(TRAF6)结合,干扰活性TLR的下游信号传导,来发挥一定的抗炎作用[33]。
LPS可通过直接刺激肾脏内TNF-α的产生和增加循环中TNF-α水平,引起肾损伤[34]。GTS-21可以有效减轻LPS诱导的SAKI,并减少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同时明显下调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TNF-α的表达[35]。胆碱作为一种nAChR激动剂,它可降低血清TNF-α以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CXC型趋化因子10(CXCL10)等促炎因子在肾脏的浓度水平,从而改善肾损伤[36]。脾切除可明显降低脓毒症小鼠血浆细胞因子和炎症反应的晚期调节因子HMGB1水平,提高小鼠存活率[12]。小鼠脓毒症期间VNS也会特异性降低脾巨噬细胞释放TNF-α,改善全身炎症反应,保护器官功能[37]。
2.3阻止T细胞分化与成熟 烟碱性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尼古丁可能通过促进转录因子GATA-3 mRNA的表达,抑制T细胞mRNA的表达和免疫细胞的异常活化,以控制炎症反应。体外实验[38]表明,尼古丁可通过影响靶细胞的裂解而改变免疫细胞,减少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诱导T淋巴细胞抑制细胞活性,进一步控制炎症的发展。烟碱同样能影响与T淋巴细胞增殖或活化相关的细胞因子分泌,来进一步调控免疫反应[39]。
3 CAP抑制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杀伤功能
AKI的发生伴随着白细胞在肾实质中的募集,这是内皮细胞黏附分子和趋化因子表达增加、血管解体和血管通透性增加的结果[40]。其中内皮细胞的激活在白细胞募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胆碱能激动剂可有效抑制内皮细胞的激活,VNS也可通过CAP明显抑制白细胞迁移及其杀伤功能。研究[41]显示,在中性粒细胞上存在多种α7nAChR,刺激烟碱受体可以抑制中性粒细胞迁移,进一步降低其杀伤功能。
4 总结与展望
炎症反应是SAKI发生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但在临床试验中减轻SAKI炎症的药理学治疗并不成功。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存在交互作用,神经系统调节免疫系统,反之亦然。CAP是神经-免疫交互作用的一条具有代表性的调节途径,已被证明在SAKI动物模型中调节全身炎症反应和肾内炎症反应;VNS或CAP激动剂可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和肾组织炎症因子水平,从而缓解脓毒症诱导的AKI。迷走神经刺激器已被应用于临床,治疗各种疾病,因此,被证明是一种很有前途的AKI治疗方法,但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42]。明确CAP在SAKI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临床为防治SAKI开辟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