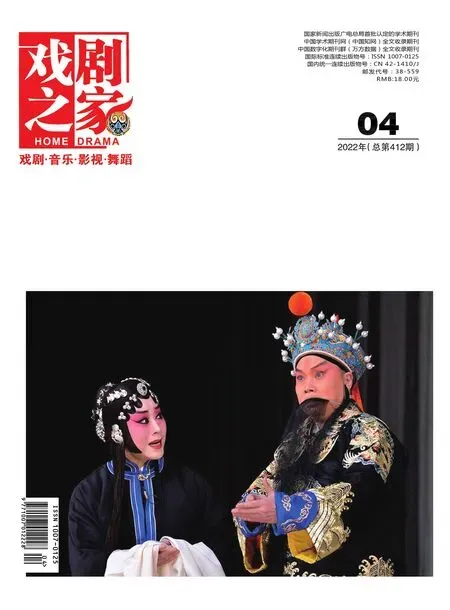19-20 世纪俄侨和移民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发展及影响
薛 瑾,王 伟
(佳木斯大学 音乐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0)
19 世纪中叶,俄国已经成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音乐国度,其在音乐文化与艺术积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19 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对外扩张,借机占领我国旅顺、大连等地,将中俄之间的铁路修建至海参崴,并先后向中国派遣驻军及约70 万的移民。至此,与俄国交通便利的黑龙江部分城市成为俄侨与移民集中区域。20 世纪初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大量俄国难民及艺术家、音乐家涌入黑龙江地区,初步形成了早期的音乐活动。虽然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不容遗忘与原谅,但也需要承认俄侨与移民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促进与发展作用,以及对后续音乐乐团人才培养的深远影响。为此,文章以辩证态度看待19-20 世纪俄侨及移民活动,以发展观与普遍联系观剖析俄侨及移民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正面影响。
一、19-20 世纪俄国音乐发展特征
俄国领土横跨欧亚两洲,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俄国音乐家不断尝试本土民族音乐与欧洲作曲技巧的融合,逐渐形成了浪漫、优美但又热情、宏大的音乐风格。19 世纪初期,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多国连年战争、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共同影响,欧洲生活秩序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俄国处于欧亚两洲交界地带自然不能免遭波及,此时西欧音乐思潮及音乐艺术涌入俄国,使俄国音乐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创作素材与思路,该时期俄国音乐也从对西欧及泛欧洲音乐、作曲风格的一味模仿转变为追求独特且新颖的音乐表现形式。
19 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崛起,此时西方音乐界格局更为复杂,俄国出现了追随浪漫主义的音乐家,但也有部分音乐家保持清醒与冷静,虽然其所创作的音乐不可避免地受到浪漫主义音乐及其他流派音乐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总体上来看风格与表现形式等更具有多元化的艺术特征,从坚持创新的音乐家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变革的烙印。伴随着西方音乐的发展,浪漫主义流派音乐开始异化,逐渐表现出其现实主义、夸张主义色彩,但俄国音乐却抓住了浪漫主义音乐积极的一面,形成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新潮主义三大流派。
从19-20 世纪俄国音乐发展进程来看,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及音乐作曲风格的转变离不开特定的音乐文化背景、社会格局及多元音乐思潮的影响,换言之,在音乐文化的融合与交互下,音乐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坚持与创新才是音乐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
二、19-20 世纪我国黑龙江地区音乐特点
19-20 世纪,我国正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俄国的十月革命运动等推动了苏联思想及音乐文化在我国的传播。此阶段我国黑龙江地区部分城市已经沦为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当时的音乐艺术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表达了穷苦大众对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但也体现出中华儿女对民族独立解放、美好生活的希冀。该时期我国黑龙江地区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抒发底层百姓情感的新民歌、地方戏等,我国音乐家也开始关注音乐创作技法的创新。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涌入,音乐家们开始探索中西方音乐文化融合的路径。
自19 世纪以来,我国黑龙江部分区域便处于俄国与日本的势力斗争范围之内。黑龙江沦陷区也成为中俄音乐家的活动聚集地,逐步构建了我国首个西洋音乐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也首次在我国境内演奏西方交响音乐。当时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演奏者多为俄侨音乐家,活动频繁但覆盖范围较为狭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国音乐,尤其是俄国器乐在我国的发展。当时我国音乐理论专家及学者将西洋音乐视作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相背离的“非主流音乐”,也将哈尔滨交响乐团看作向中国民众灌输“反面文化”的工具。抚今追昔,当时各界学者对西方交响音乐性质的界定不无道理,从侵略者有意或无意地促进交响乐团演奏活动开展可看出其侵略思维,妄图从意识形态及文化层面影响中国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但从客观层面来看,黑龙江地区西洋音乐乐团的组建及演奏活动的开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了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西洋音乐在我国的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三、19-20 世纪俄侨与移民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发展及影响
(一)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组建的发展及影响
俄国侨民与移民具有歌唱的传统,尤其喜欢教堂合唱,19 世纪、20 世纪在我国黑龙江哈尔滨地区建立的中东铁路指挥部十分重视铁路局工人及俄侨的娱乐与文化生活,经常组织家庭音乐会、音乐沙龙等活动。1908 年,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乐团成员以俄侨为主,经常演奏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西洋音乐名作,此时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发展拉开序幕,在当时历经战乱、民不聊生的中国,拥有如此规模的西洋音乐乐团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可见俄侨与移民对于我国交响乐发展的价值。
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发展经历了经费紧张、运作质量低下的初级阶段,以及人才鼎盛、活动兴起的辉煌时代。1946 年,俄国侨民撤离黑龙江地区,哈尔滨交响乐团中注入了新鲜血液,俄侨弟子及黑龙江本土音乐家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如我国著名双簧管演奏家尹升山、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刘守义等。黑龙江地区获得解放后,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发展面临着两难抉择,是延续原有演奏风格及曲目,还是探寻创新与民族根基?1961 年,“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召开,演奏了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交响音乐作品,由小提琴家胡夏独奏的《草原上》更是振奋人心。《草原上》由蒙古族民歌改编而来,虽然前辈们在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创作技法融合上早有尝试与实践,但《草原上》的演奏却昭示着中国本土音乐家独立自主的探索与努力,表明哈尔滨交响乐团正逐渐走向本土化、民族化与大众化,西洋音乐乐团不再是西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而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
(二)对黑龙江西洋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发展及影响
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组建及发展离不开优秀演奏家与音乐家的支撑。在哈尔滨交响乐团任职的俄侨与移民音乐家不仅仅是西洋音乐的表演者与诠释者,而且是交响乐文化的传播者。“老哈响”俄侨音乐家培育了诸多中国本土演奏家,至今其弟子已经成为元老级别的西洋音乐乐团演奏专家。同时,俄侨及移民音乐家们在黑龙江地区建立了一系列专业音乐院校,将音乐乐理知识、西方音乐文化、西方音乐创作技巧等教授给本土热爱音乐、未来将从事音乐创作工作的人才,培育出如张应发、王丹、王振山等优秀的交响乐团演奏家。专业音乐教育是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发展的基石,在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后,我国音乐家在交响乐演奏曲目创新、表现形式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探索以西方乐器演奏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方法,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小号等西方乐器使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表现形式更为多元,将原本西方独有的交响乐逐步转化为体现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智慧、凝聚民族力量、增进民族情感的纽带与载体。不仅如此,俄侨建立的专业音乐学院打破了我国传统“口耳相传”的器乐传习模式,将我国器乐演奏推向更加科学、系统的高度。从此种层面来看,19-20 世纪俄侨与移民不仅在推动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发展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为中国西洋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可见其对黑龙江地区西洋音乐文化融合的促进功能。
(三)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表演的发展及影响
1964 年,普尔科别拉克离开中国,标志着哈尔滨交响乐团开启了“第二代”演奏家的新时代,新一代演奏家们时刻牢记自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始终探索“西为中用”“创新求变”之道。至2018 年已经举办34 届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已然成为黑龙江地区乃至全国的音乐文化符号,在坚持不懈的练习与长期的实践中,哈尔滨交响乐团逐渐形成激越、细腻、优雅的演奏风格,所演奏的曲目也更具有民族特色,如第34 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的管弦乐《红旗颂》为黑龙江乃至全国西洋音乐乐团增添了浓厚的民族色彩。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艺术造诣与今日取得的成果,离不开19-20 世纪俄侨及移民对专业音乐教育与西洋音乐乐团组建的支持与促进,也离不开中国本土音乐家的努力与奋斗。
四、结论
19-20 世纪大量涌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俄侨与移民翻开了西洋音乐演奏在我国音乐艺术领域的新篇章,从客观角度来看,俄侨及移民音乐家组建西洋音乐乐团、开办专业音乐院校为西洋音乐在黑龙江大地上的开花结果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可忽视其对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发展的正面与积极作用。在俄侨与移民撤离中国国土后,“第二代”中国本土音乐家的坚守与创新更为震撼人心,西洋音乐从“反面文化”的灌输工具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艺术表现形式,西洋音乐乐团的发展一路坎坷、披荆斩棘,黑龙江沦陷地区解放后的音乐会活动才真正让人们感受到了交响乐的魅力,这期间离不开中国本土音乐家民族寻根与民族文化传习的自觉性。诚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音乐创新的必要条件,但黑龙江西洋音乐乐团的发展及俄侨与移民对其的影响为当下中国交响乐及西洋乐发展提供了启示:扎根民族土壤、立足民族文化,以接纳包容、去粗取精之态度发展我国音乐,致力于推动我国音乐与世界舞台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