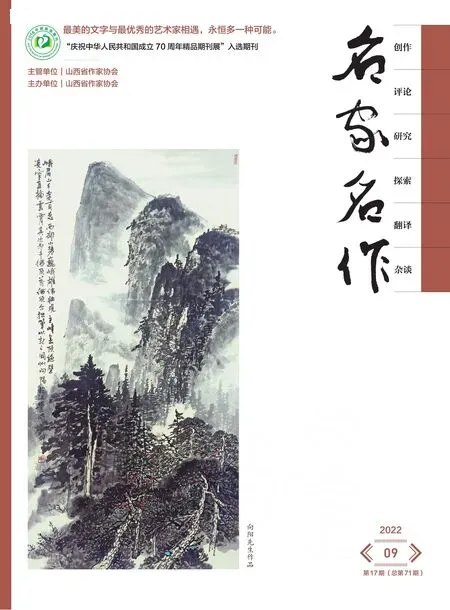小红帽审美嬗变
陈雪儿
《小红帽》是西方童话中极具伦理价值的经典文本,在过去三百年间急剧嬗变,深刻揭示了文学经典改写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作品含义是历史产物的表现方式,在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体现出读者的类型与见解。但是,如果简单地将“小红帽”类比成像“狼来了”般的寓言结论, 这无异于将众多版本抽象成统一的文本结构, 从而消解了童话的审美特性, 亦掩盖了不同版本故事中隐含的独特意义。因此, 本文选取佩罗的《小红斗篷》与格林兄弟的《小红帽》两个版本的故事作为考察对象,讨论不同的时代文化和审美趣味,建立以小红帽审美嬗变为主题的考察研究。
一、佩罗《小红斗篷》:蕴含法国上流社会性道德教育的故事
《小红斗篷》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口头故事《外婆的故事》。凯瑟琳·奥兰丝汀在《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中写道:“早在小红帽尚未出版成书之前,《外婆的故事》就是人们围在火堆旁传讲的原始版小红帽冒险的故事。”因此,佩罗的《小红帽》并不是小红帽题材的原始文本,佩罗将接受美学设置为创作起点,对源文本《外婆的故事》进行二次创作,使新文本与时代期待视野的距离拉近。“沙龙”一词是法语“Salon”一词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17世纪起,巴黎的闺秀将客厅变为社交场所,令志趣相投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名门望族聚合于此自由谈论。因此,沙龙中的故事内容定要满足名流贵族的审美需求,佩罗的《小红斗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迸发出来。
故事的嬗变可以看作是佩罗在新伦理语境中使用的改写模式。佩罗作为路易十四时期活塞学士院的院长,他致力于建立法国封建贵族的伦理秩序。与之前的版本相比,佩罗的创新之处就是在故事的结尾处加上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训诫”。产生于17世纪的《小红斗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话,增设的“训诫”部分既能对儿童起到教化作用,又能对成人产生警诫意味,表现出了法律与秩序意识。因此,本次改编既是一部写给儿童的娱乐故事,又是一部写给女性的性寓言,同时它也是作者政治生涯的文学延续。纵观全文,佩罗在提醒上流社会的小姐们要警惕像野狼般的假绅士。“小女孩,这一切似乎都在对你说:路上不要中途停止,永远不要相信陌生的人。”这一情节设定既象征着儿童离开父母的怀抱,独自去面对复杂的世界,又映射出过早进入名流圈的贵族少女就像文中女孩一样容易轻敌。狼在文中伪装成一位性感迷人的绅士,如同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但也做着勾引年轻女子的勾当。这样的形象塑造并不是为了引导观众对其行为表示唾弃之意,而是意在将“狡猾”“可恶”等标签从狼身上撕掉。因此,佩罗将小红帽塑造成为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形象,既表现了父权制度下女性地位的低下,又补充说明了作者的改编寓意在于辅助社会道德教化。
教化作用不仅来自作者的创作,也需要读者与之共同建立。结合17世纪的法国社会实景,年满14周岁的女性需顺从父母的旨意与男性步入婚姻殿堂。这样的婚姻结合往往是依据经济、地位等物质条件选择适配,并令女性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国家带来国民,为教会带来孩子,为天堂带来居民”为自己的义务。因此,这些少女虽然出生于上流社会,受沙龙倡导的“爱情和婚姻自由”的熏陶,但也不会成为一个争取自身权利的女性。佩罗通过书写女孩的悲惨结局,向读者传达了两个道理:一是教导少女要听话,服从家长的教育;二是法国社会对女性贞洁的强烈要求,少女需提高警惕。相比于《外婆的故事》,佩罗将大段的脱衣环节删减成简单的一段,隐晦地表达女性的性贞洁问题,符合了上流社会的高雅需求。女性或者女性的贞洁成为男性独占的私有财产的待分配形式。简而言之,女性的贞洁决定着未来继承的血统纯正性,这种预定的价值取向被保留且延续下来。佩罗的改编无疑是明喻社会道德规范以及暗喻男权社会构成的绝佳形式。
比较佩罗版与格林版的故事情节,发现其差异突出体现在故事结局的设置上。佩罗以“小红帽”葬身狼腹告终,而格林增设了全新的情节和人物角色:即小红帽与外婆得以重生,合谋杀死了狼;英勇的猎人;故伎重施的狼。被狼吞食与把狼置死,如此的结局设置使得前者被阐释为“惩戒性故事”, 后者被读解为“劝诫性故事”。“惩戒性故事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与惩罚成人,劝诫性故事则重在教育与引导儿童。”作为惩戒性故事,佩罗将狼赋予了人的特性。它善于有目的地伪装,而这种伪装是人类特有的文明,佩罗将伪装的伦理教育融入故事中;在《辞海》中,伪装一词的汉语释义包括“假装”“假的装扮”“隐蔽自己和欺骗,迷惑敌人的各种措施”。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天性伪装是自然选择的工具,人类的目的性的伪装是伦理选择的手段。纵观历史,早期人类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使用暴力斗争,和动物在抢占资源时所采用的方式不相上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伪装融入了智慧的元素,不再是最原始的天性伪装,而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向往通过某种形式的伪装实现以少取胜的作用,这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大有体现。例如,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奥德修斯通过木马计转败为胜,成功夺取特洛伊等。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伪装升级,生物通过学习伪装能力获取智慧,进一步向实现目的靠拢。“狼可以用千变万化的方式潜伏在你四周,它们都是善于伪装的……但其中往往充斥着锋利的牙齿。”在《小红斗篷》中,狼一共完成了两次伪装活动:第一次出现在森林中,狼伪装成路人向小女孩问路;第二次出现在外婆家,狼伪装成外婆引诱小女孩靠拢。由此可以看出,通过使用恶意的语言伪装,成功骗取单纯小女孩的信任,既体现出使用伪装的智慧性,又表达出善用伪装的可怕性。
佩罗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增设了“小红帽”这一装束描写,令小红帽们都具备了特殊的标志。相较于民间口传的《外婆的故事》,佩罗首次引入了“小红帽”的装束描写,形成了“小—红色—帽子”的三元结构。在伦理建设的道路上,每一元结构都映射着小女孩的结局。精神分析家埃里希·弗罗姆认为:“小红帽是月经的一个象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女时期的女孩既有可爱的外表,又具备女性轮廓的外显。“她非常可爱,她的母亲爱她近乎到了疯狂的地步,除此之外她还有外婆的爱。小女孩的外婆给她亲手缝制了一个红色的小帽子”,这顶红帽子成了小女孩的标志。但是,因为小女孩生长在只有母亲和外婆的母系家庭环境中,家里的女性角色将重心放在了过度保护和爱护上,缺乏“包括与外部男性(同龄男子与父亲等)的关系和自身男性特质的关系”的教育,从而缺乏鉴别善恶的技能。所以,长辈的不在场就是小红帽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辨识伪装的善恶不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技能,掌握此项技能需要教导。在魅力男性的引诱下,外婆对“小红帽”的保护不够用了,因此可以说佩罗对文本情节的修改是依据需阐释的道理而修改的。善恶之别是伦理的基本常识,善恶之辨是建构社会伦理体系的前提。佩罗通过塑造典型的恶形象,帮助读者完成了善恶辨识。
综上所述,佩罗这样创作的意义不单单为了阐述小女孩无法避免被会伪装的狼侵害的事实,同时也在提示读者要对语言伪装增加提防与辨识。的确,这样的结局设计与格林版相比残忍很多,但是删去部分不适宜儿童阅读的情节而未美化故事结局的设计体现了作者的伦理教育意图,即法国上流社会性道德教育——建立正确的善恶观,掌握趋善避恶的能力。
二、格林兄弟《小红帽》:蕴含德国主流社会礼仪道德教育的故事
相较于佩罗的《小红斗篷》,格林兄弟的改编更加适应资产阶级伦理教化的需要。从故事题目角度来看,格林兄弟把“斗篷”改成了“帽(子)”,使小女孩更加符合维多利亚式的装束;从读者对象角度来看,由成人与儿童群体双重兼顾转化为专门化的儿童群体。19世纪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巨大冲击,德国中产阶级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再加上“童年”观念的出现,使童年阶段其独有的特征和需求被人们逐步关注与认识,从而令中产阶级家庭开始逐渐重视儿童的教育。皮亚杰指出,儿童的认知水平尚未发展到理想阶段,但已具备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能辨别简单的好坏。因此,格林的改编删除了成段的“道德训诫”,使其更契合儿童目前尚未成熟的认知水平,将警告糅杂到故事中,使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在格林的改编中,作者创新性地给予了主人公改过自新的机会。书中专程安排猎人将小红帽和外婆救出狼腹,其中的猎人正是父权主义的代表。简而言之,格林兄弟将法国上流社会性道德教育的故事改编为德国主流社会礼仪道德教育的故事,赋予童话教育儿童了解自然、认识社会的功能。
此次改编有三处明显的变动。第一处是小红帽出发前,增加了妈妈的叮嘱“趁着天还早,你快去快回,你要乖乖地走……别东张西望”。前文已经提及,弗洛姆认为,小红帽处于面临性问题的年龄,妈妈的教导意在提醒女孩性的重要以及丧失初次的惩戒。从《外婆的故事》到格林改编的《小红帽》,小红帽母女之间一直保持依赖的关系。由于文中的小红帽的家庭中并未出现男性角色,导致小红帽处于男性认知空白阶段。同时从前文的嘱托中来看,女孩对世界的好奇并不被女性所鼓励,妈妈的警告暗含着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文章设置延续了前期佩罗的版本。17世纪的皇权时代,女性被视为贵族联姻时交换的资产,属于婚姻关系中的牺牲品。因而在此背景下,小红帽皆饰演了具备警示意义的反面角色,因为没有守住未来伴侣的“性私有财产”,必然遭受到惩罚。这既说明了性及贞洁对女性的重要性,又表达出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女性性贞洁的强烈需求。
第二处是出现全新的角色。猎人的出现适配小红帽和外婆获救的情节设置,也使二者共同构成男性形象的两面性——虚伪的坏人(狼)与英勇的好人(猎人)。在之前的故事中,按照出场顺序依次排列为母亲、小红帽、狼以及外婆,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母系世界的状态。在格林的版本中,父亲等男性角色在文章的前中段并未提及,暗示了他们的不在场状态,直到故事结尾才出现了作为拯救者的猎人形象。因此,女孩被拯救并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是依附于“好男性”的救赎才能获得新生。将女性改写成缺乏独立人格的形象突出了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同时也令其他童话故事常采用此类“弱女+王子(强男)”的模式,女性等待男性的救援变成彰显男权优越感的途径之一。同时,通过对两位男性形象的行为对比,更能彰显善恶观念,教导孩子明辨好坏。简而言之,猎人这一角色的设置深刻揭示了格林的女性伦理观,即宣扬男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宣扬父权制社会对涉世未深的小红帽所代表的女性的警告。不仅如此,格林童话中还暗含了潜在文本,即故事结局改编为祖孙俩在猎人的帮助下从狼的肚子里逃脱,并把狼的肚子割破,装上大石块。这样的结局在暗示小红帽代表的女性主义最终战胜了狼象征的父权制,女性赢得了自己的胜利,但是胜利是需要向猎人般的男性寻求帮助才能取得的。在父权制长期意识形态的侵蚀下,女性认为这一切欺压都是合理合规的、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邓迪斯认为:“这个被男性改编的故事和男性对这个故事的解释都构成了一种固定和支配女人的男性共谋。”所以,小红帽的故事只会对女性读者产生警示作用,而不会对狼及猎人所代表的父权制产生深刻批判。
第三处是转悲为喜的结局设置,格林改编的《小红帽》彰显了法律的意识。格林兄弟对坏人的犯罪行为给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狼的肚子必须被装满沉重的石头,溺水而亡。又如“知过必改”的儿童教育观念,让处罚或教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此次改编宣扬了父亲(男性)的重要性以及对女性的规训,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格林的性别偏见。小红帽的成长过程中缺少男性角色对她进行教导,从这方面来看符合拉康的“小对形”观念。“小对形”实际上就是小红帽在成长中有部分自我认知的匮乏,猎人的救助恰好填补了小红帽的部分自我能力。文中“小对形”发生于小红帽被狼吞入腹中的情节描述。猎人及时剖狼腹令小红帽获得了新生,使其吸取教训避免二次落入狼腹,这宣告了小红帽通过“小对形”弥补了自我的某些缺失。所以便出现了格林改编的故事结尾,与她吸取的经验教训相呼应。因此,增设的部分使故事内容更加温情,同时也增设了另外一层教育意义,即孩童犯错后要知错就改。
三百年来,童话《小红帽》不断地被演绎。语言是人们沟通的最基本形式,童话故事的语言以及情节设计,潜移默化地把社会伦理道德、角色认同、成长之道灌输到儿童的思想之中,成为儿童完成社会教育的媒介。诚然,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永恒不变的,随着作者意图与接受者的改变,《小红帽》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可变曲线,从审美的角度体现了童话的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