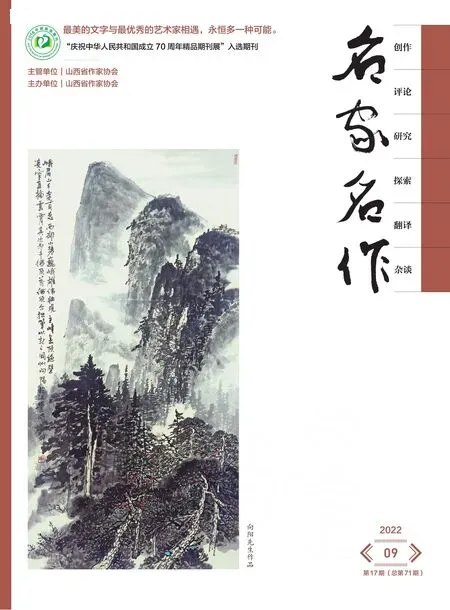躁动的群氓还是突围的现代性?—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的启示
谭登华
自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在1929年于《太阳报》付梓至今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但它蕴含的大众社会理论思想俨然超越了作者所处的那个法西斯主义烈火在欧洲燃起的年代,个人自由、公共舆论、大众文化、精英主义等问题仍是当今学界热议的焦点。循着加塞特穿越百年的目光,也许可以觅得一条有价值的运思途径。
要理解《大众的反叛》折射出的批判观念,须考察加塞特对现代性的整体看法,了解这部书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定位。《社会包围》(Sociedad el Sitio)记录了1910年3月12日加塞特在毕尔巴鄂的一次讲座的内容,他抱怨道:“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在精神层面上足够成熟的人为数不多,这个群体濒临枯竭。”这里能听到加塞特对大众反叛现象的严厉批评的先声。正如Antonio Heredia Soriano1975年发表的El krausismo español所总结的,从Juan Valera、M. J. Narganes、Donoso Cortés、Balmes、Lópe z de Uribe、Borrego、Gil de Zárate、Francisco de Paula Canalejas、Manuel de la Revilla到Menéndez Pelayo,西班牙知识分子集体性地发觉到,就思想与文化状况而言,祖国已病入膏肓;加塞特则继承了这种对国内乃至欧洲现状的悲观态度。
对于身边人缺乏对自我的定位,贪婪地追求力所不及的利益的情况,加塞特在1923年说道:“妄自尊大是我们民族性的偏嗜,是我们的原罪。”说辞颇为锋利,但考虑到当时西班牙思想界一片沸腾,此类怨声便显得合理很多,“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西班牙知识分子至少在这唯一的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西班牙没有哲学,也没有创新的思想”。
在文化颓废、知识分子奋起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加塞特的大众文化理论逐渐成型,《大众的反叛》的问世堪称一系列反省、追问、思辨的最终成果。整体而言,《大众的反叛》定义的庸人或大众人指不应且不能对自我存在发挥引导作用(no deben ni pueden dirigir su propia existencia)、不具备特殊资质(no especialmente cualificados)的群体,与之相对的是特立独行、有重大责任和使命的少数精英,二者形成了动态平衡。尽管有批评者认为加塞特未就大众人(hombre medio)这一核心概念建构完整的理论框架,导致读者无法给予大众人一个明确定位,但换个角度看,不确定性、模糊性恰恰增强了“大众的反叛”的威力。丹尼尔·贝尔评价说:“人们可以找到他对于‘现代性’的所有最猛烈的攻击。”
加塞特尖锐地认为,酿成危机的不是庸人的本性,而是他们对少数派(minorías)的僭越行为,“如果这些组成了大众的个体,自认为具有特殊资质,那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是个人犯下的错,而不是社会学的颠覆”。作者认为社会阶级、宗法血缘皆不是大众和少数精英之间的界分尺度,而是个人品行。他所认定的大众苟且于生活,对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毫无要求,以庸倦的状态消磨时光,不努力改变现状,却在日渐丰富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妄图代替少数精英来享受后者通过不断勉励自我,提出更高要求,努力使之实现而获得的后天特权。相比精英而言,大众缺乏对社会历史进步的使命感、责任感。那么,何等程度的自我约束和克制才堪称做到了符合精英标准的严格呢?怎样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奋发精神才能让一个人免于被划归大众?符合上述要求的精英在每天的生活中,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能保证责任感强于少数精英人均量吗?由此可见,大众概念作为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范畴之一其实是作者为展开批判而找到的抓手和跳板,纠结于大众人究竟是谁无益于领会加塞特的批判意图,通过开篇极具心理冲击力的说明、界定,作者已经达到了所期冀的表达效果。
考察人之性,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社会成员往往难能根据自身资质判断有无僭越行为,毕竟卢梭有言,“一个人放弃自由就是作践自己的存在;一个人放弃生命就是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个人自由的种子乘中世纪后的文明之风在人们心中找到了允许其生长为坚定意识的土壤,尤其在“充分民主之理想的平均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几乎人人都认为追求更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更强烈的满足感系发自本性,乃不可剥夺之自由。空前强调自由和解放、破除阶级隔障是时代之特征,“个人犯下的错”仿佛在所难免。大众反叛的潜在威力即在于此——谁都可能是大众人,大众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情况之严峻非在于没有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在于无法锁定解决办法针对的客体。但加塞特巧妙的批判不止于此,因为与其说他的话锋对准大众,倒不如说他将矛头引向了深层的时代痼疾。
身处社会便不得不接受它强加的环境,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成了问题的培养皿;庸众虽是人类代表,但一味围绕大众人詈骂完全于事无补,因为大众反叛问题其来已久。“无能的一代之后,强大的一代也没能到来;散漫的一代之后,只有可能再迎来虚荣的一代……我们的父辈已经把我们灵魂中的一些宛如死灰的部分传给了我们,而我们也终将无法把其激活。”如果必须把目光从大众引起加塞特种种批判性思考之表象处撤回,如果不能用相对客观的尺度来清晰地划分出大众群体以求施以引导(尽管上述论断十分悲观,但按照加塞特的观点,至少教育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就要退一步,去追溯大众人之由来。
加塞特总计提出三个原因: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换言之:现代文明是孕育大众的温床,而科学技术更是第一催化剂。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就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对人的影响所做的区分,发达的科学技术意味着更大的堕落可能性,“我们猝然得到的解放构成了一种威胁,它要求我们挖掘自己找事做的内在才智,要求我们发挥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想象力”。 死循环就此形成,精英为世界带来最初的科技之光,让启蒙降临于群氓;后继之大众循着指示,按照给定方法从事劳动生产,将新生的事业发展壮大,却又不得不自食其果,“精确可靠的方法让这种暂时的、实践性的知识脱节成为可能。运用此等方法来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 科技人员被加塞特戏谑地称为“有知识的无知者”(sabio ignorante),也被视为大众人之原型,“当令其专门化的时候,文明也把他自我满足地密封在了自己的局限性之中”。 落入现代性僵局的还有政治,自由民主政体的创设让大众获得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能对权力发挥监督、批评作用的公众舆论在社会中有了一定重量,它不再是专属于少数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精英的施展本领之场所;尽管大众仍会受到外界舆论导向的影响而做出受到暗示的判断,让公共舆论呈现出同质化倾向,但正像哈贝马斯所言,“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这种公共讨论被体制化地保护,并把公共权力的实践作为其批评主题”。 各为其利的参与者不加批判地宣泄情感,尤其无法进行自我批评,公众舆论只得宣告破产,遑论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矛盾的是,没有公共舆论意味着没有理性尺度,理性尺度随公众舆论对国家权力的批判而形成,公众据此做出超越公共权力领域的理性判断。
文明的演进势必夹带负面影响,既然作者已把大众划归只可追随少数精英的步伐而不能妄求个人权力的文明成果“继承人”(hombre heredero),那大众究竟是精英为这个世界带来的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的必然副产品或无辜受害者,还是精英在实现最初正确设想的漫长征途中不可或缺的引渡人?问题的答案关涉两种选择,或默认大众反叛是启蒙和现代性业已为我们服下的毒药和苦果,也是精英早期无意间的壮士断腕,或视大众反叛为文明进程中一段黑格尔意义上的螺旋式曲折上升期,甚至是饱受争议的现代性得以突围的绝佳契机。
在加塞特之前,已有学者就现代社会的大众现象展开讨论,勒庞于19世纪末撰写的《乌合之众》总结了四种个人行为特点:自我人格的泯灭、无意识本能的决定作用、受暗示和感染作用而转向同一方向的思想情感、暗示的观念立刻变成行动的冲动。对应的现实征象就是,过度的欲望、公共舆论的导向、快节奏的生活对人格的倾轧,席勒意义上的游戏的内在驱动力逐渐虚弱,现代性的铁幕遮蔽了世界。加塞特明确指出,“一种绝对优势和不安全感的奇怪二元性盘踞着现代的灵魂”。 一方面,空前繁盛的物质生活因大众的活动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可能性急遽增加;另一方面,一切都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人类文明不得不承担踏入歧途的风险,我们无法用盲目的安全感来自我安慰。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逆之势,少数精英和大众都要受其冲击,“科学原则的丰盈正推动着科学实现一次惊人的进步,但是后者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专业化,而专业化则有令科学窒息的危险”。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惊呼,加塞特的文锋虽然犀利,但藏在针砭时弊的文字后的是一颗何等委婉曲折的知识分子之心。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放弃专业化代表着暂歇攀登科技之高峰的伟业,当下知识储量之庞大已非19世纪可比拟,突破性的事业往往需要团队通力协作、人人各司其职。要成为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呼吁的受过真正有价值的大学教育的现代人何其难也!所以他退一步强调人文学科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科学是崇高的,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并不是”。所以,不能只从《大众的反叛》里听到一位愤世嫉俗者对庸众发起的猛烈批判,更要从中分辨出对少数精英的呼唤,要求有时代责任感和特殊资质的领袖匡正时局,为迷路的现代文明重新找到方向。
至少在加塞特看来,数量激增的庸众为陷入困境的欧洲植入了新的可能性和突破点,尽管他颇为尖锐地冷对大众,但也给危机的消除留有余地。对于现代人而言,假如“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 那无比尴尬的是,可供使用的资源尽管丰富,但却是物质性的,而亟待解决的困难则是精神性的,这种极不匹配造成了理论的空洞:物质的因导致精神的果,复求用物质措施解决精神难题只是异想天开。所以,换个角度重审貌似不可解的死结,或许会发现死结本不需解开,死结自有其功用。加塞特说:“自由主义是高尚的最高形式,今天应该记住这一点;它是多数人给予少数人的权利……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共存的决心,哪怕是弱小的敌人。”真正的达者、强者不会容不下莘莘众人一时躁动之误,更不会任由欲望、无意识席卷前人苦心经营的精神文明而去。大众与精英永远都在绝对共存的前提下构成动态平衡,这个平衡就是置身于时代发展中的大写的完整的人,他/她处于永恒的变化中,在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超我和本我间摇摆;从整体的人身上消灭掉大众人之本性,禁绝其可能引发的行为和活动,人便不复为人。
加塞特承认能力可以培养,由大众升格为少数精英的路径未被天资堵住,否则动态平衡便无法保持。回到一个经典的定义——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阐明的:“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不开展现代之启蒙,任由意志和智思沦为受他人掌控的附庸品,即便暂时解决了加塞特提出的大众反叛问题,当今社会骨髓内的现代性危机就可以随之消弭吗?在少数精英之上更有极少数精英,受监护状态之外还有受监护状态,“一种活动的原则若是依赖于另一种活动的原则,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活动,它的存在只不过是个习惯的、假定的存在”。 大众按照所谓的最理性原则,主动且谦卑地接受更优秀者施以的帮助和指引,就只能无奈接受其自我存在的附属性,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仅是“习惯的、假定的存在”。
总之,《大众的反叛》不是为精英主义政治摇旗呐喊的贵族之作,反而是加塞特向政治发起进攻的堡垒。在他看来,“半个世纪以来,在西班牙内外,政治——即理论对实用性的服从——已完全侵入了人的精神”。政治的控制之下,人不得不随波逐流。依顺和反叛终究是根植在人性中的二元对立,双方的拉锯战维持着人格的稳定;理性原则偶尔宣告失效,有时占据主导。当加塞特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角度把批判目光聚焦到社会问题,仿若准备与躁动的群氓开战,我们隐约接收到了正在突围的现代性发出的信号。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