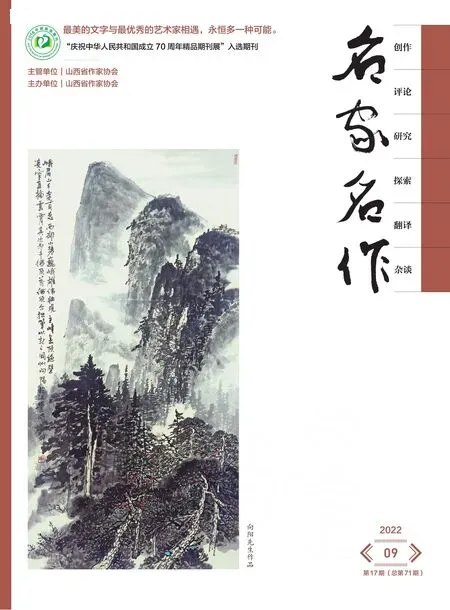鲁迅“看客”现象与加缪“局外人”现象的异同
李美森
在鲁迅(1881—1936)的作品中,“看客”现象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典型的现象之一,《娜拉走后怎样》《社戏》《示众》《无常》《理水》等作品中都有对“看客”现象直接或间接的展现。同样,在加缪(1913—1960)最负盛名的作品《局外人》中的所谓“局外人”现象,也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乃至现代生活当中不可忽略的象征之一。“看客”现象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隔绝感”的存在,即人心理上对客观现实世界的一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回避。通过两位作者生平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1913至1936年是两位作者共同在世的时期。东方与西方,外在与内在,这种同时期下所做出的选择的相似性,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深层次的研究价值。
一、外在因素与所反抗的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结合时代背景,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看客”现象的直观原因,鲁迅的一生所对抗的正是帝国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在其作品中,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劳苦大众,极端贫困,无所依靠,走向“隔绝感”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旧中国,烈士的血被人们并非故意地踏灭了,许多革命不声不响地消灭了,所有的一切久而久之就是几个字“无可奈何”。压迫与剥削,时达几千年的万般教化,对于中国人来说,“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实践得出的“真理”,是无从改变的。
对于加缪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在1岁时失去了父亲,童年时期他和母亲在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度过。在26岁时,加缪参与了由两个著名左倾作家亨利·巴比塞与罗曼·罗兰组织的阿姆斯特丹——布莱叶尔反法西斯运动。在战争的影响下,西方社会陷入了一种“迷惘”的情绪,人的生命之轻几乎不可承受,生存的意义不停拷问每个人的内心。加缪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曾这样说道:“我这代人,生于一战之初;二十来岁时伴随早期的工业革命进程,又遭遇希特勒的暴政;随后,仿佛要让他们的经历更完美,发生了西班牙战争、二战、集中营惨剧,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狱祸四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核毁灭的阴影下哺育子嗣、成就事业。没人能要求他们更乐观。”他指出:“这一代人继承的历史是腐化的,混杂着失败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疲弱的意识形态。”而加缪所反抗的,正是在战争具象下的“荒诞”,这种“荒诞”在《西西弗神话》中有着更加详细的说明。“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人与其生活的这种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所有想过自杀的健全人,无需更多的解释便能承认,这种荒诞感和想望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加缪所构建的哲学世界中,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就好像西西弗一样徒劳无益地推巨石上山,任其滚落,再不断地重复这个苦役般的过程。人生也是荒诞的,充满各种各样随机的苦难,对此人无力更改,只能拼尽全力地去抗争,接受了荒谬后勇敢地对抗荒谬。
从外在因素来谈,鲁迅所对抗的社会更加具象,而加缪所对抗的更多在其个人所构建的哲学世界中,是现实世界的投影。
二、无力对抗后的共同选择,“隔绝感”的诞生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其著作《金花的秘密》中曾提出“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正如人的身体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共同解剖结构,人的心灵也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底(substrat),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kollektive unbewusste)。”
无论东方与西方,当人们在面对无法调解的矛盾与痛苦时,总是在“集体无意识”这一框架下发现:“在较低层次导致最激烈冲突和充满恐慌的情感爆发的那些东西,现在从人格的更高层次来看,宛如从高山山顶上俯瞰山谷中的一场雷雨。这并不是说这场雷雨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说人已经不在其中,而是位于它之上。”人们往往会选择“隔绝感”,以此起到“超越”的作用,换得自己心灵上的解脱。
鲁迅对于自己笔下的“看客”,往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隔绝感”,这种不作为,通常是源自下层劳动民众世世代代的被压迫、被剥削。近代中国的变革一浪接着一浪,而每一次权力的斗争、内外的变革,受苦最多的都是底层群众。底层群众对变革不了解,没把握,更关键的是,这种痛苦的状况是下层民众无力去改变的,他们打心眼里相信无论世道如何变化,自己的处境都不会有所好转,注定是做奴才的命。久而久之,先是麻木,“隔绝感”初现,认为坑害他人的生命与自己无瓜葛,再之后是以此取乐,变得如同“野兽”一般,希望有更多的悲剧为自己无聊悲苦的生活添一丝“快意”,最后永远与世界,与自己的内心之间有一层“隔绝感”。
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作的绝妙的比喻:“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地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加缪来说,笔下的局外人面对“荒谬”,天生是无力更改,无法跨越的,他认为荒诞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在此死亡是唯一的真实”。在《局外人》一书中主人公默尔索总是感到不解。为什么要为母亲的死感到难过?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莱蒙把我当作朋友?未婚妻玛丽爱上另一个男人又有什么关系?……这一连串的疑问,都是我们正常人可能看起来根本没有必要回答,甚至没有必要提出的问题。然而这本书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绝对的“局外人”,也正是这层隔绝感使他成了世界的局外人。
默尔索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他用自己的方式无比温柔、眷恋地触碰它。“我没关窗户,我们感觉到夏夜在我们棕色的身体上流动,真舒服。”当他在法庭上已经背上了杀人罪的重负,他仍然“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的,某个我有时感到满意的时刻种种熟悉的声音在已经轻松的空气中飘散着卖报人的吆喝声,滞留在街头公园里的鸟雀的叫声,卖夹心面包的小贩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里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画出了一条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随意乱跑时的路线”。
在《局外人》的世界中,反抗的因素是“无形”的,这种“荒诞”横亘在人类全体与自身命运之间,人们或许可以感知,但往往无从捕捉,更无从将其具体化。“上帝死了”,信仰失落,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重构世界的梦想,对这一代人来说却无异于痴人说梦,加缪认识到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只有拼尽全力才能维持现状。
三、形象的最终意义指向差异
抗争难以实现,“隔绝感”业已诞生,“看客”和“局外人”两个形象的最终意义指向更是不同。
在鲁迅思想当中,反抗的要素必须与其作品另一要素“希望”联系起来。《呐喊》《彷徨》《野草》《坟》《朝花夕拾》等作品中都有“希望”一词的出现,也正是“希望”使鲁迅真正走到文学道路上来。比如著名的“铁屋子”对话使鲁迅坚信:“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这万分之一的希望,这聊胜于无的希望,正是鲁迅终生所追求的。没有路就自己走一条路出来,“隔绝感”诞生了,那就把它打碎。鲁迅希望通过“看客”形象刺痛民众,唤醒民众,争取新的中国。对于“隔绝感”,鲁迅有着另一种阐释,即精神胜利法。在人头脑的想象中,一切的流血、死亡以及屠杀都被美化了,战胜了。这对于当时正处在亡国灭种之际的中国而言是十分恐怖的,无异于精神上的鸦片,使人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如温水煮青蛙般,只会使人在自欺欺人中心满意足地走向灭亡。
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尔索所展示的是一种现象,一种破碎的警示,“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本书的最后一段描绘了默尔索受刑前所看到的诗情画意的画面,我们这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默尔索并不是厌弃这个世界,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热爱这个世界,“隔绝感”是他的自我保护,也是他对抗荒诞主义的武器。在他放弃上诉,选择死亡时,死亡自然也化为他的武器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隔绝感”破碎了,他失去了保护,同样也第一次无比真实地触摸了这个世界,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
《局外人》是加缪的早期作品,“荒谬”哲学的构建此时还并不完善,因此主人公在对抗“荒谬”时没有更好的办法,面对自称正义的法庭更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只能趋于破碎。在后期的《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找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与“荒谬”共存,在意识到“荒谬”的同时,意识到“重要的不是解脱和快乐的呐喊,而是出自苦楚的确认。对上帝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确定,在吸引力上,大大超过不受惩罚的恶势力”。
人类群体生存意义的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疑是悲剧性的,作为人类,我们永远有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永远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永远要无可回避地面对死亡。在加缪的哲学世界中,我们首先要学会真实,像默尔索一样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其次我们应当学会面对荒诞,像西西弗一样,极富人道主义光芒地去抗争命运的荒诞,尽最大可能地去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隔绝感”虽然是共通而必然的选择,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却只是虚假意义上的解脱。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面对法律逼问、罪行审判,无论是外在世界的冲突还是内心哲学世界中的矛盾,回避痛苦都并不能够使痛苦消失,只会将我们引向无可挽回的毁灭。也许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面对人生无法回避的痛苦与矛盾,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视它,以及竭尽全力地去掌控它,克服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解脱的可能,而这可能就是希望的微弱但有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