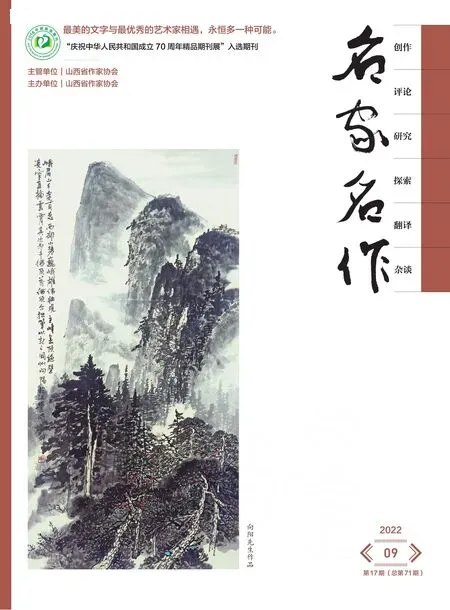石国辉诗歌
石国辉
消失的钟声
许多的事情
并不是
你看到的样子
内心空虚的人
习惯于
拒绝孤独
天空没有记忆
消失的钟声
只能在历史里
寻找
最初的伤痛
搬运着梦想
院子里
几只小鸟
带着不可名状的欢喜
旁若无人
悠闲地散着
自己的步
它们的一生
仿佛就在
蹦来跳去地
搬运时光
犹如我
不遗余力地
搬运自己
卑微的梦想
活在叹息里
路过南京
我看见了
久违的长江
淘尽了
千古风流人物的波涛
依旧在荡漾
温柔地
湮没了
往昔的叱咤风云
金戈铁马
只有江上的清风
远方的白云
还不动声色地
活在
一声叹息里
盲人的梦想
盲人的身边
放置着一盒
五彩的粉笔
他总是旁若无人
聚精会神地
用那些粉笔
一遍又一遍
不停地涂抹
永远看不见的
心中梦想
仿佛漂泊都市的我
正在挣扎着缝合
我支离破碎的人生
往事如冰凉
往事如冰
并未随风而逝
摊开寂寞
只能
看见哭泣的月光
梦想
像纯情少女
妩媚的眼神
总是遥不可及
门外的繁华
与我打个照面
又抽身远去
流落在荒野树枝上
孤独的鸣蝉
声嘶力竭地叫着
却换不来
半点同情
为了躲避钟声
我只好把绝望
揉碎成片
就着眼泪
一点一点
不动声色地
咽进肚里
悼江姐
历史的谎言
注定
要像纸牌一样
被摊开
掩埋真相的人
还故作神秘
摆出一副
高深莫测的面孔
烛照理想的灯
虽然孤独
却把黑暗
吓得不知所措
一枚落叶
还记得
那个多情的雨季
你我相识在一起
微风轻轻
又拂过山岗
小草绵绵
扭动腰肢
你对我
浅浅笑笑
我只好
默默无言
你给我整个春天
我只能还你
一枚落叶
老屋
又一次回到故乡
老屋依旧
沉默里孤独
不发一言
从锈迹斑斑的
锁孔里
看到庭院
杂草丛生
蚊蝶飞舞
同时在游荡的
还有
我的青春和梦想
我想找个理由
万物沉寂的晚上
雪花
一片又一片
飘落在梦里
我总想找个理由
去看你
看看
这些年来
你究竟过得怎样
是否
还在某个角落
偷偷擦干自己的泪
是否
还把委屈
吞咽进肚里
是否
还把我们的爱
掩埋得很深很深
你留给我的
电话号码
我只能藏在兜里
在每个
无人知晓的夜晚
反复翻阅
不可抗拒
天空一无所有
沉默依然
是生活的主题
任何眼泪
都是过时的鲜花
不会赢得
历史的同情
头戴棘冠
不敢喊半点疼
黑夜继续延伸向远方
但曙光的到来
总是不可抗拒
散发芬芳
昨天的树叶
又落在
沉重的叹息里
回忆往事
需要按住
内心的澎湃
海浪依旧
轻轻地
拍打着远方
我又来到
你曾经驻足的地方
寻找
你我共同留下的
欢声笑语
你可能到现在
都不知道
那年
给我的
你亲手削好的苹果
直到今天
还在我心中
散发着芳香
孤独的呻吟
旋转的时光里
还有什么
是我们所能拥有的
那些
年轻时
我们曾经
轰轰烈烈
追求的梦想
早已
烟消云散
穿上昨日的鞋
试图找回
逝去的青春
所谓的浪花
也只是一群水
在孤独地呻吟
中年之疼
窗外
冷漠的雨
正肆无忌惮地
敲打着地面
携带痛苦的风
咆哮着
撕裂天空
屋内
无所事事的我
散发出
欲说还休的隐痛
看见时光
正一点一点地
从指缝流走
只剩下
苍苍的两鬓
在孤独中流失
更加明亮
那天
栀子花开时
我不由自主地
又想起了你
想起那些
斑驳的往事
你那乌黑长发
飘散的芳香
还有你离去时
牵强的笑脸
曾经为你
跑遍全城
才买到的
那副银白色发卡
直到现在
还在我兜里
被岁月磨洗得
更加明亮
马
闲逛街头,见一马肉火锅店,拴匹马作标志,谓所售之马肉,货真价实。遂有感而发。
马的生命
在于草原
在于旷野
在于仰天长啸
在于纵横千里
在于驰骋沙场
在于视死如归
在于为国捐躯
而现在
只能无奈地
被拴在马肉馆前
作为名片
替代主人
招徕四方宾客
偶尔
用嘶鸣点燃
尘封多年的梦想
读陈子昂
从烟云缭绕的
历史中走来
你疲惫的双手
依旧在指点江山
褒贬古今
当年
你所登临的幽州台
早已凋落在
千年的寂寞中
唯有你那滴眼泪
和唇齿发出的叹息
还在穿越时光
孤零地敲打着
宇宙的苍茫
创造历史
漂泊的岁月里
还有什么
是我们所能把握的
人生
就像一艘
正在航行的船
犁开河流的沉默
荡漾出些许的浪花
但很快
又都平静如初
就这样
周而复始
创造着历史
漂泊在风浪里
栀子花
又连片地
开在去年的伤疼里
浅白色的花瓣
总是措手不及地
一片一片
凋零在匆忙中
我发现
所谓人生
犹如一艘
刚启航的船
无论朝着
哪个方向去努力
最后
都只能
漂泊在风浪里
一一熨平
鸟鸣又一次啄开
包裹真理的谎言
晃动历史
散落满地的失败者
总是
在某个角落
不遗余力地
舔舐自己的痛苦
而强者
正肆无忌惮地
分享那不可告人的胜利
唯有时光
才是最公平的化妆师
把那些
重重叠叠的伤痕
一一熨平
安置回家
所有的喧闹
都归于平静
所有的繁华
都饱经沧桑
我不再叹息
也不再激动
更无法修补
昨天的遗憾
此刻
我所能做的
只是
把被流放的眼泪
安置回家
石国辉,男,安徽阜阳人,兰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安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