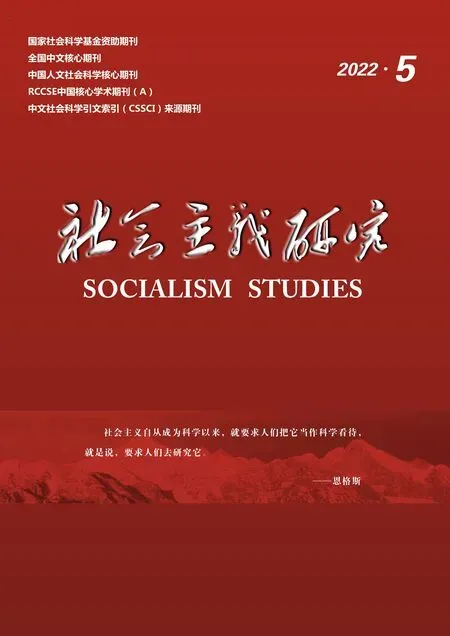政策扩散研究如何扩散?
——政策扩散研究的三波浪潮与发展逻辑
付建军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信息和知识扩散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中,关于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上。政策扩散研究主要解释一个政策从A地流向B地等类似现象背后的逻辑,但发展中政策扩散研究则转变为讨论一个政策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扩散的整体特征。这使得政策扩散研究明显不同于政策转移研究:一是研究的概括性程度高,二是采用定量而非定性研究方法,三是关注扩散的形式而非内容,四是具有一定的预测性,五是采用复杂的数学模型1Adam J.Newmark,"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olicy Transfer and Diffusion",Th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Vol.19,No.2,2002,pp.151-178.。
在发展过程中,政策扩散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经历了较大变化,这使得政策扩散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也呈现出阶段性的扩散特征。那么,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扩散过程,政策扩散研究的扩散呈现出何种趋势和特征呢?Howlett等认为政策扩散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方法日益成熟和精细化,但分析单元却仍模糊不清,这个趋势使得政策扩散研究的局限性越发明显2Michael Howlett and Jeremy Rayner,"Third Generation Policy Diffusion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Policy Mixes: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Vol.10,No.4,2008,pp.385-402.。这种局限性可以表述如下:如果说政策扩散是一种过程事实的话,那么现有的研究路径则无法向我们展示政策扩散的真实过程1George W.Downs and Lawrence B.Mohr,"Conceptu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21,No.4,1976,pp.700-7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指出政策扩散的过程在研究层面实际上是一个黑箱2Erk P.Piening,"Dynamic Capabilities in Public Organizations——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Public Management Review,Vol.15,No.2,2013,pp.209-245.。
政策扩散的黑箱表现为什么?在回应研究黑箱问题的过程中,政策扩散研究形成了何种发展趋势?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回到政策扩散研究本身,将其视为一种扩散现象,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问题与起点。本文试图将政策扩散研究视为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其主体是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政策扩散研究者,在此意义上研究内容和方法就构成传播路径,成为塑造政策扩散研究扩散形态的关键因素。据此,本文将根据研究内容和方法,对政策扩散研究扩散的轨迹和趋势进行追溯和归纳,探讨政策扩散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路径。
二、因素识别:政策扩散研究的起点
政策扩散研究的起点是因素识别,不断挖掘新的因素成为政策扩散研究扩散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的知识生产丰富多彩,理论立场、方法工具和研究结论不尽相同,至少形成了三种知识生产取向。
一是以经济因素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取向。把经济因素作为讨论核心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采纳主体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采纳主体的决策。早期的政策扩散研究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容易采纳新政策,因为政府创新需要一定的物质成本,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可能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3Nico Heiden and Felix Strebel,"What about Non-diffusion? The Effect of Competitiveness in Policycomparative Diffusion Research",Policy Science,Vol.12,No.4,2012,pp.345-358.。随着研究的深化,这一假设得到不断拓展。譬如,Carina就指出处在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政府具有更强的回应意愿,进而为采纳新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4Carina Schmitt,"What Drives the Diffusion of Privatiz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31,No.1,2011,pp.95-117.。以上两种观点构成了经济发展与政策创新扩散知识生产的主线,其背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政策采纳主体在能力和意愿两个维度的影响机理。
二是以政治因素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取向。在已有研究中,政治制度、选民和官员都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这些维度的知识生产到目前为止还未达成共识。以政治制度为例,有些研究发现制度安排更开放的国家可能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进而采纳新政策5Helen V.Milner,"The Digital Divide: The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echnology Diffus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2,2006,pp.176-199.,但也有研究发现科层制政府比有限政府更愿意采纳新政策6Fritz Sager and Yvan Rielle,"Sorting through the Garbage Can: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 Governments Adopt Policy Programs",Policy Science,Vol.46,No.1,2013,pp.1-21.。与政治制度和选民因素相比,官员在中英文文献中都是重要的讨论对象,其对扩散的作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做出采纳决策的官员认为不同地区的政策环境可能具有相似性,因此会出现政策模仿;二是这些官员认为特定的政策创新能够产生特定的政策绩效,为了获取这些绩效会进行政策学习和复制;三是这些官员可能基于政治制度的压力而采纳特定政策7Andrew Karch,"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State Politics &Policy Quarterly,Vol.7,No.1,2007,pp.54-80.。比较来看,中国官员的特殊性可能在于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稳定性,进而能够保持治理目标的持续性;而欧美国家官员受所属政党意识形态的约束较为明显8Daniel M.Butler and Miguel M.Pereira,"TRENDS: How Does Partisanship Influence Policy Diffus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1,No.4,2018,pp.801-812.。
三是以社会文化因素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取向。文化因素在个体层面主要表现为认知,其被认为能够改变传统文献中提出的近距离塑造相似的创新这一判断。社会文化对政策扩散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两个。其一,社会环境结构决定着组织和个体的互动空间,一种能够让组织或个体更加频繁交流的社会环境更能够推动政策扩散1C.Freeman,"Networks of Innovators: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Research Policy,Vol.20,No.5,1991,pp.499-514.。其二,社会环境变化也改变甚至创造组织和个体的需求偏好,进而影响政府对新政策的态度2Meng-Hao Li and Mary K.Feeney,"Adoptio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in Local U.S.Government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servi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44,No.1,2014,pp.75-91.。
四是以空间位置因素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取向。空间位置即地域模型主要强调地理位置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国内外对此都开展了充分讨论。地理相近可能通过“同辈压力”和“近水楼台先得月”对政策扩散产生影响。前者假设相邻区域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后者假设相邻区域更方便交流,表现在三点:一是地理相近的行政区域官员更容易进行政策交流;二是相邻行政区借助媒体工具可以更快地了解隔壁行政区的政策创新动态;三是决策者倾向于认为本行政区与相邻行政区具有相似性3Andrew Karch,"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Vol.7,No.1,2007,pp.54-80.。
整体上看,因素识别开启了政策扩散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政策扩散研究的主流分析路径,对新因素的挖掘也在不断深化,其中关于官员群体、地理相近的讨论为后期因素识别拓展出政府间关系视角奠定了基础。政策扩散研究的第一波能够从多个维度考察政策扩散问题,主要是因为在政策扩散研究产生以前,已经存在大量关于技术创新扩散的讨论,为理解政策扩散提供了知识基础。因此,第一波政策扩散研究关于扩散的理解还有不少技术扩散研究的痕迹和影子。在发展过程中,因素识别也经历了较大变化,以Walker和Gary为代表的学者实际上主要进行了单因素识别的研究工作,这主要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方法。在事件史方法被引入后,多因素识别开始成为政策扩散研究的主流,由此对政策扩散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三、因素识别的机制化:政策扩散研究的新路径
从20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政策扩散研究开始将政府间关系的讨论纳入到因素识别中来。政府间关系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是竞争关系。地方政府在政策扩散中会形成领先和落后的关系4Jack L.Walker,"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3,1969,pp.880-899.,领先者往往会策略性地影响落后者采纳他们的政策,以保持其领先地位5Brady Baybeck,William D.Berry and David A.Siegel,"A Strategic Theory of Policy Diffusion via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Journal of Politics,Vol.73,No.1,2011,pp.232-247.。这种效应已在中英文文献中得到普遍确认。二是非竞争关系。非竞争关系主要以学习、模仿来呈现,其存在可能依赖两种机制:一是相似情境和问题压力,即相似治理背景的地方政府会从和自己相似的兄弟政府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二是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特定的交流网络,包括专业组织(如美国全国保险委员会6Steven J.Balla,"Interstat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Innovation",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29,No.3,2001,pp.221-245.)、学术机构与智库7Diane Stone,"Transfer Agents and Global Networks in the‘Transnationlization’of Policy",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1,No.2,2004,pp.545-566.、媒体和跨政府组织8Katharina Füglister,"Where Does Learning Take Place? The Role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 Policy Diffus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51,No.3,2012,pp.316-349.等。
上述讨论的竞争关系和非竞争关系主要是指横向政府间关系。那么,纵向政府间关系和跨层政府间关系又如何影响政策扩散?研究表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互动都带有某种引导和反引导的特征。引导特征主要与实验主义相关联,下级政府的政策采纳被认为是上级政府围绕某一政策领域开展的实验。这种现象在英文中被称为“民主实验室”,在中文中则被称为“试点”。引导特征假设上级政府可以左右下级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但这种引导在中西方存在策略差异。如美国联邦可通过税收政策工具来干预州政府采纳或者淘汰特定政策9Myung Jae Moon and Stuart Bretschneider,"Can State Government Actions Affect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An Extended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Vol.54,No.1,1997,pp.57-77.,也可通过改变创新采纳的障碍难度或提供解决困难的资源来影响州政府10Andrew Karch,"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Innovations",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34,No.4,2006,pp.403-426.。而在中国,中央政府则可通过直接干预、实施排名、通报、在特定领域建构创新议程等方式来引导1Xufeng Zhu and Hui Zhao,"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with Interactive Cenntral-Local Relations: Making New Pension Policies in China",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49,No.1,2021,pp.13-36.。
当然,自上而下的引导也不是绝对的,下级也可以开展一定程度的反引导活动。譬如,英文文献中提出的“滚雪球”效应就是典型的反引导,当下级政府采纳政策的比例越来越大时,上级政府会跟风采纳2Charles R.Shipan and Craig Volden,"Bottom-up Federalism:The Diffusion of Antismoking Policies from U.S.Cities to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0,No.4,2006,pp.825-843.。这种反引导在中国场景下更为明显3Yanlong Zhang,"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The Diffusion of Land Banking Systems in China",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ol.8,No.3,2012,pp.507-533.,尤其是当政策信号自中央发出经历行政链条逐级到达基层时,各级政府采纳政策的意愿和目标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4Xufeng Zhu and Zhang Youlang,"Diffusion of Marketization Innova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in a Multilevel System: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29,No.1,2019,pp.133-150.。而当新政策无法形成充分的激励时,完成任务就成为下级政府的采纳策略,看似广泛扩散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被“悬浮”起来5付建军、张春满:《从悬浮到协商:我国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转型》,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期。。
引导和反引导主要受政策扩散激励的影响,而政策扩散激励既有可能来自政治结构,也有可能来自治理压力,还有可能受到政策议题的属性影响。譬如,Makse和Volden用27种刑事司法政策在美国从1973-2002年的扩散,检验了罗杰斯提出的五种创新属性与创新采纳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验证了创新属性确实影响创新的采纳范围和速度,同时也发现创新属性会影响政策扩散的机制选择,譬如复杂性会影响采纳者是否会通过学习机制采纳这种创新6Todd Makse and Craig Volden,"The Role of Policy Attribute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3,No.1,2011,pp.108-124.。在此基础上,不同政策领域因为属性差异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扩散特征。
这就催生了有关政策扩散的类型比较话题,属性和类型成为政策扩散比较的核心。目前看至少有三种比较路径。一是从政策类型着手进行分类。譬如,Boushey将政策分为管制、规范和治理三种,发现政府对管制政策的采纳与决策个体的专业能力紧密相关,对规范政策的采纳与政府内部的党派竞争紧密相关,对治理政策的采纳与民众表达渠道紧密相关7Graeme Boushey, Policy Diffusion Dynamics in Americ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二是从政策创新的类型来比较。一些研究把政策创新分为技术和管理、产品、过程和附件等类型,发现采纳技术创新的速度要快于采纳管理创新的技术,因为技术性创新更易于被观察,更具有试用性8FariborzDamanpour and William M.Evan,"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and Performance:The Problem of‘Organizational Lag’",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29,No.3,1984,pp.392-409.。三是按照程度来区分政策创新,譬如把政策创新分为硬创新(Hard Innovation)和软创新(Soft Innovation),硬创新的扩散取决于有效性的证明,软创新的扩散则有赖于对预期结果的价值认知9所谓硬创新主要是指工业创新和技术创新,软创新则主要是指政策创新。硬创新的形式和有效性在扩散和采纳过程中能够被客观地观察到,而软创新在扩散中的一个最大困境是很难证明创新思想的有效性。参见Anelissa Lucas,"Public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Integrating Analytic Paradigms",Science Communication,Vol.4,No.3,1983,pp.379-408.。
总之,从政府间关系出发对政策扩散开展的讨论使得政策扩散研究开始在因素相关性识别的基础上增加因果机制的讨论,机制分析开始成为政策扩散研究的重要取向。早期的机制分析比较多元,相关的梳理表明当时的研究贡献了104种扩散机制10杨代福:《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最新进展》,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随着政府间关系的讨论深入,学习、模仿、竞争、强制和社会化等逐渐成为解释政策扩散发生的核心机制。比较而言,机制分析虽然大大提高了政策扩散研究的解释力,但也面临着挑战:一是关于多元机制作用边界的确定仍然比较模糊,二是机制和因素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理清。一些研究通过加入时间变量使得机制和政策扩散的阶段匹配起来,进而确定特定机制的解释空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突破,但也难以描述机制组合的影响差异。
四、简化过程:政策扩散研究黑箱的形成逻辑
回顾政策扩散研究的早期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政策扩散研究建立在简化和抽象的基础上,即通过牺牲微观事实来获得对宏观特征的把握,而事件史分析方法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简化策略在政策扩散研究中的蔓延。这种研究对于政策扩散研究黑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微观过程的简化首先体现在对政策扩散的概念理解上。早期的政策扩散经常和政策创新放在一起,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政策创新是政策扩散的起点,只有出现新政策,才会形成围绕新政策的传播和扩散。由此,政策扩散和创新是两个具有时间先后性的过程,创新在产生后才流行起来。据此,罗杰斯将扩散定义为一项创新在通过某种渠道随着时间流逝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被沟通的过程1Everett M.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3th edn,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3,p.5.。但是此举也带来一个识别难题,到底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算是创新呢?显然,第一波政策扩散研究的多数学者采取了折中主义的研究策略,即不区分创新的程度问题,只关注政策被创新主体的采纳行为。其代表性人物是Walker,他把政策扩散定义为政府采纳一个新的项目或政策,而不管这个项目有多陈旧或被多少其他政府采纳过2Jack L.Walker,"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3,1969,pp.880-899.。
虽然此定义使政策扩散研究摆脱了程度之争,但也人为地割裂了创新和扩散的先后性问题,拉低了创新的门槛,扩散过程立马从“立竿见影”变成了“渐进积累”。由此,此定义自提出之后就饱受争议。其中,美国学者Downs的批评认为把政策创新等同于政策采纳会模糊采纳过程中的行为差异问题。他指出,尽管采纳与否这个方法能够将多元采纳者的复杂行为简单化,但很明显它无法区分采纳到底是浅尝辄止还是深度学习,即它无法揭示创新的采纳到底发生在何种程度上,而创新采纳的程度往往才是重要的创新扩散问题3George W.Downs,Bureaucracy,Innovation,and Public Policy,Lexington,MA: Lexington Books,1976,p.39.。
如果说对扩散的定义仅在理解层面简化了事实,那么关于概念的简化则加剧了研究结果的简化程度,即把采纳过程简化为采纳与否,复杂的采纳过程就变成了数字上的0和1。对过程的简化意味着无法回答创新在扩散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何种变化及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创新在新的情境中的应用效果4Henry R.Glick and Scott P.Hays,"Innovation and Reinvention in State Policymaking: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Will Law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3,No.3,1991,pp.835-850.。
这种操作简化被事件史分析方法所强化。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事件史分析方法的引入确实极大地推动了政策扩散研究。在事件史分析未引入前,对政府政策扩散的解释主要是单维度的,要么是内部决定因素,要么是外部组织关系,缺乏一个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1990年Berry夫妇首次将事件史分析引入到政策扩散研究中,把多因素分析整合在一个框架当中。Berry夫妇引入的事件史分析方法主要是州—年事件史分析,这一方法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生存数据”而非“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风险率”,因变量是二分项虚拟变量,采用的模型主要是Logit和Probit。离散时间通过州-年生存数据能够很好地观察政策扩散中的邻近效应,由此构成了政策扩散定量研究的经典工具,但也有局限性。一是无法识别中介机制对“风险率”的影响5朱旭峰、赵慧:《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1993-1999)》,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二是没有对时间因素进行控制6Janet M.Box-Steffensmeier and Bradford S.Jones,"Time is of the Essence: Event History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4,1997,pp.1414-1461.;三是难以观察非邻近扩散的内在机理7Frederick J.Boehmke,"Policy Emulation or Policy Convergence? Potential Ambiguities in the Dyadic Event History Approach to State Policy Emul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1,No.3,2009,pp.1125-1140.。
当然,事件史方法也在不断调适和发展。譬如,Volden建立了配对州-年事件史分析方法,这一方法能够更好地观察哪些政策被认为是成功政策进而得到扩散,后又经不断完善形成了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近年来,诸如连续时间分析8谈婕、郁建兴、赵志荣:《PPP落地快慢:地方政府能力、领导者特征与项目特点——基于项目的连续时间事件史分析》,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Cox比例风险模型9张闫龙:《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作政策的扩散》,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空间计量10Scott J.Cook,Seung-Ho An,Nathan Favero,"Beyond Policy Diffusi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29,No.4,2019,pp.591-608.、地理信息系统和实地试验11Daniel M.Butler,Craig Volden,Adam M.Dynes,and Boris Shor,"Ideology,Learning,and Policy Diffusion:Experimental Evide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61,No.1,2017,pp.37-49.等也被逐步引入政策扩散研究,但这些新方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简化过程研究路径。
五、把“过程”找回来:政策扩散研究的第三波
20世纪以来兴起的机制分析是对政策扩散研究简化路径的回应和补充,机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素识别的单调性,但也有局限性,除了前文提到的机制分析还没有处理好不同机制的作用边界问题外,机制分析更着眼于对政策扩散何以发生进行机制阐释,而不是对政策扩散过程进行梳理,关注的问题过于局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Karch1Andrew Karch,"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Vol.7,No.1,2007,pp.54-80.、Shipan和Volden2Charles R.Shipan and Craig Volden,"Policy Diffusion: Seven Lessons fo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72,No.6,2012,pp.788-796.都曾在论文中呼吁要关注政策扩散的微观过程,尤其需要分析在扩散过程中,新政策的目标与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3Hanna De Vries,Victor Bekkers,and Lars Tummers,"Innovation of in the Public Sector:A Systematic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Public Administration,Vol.94,No.1,2016,pp.146-166.。那么,如何理解新政策目标和结果的一致性?对此中文文献开展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反思性讨论,这些研究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在还原政策扩散过程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讨论政策扩散现象的内在机理。本文把这种研究尝试概括为“把‘过程’找回来”。
目前至少形成了三种“找回”策略。一种是把分析单元落脚在个体层面,把政府官员作为观察线索,考察政府官员的任职经历和关系网络等对政策扩散的影响,但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与之相比,把分析单元落脚在政策层面的研究不断增多,其共性是考察政策在扩散中的变化,均发现政策在扩散中存在“变异”、“扩展”、“再建构”、“再创新”现象。这些现象或缘于突出创新4管兵:《发明还是扩散:地方政府创新动力机制》,载于《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或是学习所致5周志忍、李倩:《政策扩散中的变异及其发生机理研究——基于北京市东城区和S市J区网格化管理的比较》,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林雪霏:《政府间组织学习与政策再生产: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以“城市网格化管理”政策为例》,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1期。,或受限于政策不兼容6朱亚鹏、丁淑娟:《政策属性与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或者是行动者与情境的互动产物7熊烨:《我国地方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建构”研究——基于江苏省一个地级市河长制转移的扎根理论分析》,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3期。,或是初始条件与治理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8Huanming Wang,Wei Xiong,Liuhua Yang,Dajian Zhu,Zhe Cheng,"How Does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Reinven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Bicycle-sharing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Cites,Vol.96,2020,pp.1-10.,但共性是主要出现在快速变迁、高不确定性和竞争激烈的政策领域中9Gwen Arnold and Le Anh Nguyen Long,"Policy Expansion in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79,No.4,2019,pp.465-476.。最后一种是把分析单元落脚在制度环境层面,考察特殊性的制度环境因素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如有研究发现中国场景下的政策扩散呈现出“条条创新、块块扩散”特征10陈思丞:《政府条块差异与纵向创新扩散》,载于《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2期。。
通过研究,我们看到政策扩散过程实际上高度复杂,政策在扩散中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些研究为克服政策扩散研究的简化倾向提供了思路,但也存在局限。其一,如果陷入无限还原,则可能会因治理事实的多样性导致整个研究走向碎片化。其二,过程路径可观察的经验范围比较有限,目前的研究主要观察两点之间的政策变异,但要观察更多点之间的政策扩散则需研究者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其三,过程路径虽然可以把政策变化呈现出来,但却难以精确识别跨域场景中的政策变化机理。因此,反思简化路径的目的并非走向极端的过程还原路径,而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而实现对简化路径的补充和调适,实现更好的知识生产。
目前基于过程还原路径的研究主要是聚焦政策扩散的“变”,回答了“变什么”和“何以变”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仍有很多现象难以通过这种研究来解释。如基层协商民主被认为存在扩散瓶颈,这是对基层协商民主整体扩散特征的把握,却难以解释在部分地区比较突出且得以延续的事实11付建军:《作为治理创新的基层协商民主:存量、调适与内核》,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还有很多新政策虽然不存在扩散瓶颈,在扩散中也经历了明显变化,但整体上却没有对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存在“纳而少用”(Broad but Weak Diffusion)的问题1Myungjung Kwon,Frances S.Berry,and Richard C.Feiock,"Understanding the Adoption and Tim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US Cites Using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19,No.1,2009,pp.967-988.。面对这些现象,就需要建立更全面的“过程”框架,增强解释穿透力。
六、三阶段框架:政策扩散研究的“全过程”路径
实践中,有些政府愿意采纳创新政策并且积极应用,而有些政府则不愿意采纳,或采纳了不愿意应用。这种分化现象涉及到两个问题:创新的采纳和创新的应用。在此意义上,政策扩散至少存在两种面孔:采纳的政策和应用的政策。政策采纳指形成行动能力,包括形成政策的观念、建立政策应用的工具等,政策应用则将采纳的观念和工具转化为具体实践2Nico Stehr,Practice Knowledge: Applying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2.。采纳的政策呈现的是设计逻辑,而应用的政策则是指采纳主体对创新的认知及政策的实践形态3本文关于创新两张面孔的区分受益于简·芳汀对信息技术的区分。在《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和制度创新》一书中,芳汀将信息技术区分为客观的信息技术和被执行的信息技术。。考虑到扩散中的政策变化情况,需进一步将政策采纳分为政策启动和政策再生产两个子阶段。由此,政策扩散过程由政策启动、政策再生产和政策应用构成。三个子阶段的逻辑关系是:采纳主体在决定引入新政策时对特定政策形成创新认知,创新认知引发新政策的构成要素在被采纳的过程中可能被调整,从而进入政策再生产阶段;政策再生产改变新政策的政策属性,进而影响新政策的应用。

图1:理解政策扩散的三阶段过程框架
是否采纳一项政策主要取决于采纳主体对新政策的认知,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中,采纳主体对新政策的认知是复杂多维而非单一线性的。本文认为,政府在采纳政策的过程中至少包括三种认知维度。一是效率认知。所谓效率认知,主要是指新政策在扩散中对于采纳主体而言所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操作复杂性。这与技术应用理论中的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具有相似性4任敏:《技术应用何以成功?——一个组织合法性框架的解释》,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二是身份认知。身份认知主要是从采纳主体所处的制度环境角度建构采纳主体的认知,即在特定环境下通过采纳新政策塑造的相应组织身份。从横向角度看,政府在采纳新政策时需要考虑如何体现出与同辈政府的相对优势,即通过采纳新政策“打造亮点”。从纵向角度看,当更权威政府在某个领域发出了很强的政策创新信号时,下级政府在这个领域进行政策采纳的动力就会显著增强。三是规范认知。规范认知主要是指新政策与既有通行规范的兼容程度。通行规范可以分为社会主流价值和既有政策风格两种,社会主流价值包括需求期待和地方性知识两种形态。采纳主体不仅要考虑新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体的需求期待,也要考虑新政策与地方性知识的吻合度。此外,当新政策与既有政策体系差距较大时,往往会蕴含一定的政治风险。在这个背景下,采纳主体往往会平衡“打造亮点”和风险控制的关系,即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寻求创新“亮点”。

表1:创新认知的构成与内容

创新身份认知同级竞争认知 新政策的相对优势是否明显任务压力认知 更权威政府是否有明确信号社会条件认知 新政策是否吻合社会需求期待和地方性知识政治风险认知 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创新规范认知
在三种创新认知的综合作用下,政府在采纳新政策时会形成两种行为模式:一种是在采纳新政策时原封不动地复制政策内容;一种是采纳主体根据创新认知对新政策进行修正和调整,从而在政策扩散过程中形成政策再生产现象。
进入到政策应用阶段后,需要考虑政府作为公共组织具有明显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因为不同主体对政策再生产的认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会传导至政策应用阶段。在政策扩散中,采纳者和应用者经常是处在分离状态中,采纳者往往是政府主官和部门负责人,而应用者则主要是新政策的使用者,即窗口/基层单位的具体办事部门和人员。采纳者主要从整体政府和个人政绩角度出发,侧重于从效率合法性的问题解决、政治合法性的同级竞争、规范合法性的创新风险角度建构对新政策的创新认知。而应用者则主要从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工作开展角度出发,侧重于从效率合法性的操作难度、政治合法性中的任务压力与规范合法性中的社会条件角度建构对新政策的创新认知,二者对新政策的认知差异明显。

表2:采纳者与应用者的创新认知差异
在不同情境下,采纳者基于特定创新认知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动性存在明显差异。譬如,在自上而下扩散中,创新采纳者的组织能动性很可能会逐步递减,后加入的创新采纳者调整新制度构成要素的动力并不强,政策再生产的幅度可能较小。当采纳者调整新政策的幅度较大时,新政策的政策属性就可能被改变,进而改变新政策在应用阶段的兼容性和保障条件。此时如果应用者对新政策的态度较为消极,新政策的运行就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只有当采纳者处在权力体系的中心位置时,才能够对应用者进行高激励和强约束,以确保新政策目标与应用保持一致。
总之,与现有研究相比,三阶段过程框架实现了政策采纳和应用的有机衔接,可较完整地呈现政策扩散的全过程。此外,这一框架可用来分析自上而下的政策扩散以及水平和自下而上的政策扩散,适用性更广。
七、结语
就定量研究而言,必要的简化是因素识别的基础,但在建立因素识别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就需围绕知识生产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这就需要通过非定量研究对政策扩散的经验事实进行适度还原。但对简化路径的反思并不是要否定简化路径,简化路径的优势是通过因素分析建立整体判断,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要推动政策扩散研究进而打破政策扩散研究的黑箱,可能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开展混合研究。
具体来说,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可能存在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验证-解释”取向,即通过定量研究对特定政策领域的扩散形态进行整体上的趋势分析和因素分析,在提取出相关性因素之后再借助过程追踪进行机制呈现。一种路径是探索-验证取向,即通过对特定政策扩散现象的微观考察,发现新的作用机制,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解释变量,再通过定量研究进行相关性验证。当然,这两种取向在实施过程中都可能会受到案例特殊性的影响:一方面通过验证的因素在微观过程中极有可能是通过多重机制的相互作用实现政策扩散;另一方面在特定案例中观察到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地方性知识的深刻影响,进而无法在一般层面提炼为解释变量并操作化。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混合研究的开展需要建立有效的融合渠道。
在现有的研究方法工具箱中,定性比较分析(QCA)可以为此提供帮助。在“验证-解释”取向的混合研究中,可以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来观察机制的组合模式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差异,进而识别不同因素作用于政策扩散的情境特征。在探索-验证取向的混合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调和地方性知识的作用,通过多案例的比较提取出具有中观解释力度的因素,进而降低因因素特殊性所带来的操作化难度。
在混合研究方法的支持下,政策扩散研究需拓展自己的问题视野,把焦点从描述某一个具体政策的扩散转变到回答某一类政策问题,尤其是跨领域政策扩散风格的比较上来。此外,未来政策扩散研究还需与公共治理研究进行充分融合,拓展政策扩散研究的新话题。如目前政策扩散研究都在集中关注以政府作为主体的政策扩散现象,但现实中市场和社会主体在政策扩散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市场和社会主体能发挥的作用空间更大。那么,如何理解市场和社会主体在政策扩散中作用,其作用和政府主体相比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对政策扩散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应当在未来研究中得到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