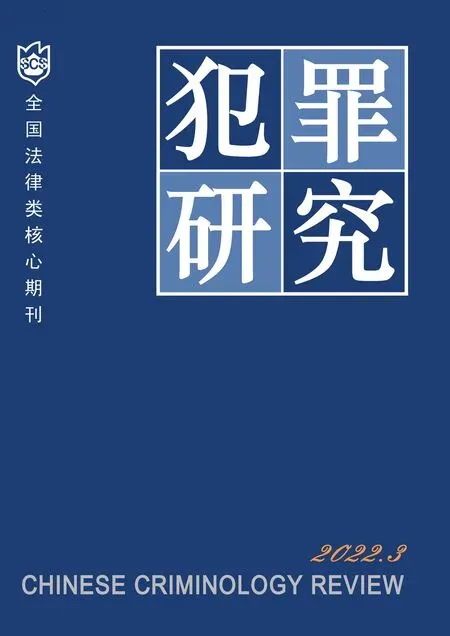美国减少审前羁押最新举措
——保释制度改革
夏 菲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7年年底在监狱中服刑的有1489400人,其中黑人男性的服刑率(每10万美国公民中被判1年以上监禁刑的人数比例)是白人男性的6倍。2017年6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县和城市地方看守所羁押的人数为745200人,其中 65%(48.2万人)属于审前羁押,看守所全年收押 1060万人次。这个数字在 2018年也没有大的变化,其结果是美国成年人中有1/3的人在23岁前曾被逮捕过,有犯罪(或涉嫌犯罪)前科记录的人员达到7000万至1亿人,即平均每3个美国人中有1人有前科记录。羁押人数多、被羁押群体中的种族差异成为美国刑事司法的突出问题。因此,近10年来,关于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由于“法律与秩序”问题在政治活动中的敏感性、重要性,重大改革举措较难获得国会和总统的批准,旨在短期内减少被羁押人数的局部性改革,即保释制度改革得到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以及记者、社会活动家等一致支持,各州也纷纷启动改革尝试。
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保释制度在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占据更重要位置,这主要是源于两种法律体系中逮捕措施在适用上的巨大差异。在美国,如果执法部门有“合理理由”认为某人实施了犯罪,可以采取有证逮捕或者紧急情况下的无证逮捕措施。当然,第一种情况是常规,即逮捕申请需经司法机关审查并同意,这是司法机关对警察权力的监督、控制,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传统上,逮捕是刑事案件正式启动的标志,只有当法院同意逮捕后,该案件才进入法院登记系统中。这种情况至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略微有变化,执法部门对交通犯罪嫌疑人以签发传票形式要求其到庭,但在大部分案件中,执法部门还是习惯于采用逮捕措施。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逮捕是针对可能会逃跑、威胁证人或者再次实施犯罪等嫌疑人采取的措施,即不逮捕是常规,逮捕是例外。制定法对于逮捕的条件规定非常明确,司法机关就具体案件中的情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同意执法部门的逮捕申请。因此,就所有刑事案件中逮捕使用的比例而言,美国的逮捕比例必然是远高于大陆法系国家的。
美国这种逮捕制度安排体现了其强调刑事司法中司法制约的理念,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都在侦查的早期阶段介入,同时也是确保所有犯罪嫌疑人都有在法官面前陈述的机会。另外,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了被告人有获得快速审理的权利,只有当案件进入法院登记系统后,法院才能掌握案件进程,进而切实保障被告人的此项权利。因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会被采取逮捕措施,而保释是嫌疑人在审判前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除非案件被撤销),因此保释制度在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法官作出的是否给予嫌疑人保释的决定,对每个个体而言意味着其自由权利是否被剥夺,对社会而言则是有多少人被关进看守所。
一、美国保释制度的历史发展
(一)有关保释制度的早期法律规定
美国保释制度最初是继承英国保释法律制度内容,后者的法律基础是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9年《人身保护令》以及1689年《权利法案》等,因此英美保释制度在起源上是侧重对个体自由权利的保障。殖民地时期最早的法律文件——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权利书》(Massachusetts Body of Liberties)规定,保释是所有非死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要求嫌疑人有充分担保保证其能按期到庭并表现良好。1682年宾夕法尼亚的立法规定:除了有证据证实有罪或者有罪认定可能性高的死刑犯罪,其他犯罪嫌疑人在有充分担保的情况下,都应当获得保释。1787 年《西北地区法令》(Northwest Territory Ordinance of 1787)与1789年《司法法》(Judiciary Act of 1789)关于保释的规定采取的都是宾夕法尼亚模式,也就是对非死刑案件嫌疑人的保释没有附加条件限制,权利性质明确。最终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专门就保释作出规定:不得科处过多的保释金。这种极其简短的表述使该条款成为宪法中最“模棱两可”的内容。仅从文字上看,《宪法》第八修正案并没有明确保释是一种权利。因此,一般认为保释不是个体的宪法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宪法》第八修正案并没有禁止国会就哪些案件可以适用保释进行界定。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当惩罚可能是死刑时保释不是必然的。事实上,《宪法》第八修正案并没有说所有被逮捕者必须被保释。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从历史渊源及早期殖民地时期一些立法推断,制宪者应该是意图规定保释权,但由于立法过程中的一些意外事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立法表述。还有学者提出,自美国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50个州中有42个州的宪法有保释权的规定,其条款表述基本采用的是1682年宾夕法尼亚模式。同时就联邦宪法而言,保释权利也是正当程序、人身保护令等宪法条款所包含的内容,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任何人,不是因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名被逮捕的,在被认定有罪前,应当允许其被保释;因可能判处死刑罪名被逮捕的,由法官决定是否给予保释。
综上,自美国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对保释进行规范的联邦立法分别有《宪法》修正案、1789年《司法法》以及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宪法禁止对被告人科以“过多”的保释金,而后两部联邦立法都明确规定非死刑罪名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保释,大部分州宪法有类似规定。因此,在死刑罪名案件中,法官可以决定予以羁押或者保释,而在非死刑罪名案件中,法官应当同意保释,而且保释金额不能过高,否则就违宪。宪法的这种限制规定,其目的也在于防止法官通过设置高保释金而实际剥夺被告人的保释权。
(二)19世纪下半叶的保释制度改革
最初保释的形式是他人担保,即被告人的家人或者朋友承诺保证被告人按时出庭。只要不是死刑案件,被告人一般都获得保释。这种保释因为不涉及金钱交付,所以不会存在违宪问题。但是进入19世纪后,随着更多的人口向西部、乡村迁移,社区、家庭联系日益松散,金钱担保逐渐成为主要形式。除了被告人自己交付保释金,20世纪初还出现了专门的商业保证——商业单位通过向被告人收取一定费用为被告人交纳保释金。
保释金多少才不是“过多”?首先要明确保释金的目的。“现代的保释金和古代的担保人保证一样,其目的都是确保被告到庭。保释金额的设定如果超过了实现这一目的所需,就是‘过多’。”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刑事司法中保释金的目的就是确保刑事诉讼程序能正常进行。其次,从哪些因素来判断是否能实现该目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提供了若干法官据以决定的因素,包括犯罪本身的性质、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情况、被告人经济能力以及被告人个体特征等。然而,这些终究是一些原则性、概括性标准,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需要就个案特殊情况与被告人个体特征来决定具体保释金额,而且很多时候不同标准之间会产生冲突,比如,犯罪性质严重,保释金应该高一些,但是被告人极其贫困,即便是较低的保释金也无力交纳。金钱保释很快显示其负面后果,交不起保释金的被告人只能蹲看守所。早在1927年,社会学教授阿瑟·比利(Arthur L.Beeley)就芝加哥库克县保释和羁押情况的实证研究就得出结论:保释金常常超出被告能承担的范围,看守所里被羁押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逃跑,而是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
无论保释是不是宪法权利,当被告人因付不起保释金而被羁押时,《宪法》第八修正案就受到了挑战。1966年《保释改革法》(Bail Reform Act of 1966)试图改变这一状况,该法是1789年《司法法》后首个就保释问题进行专门规范的联邦立法。该法规定,任何因非死刑犯罪被指控的被告人都应当通过签署个人承诺书(Personal Recognition)或者无担保保证书(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而获得释放,其中无担保保证书是指获得释放时无须交纳保释金,但是如果违反保释规定则需要交纳担保金。如果法官认为上述两种形式不能保证被告按时到庭,可以附加其他条件,包括由第三方(可以是被告人的律师、家人、朋友等个体以及机构)对被告人进行控制、限制被告人出行与社会交往、要求被告人交纳保释金等。显然,其立法目的是要求法官尽量不使用金钱保释。1966年《保释改革法》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一些作用,法院使用个人承诺书的比例有所增加。同时,该法的推行也催生了审前服务机构(Pre-trial Service Agencies)的诞生,有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禁止了商业保释模式。但是,这种以保障被告人权利为方向的改革因为美国刑事政策整体性的变化而中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他旋即启动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当年1月31日,尼克松在其首次关于犯罪控制的公开演讲中建议国会修改法律,同意对那些显然会危害公众安全的刑事被告人采取临时羁押措施。司法部随后向国会提交了具体修改建议,1970年国会通过《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改革与犯罪法案》(District of Columbia Court Reform and Criminal Procedure Act of 1970)。立法中关于保释制度的新规定备受争议,从内容上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理念,也再次引发此种规范是否违宪的激烈争论。1970年立法首先改变了传统的保释制度的目的,除了确保被告人到庭,还要保证审判前被释放的被告人不会对他人及社会造成安全隐患,也就是说保释不仅仅是针对被告人在本案中所涉及犯罪的处罚问题,还要实现预防未来可能犯罪的目的。其次,立法明确规定了对几类犯罪应当采取羁押措施,其案件适用类型大大超过原来的死刑犯罪,具体包括:实施危险性犯罪(包括抢劫、以实施犯罪为目的非法侵入或企图非法侵入他人不动产、非法销售或运输毒品等),且控方有证据显示其他方法不足以保证社会安全的;实施暴力犯罪(包括谋杀、强奸、绑架、抢劫、侵害他人身体、性侵未成年人等),且本次犯罪是10年内再次犯暴力犯罪或者正处于缓刑、假释期间的;无论何种犯罪,被告人出于干扰或者企图干扰司法之目的而实行或企图实行威胁、伤害证人或者陪审员的。对于上述刑事被告人,经正当程序,法官可以作出最长60天的羁押决定。1970年立法虽然是国会制定的法律,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4年《保释改革法》(Bail Reform Act of 1984)是适用于所有联邦犯罪案件的全国性立法。该法延续1970年立法的基本精神,明确规定法官可以基于对被告人是否可能逃跑或者对他人、社会造成危险的考虑而作出予以保释和采取羁押措施两种不同的决定。对于犯暴力犯罪、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被告人、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违反管制物品相关法律以及多次实施严重犯罪的被告人,法官如果认为有条件释放存在被告人逃跑或者危害他人、社会安全的,可以对其采取羁押措施。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保释制度立法显然相较于之前的立法发生了较大转变。在此之前,立法强调的是刑事案件中个体的权利,即非死刑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有权获得假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立法是兼顾个体权利与公众安全,“审前羁押”正式出现在保释立法中。对于这种变化,反对者认为联邦立法违宪,剥夺了部分非死刑犯罪被告人获得保释的权利。支持者认为保释本来就是制定法权利,而非宪法权利,因此国会修改制定法内容符合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坚持其一贯立场,认为保释不是绝对权利,1984年《保释改革法》在确保公共安全以及被告人自由权之间充分实现了平衡。
事实上,在1970年立法和1984年立法之前,审前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超出死刑犯罪案件。法官在决定保释金时本来就会考虑案件性质、被告人以往犯罪记录、被告人的就业与家庭状况等,对那些有危险性的、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要求高额保释金,其目的是对其施以羁押而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将司法实践固定下来。不过,即使联邦法律发生巨大转向,很多州也跟随联邦立法的变动而改变,但仍然有24个州的宪法保持原来的传统,坚持非死刑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有权获得假释的原则。学者关于保释为宪法权利的观点也仍然具有影响力。因此,关于保释权的法律地位,就联邦层面而言,属于制定法权利;就州层面而言,不同州因宪法规定不同而分别属于宪法权利或者制定法权利。
二、保释制度最新改革
(一)改革的社会背景
美国国会1984年立法肯定了对某些案件被告人予以审前羁押的必要性,在联邦政府大力推进“严打”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审前被羁押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被告人因付不起保释金而被羁押的情况愈发严重。自1983年至2013年,看守所年入所人次从600万增加到1170万。在联邦层面,审前羁押比例持续上升,从1988年的30%上升到2018年的近75%,其中违反移民规定的犯罪、暴力犯罪、涉及武器犯罪、毒品犯罪是羁押比例较高的犯罪类型,而财产犯罪、公共秩序犯罪的羁押率较低。在州的层面,据统计,1990-2004年,美国75个较大的县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62%的重罪被告人获得审前释放。自1998年起,更多使用保释金保释,而非被告人自己签署保证书保释。在经法官审查最终被审前羁押的人员中,平均每6个人中有1人是其保释请求被法官拒绝,5人是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根据司法部另一项有关州重罪情况的报告,2009年,38%的重罪犯罪人在审判前的整个时期被羁押在看守所,这其中90%的人是因为付不起保释金而被羁押,而非法官直接决定予以羁押。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犯罪数量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严打”刑事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这不仅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对个人、社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个体如果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其申请公共住房、大学贷款、就业、子女监护等都会面临巨大障碍。大量生活在曾被刑事司法体系处理过的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其日常物质生活质量会下降,心理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恶性发展。如今,过度使用羁押导致的经济、种族不平等已经成为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新一轮保释制度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着眼于长期存在的由保释金额限制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并通过对“现金保释”的改革快速实现减少被羁押人数的目的。
(二)新泽西州的保释制度改革
本次改革目前集中于州的层面,虽然从比例上看,州法院已经较联邦法院更少使用审前羁押,但由于州执法机关处理的犯罪案件远远多于联邦执法机构处理的案件,因此从总量上看,州的改革对于全局的影响意义更大。走在本次改革前列的是新泽西州。2012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在新泽西州,每8个被审前羁押的人员中有1人是因为无力支付2500美元及以下的保释金,而不是因为其可能会逃跑或者威胁他人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对公共安全有威胁的人则通过支付高额保释金获得保释。改革的方向就是羁押少数应当羁押的被告人,对于其余大多数案件中的被告人,则尽量使用非保释金的方式予以审前释放。
2014年12月,新泽西州投票通过修改宪法有关保释的规定,明确法官可以为了保证被告人到庭以及保护公共安全而作出羁押被告人的决定。在此之前,法官几乎给予所有被告人保释决定,但是很多被告人因为付不起保释金而被羁押。2014年,立法机关通过了《刑事司法改革法案》(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ct),修改审前释放、羁押具体法律规定,新法于2017年1月1日起生效。新法强调,对于那些能按时到庭、对他人和社会没有安全威胁、不会妨害或企图妨害刑事司法程序进行的被告人应当予以非保释金释放,只有当所有附条件的释放都无法保证被告人能按时出庭时,才能使用保释金保释。控方可以对一些严重犯罪(如严重暴力犯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曾经两次以上实施过前述两种犯罪、严重的贩卖人口犯罪、持枪犯罪、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等)被告人或者控方认为存在不按时到庭、对他人和社会安全产生威胁、妨害或企图妨害刑事司法程序可能性较大的被告人提出羁押动议。在有关审前羁押的庭审中,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或者获得指定律师代理,可以提供信息、证据、证人,并可交叉询问证人,以反驳控方提出的羁押理由。最终由法官综合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对被告人所作的风险性评估等信息作出决定。法律要求法官尽量不使用保释金释放,对于符合审前释放条件的,首先选用被告人个人承诺书或者无担保保证书,其次是附条件释放(如由他人担保、被告人需就业或者将要就业、进行或将要开始教育项目、接受社会交往限制、定期到执法部门报到、不持有枪支或者其他破坏性器具、不过量饮酒、不使用毒品以及进行医学、心理、身体治疗等)。只有当上述方式都无法保证能按时到庭时,才能使用保释金释放。而对于那些对他人和社会危险性高的被告人,则予以羁押,不予保释金保释。
本次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提高传票指控(Complaint with Summon)措施使用比例,以便从源头上减少被羁押人数。对于较轻的犯罪,警察只是申请法院签发传票,要求嫌疑人按照要求到庭进行相关程序,而不予以逮捕。对于较严重犯罪的嫌疑人或者再犯犯罪嫌疑人等则采取逮捕措施(Complaint with Warrant),此类犯罪嫌疑人在被捕后将被临时羁押最长至48小时,在此期间对被告人进行危险性评估,评估结果交给法官作为其决定是否释放嫌疑人的重要依据。
改革启动以来,其成效已经获得全美关注,在一项非官方评估中,新泽西州的改革在实现审前正义方面被评定为“A”级,而各州的平均成绩是“D”,17个州是“F”。根据新泽西州法院发布的报告,其改革成效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充分显现:2014年,54%的被告人以传票形式被指控,而非逮捕,2017年这个比例达到71%,2018年为67%;2018年共有135009名被告人被指控,44383名被告人被逮捕,8669名被告人被法官决定审前羁押,即6.4%的羁押率,审前释放率为93.5%;在所有被逮捕的被告人中,法官只就 102人给予保释金保释;2018年10月3日当日看守所人数与2012年同日相比减少了6000人,当日被羁押人员中因为无力支付2500美金以下保释金的为4.6%,2012年的比例为12%。在大量减少审前羁押的同时,被释放的被告人在待审期间再犯罪或者不到庭的比例较改革前没有大的变化,被告人在待审期间犯大陪审团指控罪(Indictable Crime),即相当于其他州所称的重罪(最低刑期为1年以上的犯罪)的,2014年为12.7%,2017年为13.7%,再犯违反秩序类犯罪(Disorderly Persons Offense),即相当于其他州的轻罪的,2014年为11.5%,2017年为13.2%;被释放被告人的到庭率,2014年为92.7%,2017年为89.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泽西州刑事司法改革达到了预期目的:在运用循证风险评估(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工具基础上,大幅降低审前羁押人数、保释金保释数量以及看守所羁押人数,与此同时确保了公共安全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新泽西州的改革成效为其他州推动改革提供了正当化理由与参照样本。据统计,2018年,有24个州通过了包括保释制度在内的有关审前正义(Pretrial Justice)方面的立法。最新的、引起较多关注的是纽约州的保释制度改革。
(三)纽约州的保释制度改革
纽约州于2019年4月1日通过《刑事司法改革法》,该法于2020年1月1日生效。保释制度改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改革目标与新泽西州相同:减少保释金保释,减少审前羁押。新法首先明确规定法官在作出决定时的选择排序:要求被告人签署承诺书的释放、附条件(但不是保释金)释放、保释金释放、羁押。对所有犯罪,法官都可以作出审前释放的决定,对于大部分轻罪、非暴力重罪以及个别暴力犯罪,只能适用前两种释放,而且要选择最少限制性的附条件释放,在法官认为被告人签署承诺书释放无法保证其到庭的情况下,也应当选择最少限制性的附条件释放。被告人因为释放申请被法官驳回或者因无力交付保释金而被羁押的,可以提起变更为审前释放的申请,并有权获得律师代理。
附条件释放主要是指法官决定让嫌疑人进入社区监督项目(Supervised Release Program),由社会工作者对嫌疑人进行监督。法官或者社会工作者根据嫌疑人涉嫌罪名的严重性以及是否会按时到庭的评估将其分为不同监督类型,从嫌疑人每月一次电话签到的一级监督管理到嫌疑人每周一次亲自签到的五级监督管理不等。社区监督项目于2009年开始在纽约市皇后区进行试点,2016年3月正式在纽约全市适用,5年里,有25000名待审嫌疑人免交保释金而被释放,大大减少了审前羁押人数。2020年立法将社区监督项目适用对象扩大至所有嫌疑人。这种立法被认为是确立了“释放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Release),即审前释放是原则,羁押是例外,可以说改革力度空前。或许也正是因为立法迈出的步伐过大,改革也引起一些民众和专业人士的反对,他们担心嫌疑人不被羁押会给公众带来危险,犯罪率会上升。2020年4月,有关保释改革的法律被修订,主要内容是增加了可以适用保释金保释的罪名,给法官更多自由裁量空间,并增加了对释放嫌疑人进行控制的手段,比如要求嫌疑人交出护照、接受心理治疗、亲友进行担保等。
在纽约州,纽约市犯罪数量占比较高。2020年,纽约市犯罪报案数(177319件)、逮捕成人数量(118362人)都占到纽约州的(分别为342353件、255592人)一半左右。因此,纽约市刑事司法体系运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纽约州的状况。在 2020年保释改革法生效之前,纽约市刑事法院的法官对于绝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作出了审前释放的决定,但一个突出问题是大部分获得保释金保释决定的被告人因无力支付而被羁押。以 2018年为例,当年纽约市刑事法院提讯案件203443起,其中32%在提讯程序中结案,在剩下的138387起案件中,76%的案件被告人被无保释金释放,22.8%的案件被告人被要求提供保释金,最终有3.2%的被告人通过保释金获释,19.7%的被告人因为未交付保释金而被羁押,法官直接否决被告人审前释放申请的仅有1.2%。因此,新法致力于减少保释金保释的确是抓住了解决审前羁押问题的关键。法律执行1年后,其成效也十分显著:2020年与2019年相比,轻罪嫌疑人进入社区监督释放项目的从 2.9%增至 7.9%,暴力重罪嫌疑人进入社区监督释放项目的从2.1%增至13.8%;非暴力重罪和暴力重罪嫌疑人被裁定交保释金的都下降了近12%。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第一顺位审前释放——要求被告人签署承诺书的释放并没有明显增加,但附条件的审前释放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法官更少要求嫌疑人交保释金以获得审前释放。当然,这种下降的趋势在2020年表现得并不均衡,前3个月,纽约市审前羁押人数下降了40%,但自年中以后出现了一定的逆转。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是纽约市2020年枪击事件几乎是2019年的2倍,部分民众和政府官员认为这与保释制度改革有关,这种舆论对法官、检察官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美国保释制度改革带来的启示
(一)个体权利与公众安全是立法关于审前羁押或释放的基本考虑因素
美国殖民地时期立法以及宪法修正案有关刑事司法制度的内容体现的是个体权利本位的理念,在制度设计上强调防止政府对个体权利不必要的侵害,因此对于非死刑犯罪嫌疑人规定了保释权,即审前无条件释放,也由此确立了审前释放为常态,审前羁押为特例的基本原则。当然,早期联邦和州刑法中死刑犯罪罪名比当前立法中的死刑罪名要多,比如,在18世纪末,一些州的刑法规定,除了谋杀,强奸、纵火、入室盗窃、抢劫也可判死刑,个别没有制定刑法的州则按照普通法规则,对所有重罪适用死刑。随着死刑罪名逐步减少,各州的立法仍然保持这种模式,比如,加州的立法就规定除了极少数犯罪以外,其他犯罪的嫌疑人在有充分保证的情况下都应当释放,这被认为是赋予了嫌疑人保释权。然而,刑事司法制度始终要在个体权利与公众安全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早期立法未赋予涉嫌死刑犯罪的嫌疑人保释权的做法已经隐含着对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评判,司法实践中法官设立高出嫌疑人经济承受能力的保释金同样折射出法官对公共安全的考量。20世纪70年代,联邦立法开始突破只能对涉嫌死刑犯罪的嫌疑人拒绝保释的传统法律规定,这种变化更多考虑公众安全需求。当然,以审前释放为主的模式并没有改变,从上文中对于新泽西和纽约州的相关数据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改革前,法官直接决定羁押的比例也是极低的。
在改革过程中,对某项改革内容的争论也往往围绕着如何理解保释权以及兼顾个体权利与公众安全展开。新泽西州的改革是在先修改州宪法以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保释权为前提展开的,修宪体现了对公众安全需求的认同,而之后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则聚焦于如何减少保释金的使用,真正做到绝大部分嫌疑人审前被释放。加州的改革没有采取这一路径,其过程颇为曲折。2016年年底,保释金制度改革法案(又被称为“参议院10号法案”)被提交州立法机关,其主要内容是彻底废除保释金制度,而代之以嫌疑人个人签署承诺书释放、嫌疑人进入监督项目释放以及非担保型保释金释放,其中非担保型保释金释放是指嫌疑人在释放前无须提供保释金,但是如果未按时到庭则需交付。该法案于2018年8月被立法机关通过并由州长签署。然而,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起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再加上保释金行业发起公投倡议,最终导致该法于2020年11月的州公投中被否决。在这场改革争斗中,保释金行业的主要动机自然是维护行业的经济利益,但其提出的理由还包括获得保释金释放是嫌疑人的一项州宪法权利。此外,被保释人员不按时到庭甚至实施严重犯罪的个案也对公众舆论产生巨大影响。
综上,从美国保释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立法上经历了从侧重保障个人权利向更, https://edition.cnn.com/2020/09/21/us/new-york-gun-violence/index.html.多考虑公众安全的变化,司法实践中则早就因保释金的使用而导致出现大规模审前羁押现象,从而偏离了立法精神,最近的改革旨在纠偏。显然,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制度必须兼顾个人权利与公众安全,单方面强调某一方面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刑事司法圈的扩张必然导致审前羁押规模的扩大
刑罚本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最后手段,然而随着社会行政管理日益复杂化,大量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被纳入犯罪圈,而且政府在面对犯罪问题时又容易选择“严打”刑事政策,由此导致立法和司法层面刑罚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被卷入刑事司法体系的个体数量持续上升。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推行的“严打”刑事政策持续了约40年。在此期间,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立法,加大犯罪惩罚力度,其中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4年签署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为典型代表。该法扩大了死刑适用的罪名,对于数次犯重罪的人规定了强制性的无期徒刑的量刑,这被称为“三振出局”,并且拨巨款用于增加警察、监狱的数量。在警务方面,以纽约为代表的大城市警察局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推行被称为“零容忍”的警务模式,加强对破坏秩序的轻微犯罪行为的打击。该警务模式由6大行动构成:重新控制街面、减少青少年暴力行为、减少家庭暴力、减少机动车相关犯罪、减少毒品交易以及控制枪支数量。此类立法和执法最终导致美国的高羁押率。大量实施轻微危害行为的个体被卷入刑事司法体系、被审前羁押或者定罪后入狱服刑,必然会起到使这些违法者在短期内无法实施危害行为的效果。但是,个体被羁押的经历会产生“污名化”效应,使其回归社会更为困难,由此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社会控制对刑事司法体系的依赖必然要求国家对刑事司法体系投入更多社会资源,这又造成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资源投入相对不足,而这些投入恰是有利于减少犯罪根源问题的。因此,被卷入刑事司法体系的人员数量庞大,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个突出问题,而上述人群在种族分布上严重不均,又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警察等执法机关是刑事司法程序入口的把关者,警务工作中的种族歧视一直是美国社会的敏感问题。
(三)社会需理性认识审前羁押的个人和社会成本
审前羁押对被羁押人最直接的后果是其人身自由在一定时间内被剥夺,而自由权对个人而言是仅次于生命权的权利。羁押对被告人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包括:在逮捕、羁押过程中的不良体验,比如,看守所中较容易出现交叉感染问题;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充分得到保障,如被告人会见律师困难,也就无法有效开展辩护工作;与家庭、社区、单位隔离;失业以及以后在就业、获得相关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处于劣势等。美国学者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羁押对个体的负面影响。一项对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2008年至2013年间38万多轻罪案件的数据分析显示,审前羁押增加了辩诉交易达成以及被羁押者之后重新犯罪的比例。关于审前被羁押与其最终审判结果的关系,劳拉与阿诺德基金会(Laura and Arnold Foundation)就2009年肯塔基州15万多个被看守所审前羁押的个案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低风险被告人如果审前一直被羁押,其被判处看守所服刑的可能性是同样低风险而被释放被告人的5.4倍,被判处监狱服刑的可能性是 3.76倍。关于被审前羁押人员在就业方面的劣势,有研究得出结论是其时薪减少 11%,年薪减少 40%,即使是因为极轻微的违反秩序行为被捕且最终未被定罪,其就业负面影响也有4%。除了对被告人本人的影响外,审前羁押对于其家庭同样造成不良后果。被羁押者无法工作甚至失业,直接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家庭中需要被抚养儿童、被赡养老人生活水平下降。同时,被告人家庭成员还同样会面临社会歧视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羁押的社会成本,首先是刑事司法体系处理个案的经济成本。美国学者就逮捕这一措施的最低社会经济成本进行了计算,仅就警察执行逮捕所耗费的工作时间(平均5小时)乘以警察平均时薪,每年就需18亿美元。而美国审前羁押每日费用达3800万美元,年度费用为140亿美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同程度上要使用强制性手段,这必然导致警察与被采取措施人员之间的情绪甚至行为冲突,而过度使用武力、错捕等违法执法的社会成本就更高,不仅涉及国家经济赔偿,还大大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公信力。此外,如果被羁押人员的家庭陷入困境,最终也需要社会资源来解决。
(四)科学技术发展为推进审前羁押相关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效工具
美国法官在决定是否释放或羁押被告人时曾依据相关材料作出主观判断。然而,本轮保释制度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使用循证风险评估工具,强调数据基础与实证导向,通过对大量数据和案例的分析形成算法,自动计算嫌疑人不按时出庭与再犯罪风险。保释制度改革中,如何评估被告人的危险性,是释放还是羁押,如果释放是适用个人承诺书释放还是保释金释放,这些不同的决定都取决于法官对被告人未来可能行为的判断。新泽西州使用的是由劳拉与阿诺德基金会开发的公共安全评估工具。该评估工具以肯塔基州使用的评估工具为基础,对美国300多个法域的150万起案件进行数据库分析,选出9个最适宜于判断被告人危险性的指标:被捕时年龄、当前犯罪是不是暴力犯罪、指控罪名、以前犯的轻罪、以前犯的重罪、以前犯的暴力犯罪、过去两年中未按时出庭情况、两年之前未按时出庭的情况以及以前被判入狱服刑的记录。这些指标用来评估嫌疑人在三个方面是否存在风险,即不按时出庭、再犯新罪和再犯新的暴力犯罪。可见,上述9个指标都是个体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相关情况,而不包括个体的经济、家庭、职业、居住社区等情况,其目的是避免数据本身具有歧视性倾向而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呈现出经济、种族不平等。即使如此,还是有学者提出,不能简单依赖评估工具,检察官可以通过选择指控罪名来操控评估结果,而法官并不完全受评估结果制约。因此,公安安全评估本身无法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减少羁押人数、促进平等的结果,而是需要有相关联的整体制度建设,如要求检察官、法官在不按照评估结果作决定时说明原因等。此外,为履行危险评估以及对附条件释放被告人的监督职责,在司法机关中设立审前服务部门(Pretrial Service Agency)。据统计,至2017年年底,美国有25%的人口居住在使用此种危险性评估工具的法域中。而此项工具在新泽西州保释制度改革中的突出表现也促使其他州相继学习、效仿。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科学的评估工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预知个体未来的行为,法律执业群体和公众要理性接受一个现实,被审前释放的人中会出现逃跑甚至实施新的犯罪,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执法部门以非羁押方式控制个体行动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如电子脚环、电子监控、通过诚信系统限制消费(进而起到限制特定行为的作用)等。即使出现被告人逃跑,摄像头监控系统、交通枢纽的人脸识别系统都可以快速锁定目标。
四、结语
2020年,美国看守所年中单日审前羁押人数为38万,较2017年减少了10万,年度收押人次为870万,较之2017年减少了190万,降幅明显。虽然疫情是导致看守所羁押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保释制度改革的作用也不应当被低估。改革中倡导的理念、发展起来的新的审前服务模式为疫情期间减少审前羁押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同时,保释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减少审前羁押人数,更是为了实现刑事司法正义价值之平等性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应当因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得到被审前羁押或释放的不同结果。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