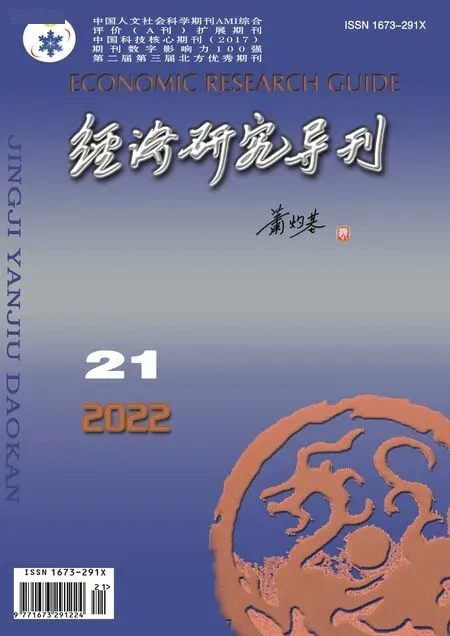上海社区基金会的提升路径
杜耐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201620)
一、相关背景
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桥梁,在促进一定区域内居民物质差距的缩小以及拉近心理距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几次全会中五次提及社会组织,从具体方面对其进行阐述,认为其是社会治理创新体制机制的载体,这充分肯定了其功能和作用。为了完善社区治理机制,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促进协同治理的发展,我国自2008 年第一家社区基金会成立以来,社区基金会在这十年通过培育社区资产,支持本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时地补充社区社会救助和政府公共服务覆盖面不足的部分,成为社区慈善救助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回应了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使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社区基金会普遍开展的项目是帮扶救助,社区关怀类,由于社区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和执行成员居住在社区,能够在迅速掌握社区居民救助需求的同时,及时进行相应对策实行和帮助。
随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政策文件的颁布,明确了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中重要的参与主体,社区基金会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通过支持社区建设,为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需要以及补充政府在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不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为适应社会治理的创新理念以及多元共治的格局要求,上海在社会公共服务上也不断探索。上海社区基金会自2014 年后得以迅速发展,与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程度密不可分。在经济的带动下人民经济水平和公益意识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很多居民主动参与公益活动。
关于社区基金会概念界定,全球并未对社区基金会明确定义,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可以结合各国的概况进行不同的趋向选择。学者们通过了解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现有成熟模型的概况分析给出相应的理解。Lucy Bernholz &Katherine Fulton & Gabriel Kasper 呼吁社区基金会应从管理金融资产转向长期领导。尽管关于“以捐助者为中心”模式和“以社区为中心”模式的跨世纪辩论由来已久,但一些学者已开始采取中立立场,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结合是社区基金会的良好象征。Judith L.Millesen &Eric C.Martin 通过分析现代社区基金会的战略布局,研究了社区基金会董事会解释组织和环境现实的方法,同时平衡了捐助者、受援者和社区之间的相关目标。章敏敏、夏建中则以我国较为成熟的桃居会和南坑社区基金会作为实证案例,将社区基金会发展分为混合和集聚两种发展倾向。而徐家良、刘春帅是在资源依赖理论背景下,选取我国已经存在的案例,以推动主体为依据划分社区基金会类型并进行比较。俞祖成则是通过对日本的研究从而概括经验推动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认识的,他研究发现,日本第一家社区基金会的出现到成功实现本土化融合的市民社区基金会的数量持续增多,各级政府一直从制度、资源两个方面对其发展进行协助和支持社会力量成立并运行社区基金会,并没有随意介入其中。同时认为我国必须重新理解政府对于社区基金会发展的角色定位,如何支持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急需转变政府的处境,通过支持和帮助以保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的独立性。
二、上海社区基金会的实践困境
(一)政策法律: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备
国务院2004 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是适用我国所有类型的基金会,而社区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相比较为特殊,《基金会管理条例》无法对社区基金会作出针对性的指导和规定。目前我国社区基金会管理领域的最大问题便是专门法律的缺位,至今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整体性规范,社区基金会的权利得不到国家层面法律的保障。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范围过于宽泛,设计法律规范和条例太多,目前只有上海、深圳等城市对社区基金会的运行设置《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与《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对于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也不能完全恰当地用于社区基金会的运作中,法律规范下的条例和约束范畴不完备存在,不利于社区基金会的长远发展。
(二)人力资源:缺乏专业的专职人员
社区基金会处于发展初期,大多数社区基金会存在人员短缺和兼职等现象。一方面,受收入待遇和费用标准等影响,工作人员离职跳槽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工作的专业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工作人员能力建设短板问题凸显,如对“慈善组织”认定不熟悉暴露了社区基金会工作人员对相关法律及制度的学习和认识不足问题。
(三)资金管理:资金的筹集渠道单一
充分的资金筹集渠道和运作资金是所有企业及组织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通过对上海市社区基金会现有的资料查询,大多数社区基金会的产生和运营都是依靠政府或者企业的资助,其自身资金的升值空间不大,资金的依赖性高不利于保持社区基金会的独立性。首先,在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目前仍处于探索初期,居民对社区基金会的了解度不高,从而对社区基金会的捐赠意愿较低。就现实情况来看,大量捐赠的情况只有在灾难发生后较短时间内井喷式涌现,捐赠人和捐赠组织对非灾难事情的慈善意识较低,对社区捐助的公益性认知不足。其次,由于基金会准入门槛较高,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占多数,而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公开募捐,限制了社区基金会的筹资渠道。最后,捐赠人和捐赠组织并没有全面了解社区需求,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常常被忽略,信息披露不充分,内部工作人员兼任监事,监事取酬现象存在,对资金运作的详细过程缺乏专业的监督组织和机制。
(四)参与主体: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社区基金会作为链接资源和社区,为社区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便利的公益平台,只为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组织,居民的了解度提高和积极参与是促进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有效举措。由于商业住房和就业范围较分散,邻里之间相识的几率随之下降,社区大范围内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的复杂化,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不足以拉近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以群众满意为主要标准的社区工作评价机制尚未建立,群众利益表达不畅,社区协商平台缺乏,社会组织、居民多元参与,协同合作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导致社区基金会不能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需要,从而更好地进行战略部署。社区居民了解度和参与积极性较低,降低了居民对社区基金会发展提供建议和监督的关注度,不利于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同时,民间对社区基金会的监督力量也尚未发展起来,尽管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工具已在国内广泛使用,但我国却没有制度来整合网络的理性力量,不利于社区基金会整体健康发展的舆论环境。
三、上海社区基金会的提升路径
(一)政策法律:完善社区基金会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在法律层面仍没有对社区基金会作出针对性的指导和规定,社区基金会主要是依赖当地所提出的相关规划。在国际范围内,美国一直使用法治的手段,通过对社区基金会的税收政策和法律制定促进社区基金会发展;日本虽然政府一直并未参与到社区基金会的运作之中,但是也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支持促进其发展;英国从国家层面上设置了参与社区服务作为公务员考核的衡量指标之一,并制定相应法规,规定国家16 岁的青少年参与社区服务。我国在关于社区基金会方面,法律法规没有对其作出针对性的指导和规定,应该综合分析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社区基金会的建立、运作及筹款等活动作出针对性的法律规定,保证各级政府在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中有法可依。市级政府应设立社区基金会相关规定,保障社区基金会的运行和权限,街道应加强与社区基金会的联系,促进职能下放,将街道下设的公益性项目纳入社区基金会中,促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二)人力资源:培育社区基金会专业人才队伍
公司制是美国慈善基金会大多数都采用的形式,设立董事会管理和运营,通常由捐赠人、不同行业领域的成功人士等组成。董事会的成员人数较多,而且涉及志愿者、学术人才、企业领导者及相关人员,还有政府组织的工作成员等多元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分保证了社区基金会决策的多元化、专业化。而经过调查,上海的很多社区基金会成员普遍不足,成员很多都是由政府公务员兼职,不利于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需要有社会经验、有公益意识的核心团队成员,才能确保培育社区精神,打造社区共同体,促进社区居民需求得到充分实现。专业的人才队伍不仅仅是活动举办的需要,在项目筛选、传达规定、项目经费公开、宣传活动以及后期监管等活动都需要专业的专职人才来完成。所以在人才队伍方面,应该符合社区基金会的有关人员分配规定,通过聘用和培育相关专职人员,提高人员薪酬制度,促进高素质志愿者队伍的发展,缓解社区基金会运行过程中事务处理的压力。政府也应在引导和补助社区基金会成员分配上推出相应举措,通过协同治理的方法完善对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和监督,提高社区基金会的决策及运作水平。社区基金会应通过培训交流、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结对帮助、优势互补等方式在针对社区基金会人才队伍培训方面发挥作用。
(三)资金管理:拓宽社区基金会资金筹集渠道
政府的投入对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十分重要,很多企业愿意出钱用于社区公共服务,需要积极鼓励。同时居民捐赠也很重要,尤其是社区居民。我国社区基金会应该在加快认定慈善组织的基础上,快速取得公开募捐进程,从而获得公募资格,拓宽管理费用支出和募捐地域与方式。在社区基金会资金筹集过程中,可以参考借鉴商业化模式来运作公益,首先应该拥有专业的组织架构与完善的内部管理,通过年报等方式做到财务的公开透明,通过设立不同类型的资金池、全面的预算制,提前做好资金来源的策划、稳健的资金策略,做到严格的资金管理。被监管方应依法落实强制性信息发布的各项要求,让本组织的资金、项目和负责人情况呈现在阳光下,及时准确发表资金使用信息以保证社会公众和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使捐赠方和受益公众都能够一目了然。
(四)参与主体:促进社区居民积极有序参与
加拿大多伦多部分社区基金会会采取收集影响社区生活质量的指标数据,建立图表来分析社区的动态变化和社区居民的实时需求。英国将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和周期次数变化作为公务员考取的重要参考维度,并进行规划,限定16 岁的青少年参与到暑期社会服务工作中。我国可以参考加拿大和英国关于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中的举措,从制度和规定层面首先确保公民的参与度和了解社区基金会的运营,其次通过特色项目维持居民参与的意愿。社区基金会在一定的责任内应保证社区的有序,在南京Y 社区基金会的服务区域内,志愿服务作为一项对公众和受益者都有正面的效应,但是由于管理混乱和分散,导致受益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应困扰。所以,社区基金会在提供服务时,不仅要注重项目开展的行为,同时要充分了解参与群体的感受,维持合理的服务秩序,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的提高,也要保证其项目开展过程的有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