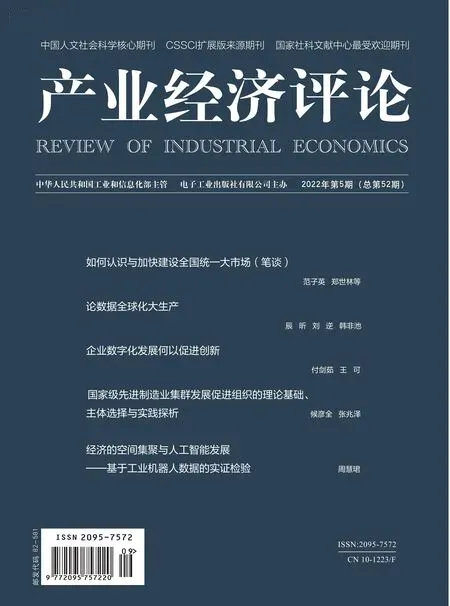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四个经验教训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意见》发布以来,引发了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客观来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短期看,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已经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化解“三重压力”非常重要。从长期看,无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追求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2035年和2050年远景目标,实现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都需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不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有文件可考的文献中,早在1962年7月10日,当时的中央财经小组就已经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代拟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工作集中统一的决定》的稿件,这个《决定》的草稿中就要试图克服商业管理中的分散主义,打破划地为牢、层层封锁等一系列的问题,旨在恢复和加强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在《决定》过去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谈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说明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顽疾,我们必须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破解背后的障碍。这其中,有四个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借鉴。
经验教训之一:用政府行政命令和直接干预的方式去构建统一市场,常常会适得其反。现实中,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出于惯性思维,常常试图以行政命令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让市场统一,然而,越是采取这种命令和干预的方式,市场就越不可能统一。这是由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市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分工网络,这个分工网络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公平地参与竞争,市场通过价格体系向所有参与者发送信号,每一个参与者根据价格信号来调剂供给和需求,从而让供给和需求能够有效调整和对接,让整个网络畅通。如果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市场运行,必然会引发几个致命问题:第一,一旦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必然会面临信息如何有效搜集和传递的问题,政府本身并不擅长搜集和处理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市场的价格体系势必会受到干扰,信号传递就会产生扭曲和偏误,供给和需求无法有效匹配,也就无法构建统一的市场。第二,一旦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就会天然地要求政府内部的各个具体部门来执行这些干预政策。这就天然地将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团体利益、个体利益等引进来了,从而,管制和壁垒有可能被内生地创造出来,而这些恰恰是需要清除的障碍。例如,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行业壁垒”,背后就是因为牵涉了太多的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从而一直难以破除。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内在地要求政府“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做多的事情”。政府需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提供好应有的公共服务,对那些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壁垒和障碍予以及时清除。
经验教训之二:在构建统一市场时,“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要统筹兼顾。构建统一市场,势必要进行改革,而这些改革都会牵扯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利益,一旦牵扯到利益的调整,改革往往就会受到一些羁绊,很难推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改革之所以相对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更接近于帕累托改进,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比较容易。但是改革走到今天,好啃的骨头基本都已经被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边际收益不断下降、边际成本不断上升,改革的难度在加大。而且,改革会牵扯到利益的再分配,这时候“存量改革”的困难就会加大。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有限,存在很多短板,还有很多的“增量改革”要做,所以,依然有很多增量空间可以利用。比如,目前依然缺乏全国统一的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碳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这些全国性的市场,因为更多的是“增量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改革起来也将更容易一些。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进行“存量改革”,坚决打破阻碍统一市场构建的重重障碍和壁垒,另一方面也需要进行“增量改革”,把那些增量空间发挥好、利用足。
经验教训之三:在改革“法”的时候要同时修改各类“办法”,才能更好地推动统一市场政策落地。我们都知道在统一大市场构建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但只有法律法规层面的改革,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法律法规要兼顾到普适性,不可能对所有具体事项明确规定,部分条款停留在原则层面,从而导致基层在具体执行中拥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于历史因素,很多问题缺乏法律法规层面的具体而明确规定,因此,历史上就会有很多“办法”和“暂行规定”,来对一些具体问题予以规定。这些“办法”和“暂行规定”在整个法规体系中的层次和位置不高,但是却切切实实地起到了对于具体问题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在基层行政人员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即使某一个上位法已经发布,但如果原来的一些“办法”和“暂行规定”还没有废除或修正,那么,基层行政人员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避责,就会依然遵照“办法”和“暂行规定”的条款办事,出现很多上位法中看似很好的条款无法落地的情形,也就很难真正推动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些顶层设计统揽全局的文件、法律、法规来推动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另一方面,在出台上位法和上位规定的同时,也一定要研究清楚,现实中有哪些“办法”和“暂行规定”中的条款是阻碍统一市场构建的具体障碍,对这些条款进行修正和废除,才能更加有效。
经验教训之四:构建统一大市场,要充分调动政策制定者和改革决策者的积极性,界定好职能部门的权责边界。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那些推行得比较顺利的改革,都是因为做到了激励相容,让政策制定者和改革决策者在“想改革”“能改革”的前提下进行的,反之,如果内部的激励机制出现不相容的情形,就一定会阻碍改革的落地。在统一市场构建的过程中,也需要构建激励相容的利益协调机制。例如,在构建统一市场的过程中,除了一部分增量改革外,还有一部分牵涉到存量改革,这时候,如果不能兼顾原有利益,只是简单地发个文件来推动改革,很可能就会导致改革拖延,最后常常会“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导致改革“实质性流产”,无法真正启动和落地。因此,任何一个改革文件,在实施细则的制定过程中,都必须要考虑到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本身的利益,加强这部分利益群体的兼容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有可能更好地推动改革。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各个职能部门的权责边界。在改革的过程,经常会出现改革的“公地悲剧”,由于各个部门的权责界定不明,在有监管利益的时候,各个部门都争着监管,结果往往“九龙治水”,行业“一管就死”;在有监管责任的时候,各个部门都争着避责,结果往往无人监管,行业乱象丛生。所以,在构建统一市场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真正调动政策制定者和改革决策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清晰界定各个职能部门的权责边界。这就意味着,统一市场的构建,客观地需要一个政府内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在政府“做对激励”和市场“做对价格”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