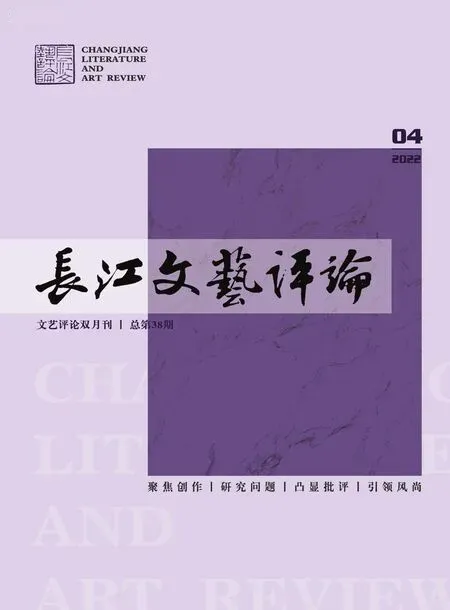“蛇”与“鸟”:许鞍华的任性与回归
◆牛淑娟
2021年10月22日,许鞍华改编自张爱玲《第一炉香》的同名电影在喧嚣未止的争议声中上映了。无论抱着何种目的,许多人走进电影院为其贡献了票房,但是关于影片的争议不仅并未停止,而且还从对男女主角不搭的外形的调侃发展到了对电影更深层次更细节的吐槽——强化痴爱的主题、青春疼痛的气质、荒诞搞笑的台词,同时也伴随着对导演许鞍华妥协商业模式的猜测等等。电影《第一炉香》的导演许鞍华出生于1947年,编导经验丰富且一度颇受大众及专业视角好评,曾数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并于2020年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不仅身负如此盛名,许鞍华还是改编张爱玲作品最多的导演。在《第一炉香》之前,《半生缘》《倾城之恋》被她搬上大银幕,舞台剧《金锁记》也由她执导,当时的评价不像今天这样几乎一边倒的嘲讽。已成电影的《第一炉香》是属于许鞍华的作品,她“好好爱一次”的主题预设在电影中有所达成,这已然是一种成功。而其实张爱玲苍凉无望的人生观与发人深思的人性探讨也隐含在这部电影之中,通过许鞍华“蛇”这一意象的增加就可以得见。
一、“蛇”意象的多重隐喻
意象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近年来,在电影美学研究中,意象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电影是声音与画面两相结合的艺术,其中最直观的画面呈现主要由意象组构,因此意象是导演和观众进行链接的重要桥梁。游飞曾经表示:“电影的意象必须以形象作为依托,而电影的形象只有在被赋予了符号价值之后,才能够成为具有表意价值的意象。”由此可见,意象是通过外在形象及内在隐喻传达导演意图,并引发受众联想的。但是相较于文学作品、音乐作品中的意象,电影中的意象因其呈现方式更加形象化,更加具有直观性的特点,所以受众在解读时反而容易强化意象的外在面,而消解导演赋予其的深层内蕴,即使是梅、兰、竹、菊这种经历千百年,隐喻几乎高于形象的意象,在电影中出现也容易被观众当成是布景或装饰而被忽略。所以在电影意象的审美过程中,更要抓住导演在意象选择与设计上的深意,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电影主旨。
在电影《第一炉香》中可以看到许鞍华一以贯之的风格呈现,她习惯温情沉静地从另一角度阐释张爱玲的苍凉阴郁。在主题的理解与诠释上,许鞍华表示“要好好爱一次”,可以说这是她少见的不顾一切、放手一搏、任性恣意了。在意象上她也突破了张的原著,有属于她自己的大胆尝试,甚至对原著作者张爱玲有一定的挑衅。小说《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在乔琪乔深夜从薇龙房间的阳台爬到山坡上,然后经过荒草地离开梁宅时清清楚楚地写道“他怕蛇”,而许鞍华却在电影中给男主角乔琪一条蟒蛇作为附属意象。附属意象,相对于意象而言是一种更有价值有意义的隐喻,对被附属的人物主体有本质外化和凸显的作用。电影中“蛇”这一附属意象在乔琪的剧情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乔琪还不认识葛薇龙的时候,他在梁家酒会上不受父亲乔诚爵士和梁太太待见,回家后向妹妹周吉婕撒娇讨零花钱,拿到钱后回到自己昏暗的房间里,从桌子下抽出一个箱子并打开盖子逗弄,但导演此时有意留有悬念,让打开的箱盖挡住了观众的视线,因此观众此时还无从知道里面是什么;第二次是在乔琪与葛薇龙初见后不久,薇龙来到乔琪家,先见到了周吉婕,并由周吉婕发出了原著中睨儿对薇龙的劝说“你不惹他,他来惹你,也是一样的”,然后乔琪出现将薇龙带到他的房间,向薇龙也向观众展示了箱子里的礼物——一条大蟒蛇;第三次是葛薇龙决心留在香港,并向姑妈梁太太提出一定要与乔琪结婚且愿意供养他的决定,梁太太与乔诚爵士不顾乔琪的意愿,单方面就此事基本达成一致后,乔诚爵士在院子里发现了蛇,也不顾乔琪的反对与求情坚决赶走了它。蛇的三次出现都在电影情节发生重要转折的阶段,构成了影片的暗线,带有不可忽视的隐喻作用。现有的相关评论中对此也存在着多重解读:
首先,据电影编剧王安忆在访谈中透露,蛇这一意象的添加是导演许鞍华的主动要求。原因是许鞍华了解到,张爱玲创作小说《第一炉香》时的原型是香港大亨何东家族的事情,而何东家里就有蛇。贴近原型塑造人物,这是导演和编剧明说出来的目的,而构想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这条蛇显然有更多可深挖的隐喻内涵,或许是导演许鞍华未曾明说,也或许是她兴致所至的无心插柳。
其次,电影中蛇这一意象所附属的主体是乔琪,而饰演乔琪的彭于晏对此意象也进行了较多主观上的思考与努力演绎,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角度:第一,蛇的美丽、毒性、冷血与善于伪装和自我保护的特点是在隐喻乔琪与之相对应的丰富而又矛盾的人物特质;第二,养蛇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很酷的行为,用以突出乔琪没钱还单纯爱玩爱享受的性格;第三,乔琪照顾小动物也是他爱心与责任感的体现。
最后,观众及影评人在电影主创人员的解读基础上,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延伸,提出电影中的蛇是乔琪的个人宠物,是他想要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私有物的一次尝试以及渴望挑战父亲权威而成为主宰者、支配者的心理隐喻。这一解释角度有其可取性,体现出增加蛇这一附属意象赋予乔琪这一角色的深层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电影中蛇这一意象在不同情节阶段的出现有不同的隐喻意义和结构作用,如蛇的三次出现还对应了乔琪寄托于蛇身上的独立话语权的高潮与失落。同时,蛇在本质上还可以被看作是诱惑的象征。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由此坠落人间,《第一炉香》书写的也是一个“诱惑之后堕落”的故事。电影通过添加蛇的意象也将这一主题可视化,并深化相应的人物特质。总而言之,蛇的附加是导演许鞍华在原著基础上的一次意味丰富,于电影人物、结构及主题的整体性都有完善作用的再创作。
二、许鞍华的“蛇”与张爱玲的“鸟”
许鞍华在张爱玲的原著基础上,给电影附加了一条蛇。其实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动物意象相比于月亮、镜子、旗袍等意象是更为少见的,但是用动物来隐喻人物也是她所娴熟的手段之一。张爱玲着力刻画女性,人物附属意象及象征隐喻的功夫也多用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身上。林莺在《隐喻的范畴化与心理机制:张爱玲文学语言中的隐喻》一书中对张爱玲的女性意象隐喻做过取样与统计研究。从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张爱玲在原著中对女性也曾用过一次“蟒”“蛇”意象——“荀太太到上海来了发胖了,织锦缎丝棉袍穿在身上一匝一匝的,像盘着条彩鳞大蟒蛇”(张爱玲《相见欢》)。张爱玲在这里赋予荀太太的蟒蛇意象不像许鞍华赋予乔琪的蛇存在多重意味,基本上只是与其身材及所穿服装的本喻体对照。同时这句话后面紧接着写道“荀太太……两手交握着,走路略向两边一歪一歪,换了别人就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张爱玲《相见欢》)。除此之外,还有这些例句值得关注——“全少奶奶年纪还不到四十,因为忧愁劳苦,看上去像个淡白眼睛的小母鸡”(张爱玲《创世纪》)。“也许她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女孩子,不过因为年轻的缘故,有点什么地方使人不能懂得。也像那只鸟,叫这么一声,也不是叫那个人,也没叫出什么来”(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油锅拍辣辣爆炸,她忙得像只受惊的鸟,扑来扑去”(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张爱玲《茉莉香片》)。“是他母亲——她想必看见他们了,马上哇啦一喊:‘陈妈,客来了!’声音尖利到极点,简直好像楼上养着一只大鹦鹉”(张爱玲《半生缘》)。“他太太至少比他小二十岁,也很有几分姿色,不过有点像只鸟,圆溜溜的黑眼睛,鸟喙似的小高鼻子,圆滚滚的胸脯,脂粉不施,一身黑,一只白颊黑鸟,光溜溜的鸟类的扁脑勺子”(张爱玲《殷宝滟送花楼会》)。“平常她像个焦忧的小母鸡,东瞧西看,这里啄啄,那里啄啄,顾不周全”(张爱玲《创世纪》)。在这些例句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女性作为本体,从声音到动作,从面容长相到精神气质都可以用各种鸟类作喻体进行隐喻。
“鹅行鸭步的鸳鸯”“忧愁劳苦的小母鸡”“扑来扑去的受惊的鸟”“绣在屏风上、死在屏风上的鸟”“声音尖利的大鹦鹉”“有几分姿色的白颊黑鸟”“焦忧的小母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用以隐喻女性频次最多的喻体是鸟类,且都是无攻击力的小鸟。不得不说,“女人是鸟”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女性隐喻的一大基调。张爱玲的“鸟”是“扑来扑去”“东瞧西看”的,或者是直接“绣在屏风上”的,是“笼中鸟”,这样的隐喻实则说明了张爱玲对“五四”之后中国女性的深层解释。她们在行动上获得了一些自主性,自身长出了翅膀也有了想飞的念头,但在社会上终究是处于卑微地位,处于男性话语的压迫之下,怎样的行为都是无法飞出囚笼的无意义的。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张爱玲:苍凉的莞尔一笑》一章有这样的评述:“‘绣在屏风上的鸟’,是张爱玲叙境中的核心隐喻。那是永远桎梏中的双翅,是永远于想象中的飞翔。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飞翔与逃遁的意象,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囚禁的意象。”这句话十分深刻地阐释了“笼中鸟”的隐喻意味,“飞翔与逃遁”是主动的选择,而“死亡与囚禁”是被动的下场,女性无法选择,只有为人所迫,在被动中走向死亡。在许多其他的张爱玲改编电影中,“笼中鸟”的主题意象也都为导演所重视,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电影技巧有所呈现。如在电影《倾城之恋》中导演许鞍华展示出白流苏是被物质禁锢的鸟,在电影《半生缘》中许鞍华暗喻顾曼桢是被身份禁锢的鸟,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导演关锦鹏塑造了佟振保是由道德禁锢的鸟。这几部电影基本继承张爱玲原著的叙事结构,因此结构天然就是囚笼,将主人公困成了“笼中鸟”。在置景和构图上,这几部电影也多次通过窗户、栏杆、铁门等作为隔断物的意象在画面上直接将人物分隔,呈现出人物被囚被缚的画面,营造了压抑束缚的压迫感与窒息感。
在许鞍华的《第一炉香》中,“笼中鸟”的主题意象由更巧妙而隐晦的手法得以表现出来。导演许鞍华通过给男主角乔琪增加蛇的附属意象,不仅隐喻男主角乔琪的性格,也隐喻女主角葛薇龙无法逃脱的处境。因为这部电影中用来隐喻男性的“蛇”与张爱玲原著中用来隐喻女性的“鸟”本就是自然界中的天敌。蛇是猎手,而鸟是猎物,就算鸟能侥幸振翅逃脱,也无法保证次次都能化险为夷,何况张爱玲笔下的都是笼中的鸟,这就决定女性的结局总是悲剧。《第一炉香》小说与电影的创作时间虽相隔数十年,但张爱玲“笼中鸟”的主题意象为人熟知。作为改编张爱玲作品次数最多的导演,且曾在以往的改编电影《半生缘》中直接将“笼中鸟”的意象置于困住顾曼桢后半生的祝鸿才手中的导演,许鞍华此次“蛇”这一意象的设置是否真的像她说出来的那样只是为了契合人物原型是存疑的。许鞍华的“蛇”与张爱玲的“鸟”附属在文本主人公身上,隐喻了作品中互为天敌且女性要么被缚要么丧命的男女关系。这种隐喻的解释符合许鞍华《第一炉香》中薇龙给乔琪供养而自身无法逃脱的结局设置,也符合张爱玲对男女关系中女性在男性话语权威下挣扎痛苦的一贯书写。除此之外,电影《第一炉香》中作为猎手,也作为乔琪附属意象的蛇是一条家养的宠物,从始至终不是在箱子里就是在笼子里,想跑不成且最终被赶走,不再属于乔琪。有一定自主性,但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自主选择,像“笼中鸟”一样,这也是一条“笼中蛇”。这样的设置其实体现了许鞍华对乔琪人生境遇的关注与隐喻,“笼中蛇”即使本性凶猛,能震慑一些“笼中鸟”,但终究是徒有其表,仰人鼻息,无法突破牢笼。许鞍华通过对蛇这一意象的结局设置,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铺开,是对影片中所有身不由己的悲悯,包括薇龙、乔琪、梁太,还有周吉婕、卢兆麟、睨儿、睇睇都是许鞍华为之叹息的对象。这样“温润如水”的与张爱玲不合的气质却反而使电影的主题回归到了张爱玲的人性探讨———不论男女,不论贫富,不论处于食物链的高处还是底端,特定时代下的人都只不过是命运的猎物,结局总是可悲可叹。借助“蛇”的出现,许鞍华“任性”地让观众面临了释义挑战,甚至陷入怀疑与自我怀疑,而其实这是她“回归”于原著主题的另辟蹊径与精妙表达。通过“蛇”与“鸟”的意象隐喻,展现出的是两位女性站在艺术家的视野上给予人性的深刻叩问。这是电影与原著在主题内涵上的深层关联,更是许鞍华与张爱玲在艺术话语里的灵魂碰撞。
结语
许鞍华《第一炉香》上映已经足月,来自四面八方的评论多是不满与嘲讽。其实电影作为一部爱情片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些负面评价大多来源于电影改编后与原著在气质上的不合。不论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作者已死”的观点,都在阐释读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发挥其主观性。观众是电影的读者,而许鞍华也是张爱玲的读者,许鞍华的解读有其合理性,因此观众大可不必苛责过多,更不应该全盘否定。因为除本文讨论的意象之外,电影中还有许多细节体现出了许鞍华的功力,给人审美体验,可以探讨之处不在少数。
无论中外,从影视媒介诞生以来,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都数不胜数。这其中成功与否且搁置不论,影视作品的再创作能够引发受众对经典的关注与重读,让经典“活”起来,这样的效应于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已经是难得的。在如今良莠不齐又蓬勃蔓延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市场中,经典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加入其中,在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中被再次经典化。因为这不仅是大众审美的选择结果,更是大众审美的提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