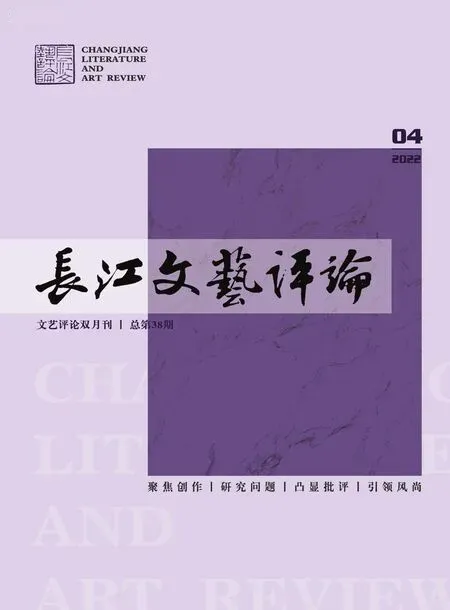电影场景构建与对原著的还原度
◆余 妍
根据张爱玲第一部小说《第一炉香》改编的电影制作班底豪华,导演许鞍华和编剧王安忆都非第一次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加上金牌摄影杜可风、顶级配乐坂本龙一、声音指导杜笃之,如此强大的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电影《第一炉香》,然而影片上映之后褒贬不一,甚至贬义更多。本文着意探讨电影场景构建,对原著的还原度等问题,以此来回应相关的争议。
“场景”这个词在小说和电影中的内涵是不太一样的。在小说指藉由某一时间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一个一个“横切面”,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组成人物、事件和环境的小说场景。但在电影中,场景是指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人物行为,由人物关系而组成的具体生活画面,是人物行为和生活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展示。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地点拍摄的一组连续镜头。因此,在场景方面,小说场景较电影场景更灵活,更自由。当然,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电影中,有关场景的描写或是搭建其实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
一、从场景分析电影对小说的还原度
张爱玲的小说被称为“写在纸上的电影”,她的小说有容易改编成电影的特点。张爱玲小说中运用的色彩词和详细的场景描写很容易呈现在大银幕上,而原著中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那种像水流一样的心理演变过程很难搬上银屏。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更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追求表现人性的苍凉,运用对比度强烈的色彩词,将那些难以呈现在小说语言中的情感视觉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形成一种视觉冲击。电影中故意选择能表现光影变化的场景,利用电影画面的色彩对比将梁公馆的声色犬马表现得淋漓尽致,确实给观众一种视觉冲击。观众不易像读者那样通过带有张爱玲个人偏向的几个词来体悟场景背后的隐喻,只能通过镜头语言体会场景,只能夸电影画面有质感而难以说出这些画面有什么内涵。
电影中的场景大部分取景地是在厦门的鼓浪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具有年代感的建筑风格,使鼓浪屿十分符合电影环境,小说中的姑母居住的小白楼是鼓浪屿的观海园,电影里的乔家是鼓浪屿上号称“别墅王”的荣谷别墅,电影中乔家的两场婚礼都在这里拍摄。同时为了体现出小说中梁公馆的中西混搭风格,剧组还新建了一个中式亭子,由于鼓浪屿曾是英美德法、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日本等九国公共租界,因此建筑风格和人文气息很符合小说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气息。从电影拍摄地的选择和场景的布置来看剧组是下了功夫的。降低了色彩饱和度加上灰败的画面质感,让电影画面含有古典油画美感,同时还尽力复原了张爱玲原著中的“虾子红”“鸡油黄”等高饱和度的颜色。
但这里所述的“下功夫”和“还原”却并不能代表电影场景完全做到了对原著的还原,只能说电影在画面的还原度上做得不错。剧组忠实原著的场景搭建还是值得钦佩其用心的。
以下从几个典型场景分析电影还原度问题。
(一)梁家花园
原著一开头,张爱玲便用薇龙的眼睛展现了梁家花园的全貌:“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阑干,阑干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不过是”“矮矮的”“荒山”这三个词明显包含贬义,可以推断出张爱玲在描写姑母家花园时的态度是偏向负面的,刻意雕琢过的花园阑干与起伏连绵的荒岭形成对比,烘托出荒芜、落寞的感觉。“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一句,将花园背后荒山的暗色调提亮了,薇龙被闪闪发亮的花园吸引,但她并未察觉光亮的背后是一片荒芜,梁家花园的精致与荒芜也对应着薇龙此后外表光鲜实则凄惨的人生。
在电影中梁家的花园是通过一个全景镜头呈现出来的,着意体现梁公馆的繁华。镜头拉近,女主角葛薇龙登场,此时镜头跟随葛薇龙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这座繁华的大花园,电影运用两个镜头将一个孤零零且单薄的女学生与梁家花园繁华的背景相映衬。这样处理确实能够凸显葛薇龙的渺小,但却缺少了小说中的伏笔之意。
小说中还有一处对于梁家花园的描述,是薇龙第一次从姑母家出来时的回望:“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印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依旧是近看时的豪奢,华丽,无比威风。用几个表示颜色的词:“黄地红边”“绿玻璃”“白房子”,用“像古代的皇陵”,来表现梁家花园的违和,这个葛薇龙之后生活的地方,暗示薇龙将在这座“皇陵”中埋葬自己的青春,走向堕落的人生。这几个颜色词在电影中主要还是通过场景和画面的构建表现出来的。在电影中这样的对比色调时时刻刻存在,但却仅仅是充当电影背景,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很难体会到小说中所蕴含的象征意味。
(二)琉璃瓦与白石圆柱
葛薇龙和姑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既受域外特别是西方思想的影响,同时东方固有的传统同样存在,是张爱玲笔下“犯冲”的生活环境。从小说中对梁公馆装修风格的描写就能很好地看出来:“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形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地下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梁公馆的场景是“荒诞、滑稽”的。在荒诞滑稽的环境中,薇龙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为什么会感到不真实?不真实换个词就是虚假,正因为葛薇龙与不和谐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因此在她的眼中一切都显得虚假。与葛薇龙的感受对应的是姑母的享受,这样的对比为葛薇龙往后也像姑母那样享受虚假的悲剧人生做了不动声色的暗示与铺垫。
不伦不类的装修风格点明葛薇龙生活在“犯冲”环境之中,因此在小说中,场景是被赋予了揭示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的作用,而在电影中因为镜头语言的有限性,场景多被充当为背景而起不到解释社会环境的作用。
白石圆柱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在梁公馆宴会上乔琪乔与中年妇人跳舞,葛薇龙离开香港未遂与姑母谈话,在这些桥段中白石圆柱都是作为背景随着镜头短暂出现,观众甚至来不及思考柱子是什么风格,镜头已经转移到角色身上了。而琉璃瓦则基本没有在电影镜头中呈现,原著中利用琉璃瓦与白石圆柱进行中西对照,突出人物生活的矛盾环境,而在电影中这些建筑仅作为一种背景存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消失,社会动荡时期的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当葛薇龙不能继续念书,又不想回上海,就只能去找姑母和姑母一起在交际场中谋生。社会大环境下女性是痛苦的,几乎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小说的最后没有明说葛薇龙的结局,给读者留下遐想空间。小说并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描写逼仄的社会环境,而是通过各种中西杂糅的场景描写包括建筑风格、人物装扮等刻画体现出来的。在电影中电影镜头也很少对焦故事发生的环境,或许在电影中想要呈现的是《第一炉香》小说中表达爱情悲剧的一面,但只有场景的复刻让观众缺少代入感。
(三)葛薇龙的卧室
小说用姑母的话点明葛薇龙卧室的主色调:太太因低声把睨儿唤了过来,吩咐道:“你去敷衍敷衍葛家那孩子,就说我这边分不开身,明天早上再见她。问她吃过了晚饭没有?那间蓝色的客房,是拨给她住的,你领她上去。”读完这段话,读者心中已经有了对薇龙蓝色卧室的印象了,接着张爱玲又对这间小小的卧室进行了详细而浪漫的描写:“薇龙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薇龙拉开了珍珠罗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阳台,铁阑干外浩浩荡荡的雾,一片濛濛乳白,很有从甲板上望海的情致。”这里将薇龙的卧室比作小舟,又用“窄窄的阳台”和“铁阑干”等词语,将卧室与窗外的浩浩荡荡如海般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卧室这一场景中,窗外的景是被阳台和阑干切分开的,这种间隔让眼前的景致像望海一样遥远。张爱玲用小舟作比,又将“小舟”即薇龙的卧室放置在雾蒙蒙的“海上”,因此这间卧室是有象征意味的,它象征着薇龙接下来的人生如同窗外的雾一样变幻莫测,又如一叶小舟在海上孤苦漂荡。
在原著小说卧室这一场景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那就是卧室中的衣柜,小说中运用一句心理描写:“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写出薇龙面对橱柜里的漂亮衣服时敏感地意识到姑妈的用意,小说几笔就将未经世事的小女孩对名利场浮华的想象,对欲望的向往刻画得十分到位,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葛薇龙是清醒的有小算计的而绝非天真无知的懵懂少女。电影中这句心理描写成了丫鬟睨儿的台词,当镜头给到葛薇龙时,她正呆呆地望着天,全然像一个傻白甜。电影中这样的处理与原著小说相比,高下立见。
电影还原了小说卧室的蓝色调,还给了衣柜里的灯饰和几件珠光宝气的衣服几个特写镜头,在这几个镜头中,笔者注意到了在一柜子衣服中,有一件亮蓝色的裙子,这是导演借助道具为葛薇龙之后的人生选择埋下的伏笔。这时不得不提到电影开头,葛薇龙出场时的一身蓝色布衣学生衫,她是穿着这身蓝布学生衫走进蓝色调的房间。在电影中摄影师运用光线的明暗配合,卧室场景画面中的墙壁、柱子、灯饰一片蓝色,相比之下画面中只有女主角葛薇龙身上的蓝是最灰沉沉的,但随着电影的进程,葛薇龙在交际场周旋几回合之后,裙子变为亮色的蓝,这条亮蓝色的裙子正是在卧室中导演给过特写镜头的那件蓝色裙子,毫无疑问这样的亮蓝色与房间的蓝色调搭配得更和谐。电影运用服装、美术与视听语言还原了小说中葛薇龙在面对一柜子漂亮衣服的诱惑缴械投降的过程,凸显了一个小女孩的内心变化,葛薇龙受到了衣服的诱惑从而走向堕落的深渊,在小说中是通过对卧室的描写和葛薇龙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的,在电影中这一点导演通过还原小说场景,借用特写镜头和电影画面呈现突出一条裙子的颜色变化,用符合电影叙事的方式做到了小说想表达的内涵。
二、小说中的场景内涵为何难以在电影中呈现
电影场景是电影创作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在气氛的渲染、人物性格的揭示、增强观众对电影的理解等方面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文中的场景包括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以及装修风格和室内陈设等。作为一部由原著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第一炉香》在还原小说场景的同时甚至还要还原出原著场景背后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以及文化内涵,这一点确实是有难度的。
小说中有一段对梁家客室内盆栽的描写,“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磁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原著中葛薇龙将客室里的盆栽视作一窠青蛇,蛇是一种冷血危险的动物,这里的盆栽揭示着葛薇龙知道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并且敏感又谨慎。在电影里盆栽也出现过,但是在电影语言中,这样的不起眼的细节导演只会给一个镜头一扫而过。
原著小说在接近尾声时,葛薇龙与乔琪乔在阴历三十夜一同逛湾仔的新春市场,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在人堆里挤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是紫黝黝的蓝天,天尽头是紫黝黝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磁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巴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着大红穗子的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小十字架、宝塔顶的凉帽。”原著中运用重复的叠词、色彩词描述了湾仔这个下等娱乐场所的嘈杂和热闹,与葛薇龙此刻的荒凉心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电影中,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形象,导演特意将作为背景的湾仔市场进行了镜头的虚化处理,因此观众难以在电影画面中找到原著描写的各色琳琅货物,自然也不能将湾仔的热闹与葛薇龙的落寞心理进行对比。
电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小说的作者是一个人,而一部电影的拍摄是多个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电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表现出吸引观众目光的艺术效果,不仅是因为最佳审美时长的制约,还因为电影拍摄资金的运转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这就导致电影不会对原著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进行还原,也无法像小说那样细致地挖掘场景背后的内涵。《第一炉香》原著中有同情,有批判,有审视,但绝不仅仅是爱情悲剧,但将小说的丰富性全部置于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中又是不现实的,因此导演许鞍华只能选择其中一方面来讲述这部电影,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悲剧。
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之间有明显不同,但都具有叙事功能,所以文学作品总被拿来改编成电影。著名编剧林奕华提出:“张爱玲运用拍电影的手法来创作小说,使得每次改编都是‘第二次重拍’。”张爱玲作品的这种特征要求导演在拍摄张爱玲的原著时既要超越作者的描述还要符合读者的想象。毋庸置疑,张爱玲作品的丰富性为电影改编提出了难题,如何在一部电影的时长内完整地呈现张爱玲原著小说的命题和立意是每个导演和编剧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结语
电影评论人克莱·派克说过:“当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它不仅仅是通过摄影、剪辑、表演、场景和音乐把原著相对地变形,而且是根据独特的电影法则、惯例、文化等元素,以及根据制片人和导演的理解作相应的转化。”因为电影《第一炉香》的“作者”并非一人,而是包括导演、编剧、摄影、声音、服装在内的团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导演许鞍华在《星映话》专访中就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刻画一张上流社会利益、情感的关系网。许鞍华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准确描述了社会形态,电影《第一炉香》不一定一样,但独特,因而她觉得场景构建是成功的。电影制作团队的每个人对《第一炉香》都有自己的见解,在制作特辑中,摄影杜可风就表明自己将电影画面高标准的呈现作为自己的责任,服装师和田惠美根据演员本身的气质在服装设计上做出改动,而不会完全遵循历史,负责声音的坂本龙一为了电影画面制作原创音乐。正如许鞍华在采访中说的那样:“他们是为每一个戏的具体需要而不想着之前的成就。”电影团队每个人都为这部电影尽全力,单从观众的反馈来看显然是没能达到团队对电影的预期。
电影《第一炉香》制作团队对于张爱玲笔下的梁家花园中西杂糅的装修风格、葛薇龙的卧室甚至小到客室内的盆栽都做到了堪称一比一的恢复原状,但本文讨论的“还原”又不仅仅是恢复原状而已,在这一层面上看电影《第一炉香》是没有做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小说与电影叙事方式的不同,在电影中完全套用小说叙事手法是行不通的,因此电影对于场景的构建必须符合电影叙事学逻辑,本文探讨的电影叙事学是指20世纪70年代建立在索绪尔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基础上的电影叙事学,索绪尔将语言看作符号系统,认为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利用索绪尔的观点本文将电影场景看作符号系统,电影场景的构建与电影特写镜头,蒙太奇闪回手法等电影叙事方式的组合使得电影场景产生意义,电影中对葛薇龙卧室的呈现就是利用这种组合以电影场景构建表达出小说场景描写背后的内涵。
观众普遍把忠于原著作为好电影的标准,但电影能够利用符合电影叙事的手法进行表达未尝不是对原著的忠实。美国电影评论家乔治·布鲁斯东说:“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电影中的人物情节是可以互换的,小说是一个规格,电影对它有所脱离是自负其责的,由于一些含糊不清的理由———比如说,为了长度或视觉上的需要——这种脱离是被允许的,而脱离的幅度大小则直接决定于对原著‘尊重’的程度;不管原著如何,任意加以改动并不一定会损伤影片的质量,但这种改动却不知为什么必须瞒过观众的耳目才行。”乔治·布鲁斯东认为让观众有代入感的电影才算是改编成功的电影,电影《第一炉香》尝试将场景构建用符合电影的形式表达但却忽视了观影者的诉求。
符合影视叙事艺术的电影改编就是要把小说中的细节转换成电影中真实的场景,借助场景再现小说,让观众有代入感。阅读小说时对梁公馆的想象电影通过场景搭建实现,因此读者的视野期待在电影中以画面形式实现。德国电影批评家克拉考尔说:“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真正名符其实的电影。”电影场景的一个重要的再现性特征就是真实。在场景真实性上电影《第一炉香》做到了忠于原著,但运用符合电影叙事的手法让场景呈现小说文化内涵部分尚有欠缺,因此电影《第一炉香》是否是成功的改编还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