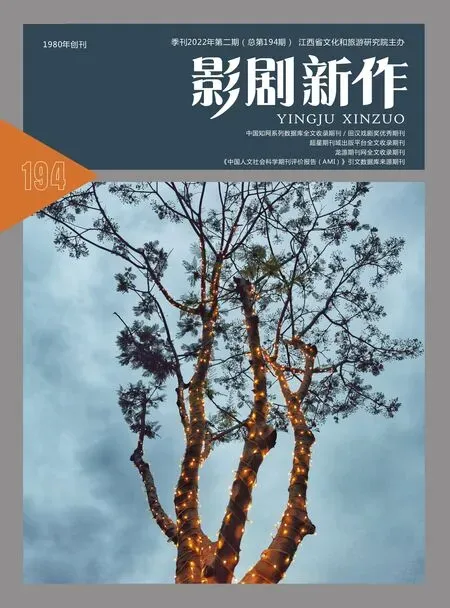长征出发地的长征新言说
——评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闫江南 简贵灯
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位于长征出发地赣州的赣南采茶歌舞剧团推出革命历史题材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向共和国献礼。该剧由张曼君执导,盛和煜编剧,杨俊主演,讲述一个名叫骡子的青年马夫拼死携带黄金突围,用行动诠释“一诺胜千金”,逐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成长故事。不同于以往聚焦于英雄人物全景式的铺陈历史,《一个人的长征》通过复调叙事将厚重的时代主题与精神价值纳入本土“小人物”的生命中,通过赣南本土小人物的成长历程讲述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之时“舍小家,为大家”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长征》创新性地引入小乐队,搭建起演员与观众情感交流的桥梁,共同叙写长征故事,重构宏大家国情怀,言说草根长征精神,是革命历史题材剧不可多得的有益探索。
一、复调叙事:革命历史题材叙事
新表达
作为音乐术语的“复调”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才由巴赫金将它引入欧洲文学领域, 强调小说作品中的“复调”结构。在跨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 复调理论被应用到戏剧创作中。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剧相比,《一个人的长征》在叙事结构上一改以往单线叙事的结构,将小说中的“复调叙事”引入采茶戏创作中,通过多个主人公的多声部对话,形成立体式、多层次的整体结构,讲述战火纷飞年代小人物的长征故事,丰富革命历史题材新的表达方式。
1.同一事件的多重聚焦
复调作品是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人物需要在心灵世界的探索中实现自我确认,构成的统一世界。纵观《一个人的长征》的四位主要人物,骡子与花姑,邱排长与古玉洁,构成了两个声部、四个音符。他们因为一箱黄金,精神与命运有了交织与纠缠。骡子与花姑代表的是传统农民阶级,骡子只想过“吃饭穿衣讨婆娘”与世无争的平民生活,“我会亲手交给他”的承诺“牛踩不扁,马拉不回”,他在行走和追寻中不断进行精神攀升,用品格践行了一场关于“诺言与使命”的长征;与骡子相伴的花姑是小农经济下的传统女性,秉承着“要看郎的妻,先看郎的衣”“丈夫是天”的传统思想,一路追随骡子,从一开始非要“抓”骡子回家结婚,到后期支持骡子运送黄金,花姑在追求爱情的长征路上得到思想上的升华。邱排长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凭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是他信仰的独白,因为这份信仰,强渡湘江、遵义遇险、飞夺泸定,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守护着人民,他用生命行走了一场关于“信仰与忠诚”的长征;古玉洁是具有新思想、新教育、新追求的留洋学生代表,放弃优越生活,甘愿“参加红军去战斗,为主义甘洒热血抛头颅”,她犹如那只“高傲的海燕”,在暴风雨来临时努力飞翔,挥洒热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她在遵义大地上追逐了一场热忱追求革命信仰的浪漫长征。四个价值观大相径庭的音符,站在各自的立场共同谱写“长征”复调,完成“组歌”的吟唱。人人有戏、场场有情,复调叙事的结构多角度、多方位、多立场对“长征”进行诠释,避免了平面化的场次和平铺直叙的线性叙事,使得作品更加饱满,更加立体。
2.独立意识的交流对话
“对话”是巴赫金在复调理论中着重强调的部分。巴赫金《诗学》将复调理论的对话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隐性辩论的微型对话暴露人物内心,另一方面以显性辩论的大型对话突显交流的开放性。张曼君导演在处理人物作为独立意识交流时,抓住了“对话”这一关键词。第一场“湘江突围”中,骡子作为舞台上唯一幸存者得知箱子里是五十根金条时,面对天降横财,“本我”欲望与“超我”道德化为独立意识进行辩论对话,一方面是拿着金条娶妻生子、过上小农生活的本能欲望,另一方面是信守承诺的人伦道德天性。两个独立意识在舞台上的辩论对话“针尖对麦芒”,在一来一回的快节奏中,“自我”意识跳出修罗场,大吼一声“我还是把金条还给二号首长去!”至此,骡子挣脱欲望枷锁,在内在思想斗争中显现其天生善良的真心与本性,也让他信守承诺的品质基调站稳了脚跟。在第四场“黎平篝火”中,骡子与古玉洁围绕“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次开放性的“大型对话”。骡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思想”和古玉洁外来先进的“革命思想”直接摊开给观众看。这次对话是推使骡子从小家意识转向大国情怀的重要转折点,骡子正是在外部语言与内在思想的对话交流碰撞中,进行精神洗礼与成长蜕变。最后,二者在一唱一和的理想对话中走向“个人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合唱,与观众“小家温馨与大国崇高”的审美感受齐鸣。以上,张曼君导演通过“对话”这一方式处理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自我之间的横纵两个维度的交流,不仅直接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也间接让作品“活”得起来,有了属于自己的表述方式。
3.叙事结局的留白
《一个人的长征》,单看剧名,看戏之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主人公最后完成长征了吗?其实不然,编剧盛和煜在改编时跳出“观众思维”,给整部戏的结局做了“留白”处理。这种结局的留白与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结局的未完成性”不谋而合。编剧盛和煜笔下的“长征“是具有双重含义的,一层是实际意义上的“骡子运送金子”的长征,另一层是骡子思想上的自我长征。不论是具象的长征还是抽象的长征,都以“草地红星”作为故事结局。从具象长征来看,路程只行进到泥泞草地,长征的道路还有千难万险;从抽象长征来看,思想的红星代表着骡子的个人成长的节点,是否坚定还有待考验。巴赫金认为,具有独立意识的角色具有不定性,正是因为这种不定性,才能够体现角色结局的不确定性。在第四场“黎平篝火”之前,可以说骡子是草根农民本色出演,小农思想在举手投足、话语表达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在黎平,骡子的独立意识苏醒,与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共生存,在特定生存环境中,骡子的小农愿景被这三股力量“撬动”,逐渐显露其“不确定性”,逐渐将国家命运纳入到自己的考量范围内,再经过“遵义遇险”“泸定行乞”“草地红星”,使得“不确定性”逐渐“确定”,骡子从平民百姓成长为实际意义上的红军战士,故事至此升华,想要传达的精神价值观已经浮出水面,孑然一人,漫漫征途,历史上的骡子是否将金子成功交给二号首长化为美好希冀,留与观众自行想象。
二、小乐队:观演交流与距离的桥梁
戏剧学上的空间是由演员与观众构成,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与“交流”成为观演关系的核心。中国戏曲起源于民间歌舞和宗教仪式,自其诞生,观众便有很强的参与性。然而,戏曲发展的规范化导致观演关系依靠演员与观众约定俗成的假定性,观与演、看与被看,在“镜框式”舞台的隔离下截然分明;上世纪八十年代“戏剧危机”,小剧场的兴起意味着新时代观演关系的新探索,观剧距离缩小、交流意识增强,观众由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 观演彼此交融。值得肯定的是,《一个人的长征》借鉴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引入小乐队,有意识的利用小乐队在观演交流与舞台距离上做文章,拉近观演距离,传递文本精神。
1.打造“延出式”舞台,拉近观演距离
《一个人的长征》虽然没有在物理空间建造独特的舞台,但是通过在主舞台两侧引入固定式小乐队与移动式小合唱队,从物理与心理上同时建造延出式舞台,缩短观演距离,与观众融为一体。戏没开场之前,观众可能并未察觉到特殊的舞台设置,而当大幕拉开后,合唱队移动式登台或演员与代表“观众”身份的小乐队冲破“第四堵墙”进行互动时,观众才发觉,自己已经置身在戏剧环境中,成为整部戏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在第三场“马夫救美”中,一开场王火彪一行人押着被误以为是“红军师长”的骡子进入大余县城集市吆喝邀功,小乐队脱离乐队身份,扮演集市里的百姓,一听到有“红军师长”被抓,立即探出脑袋、交头接耳式看热闹。俯视整个剧场,小乐队设置在舞台右侧,以小乐队为中心,观众围绕小乐队呈辐射状排列。当小乐队开始与演员产生互动时,周围观众既自觉又不自觉地被影响,自觉的是“大余县城集市”这个特定戏剧环境意味着鱼龙混杂,一呼百应的效果被无限放大;不自觉的是观众不仅在看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也在看作为他者的观众发生了什么。不难看出,在这场戏中,观演关系正是在特殊戏剧环境中,通过“小乐队”建立桥梁,这样的设置使得观演关系十分灵活,不仅让观众在出戏入戏中达到高峰体验,更是扩充了戏剧张力。
2.演员显性言语对话与观众隐性情感共鸣
演员通过言语交流与观众进行显性互动,这里的显性互动并不意味着演员直接打破“第四堵墙”与台下观众挥手呐喊,依旧是借助主舞台旁的小乐队,赋予其“观众”身份,依据情节发展,代表观众与舞台上的演员互动,以己之手推动情节发展。比如,第一场“强渡湘江”中,骡子沉浸在黑骡子去世的悲伤情绪中,忘记理会箱子,观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又不能直接提醒骡子,小乐队以观众的身份,向骡子喊“你的箱子”。再如,在大余县城内与古玉洁一行广东人相遇,骡子问到:“他说的什么话?”骡子在内的众人皆是赣南人,自然不晓得是广东话,所以,小乐队再次以观众身份告知骡子“广东话”,替观众解决看戏时的燃眉之急。诸如此类的观演双方直接言语互动在整部戏中还有很多,这样的设置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中,观众在作为“他者”完成观剧使命的同时,无意识、自然地参与到表演中,成为故事的宏观讲述者。其次,观众亦在情节高潮与演员产生隐性情感共鸣,献礼剧作为主旋律传声筒更多的是“以情动人”,让观众以通过内在情感共鸣这种隐性方式与演员通感,在高峰体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洗涤精神世界。遵义遇险、泸定行乞,长征路上一连串的打击给骡子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连问三回“怎么会有红军这样的人”代表着他的心理成长。直至最后邱排长阵亡,骡子坚定信念,伴随着小乐队唢呐独奏,再次唱起“大步走来是喂是喂”,悲剧的崇高在唢呐声中充斥观众内心,情感一触即发,为邱排长的大义落泪,为骡子的执著鼓掌,这皆是观众情感共鸣的出口。
总结而言,演员以言语输出为动,观众以情感释放为静,一动一静,动静结合,使得观演关系既没有五六十年代革命样板戏的死寂,也没有八十年代小剧场戏剧实验的尴尬。以中介作为情感双方的沟通纽带,更符合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让观演双方在各自的情感舒适区共同完成整场戏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退场,掌声不断,讨论声此起彼伏,戏剧影响力走出剧场、走进生活,这是观演互动的意义之一。
三、文本与舞台互为表里,言说新时代长征精神
《一个人的长征》立足于“情感与选择”,采用复调叙事的方式,独立而又统一地讲述四位主人公的长征故事,描绘了赣南青年英雄人物形象。文本采用复调叙事的叙事手法叙述事件,并没有解构事件本体的意义,反而画龙点睛,再三聚焦事件本体及反映出的精神内核,使得长征精神不再高度浓缩在“高大全”的人物身上,而是具体、明确的体现在小人物自身,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骡子重诚信、花姑明大义、邱排长有信仰、古玉洁洒热血……这些小人物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与艰苦环境培养起来的长征精神更加接地气,在新时代同样具有普适性。如何将文本所要传达的精神渗透给观众,《一个人的长征》别出心裁。利用小乐队嫁接延出式舞台,拉近观演距离;情绪起伏处演员多角色扮演,观众互动参与叙事。节奏分明,环环相扣,让台下观众观戏如省己,为骡子坚定送金子的诚信品质频频点头,为花姑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正确选择点赞,为邱排长的坚定信仰献身革命潸然泪下,为古玉洁赤子热忱的浪漫追求感动,观众在情节高潮时亦可情感与共。骡子的扮演者杨俊是红军后代,他身体里流淌着与生俱来的红色血脉,先烈故事耳濡目染。演员杂事的基本功配合真挚的情感倾注,对于这片红土地上的观众来说,无疑是最有效的说服。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一个人的长征》将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的融合已经演绎得淋漓尽致。美中不足的是,个人故事叙述方面欠缺完整,如花姑最后的去向尚不明确。主题升华方面有些落入传统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窠臼,一味歌颂正面人物,脸谱化反面人物等等。
《一个人的长征》横空出世,在文本叙事与舞台表现形式方面各有创新点,特别值得赞扬的是该剧文本与舞台表现形式二者互为表里,配合得当,给观众带来感官与精神的双重盛宴。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剧文本赋予舞台实践方面有意义的尝试,为革命历史题材剧今后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它让革命历史题材剧更接地气,并充满人性的光辉,就此而言,《一个人的长征》作为献礼剧称得上是匠心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