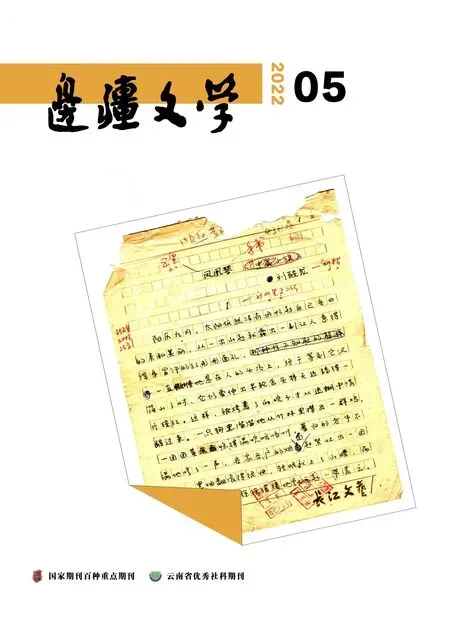在高原上发呆组诗
范庆奇
早晨
时间加快了速度,从高原的东边
转过身来关照西边
山路上疾驰而过的客车
抖落树木去年积攒的灰尘
悄悄离开的人,走路时步子很轻
这是一次仓皇的出逃
我注视着村庄
像陌生人对待陌生人那样
越来越视若无睹
我对人近乎无情,对草木有了
格外的感念。常常蹲下身
为一棵草扶正身子,也时常会
注视一朵花十几分钟,就为数清
它的花蕊,以及这一朵和另一朵的不同
就是这样的时刻,一朵杏花落下
我仿佛感受到鸟儿飞翔的感觉
自己变成了带着淡淡香味的飞鸟
越过灰白的村庄和银色的夜幕
撒落的月光都有我的气息
季节敲落的果壳
灰白的暮色中,时间
如同山上冲刷而来的暴涨河水
携卷着所经之地的碎屑
在黑和白的空隙中
路旁的杏花抽身打开了
另一个隐秘的世界
我从这盛开的空间里洞见
死亡是最持久的永恒
我们恐惧离开和再见
哪怕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
在众多的败局中,仍然
会选择一种方式不朽
这种决绝就像一朵花的坠落
你知道吗?我宿舍后面的杏树开花了
去年它刚从别处移栽过来
开出九朵花
其中一朵被我夹在一本诗集里
粉色的香气被我摁进了文字
而这个春天,它的繁盛让我莫名心慌
登靖宁塔
在滇东高原登一座高塔
无异于在高山之上,堆砌一座高山
拾阶而上,多年前的石头布满青苔
上面细小的苔花,正怒放
白色的点点花蕊,正如奔向塔顶的芸芸众生
那么渺小,那么值得赞美
不管用多少诗句来描摹
都写不尽人世间一个卑微的生命
站在塔顶往远处看
养育我的红土,这红进骨子里的颜色
让我有一种想舀水的错觉
舀起一捧土,泼出去
细碎的灰尘落满沉默的高原
落日
雪山挡在面前,落日浑圆的身子
只露出一半,我站在巨大的岩石上
也许,这块石头来自雪山
在数亿年的地壳抬升,河流搬运中
它成了一粒浮萍,搁浅在时间的滩涂
长久的落寞中,被人遗忘忽视
而此刻,我与它有肌肤之亲
石头的心脏,捂出了温热
黑色和白色是这里的基调
动人的黑,惊人的白
被处理得恰到好处
河流黝黑,雪山清白,它们也有心情
和居住在周围的人一样
会因为暴雨悲伤,烈日心烦
面对染红的落日,冷峻的山
这的人习惯沉默
为了宣传神旨,他们驮着石头
走几里山路,爬上峰顶
在山上修建一座石头的寺庙
凿刻一尊石头的菩萨,将自己化作石头人
守着雪山、岩石、寺庙,等待落日
弥留之际
他躺在床上,呼出人世间的浊气
许多天以来,没有进食
只喝一勺凉白开
这颓败阴暗的屋里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有木墙上那扇窗
洒进一点光亮
来看他的路上,油菜花开了
蜜蜂成群结队
它们是没有情感的小东西
并不懂得人间过多的悲伤
而我的心随着落地的花粉
被摔成另一种尘埃
不说谎的我,那一刻
却对他说了许多谎话
诸如安心养病,一切都会好
可对于弥留之际的人来说
那些话不及一颗止痛药的余温
又过六盘水
凌晨时分,紧赶的月亮悬挂天空
一些人背负凶心下车
他们眼里藏着杀机
立誓要在这个高原小城立足
来之前,宰鸡祭祀,烧香祷告
亡故的祖先曾经到此贩盐
累死的十匹马换回三世荣光
多年过去,马骨已腐烂
家传的马掌锈蚀殆尽
作为家族子孙,我谨记先言
将光宗耀祖担在肩上
从滇东跋山涉水而来
一路上那么凉,那么孤寂
倒退着
树木、房屋、轨道,都在倒退
唯独时间一直向前
它是不畏死的士兵
执行着宇宙之神的命令
我和众多人一起被推上绞刑架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人提前死去
有人不舍人世,苟延残喘地活
我应该是中立
想活得久,也想体面一点
像荒地里的野草,枯黄着挺立身子
如果可以,我愿意用双倍的时间
换取时间倒退,两年就够
那时的我不写诗,没有那么悲悯
将会省却很多冲淡的眼泪
理想的自己
我在薄薄的纸上写下重重的字
需要精美的钢笔,虔诚的心
理想,是神圣的语
我不能轻易言说
不然你会指责我,虚伪做作
坐在荒芜里,我侧耳听风
它们在吵架,也是关于如何定义理想
我插不上嘴,更自顾不暇
走到湖边,看着湖里的自己
我羞于表达,内心有愧
过去的风又回来了
它们还在讨论理想,激烈的争论
打碎了湖里的我
水波薇荡的褶皱里
是我无法解答的疑惑
水鸟
站在黄河边,水鸟掠过
激起水花。我羡慕它
在这嘈杂的人世,可以远离地面
悬空生活
逐水而居,从上游到下游
扑打翅膀,带上清风
小洲、水草,便是繁衍的居所
而我,奔袭千里
背离家乡,才能勉强生活
借着北风,胸中积压已久的思念
喷薄而出,随水鸟南下
去我的家乡,山高林密的地方
那天傍晚,站在黄河边
看水鸟徘徊,水流放慢速度
飞翔的鸟在寻找,它们和我一样
有一个故乡,又一无所有
草原之夜
垭口传来的风声在耳边呼啸
这片枯黄的草原临近末期
就连毡房里的灯也似乎衰老了
谁能托住一片草场的亡魂
谁又能抹平那留在山上的伤痕
这几年羊群逐渐扩大
曾经绿草如同汪洋,遮盖了头顶的天空
如今石头露出了面目
低矮的灌木退居山坡
剩下的草都有石头一样的骨骼
在牛羊踩过的地方咯咯作响
歇息一夜吧,明日将奔赴下一片草场
聚居的牧民搬走了
山谷的小寺庙还在
那里住着一个苦修的喇嘛
他为离开的人画像
画完后挂在墙上,为他们祷告
喇嘛说这里不会再有白鹿
只有一片虚无,一片不愿死去的草原
松赞林寺
在这里所有都是矮的,只有金顶是高的
在这里所有都是低的,只有经声是高的
早晨六点透过窗户,远处的山顶被冰雪覆盖
山上是一片空白,山下是一片枯黄
我们用手机记录这个时刻
将一次又一次的远行留下
阳光适时照在脸上,我们被金光包裹
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了新的洗礼
沿着弯曲颠簸的山路,一直往北走
被人称为左青龙,右白虎的山谷里
有一座古老的庙宇
站在远处的坡上,金瓦披覆其上
佛法僧三宝照耀着雪域高原的角落
深红色的墙体藏着佛堂、经殿
庙宇的顶空,一些乌鸦来回盘旋
这些鸟儿离我是那么近
伸手就能触碰它们的翅膀
这些鸟儿离我又是那么远
我知道天空浩渺,大地广阔
喇嘛说这是红嘴鸦,叫声清脆
它们有情于众生,成了慈祥的象征
就像这山间寺庙,形如八瓣莲花
环山湖是花瓣,每条路都刻满心经
每个路口都有玛尼堆
去世的人将肉身布施于万物
这里便成了诸佛慈悲之道场
放眼望去,每座山上都有经幡
都有人世间最微小的慈悲心
圣诞夜
下雪的夜晚我们乘车从香格里拉到丽江
这条路上很少能遇见车辆
好像这崎岖的小路就是专门为我们而开凿的
我们也是专门挑选圣诞夜从这里路过
不管了,不论是谁选定谁,这个夜晚注定相伴
山上下雪,山谷里冷风呼呼吹过
那些随流水,石头而不断改变的风声
在我们路过金沙江边的时候被拉长放大
也许是江水滔滔,也许是江水欢迎异乡人
我们遂停下车子,在江边听水声
抬头看天空,星星很稀疏
这样空大的山里,一条江的声响就如同
丢入大海的一颗石头,悄无声息
许多常年游走于外省打工的年轻人
他们像是被打包好的物品被班车带走
融入某座城市,至此渺无音讯
有的去了几年,有的去了一辈子
有个朋友说,他在上海看长江
总是会想起上游的家
雪落下的声音
门被风吹得咚咚作响
街上很少有行人
站在街中心,能看见山坡上的经幡
摇晃着明黄的彩色
还有牧羊人在外放牧
他们赶着一大群羊在枯草间迂回
从一座山头到另一座山头
这跋涉之苦,延续牧羊人的一生
每到夜晚他就在山间搭建帐篷
把羊群赶到一块大岩石下
这一夜雪落下的声音很急很重
天亮起来,大雪掩埋了帐篷入口
他焦急地抛开大雪,奔过去看他的羊群
一只小羊躺在雪地上,它白色的毛像极了雪
牧羊人紧紧地抱住它
眼泪落在雪上,结出一粒冰晶
凌晨五点记事
凌晨五点的医院,空旷而寂寥
楼房熄灭灯火,路灯点燃黑夜
走廊里绿色的指示牌亮着
预示无论如何黑暗,终归有一丝光明
站在七楼的栏杆边,抬头望见头顶的北极星
那是多么漫无边际的一片漆黑
透着诱人的神秘星空之下,大地变得渺小
我眼前却是最真实的存在
这里的人按时起床,抽血,吃药,做治疗
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切开身体,只为多活几天
我知道诗歌不是良药,救治不了将死之人
便躲在黑夜里写诗,一边写一边抹去
我听见街上收垃圾的车走过
天又快亮了,人间每一个脚步都有回响
那些被晨曦照亮的生命,将会执着地活着
大雪过后
大雪过后,我看到你离开
去年渲染的白消失
春天在某处缓慢接近
枯黄死寂只属于那场大雪
人们就像地里的稻草人
呆愣愣地看着前方那片墓地
落光叶子的树像是裸露的男人
在人群中慌乱奔逃
怎么也找不到可以遮蔽的东西
随着车子走远的地平线
串起了一个红色的太阳
戴口罩的老人从中间将远和近隔开
他低矮的影子化作一团黑影
大雪过后,街上多了许多流民
大雪过后,捡垃圾的小女孩并不觉得温暖
大雪过后,凤凰花落了一地
人和人以体温取暖
阳光下
阳光下的房屋显得更旧
男人斜靠在断墙上抽烟
他闭着眼睛,沉醉在尼古丁的世界
旧时代的理发师为老人们剪发
他颤抖的手好像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瘫痪多年的女人在轮椅上看着他们
手里的药掉到地上也全然不知
从这里向前是教堂
欧式建筑与这条街格格不入
老神父宣扬着自己的信仰
而这里的人不想知道何为上帝
废弃工厂里居住着乞丐和流浪狗
每天都盯着房梁上栖居的鸟儿
我写下几行诗,同时也写下我和他们
生死课
她的哭声很大,响彻楼道
旁边的人不敢靠近
死亡在这种时候更令人恐惧
空气中弥漫着苦咸的味道
我们离亡人只有一米之隔
还记得上课时老师说人命关天
实操异常严苛,一遍一遍熟练技术
终究人力有尽,死还是发生
就像我们每天都在练习躺下的姿势
花费一生还是学不通透
倾诉者
我预感到危机提前来临
衰老的颓势侵轧本就虚弱的生命
她越来越唠叨,方言从她的嘴里逃出来
全都击中我的要害
结婚生子,学会节约
像是无形的大山压在我的头顶
很多次迫使我不敢回家
许是知道生命短暂,余下的时间不多
她重复一件事十几次
我不理解,打断她说话
直至今日,我明白她的担忧
仅是奶奶对孙子放心不下
如果有来世,我会做倾诉者
用一生的时间来讲述今世的悔恨
下落不明
吹过的风下落不明
开花的春天下落不明
此地荒草萋萋,不见行人
每一块石头都刻上了名字
每一棵树都压低生长
生怕来人不知他们的存在
走进石丛中,他们盯着我
这些下落不明的人
找回了身份,重新证明自己
我摸着粗糙的碑刻
上面的字满布风尘
一生不过寥寥几字
死后如同倒插的葱紧紧依偎
无聊的下午
窗外狂风吼叫,新开的花落了一地
像是手术台上疼痛大喊的病人
我坐在病房里,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
这是多么安详的下午,奶奶睡着了
没有因为头疼而翻来覆去
我手捧诗集,逐句分析着山河地理
有诗人写到天山,此刻它是静默的
有诗人写到兴安岭,此刻它是乖巧的
所有的文字都呈现顺服的姿态
等待我收割上面附着的诗意
合上书本,窗外的风还是很大
院落里坐着轮椅的人,持着双拐的人
他们一个接一个我从眼前过去
热烈的阳光下,他们身上闪着金光
光晕昭示着忧郁和无奈
下午四点,这个医院灌满了苦难
楼下的花更像是病痛的另一朵分身
在梅里雪山静坐
我能确定,今夜星光在我身上
种下一片短暂的银河
我清瘦的肩头担着风尘赶路
从高原的东端奔赴西端
天空被撕裂之前,我望着漆黑的远方
不知那里是否也有人和我对望
太阳在时间的伤口中抖落
梅里雪山顶峰泄露金光
雪白的峰丛和白云融为一体
澜沧江从山脚奔腾而过
山腰的村庄在日复一日中老去
你看,卡瓦格博是撑起高原的脊梁
天空,也为一座神山沉默
环顾群山,经幡静止,风停在耳边
时间静止,凡心被雪水带走
你知道吗?6740 米的地方住着神明
伟大而古老的神话被一代代相传
佛塔前僧侣合十的指尖倾向雪峰
我身后的人群坐在寒冷的地上
安静如同山间一块风化的岩石
筑巢
列车驶过浓雾
一路春色突现眼前
干涸的小溪饱满了许多
垂入水中的柳枝冒出嫩芽
地埂上漆树挂满老鸹窝
像是它结的果子
一个冬天过去,沉寂的生命在涌动
生命之间的萌生
触碰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喜鹊衔来枯枝
它黑白相间的翅羽在树间跳动
春风是一把古琴
它是最擅长演奏《春风》的琴师
这个春天还不是很美
凌晨两点十四分的兰州
一些灯光黯淡下来,一些声响压低声音
一些人还在夜里私语
过去的风不会再吹回来,就连风声
也隐匿于夜幕
就像流水,从来不会停歇
不会停下看看身旁的水草
在兰州,黄河是最宽的水
多少人只为一睹它的浑浊
见了它,只说,黄河水真浑
你可曾了解过它暗地里流下的是浑浊的眼泪
是多少年洗不清的青山的魂
就像我,站在五楼的窗台边
眼前闪烁着灯光,背后又有多少烦苦
凌晨两点十四分只停留六十秒
我说不出口,也无从说起
风声
四野寂静,平原上无风吹过
柳树下堆满石灰岩
它们拥在一起,像重逢的故人
如果下雨,那该是情不自禁的眼泪
老人弓着腰在另一头搬运石头
他缓慢地朝着墓地走去
他有时在想,一块石头落地
是不是不会觉得疼
三年前老妻摔倒亡故
他成了人世间的一个亡魂
每天搬运一块石头,为他和亡妻修葺坟墓
他能听见胸膛里呼啸而过的风声
却没办法克制它们
就像他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思念亡妻
心事
一个人走在旷野上
遇见从远处赶来的夕阳
这傍晚颓势的热,像是我失意的朋友
他渐凉的身躯刻满了一天的劳累
而我的怀中,藏着一杯待喝的酒
席地而坐吧,用荒地作为桌椅
饮尽这几年彼此的不易
几年前,我连夜赶路,经过绵阳
我知道,我们体内都有一杯未饮的酒
此后的某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遇
山背后升起的月亮有了酒的味道
饮一缕月光,该是遗落人间的芬芳
今夜的月,今夜的酒
醉了黑夜里赶路的远行人
夜雨苍茫
雨让黑夜更漫长
压抑的雷声在头顶响起
列车穿过春天
雨中带有花香,花香夹杂土腥
内部的力量,源于一场雨
携带行李的人,在雨中丢失身份
如果雨更大一些,就把生为人的痕迹
一并冲刷干净
隐忍的雨,暴怒的雨,支离破碎的雨
重新定义这个夜晚,这辆列车上某个我
低着头,看窗外疾速飞过的树木
略微颠簸的车厢滚动我的肠胃
中午吃下的馒头被酶吞噬
留给我的是未知的路程和空洞的黑
从北盘江头顶过
江水流过家门
儿时在里面洗澡捞鱼
年少幻想江水的去向
青年无数次路过嘉陵江
体内总有一条奔腾的江水
在血管里激荡轻狂
不用查询来路和归途
它的长度足够在体内
耕种平生的辛酸
江边有一个叫纳丙村的寨子
他们守着流水度日
将亡故的人抛入水中
江水深处,亡魂用水流
镌刻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