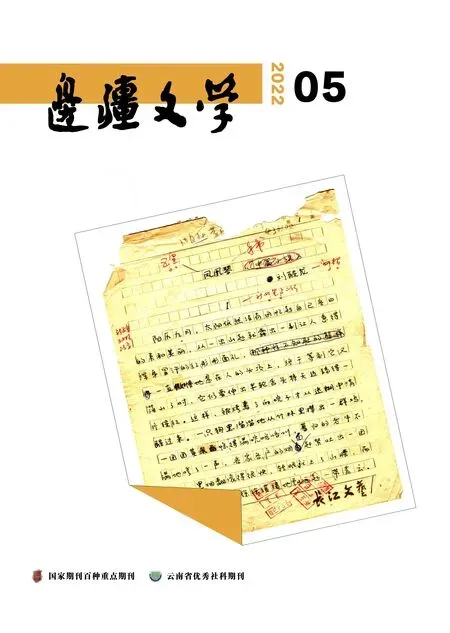大路从门前过
叶梅玉
一
天还没放亮,老人就醒了,窗外黑黢黢的,有早起的鸟在啭唱。老人摸索着爬起床,穿上衣服,草草洗漱起来。洗漱完了,天还没亮,晨曦像害羞的新嫁娘,在东山重重叠叠的盖头里藏得严严实实。老人在院坝里站了一小会儿,拉过一把板凳在老槐树脚下坐下,吧哒抽起纸烟来。风很轻,东边的天幕上,一颗启明星忽闪着,似乎在笑话他:天亮还早着,着什么急咧?
是啊,天还早着啦。平常日子,老人是不急着起床的,缸里有米,园里有菜,兜里有钱,有什么好着急的?不做农活有十多年了,前些年还喂头猪自己杀了吃肉,这两年也不喂了。儿子买了一台冰箱,肉啊,鱼啊,隔三岔五送新鲜的来,切成厚薄均匀的片片,用保鲜袋装着放在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拿出来炒。老了,就该好好休息,睡到太阳晒屁股才对。可是今天,老人却怎么也睡不下去了。
今天特殊呢,今天是苗集赶场的日子!
老人抽完一袋烟,天又亮一点,山啊,树啊,都开始清晰起来。老人去屋檐下拿起竹扫把,开始扫地。老人弯着腰,慢慢打扫着。他扫得很仔细,把每一个角落都扫到了,把每一粒尘埃,每一片落叶都扫到了。然后,老人在大槐树根边挖一个小坑,把这一小堆灰尘和落叶埋起来。落叶归根,这是最好的肥料,也是树叶最好的归宿呢。老人直起腰来,头上冒出细密的汗水。看来,真的老了,扫个地也感觉喘气不匀了,老人想,心里有点悲哀。他满意地看着干净的院坝,又向外面张望起来。不知不觉间,天亮了,对面大寨子里,传来鸡鸣犬吠声,还有打开木门的吱呀声,打开牛栏放出牛儿的哞哞声。这个世界,继于他醒了过来。
老人拍拍手,转身进了屋,再从屋里出来时,佝偻的怀里多了一张小木桌。老人走得有些趔趄,跨门槛时桌子脚挂在门槛上,差点就绊倒了。老人把木桌放在院坝中央,又回头搬了一张,再一张,总共四张桌子,整整齐齐地摆好,然后开始搬板凳,一张桌子六把板凳,都摆成了一圈。最后一把板凳摆好后,他感觉有些困,干脆在这张板凳上瘫坐下来。以前可不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他扳着牛角能摔倒一头水牛,那些力气都去哪儿了呢?老人坐了很久,也许十分钟,也许半个小时,直到风箱一样的呼吸平和下来了,才又站起来,去屋里找来抹布,浸了水,把桌子板凳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露出黄灿灿的木质底色才满意地停下来。有了桌椅,本来空荡的院坝一下子变得充实,变得热闹,变得喜庆起来,好像这家人即将办一堂大喜事,请一堂客一样。老人不由得有些愣怔,好像时光倒流了。他一生里请过两次客,就在这院坝里。一样摆着整整齐齐的桌椅,每一张桌边都坐满来客,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热热闹闹地喝着酒,说着祝福的话。一次是儿子考上外面的大学堂,还有一次是儿子成亲。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讨了城里的媳妇,想在城里操办,可他不同意,要在这院坝里也办一次,儿子依了他。那两次办得热闹啊,乡亲们来了,好多年不来往的亲戚们也都来了,流水席开了两天!
愣怔了好久,天终于亮透了。老人不由自主地频频向外面张望,那条大路还没有醒来。大路很长,一端牵着寨子,一端连向寨子外面。比大路更长的是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路上不见一个人影,不见一只鸡、一只鸭、一条狗,以往这个时候,摆摊的、卖肉的、卖菜蔬的、卖服装的……背着背篓,骑着摩托,都会赶早从这条大路上出现。老人想起今天或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场,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像水一样漫上来,湮没了他。
昨天,儿子又打来电话,要接他去城里住。这次儿子态度异常坚决,儿子不放心他。老人单门独户,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木屋里,身子骨一天赶不上一天,像风中的树叶一样,说不定哪天风一吹就掉下来了。很多独门独户独身的老人死了十天半月,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这样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了。儿子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他真的是个老树蔸了,老得常常错把路边晃动的树影看作是人呢,老得一想起许多许多的往事,心窝窝里就疼呢。而他的木屋比他更老,说不定哪一阵风,哪一场雨,就把它给掀垮了。
他经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答应了儿子,但他是有条件的。他掐算好了,今天是赶场天,他要再摆一次摊,再过一个乡场,然后安安心心和儿子去城里住住。儿子答应了他。儿子是个孝子,知道当爹的心里想着什么。
太阳从对山背后一蹦,蹦了出来,院子上空,一下子明亮起来,院坝里亮晃晃的,像铺了一层稻子。老人站起身子,去厨房接了一壶从竹管里流出的清亮亮的山泉,放在院坝炉子上生火烧水。又去洗茶杯,茶杯半年没用,积上了灰尘。老人撮上一捧草木灰,用水淋湿,细细地擦拭着瓷杯,擦洗得雪白透润,整整齐齐摆在桌上。茶叶是现成的,黄金茶、乌龙茶,当然还有包谷茶和姜茶。黄金茶是自家产的,茶场就在屋后,自己一叶叶地采摘,一把把地揉,一点一点地文火慢炒,隔老远就能闻得到清香。乌龙和碧螺春,是儿子买来的。至于包谷茶,就现做了,这种茶年轻人不喝了,老年人还在喝。老人从地楼上取下几棒包谷棒子,剥开,塞进灶炉里烧着,要烧糊了,包谷变成焦黑,用开水泡上,就是红黑色的包谷茶了。老人不慌不乱地做着这一切,脑海里不由得就恍惚起来,想起好多事,想起许多年前的事。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爹和娘也这样在院坝里摆满了椅子,也这样用草木灰擦洗茶杯,也这样用焦糊的包谷泡茶,耐耐烦烦地等着赶场回来的人像南迁的鸟儿一样在院坝里歇脚。乡场远着呢,最远的有十几二十公里,赶场人回来,哪能没有一个地方歇脚呢?口渴了,哪能没有一碗茶呢?乡场上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笑话,家长里短,怎么能没有一个地方交流呢?不知从哪时开始,他家成了赶场人歇脚的地方,赶场回来的人们有人口渴了,有人走累了,有人纯粹是憋了一肚子的笑话没地方说了,把背篓、箩筐、马架往路边一扔,着走上路坎,叫一声“东家,讨碗茶喝”就进来了,像进了自己家一样。那时只有本地黄金茶,另外就是包谷茶,乡下人喝得爽快,喝得高兴,爹和娘乐颠颠地在桌子中间穿梭着,给大家续开水。歇够了,喝足了,叫一声“东家走了呵,”拍拍屁股走了。茶水,桌椅,一切免费,东家倒贴。乡下人最怕人说一句你家的水都要钱,那是侮辱人呢。那时他不知道爹图个什么,曾问过爹。爹说,我们家招客呢,主好客来勤,人家愿意上门,是看得起我们家呢。有时爹外出有事了,娘就顶替着,每个赶场天,院门都开着,开了几十年。“大槐树人家义气呢,”“大槐树人家开通呢,”就赚了这些的话,却让爹娘乐呵了一辈子。
父母都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父亲死时对他说:“崽,赶场天院坝门不要关,让乡亲们歇脚。”他答应了。办丧事那几天,山前山后的人都来了,像赶场一样,有认识的,更多的是不认识的。大家都说,那堂丧事比乡长家办事还要热闹,比县长家办事还要热闹。人们都沉默着,各自做着自己的事,办厨,挖井,招呼客人,他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守灵的时候,大家坐在火堆边,摆着死者的好,摆着摆着,就有了眼泪,就有了感慨。那一刻,他明白了父亲的坚持。
父亲上山后的第三天,又是赶场天,他早早拉开院门,摆上桌椅,洗好茶碗,烧好开水。从那以后,院门一开,就是几十年,就是一辈子。他成了家,有了妻子,有了儿子和女儿,头上有了白发。粗黑的茶碗也变成了晶莹的茶杯,黑糊糊的包谷茶,变成了黄金茶,碧螺春,甚至西湖龙井……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都在这院坝里发生。
二十五岁那年,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婆子。那也是一个赶场天,一个经常歇脚的妇人带着她走进院坝,她们各背着一背篓采买的红薯秧苗,她们累了,随着人们走进来,在他家院坝歇气,喝茶水。那时她还小呢,穿着姐姐们留给她的松松垮垮的花衣裳,显得孱弱,稚气,脸蛋因为走路而涨得红红的,夕阳照过来,脸上的细细茸毛闪着光。不知为什么,他见过许多好姑娘,都没有那么动心过。父亲叫他出来倒茶的时候,他慌张地把水浇到桌上,引起一片善意的笑声。他脸更红了,眼睛都不敢朝她看一眼。
自那以后,她和她的母亲就经常来歇脚了,每次都安安静静地喝茶,一句话也不说。每次看到她,他的心就快要从胸腔里蹦跶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交谈,她和他一样,一开口脸就红到耳根。有一次,她接连三个场都没来,他像丢了魂一样。原来那段时间下雨,她走山路,一块石头被雨水长时间浸泡,松动了,她一脚踩上去,连同松动的石头一块滑下了山坡,幸好只被树丫挂出了一道伤口,幸好只崴了脚,没有伤筋动骨。听到这个消息,他心尖尖儿都在颤抖,都在痛。第二天,他把家里攒下来准备去场上卖的鸡蛋全部带上,又用赶场卖掉一只水鸭子的钱买上一些礼品,走了二十几里山路,翻过两座大山,去她家看她……
三年后,他把她娶回了家。那天凌晨三点多钟,迎亲队伍吹吹打打,一路欢歌,一路笑语,女的背着贴有红艳艳喜字的背篓,男扛着抬嫁妆的包杠,他的表哥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只鸡,一头是一个大陶瓷坛,又喊“盼子坛”,坛子里装的是苞谷烧。他们热热闹闹来到她家喝拦门酒,对拦门歌,把她接回来。目送着接亲队伍走远,他真想跟上去,亲自去她家把她接回来,可是风俗不允许。老人们都笑他,说他等不及了,“三年都等了,怎么在乎这一个早晨?”他们哪儿懂,他一刻都等不及呢,一分钟都等不及。好不容易捱到日头出,接亲的回来了,女的背着娘家打发的新铺盖,男人抬着油光发亮嫁奁,有半里多长,打着的火把照亮了半个山坡,喜庆的唢喇和欢笑唤醒了沉睡的大山。按照风俗,新娘子进屋时他要回避,他躲在外面,看着她跨过火把进了院坝,进了家门。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分开过,一起插秧,一起打谷,一起生儿育女,一起生出白发。
十年前的一天,她走了,从田地里回来,她有些头晕,睡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可是在他心里,她并没有走,一直都在呢,坪上坪下有她,屋里屋外有她,醒里梦里有她。她没有离开他呢,她只是害羞,和做姑娘时一样,处处躲着他,不出来见他。
他把两个儿女抚养得有出息了,成家立业了,对得住她了。儿子替他长脸,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家落业了。女儿也远嫁在外,嫁了一家好人,日子过得巴适,过得安稳,过得幸福。女儿隔三差五给他打电话,从电话里可以听出女儿的幸福,女儿的喜悦。他满足了。
她走了以后,来他院坝歇脚的乡里乡亲更加多了。大家极力和他扯白话,谁家的娃出息了,谁家的娃在外面打工搞发了,谁家脱了贫,场上干什么东西涨价了等等。他知道大家的好,大家怕他难过呢,怕他寂寞呢。尤其是儿子上大学,女儿出嫁以后,这个家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怎么能不寂寞呢?五天一场,他寂寞了四天,可一天就能消解掉的,那一天,九里十八寨都是他的亲人,都是他的家人,都是他的兄弟,都是他的孩子。他们簇拥着他,围着茶桌,天南海北,东长西短,叫老哥弟,叫老伯老叔,叫表叔舅舅,给他递暖心的话,递香香的香烟,他满足,陶醉,感激。
坐到太阳下山,人们起身要走了,这个顺手丢一把没卖完蔬菜,那个放几个鸡蛋;这个给一斤新采的茶叶,那个留两个才买的温热的蒿菜粑粑……他不推托,照单全收。都是真心真意,推托就假了,就生分了,就对不起人了呢。
二
渐渐地,太阳升到头顶了。院坝里的阳光铺天盖地,一簇簇,一缕缕,在树叶间翻飞着,轻舞着,在地上涂抹不规则的光圈。一串串槐花在微风中铃铛一样轻轻摇曳。院坝一角,小炉上的水壶在“突突”地冒着热汽。这是第几次续水?不记得了,水煮干了加,加了再煮,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茶杯里,茶水已经喝光了,老人重新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这才想起,从一早到现在,他还没吃东西呢。他来到厨房,草草地下了一碗面条,才吃两口,却没有了胃口。
该是圩场散场的时候了,大路上空空荡荡,谧无一人。虽然心里早有准备,老人还是有些空落落的难过。也许,他又要空等一场了,他已经空等了半年,不害怕再空等一场。可是还是要难过,还是要失落,就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儿子在县城工作,很攒劲,也很出息,买了房,还升了职。儿子买了房子以后,就一心要把他接去城里住。儿子说,爹,你苦了一辈子,就进城里来住吧,享几天福。他跟着儿子去了,不能拂儿子媳妇的美意呢。可是只住了十天半个月,他就住不惯了,夜夜梦里头都是在乡下,在院坝里,梦到赶场,梦到乡亲,当然也梦到她。他吵着闹着要回乡下,弄得儿子媳妇很为难,像是哪儿没照顾好他似的。儿子说,乡下没有亲人了,你一个人住在那里孤单,要是有个三病两痛的,谁照顾你?儿子又说,爹,是不是我不够孝顺,你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儿子还问他,是不是媳妇嫌弃他,往外赶他?没有,都没有,儿子孝顺着呐,媳妇也孝顺着呐。那可爱的小孙子,虽然只有两岁,也知道把糖塞在他手里,口齿不清地叫他:“爷爷,吃……吃。”可为什么还要想着乡下呢,儿子百思不解,还说了重话。儿子说:“爹,你不愿和我们住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不孝。”是啊,道理他都懂,都明白,七十多岁的老树蔸,他有什么不明白?他应该和孩子们在一起,养儿防老,贮谷防饥,他已经老了,到需要儿女照顾的年纪了。可是,为什么睡在软软的席梦思床上就难受,为什么梦到的却总是老屋呢?为什么一踏上返乡的汽车,一听到乡音,就通体舒泰,百病都无了呢?
乡下人都羡慕他呢,羡慕他养了个好儿子,又懂事又孝顺,成了公家人,城里人。也有人笑话他不会享福,城里有吃有穿,有大街有洋楼,还有好多新鲜的东西,却一心要往老家跑,也不知惦记着什么?木屋比他还老,用许多木棍撑着,摇摇欲坠,有什么值得记挂的呢?可是他还是要记挂,没来由,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再后来,他明白了,他是记挂人呢,他不在家,赶场的乡亲们在哪儿歇脚呢?要是下雨了,他们去哪儿避雨?他们口渴了,又去哪儿喝一杯茶?和他一样老的老人们,把每场都当最后一场赶呢,要是他们来到紧闭的院门前叫一声东家,却没有人答应,该会多么难过!还有,在城里,没有人认得自己,在乡下可不是,没有人不认得自己。伯伯、满满、舅舅、家公……他的头衔可多呢,多得都数不过来。他们都会把自己经历的,听到的,各种稀罕事在院坝里说给他听。要是他不在了,他们说给谁听呢?说给那株老槐树听,它听不懂,也不会答应啊。
所以,他不管不顾,奔生奔死地回来了,五天只盼一天,用四天来擦拭茶壶,用四天去探试桌子,只为了到那一天逢集赶场的日子,当一个贤惠的主人,家里坐满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只为了听一声亲亲热热的爷爷、伯伯、满满、舅舅……
还有呢,在城里回忆不起来的一切,在这老旧的院子里,就都可以想起来,想得细细碎碎,想得丝丝缕缕,连一点细节都不会忘记,他人生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里,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在这里。老人至今还记得第一回当爹的滋味呢,她痛了几个晚上,他就痛了几个晚上,她熬了几夜瞌睡,他就有几夜睡不踏实。直到儿子“哇”的一声来到人世。他捧着婴儿,就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品,横着抱也不是,竖着抱也不是,左抱也不是,右抱也不是,生怕把儿子抱坏了。后来,女儿出生,他就沉稳多了,不像第一次那样慌手慌脚。抱着那个粉嫩粉嫩的小人儿,他的心都要化了,怎么看也看不够,恨不得把她装进眼眶里。还有,屋对面的山上,还有父母和她坟墓呢,每天早上打开院门就看到他们,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离开一样。在城里,这一切都远了,山重水隔,想他们的时候,他去哪儿看呢?
就这样,他回到乡下,一个人守在老屋,守着这五天一次的乡场,很满足地生活着。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乡场渐渐有些冷清起来,赶场人少了,摆摊人少了,来歇脚的人也少了。年轻的出门打工了,年纪大的,去城里带孙儿孙女了,年纪更大的,也许就走不动路,赶不动场了。场冷了,人少了,可毕竟还有人来,一些许久不见的面孔,突然哪一场就见到了,彼此问一下去了哪里,说一下外面的世界。日子就那样咸咸淡淡,有滋有味地流着……
终于,一年前,通往乡场的大路改了道。院坝外的那条大路安静下来,也落寞下来。渐渐地,野草从路边的坎上长过来,从石头缝里长出出,把路边吞噬得只剩下瘦小的一条……那段日子,每逢赶场天的清晨,他躺在床上,支愣着耳朵,倾听着,期盼着。院坝外,一切安静得反常,没有拉货的拖拉机的突突声,也没有杂沓的脚步声。他明白,这条路老了,老了,就该废了,这是规律,他虽然不认得多少字,却懂得这个规律。可是他还是起了床,像往常那样准备着,把木桌搬到院坝里,把椅子围着桌子摆好,备好茶叶、茶杯、茶水。他喝着茶,看着太阳升高,又看着太阳偏西,喝到露水打湿衣裳,再看到月亮爬上来,把清晖洒在院坝里。灶炉里,灰烬早已熄灭,开水冷了,他终于意识到不会有人从这里经过去赶场了,不会再有人在院坝下面高声喊着“东家,讨碗茶喝”了。明白了这点,他沉默起来,像被谁打了一棍似的,摸索到床上,倒头就睡了。
可是,每逢赶场天,他仍然要怀着隐隐的期盼,做着几十年来做着的一切。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三
不知不觉,太阳开始向后山落下下去了,山顶的影子推过来,堆过屋脊,向院坝中央推来。老人把煮干的水壶提起来,再接了一壶山泉水,放在炉子上烧,又在炉子里加上几块柴,看着柴火轰的一声升高,才直起腰来,向院门外走去。
院门外,是一个石头码就的石坎,站在上面,可以把大路一目了然。长满杂草的大路一头从山里伸出来,另一头向另一个山洼伸去,消失在开始泛黄的稻田里。有鸟鸣从后面的山野里传来,那是归巢的鸟鸣,又一个傍晚到来了。
老人倚在院门上,有些累,也有一点落寞,甚至有一些悲哀。不过,他很快笑了起来,笑自己孩子气,笑自己傻。是啊,怎么不是傻呢,大路改道了,怎么还会有人从这儿走过,怎么还会有人来歇脚讨茶喝?早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还悲哀什么,落寞什么?
老人笑着,夕阳照在深深裂开的皱纹上,闪闪发光。老人觉得脸颊有些发痒,用手一抹,抹出一手的湿。我哭了吗?他问自己,又是点头,又是摇头。
他看着满院子的桌椅茶具,突然就有了一种轻松,一种解脱似的轻松。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打开院门,在院坝里摆上这一切了,过了今天,他就要进城和儿子团聚,这一去,也许要到死神降临的那一天,他才会回来。而他今天所做的一切,由此更生出了一种仪式感,一种象征……
大路改道之后他还每个逢场天在院坝里摆上茶桌的事,终于传到儿子耳边。儿子不放心了,儿子专门回了一次家,还把女儿也带了回来,两大家六个人。儿子生怕他精神出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问了他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都回答了。医生说,伯伯没心理毛病,一点病都没有。孩子们放心了,放心后他们向他下了最后通碟。儿子说:“爹,赶场不经过这里了,你还留恋个什么?难道有什么比我们还重要吗?你再不进城,我就不认你这个爹。”女儿更狠,说:“你不答应和哥进城住,我就把这屋给拆了,看你住哪里去!我说到做到。”孩子们话说得狠,可他听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这哪儿是狠,这是爱啊,这是孝道啊。他也年轻过,也有自己的父母,他怎么能不懂孩子们的心?他答应了,条件只有一个,让他再摆一次,只一次,不过有人来没人来,摆一次就死心了,摆一次就满意了,摆一次,就跟他们进城去住,永远和他们在一起。儿子和女儿犟不过他,答应了。几个孩子和外孙还和他拉了勾:“拉钩拉钩,哪个骗人是小狗。”他不会骗人,他摆了这一次就进城。
终于,后山的影子推过院坝,推到对面的大寨子上。暮色准备降临,天空却变得异常澄明起来。看来,是不会有人来了,老人叹了口气,趔趄着回到院子里,开始拾掇。这次是要做长期不回来的准备呢,桌子和凳子都得码起来。老人弯下腰来,费力地把两条长条凳叠在一起,蹲下去扛在肩上,搬回屋里码好,再回来把桌子搬回屋里,也照样码好。
院坝里空旷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老人搬起最后一把桌子,直起腰来,愣住了,仿佛太阳一下子重新升高,老人看到院坝里突然亮堂起来。
“东家,讨碗茶喝啊。”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院门外的坎下响起。老人放下长条凳,急步向着院门走去。霎那间,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坎下大路上,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一个年轻人的搀扶下向上走来。老人的背后,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背着背篓,挑着空箩筐,笑盈盈地看着他。
“伯伯,讨碗茶喝。”
“满满,好久不见了。”
“舅舅,散场了……”
“爷爷,我给您带了点油粑粑来,你尝尝……”
……
老人站着,只是点头,什么都回答不上。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老人小孩子,男人女人,叫他先答应哪个,后答应哪个呢?这真为难。老人呆呆地站着,看着人们像进自己家一样鱼贯而入,站满了院子。耳边是人们亲热的埋怨,“你这个老树蔸,桌子呢,茶碗呢?”这是和他一般大的老人说的。“伯伯,怎么这么早收摊了?你真不贤惠!”这是年轻一辈的,“不劳驾爷爷了,我们自己有手,搬啊。”这是孙子辈说的。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说一声搬就七手八脚搬起来了,不一会儿,四张桌子,十几、二十张凳子,摆满了院子。自己烧水,自己泡茶,满院子都是亲亲热热的乡话,满院子都是亲亲热热的目光。
老人愣怔着,恍恍惚惚。“歇个脚,讨碗茶喝啊。”门外,大路上,喊声还在不时响起,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有了那么多人,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挤满了院子,挤得阶檐下都站不下了。老人抬起头,迎接着每一双目光,不知为什么,他喉头哽咽起来,泪水涌出眼眶。
“大家歇好脚,喝好。”老人费了很大劲头,才压抑住哽咽说出这说了几十年的话,然后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他用力仰起头,想让泪水流回眼眶里去,却意外地看到,澄明夜空里,挂着一弯新月……
——璧山区建立三级院坝会制度推进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