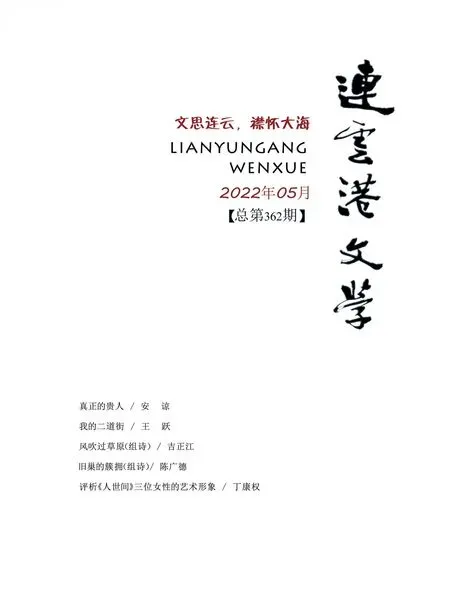蜻蜓,蜻蜓
徐 凝
他说,很大很大的一只蜻蜓,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蜻蜓,我把它从山上带回来了,就放在那个窗台上。
他欠了欠身,伸出白皙的手指,指着靠近房门的那个窗口。
林非于是就回过头去朝那边看。
现在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很大很大的一只蜻蜓,放在那儿,都干瘪了。他说着,眼睛仍盯着窗台方向。
林非当然相信他说的话,甚至脑海里已经出现了那只蜻蜓的模样,是的,很大很大一只蜻蜓。即使自己没见过,心里没有底,但是那只蜻蜓的模样是一下子飞到脑海里的,丝毫没有经过几次三番的修改,林非认定脑海里的这只蜻蜓就是他说的那一只。
蜻蜓没有了,而且还是一只死的蜻蜓。——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事实并没有掩盖住回忆。真正的事实是,一只活的蜻蜓,很大很大一只蜻蜓,被他从山上带回来了。
他说的这一切无疑令人神往。
在林非心里,很大很大的一只蜻蜓,两只大眼睛骨碌碌地,还在转动着,它还活着,在它所有的小眼睛里还晃动着各种各样的事物,松树,白云,飞翔的鸟雀,还有面前的这个人,正在山坡上站着……
他说,我相信天意。
天意,当然是天意。如此巧合的事物出现,就是天意。当然,天意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求来的巧合,只能称之为人为的安排。林非没有经历过天意的出现,所以,心里除了神往,又增加了羡慕和崇敬。
屋里很窄小,几样一览无余的家具在稍显暗淡的光线里错落有序,这就是他的家。屋里很安静,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林非背对着门,他坐在床沿,一个下午静静的时光里,房里其他的空间慢慢地被他的回忆充满了。
林非是看了他发表在刊物上的小说,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几经打听,终于找到这儿来了。之前应该已经来过一次,他不在家,邻居的话证实了这儿就是他的家。
他说,小说写完了,头发都变得硬扎扎的,竖起来了。说着,他把右手罩在头发上,然后又向上抬了一下。
林非脑海里像有一组镜头在转换,立刻又出现了一头直竖的发丝,一根一根的,看得很清楚,看得久了又感觉不像是头发,像是什么呢?
刺猬。
想到这,林非嘴角上就有了浅浅的笑,旋即却又满怀歉意,很自然地把头低下了一点。
是的,很费精神。不过,我相信我的文字是对得起自己和别人的。他说,山上的那段日子很好啊。
整个下午,他们谈的就是他的文字,他那只很大很大的蜻蜓,他没有问及林非从学校里出来后的近况或者家庭情况。其实,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当然林非也不是,两个不善言谈的人怎样度过了那个初春的下午,以致让林非在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颇感诧异,甚至怀疑那个下午的一切是否存在过。
然而,蜻蜓是真的存在的,很大很大的,是他从山上写完那篇小说带回来的,后来放在了自家的窗台上,再后来干瘪了,又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
林非从他家里出来的时候,竟然扭头朝窗台看了一眼,好像那只蜻蜓还在那儿。
离开他家,很久又没有了他的消息,林非也没再到那儿找过他。
林非喜欢他的那些文字,从第一次见到就喜欢了。那时他是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新学期的第一次作文课,林非写得很不顺手,内容是描述家乡的变化,命题作文,搜肠刮肚好歹交上去了。过后本子发下来,他给批了七十多分。林非有些不服气,心里想,自己在初中时就发表文章了,现在刚上高中,即使写得不好,也不至于给那么点分吧。
第二次作文课,他说可以自己命题,想写什么写什么,明早交上来。放学回家,林非熬了一夜眼,也没打草稿,直接在作文本子上洋洋洒洒地写了十来页,畅快之至。
后来发生的事情,成了林非一辈子引以为豪的片段。
作文本子再次发下来了,上一次写的那一篇被红笔改成了八十多分,而新写的那一篇得意之作却没有任何得分和评语,开始以为他批改时漏掉了,后来知道完全不是。
他说,这次作文都写得很不错,我还看到了一篇最好的,本想念给大家听听,很遗憾那大约是抄袭的,我就不念了,希望这位同学以后注意。
在那一刻,林非就隐隐觉得,他不是一个寻常的老师,他的语气里除了一些责备之意,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吸引力。他的身上像是拥有一个磁场,在那个磁场般的世界里,一些美丽的文字在旋转。
真正的了解是在几天以后。他在放学之前把林非叫到了办公室,拿出一沓打印的文字,说,我写的,回家看看吧。
林非不知道这个突然发生的转变是怎么来的,但是就这一瞬间,林非知道他已经认可了自己,那篇没有批改的作文显然不是抄袭的,而且,不但得到了他的认可,两人的关系也超出了普通的师生界线。
林非默契地接受了眼前的现实。
那个令人难忘的秋日的黄昏,地里的稻子即将收割,夕阳下遍野的金黄。林非骑着自行车飞奔在回家的林荫道上,书包里的那件东西简直就是一块烧红的铁板,在一路炙烤着他狂跳的心。
这是一首打印好的抒情长诗,是林非和他要一辈子交往下去的开端。
大梦褪尽,思想归于原始。幕布拉开
款款而行的是一队女子,一切那样寂静
露水打湿了大地的唇吻,薄雾掠过黎明的眉睫
太阳在上升,四野沐浴在巨大的安详里。阳光
洒在女子的发梢、裸露的臂膊和双乳上面
啊,这世间耀眼的无比的母性的光芒……
他写道。
林非更加坚定了那个磁场般的世界真实地存在。
所以,在多年以后的那个初春的下午,在一间窄小的职工宿舍里,他说,我相信天意,他指的是蜻蜓,林非没有过类似的巧遇,但是,和他的相识,应该也是天意吧。
林非完全沉浸到那个磁场般的世界里了。
他在教室里朗读课文,许多同学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地提起,那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啊!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林非似乎已经感觉到了那月色下的一片荷塘,一阵凉凉的水味儿,在教室里油然而生。
这样的声音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就彻底在教室里消失了,他离开了那所学校。林非曾辗转联系上他,通过几次信。
三年高中生活倏忽而过,林非回到了老家,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游荡生活。那段时间,林非能灌下一瓶白酒而依然言语不乱,在伙伴当中甚至整个村庄里留下了善饮的美名,以至后来的某个场合林非说自己已经连一小盅白酒也喝不了的时候,当年的伙伴们一点也原谅不了了,这个曾经在酒桌上喝倒过别人的人,如今他扭捏的样子,让人感觉是那么的可笑和不可思议。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林非跟随伙伴在一个一个村庄游荡,酡红的面庞、布满血丝的眼睛、乡间小路上的狂喊乱叫……那段丑陋的岁月啊!
每当深夜回到家里,林非却陷入了一望无边的孤独之中。摊开日记本,之前发生的一切从脑海里移到了纸上,详细地记录着自己的所作所为,高兴的、迷茫的、龌龊的,几乎一日不落。那些日记本现在静静地躺在角落里,林非简直不敢去触碰。
林非心里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教师,虽然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似乎并没有教过自己什么,但是那个磁场没有消失,那个两人之间无法言说的世界依然存在。
林非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
他减少了游荡的时间,找到了一个让人安静的办法,就从阅读开始吧!
在县城图书馆那栋破旧的二层小楼里,林非从管理员手里接过了新办的借书证。那位中年妇女的眼神云淡风轻,借书证却带着温度,带着力量,一刹那就让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感觉,暖暖的,怦怦地跳动。
读书真是一个好办法,林非真的安静了下来。本来少年时期就有的那份对文学的爱好,林非很容易走进文字的天地里,借书证上很快就填满了一长串书名。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林非趴在床上,在橘黄的灯光里,一个人静静地读着,掀开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走进那个世界,就不再孤单,就远离了喧嚣,那是多么令人喜欢的世界!
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林非还了书,准备再去找一本新的。他随手拿起一本杂志,一本薄薄的文学杂志,先看了一下目录,蓦地惊喜不已,一个熟悉的名字竟然出现在里面。是的,自己老师的作品在里面!多年音讯全无的他忽然来到了眼前,林非如获至宝,简直要狂跳起来了。
林非借出了那本杂志,下了楼,心急火燎地往家赶,要去家里静静地读一读他的文字。自行车在沙石路上颠簸着,背包里放着那本杂志。林非想起了多年以前,那一个黄昏,林非骑着自行车出了校门,飞奔在回家的林荫道上,书包里放着他的一首打印的长诗,那一叠诗稿就像一块烧红的铁板,一路炙烤着他。如今,昔日重来,林非一样地激动。
回到家里,林非迫不及待地先把他的那篇小说读完了,一口气读完的,兴奋地来回在屋里转圈圈。这是林非第二次读到他的文字了,多年以前那首抒情长诗还记忆犹新,而眼前的仍然令人着迷。他的文字是独特的,有魅力的,像一个形象特别的人,让人过目不忘。
小说写了一个遥远年代的故事。那是一个梦幻一样的故事,故事的场景里飞翔着无数的蜻蜓。
林非知道,这样的小说属于先锋文学。
借来的杂志要及时还回去的,林非找到了一家复印社,将那篇小说全文复印下来,这样就可以随时翻阅了。
——我要去找他!
林非在心里说,应该找到他,看看他。
在林非的记忆里,似乎并没有找过他,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找到他,看看他,只是一个愿望而已。
那么,后来的那次见面,他那简陋的职工宿舍的家,那只他从山上带回来的蜻蜓,都是臆想?
林非自己也不能确定,也许根本没有去找过他,那次见面确实没有出现过。
天意!林非也相信天意了。
但是,接下来的记忆是清晰的。
林非从同学口中得知,他真的调动了工作,不再做教师了,他的新单位就在杂志社,就是他发表小说的那家杂志社。
林非坐上去市区的班车,一路打听,找到了那家杂志社,找到了他。
老师!
林非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看见他坐在那里,抬头、起身、让座。
对于林非的到来,他的眼里露出喜悦的神情,却又有些矜持。
两人坐定,他拿起桌上的一根烟,递给林非。桌上还有几根,那显然是有不少作者来过,给他的。
林非已经学会了抽烟,他难道是闻到了自己身上的烟味?接过烟,点上,他也拿起一根点上。
两个不善言谈的人不会有热烈的话题,小小的办公室旋即陷入寂静。
他看稿子,林非翻看那些书刊。
已近中午,他似乎猛然记起该吃午饭了。他匆忙带着林非去食堂,食堂的人很少,果然是有些过点了,人家大多吃过了。
他打来了饭菜,很简单的几样,食堂的菜估计没剩多少了。
饭菜都已经凉了。
林非尝了一口,看了看他说,吃啊!
林非把饭菜都吃完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林非数次想到了这里,心里却是热的。
也许谁也不会理解他们这样的交往,对于当时初涉世事的青年而言,林非隐隐地觉得,荷塘的月色是美的,他的磁场一直都在,能在他身边看一看,就很好的,不需要别的。
有一个词叫“思念”,林非其实是很敏感的,总爱一个人胡思乱想,想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对他,林非就常常陷入回忆,想念在市区工作的他。他不是亲人,也不是朋友,他就是一个深深地印在脑海里的、说不明白关系的人,想起来就觉得温暖,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却又得到了很多。
林非把这些思念记在日记里,记在心里。
日记里记录了他们之间最初的相遇,“作文事件”,阅读了他的抒情长诗的感受,他在课堂当众对他的表扬和期许,同台参加学校文艺会演,以至后来的通信内容……
但是这些过往的日记,有很多令人心痛的心路历程,林非几乎不去翻阅那些内容,记完了一本就放到抽屉里,一本一本放在那里,保存着,看着它们,就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时间啊,会让一切都过去,过去了就好,我们再去迎接新的一天。
新的时光又一天一天过去,林非结婚了,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林非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庭。
可是,命运总爱捉弄人,林非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多少个夜晚,林非难以成眠,脑海里浪花翻腾。
林非觉得自己就要滑进深渊里去了。
——我要去见他!
林非突然有了这个想法,虽然不知道见到他能怎么样,心里就是想去见他一面,跟他说说话,即使他不善言辞。
当林非来到了市区,下了班车,找到杂志社,可是门卫告诉他说,杂志社已经搬迁走了,新址在某某地方。
林非对市区不熟悉,点了点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钞票,咬咬牙叫了一辆出租车。
杂志社到了,可是他不在那里,有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今天歇班,林非于是要了他的手机号码。
林非站在杂志社楼下,中午的阳光肆无忌惮,有些晃眼。
电话打了几遍,终于通了。
他说他刚做完饭,让林非在这儿等着,他一会儿就到。
他骑着摩托车来了。
走,先吃饭。
他说。
林非坐上了摩托车的后座,第一次和他靠得那么近。
老师,你有白头发了。
林非说。
摩托车在市区里穿行,在一条街巷里停下,停在了一家饭馆门口。
市区的作家们常在这里聚会、吃饭,带你来尝尝。
他说。
他还捎来一瓶酒。
两个人吃饭,他点的菜有些多了。林非没有说什么,只有默然接受。
边吃边聊,他不断地给林非夹菜。他说他全家已经在市区安顿下来了,但是还算不上安逸。他说他一介书生,不善经济。
林非也诉说了这些年的境况,有些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
林非在这家简陋的小饭馆里,吃着丰盛的午餐,而且只有两个人,说了很多的话,许多年以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啊!
在回家的班车里,林非暗暗下了决心,要坚强地飞翔,“为了那些挚爱的眼神!”
很多时候,我都想轻轻地走近你,看看你在那儿干什么,一个洒脱倜傥的男人,一个拘谨木讷的男人,在嘈杂的人群里,怎样地把身子转过来。
我们的相聚那样短暂,两个人眼里,有灿烂的星辰。你告诉我,多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谈,什么叫幸福?
是的,你喜欢安静…… 但是繁忙的工作完全淹没了你的爱好;我常常仰望星空,不敢去面对明天,我的大海飘摇不定,暴雨狂风,几乎要把我打垮,沉进无底的蓝。生命何其脆弱,我的力量,有时远远不及一只蚂蚁。
就这样坚定地走下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谈。
林非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
林非和妻子做起了小吃的生意,起早贪黑,最初的那段时间,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每天,在嘈杂的小市场里,和相邻的摊主们说说笑笑,赚钱也不少,林非的身子发福了,一年多胖了三十斤。后来还购置了电脑,联了网。
在网络上,林非找到了他的博客,找到了他的邮箱。
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他已经不骑摩托车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出现在他的照片里,他开着它出去采访,“车行如箭”。林非在评论区留言:老师,注意安全,别开得那么快!
闲暇时候,林非就在网络上浏览,这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一双儿女在院子外面玩,欢笑声时不时地传来,林非很欣慰,那么困苦的日子总算走出来了。
蜻蜓,蜻蜓!
孩子们大喊着,爸爸,快来捉蜻蜓!
蜻蜓?
林非和孩子们真的捉住了几只蜻蜓,看着手掌里那可爱的小东西,忽然就想到了他的那篇小说,想到了那一天的下午时光,他们相对而坐,他说,他写完了小说,从山上带回来一只很大很大的蜻蜓。
那篇小说是真的,但是那个下午存在的真实性有待求证。
林非怀疑自己想错了,可能是做了一个梦。写小说为什么要到山上去?怎么那么巧看见了一只很大很大的蜻蜓?自己是怎么知道他的家的?
林非的生意很忙,闲下来的时间很少,不然,真想再去市区看看他。
——他会想起我吗?
林非几乎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生活着:凌晨起床,准备早市;早市结束,去街里买肉买菜,买油买面,回来稍事休息,准备午市;午市结束,稍事休息,准备晚市……周而复始。
林非看着捉来的蜻蜓,出了神,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千变万化,却又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据说蜻蜓的复眼成百上千,蜻蜓看见的人世间是不是各不相同、光怪陆离?
应该是的。
这个夏天的傍晚,天气闷热,林非去书店给女儿买书。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枝叶繁茂,形成了大片的阴凉地,买完了书,林非站在树下抽烟,虽然避免了阳光的直射,但还是有些热。这些法国梧桐有些年头了,林非记得年少时来县城玩,这些树就有了,似乎就是现在的样子。
林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那些飞逝的时光带走了太多的东西,又证明了自己已经远离了童年、少年,甚至“青年”也不算了,开始步入了中年,那些无忧无虑、我行我素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街道上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不知道他们都在忙着去干什么。热浪涌过来涌过去,林非感觉脑袋晕乎乎的,有些困意,真想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好好睡一觉。
林非的视线停留在了街道对面,在法国梧桐的枝叶间,有一片矮小的红砖灰瓦的老房子。林非恍惚觉得自己去过那里,那是他原来住过的地方。在一个春日的下午,在他简陋的家里,他讲了创作小说的经历,小说是在山上写的,写完了,遇到了一只很大很大的蜻蜓,他把蜻蜓带回了家,放在了窗台上。
那个下午很遥远了,林非一直认为那只是自己曾经的一个梦境,只是那个梦境如此清晰,如此温馨。
——我真的去过那里吗?
林非依然不能确定。
林非想去街道对面那里看一看,看一看他的家。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又瞬间打消了。
到底去没去过那里,其实并不重要了。
忙忙碌碌的日子容不得自己胡思乱想,知道他在市区编杂志,早就不在那里住了,偶尔的网络交流也是很好的。林非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好好地谈一谈,什么叫幸福。
林非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但是现在最要紧的,要赶回去准备晚市出摊子了。于是匆忙骑上车子,在阳光下疾驰而去,臂膀上渗出的汗水,又黑又亮。
街道有成群结队的蜻蜓在低空飞翔,它们用复眼看着人间百态,透明的翅膀“唰唰”地扇动着,看来一场大雨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