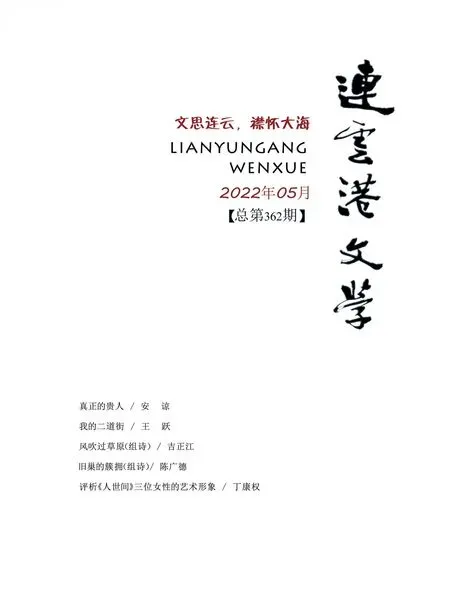我的二道街
王 跃
风与味道
二道街的风是圆的,它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滚下来的风,从我身上碾过,又重重地跌落在地,把随身携带的味道,跌得到处都是……
二道街的杨家很有名,普通的猪下水,经过杨家的摆弄再摆到盘子里,全变了,变成一种味道,变成一种只属于杨家的味道。
杨家的卤货,颜色不同于与一般人家。一般人家的卤货,颜色是红的,杨家卤货的颜色是黑的。杨家卤货,用几十味中草药卤,都卤黑了。杨家卤肉,用眼看,看不出什么门道。你不能动它,一动它,它就笑了似的,抑制不住地飞出香味。所以杨家卤货是不老实的,你一口咬下去,它就崩不住了,香味就长了腿似的往外跑。一天下来,杨家的味道在二道街不知翻了多少个跟头,不知挠过多少人的鼻子,不知慰藉过多少人的味蕾。
二道街西面有一条山路,过去是野路,夏天一到,不要说摞一根,有时就是摞三五根棍,也砸不到一个人。天气一寸一寸地热,山路上的草三五寸地往外长。等天热得喘不过气时,已看不到路,路浑身裹满了草。每下一场雨,路面就塌陷一些,尽管有草裹在路上,也不顶事,路像掉了牙,豁了嘴。在一场场雨的折磨下,路伤得很厉害。
伤得很厉害的山路,也有人走。只要是路总有人走。山路的那一头,住着不少人家,那些山上人家,尽管早已是城里人,其实是城中村,祖祖辈辈喜欢侍弄地。山间的地金贵,他们在碎石中开采,开采出的地有的如桌面大,有的如席子大,有的甚至只有脸盆大。地虽小,一年四季不闲着,该红时红,该绿时绿。
不知什么时候,二道街桥头多了一个卖南瓜的老人。老人的腰已弯成一张弓,她走路时两只脚像拴了一条无形的链条,挪不开,紧紧地蹭着地皮。她是顺着山路挪过来的,篮子里睡着瓜,如果瓜大就睡一个,如果瓜小就睡两个。
她在桥头卖瓜,不吆喝,也许她已经没有力气吆喝,那么难走的山路,已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到二道街,她只能眨巴着一双浑浊的眼睛,看来来往往的人。来来往往的人,不知能不能看到她。
有时临近午饭时,她还死守在篮子边,瓜还睡在篮子里。瓜没卖出去,她就不回家。心眼真是死。热气渐渐升了起来,街上连一个人影也不见。
后来老人的瓜很好卖。
买瓜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喜欢吃瓜,后来才发现,他把买下的瓜悄悄丢在一根电线杆下,任人捡拾。原来他不爱吃瓜。二道街人只听他说过一句话,“赶紧买下来,让她回家,天太热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很善良。也许他的名字就叫善良,谁知道呢?
整个季节,电线杆下不知放了多少个瓜。卖瓜老人一直以为自己种的瓜好吃,浑浊的眼里有了精神,但她走在山路上的步伐还是那么沉那么沉。
青年不爱吃瓜,二道街人都知道。也许她不知道,直到她种不动的那一天,都不知道。她种的瓜有一个青年最爱吃,也许是她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
青年买的瓜,二道街人没有尝到,但二道街人分明能闻到南瓜散发的甜甜味道。
二道街东面有山,是高高的屏障,它好像是太阳的冤家,太阳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爬到山顶,爬到山顶时的太阳给二道街送来的不仅是金色的光,还有太阳的味道,太阳的味道是二道街金贵的味道。可不是吗?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日子,山间都飘着云,飘着雪白的云,飘着铅灰色的云,飘着淡蓝色的云……在二道街看云,不能只看一次,要看多次,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明白,连云港的云是有味道的,它不光颜色不老实爱多变,连味道也不老实,有时飘逸,有时阴郁,有时奔放……但更多时,它会散发出棉花糖的味道。
云雾笼罩下的云台山是一个神秘世界,绿植多,多得你数不过来,高大的树,矮小的灌木,贴着地皮长的藓类,应有尽有。大诗人苏轼见多识广,他写云台山的诗有一句是这样的,“旧闻草木皆仙药”,这有点夸张了。但云台山上的草药真的很多。上了岁数的二道街人识得,身上痒了,不小心让火烫了,冷不丁摔了,手掌刮破皮了,内火旺了……二道街人拿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上山了,想什么就来什么。
作为女人的我,小家子气,山上那么多好东西不爱,爱山花。云台山上山花多,有名字的,没名字的,从春天开始就一个劲地嘟着嘴开。山花花朵不是很大,但颜色正。山花中名气最大的当属映山红。云台山上的映山红,每到春天就成为云台山的一面旗帜,在风中,在雨中,在春雷滚动中,哗啦啦地开。
从云台山上滚下来的风,是阔少,携带着云台山的味道。云台山的味道是石头的味道,是树的味道,是云的味道,是药草的味道,是山花的味道,是溪流的味道,是笨拙的我脑袋想破都想不出的味道。
风来了,怕风的我,哪怕头上顶着帽子,身子也不敢伸直,但在二道街不同,在二道街我是勇敢的,我昂着头挺着胸任风任性地吹,吹乱我的头发,吹乱我涌上心头的事。
二道街下是大海。刮向二道街的风是长了脚的,长了许许多多的脚,不然它怎能爬到位于半山腰的二道街?
海边风大。是的,位于海边的二道街,海风很大。大大的海风,连滚带爬地爬到二道街,累得直喘粗气。
二道街人可不管这些,在风中自顾自地忙碌。街上,海蛎子有了,小黄鱼有了,花蛤有了,八爪鱼有了,大螃蟹有了……二道街是海鲜的世界。在二道街桥头,你会有出其不意的遇见,遇见刚刚打捞上岸的海鲜,鱼嘴一张一合,螃蟹在一边无聊地吐泡泡,虾子弓着腰一纵再纵,八爪鱼在装死。卖海鲜的人,直嚷嚷,你看你看,都透活的,多好。是的,在二道街你吃过海鲜,在别处你就再也不想动筷子,因为找不到那个味了。
二道街的海鲜是直接从海里跳到锅里,跳到碗里,跳到盘子里。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美的日子天天有,受天时限制的。如果在二道街桥头,你看到卖海鲜的,你要抓住时机,哪怕贵一点,你也要买,大海是什么味道,在我们二道街你能逮个正着。
走在二道街,我还想起母亲上山采的蕨菜苗,想起父亲用海蛎子包的肉饺,想着想着,我眼里噙满了泪,我努力地憋着憋着,我不想让泪水流下来。二道街已没有我的亲人,我的眼泪流给谁看?我噙满泪水的眼睛,不能动,一动它就滚落下来。
二道街的风是淘气的,它可不管这些,伸出小手使劲地揉我眼,揉啊揉啊,把我脸上揉得是一片狼藉……
小石块
一枚不起眼的小石块,在二道街是有大用途的。
二道街人用石块砌墙,比较狂热。房前屋后的围墙,都是碎石砌的。一块一块都粘有人的温度。燕子衔春泥。二道街不少人都发扬燕子精神,把一块块小石块,甚至是小石子,都集中到一起,也不需要水泥勾缝,就这么见缝插针式地砌,砌成一堵堵或高或矮的墙。
我高中时,经常到一同学家玩,她家住半山腰。她家的院墙就是石墙,呈弧形。因为是山地,地不正,人要顺势而为,否则很难把事做成。三十多年后,我去拜访她。当年的红瓦房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二层小楼。碎石砌的院墙还在,她父亲搞了一辈子建筑,不知推倒了多少堵墙,在这堵石墙前,手软了。
一堵碎石砌的墙,即使被风雨抽打得斑驳陆离,也舍不得让它倒下。
二道街山上人家盖房子起楼,要先垫地基。地基是人造的,是从山底长出的石墩子。在石墩子上盖房,人才踏实。
二道街人家的地基,有特色,全是碎石砌的。有的房子,地基是从涧沟底部开始,一粒一粒有条不紊地往上爬,爬到沟畔时,回头看,碎石变成了一堵墙,一堵好看的花墙。一块石子不美,许多石子砌成墙就美了。
在二道街,碎石砌的地基,比正经八百的墙还高出一大截,这不是新鲜事。连云港海峡巷的朱家大宅,地基活活被砌成了一幅画,足足有几米高。朱家是有钱人,与二道街许多人家地基不同的是,朱家碎石砌的地基,用水泥勾了缝,每一笔都像描过的眉。勾了缝的石墙,是被打扮了的,有修饰的美。
一粒粒不起眼的小石子,被普通的二道街人,拼成了一幅幅看似柔软实则坚硬的画。在店里,我曾看过这样的墙纸,花纹就是石块砌成的,质朴而含蓄。二道街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石头砌成的墙,分明就是画。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二道街人砌出的墙,古朴浑然天成,和装饰店里的墙纸有得一比。
在二道街,只要涧沟里有水,女人的腿你用绳子扣都扣不住,她要到山涧洗衣服。二道街的女人说,在山上洗衣服,一把清。一把清,听过吗?只有在山涧洗衣服才一把清,不需要多次淘洗。
水流变细的季节,石头派上用场了。用石块拦截水流,不一会儿你会看到眼前原本浅浅的石窝,水渐渐地往青石上爬,爬着爬着,你眼前就是一大汪清亮的水。这时你就有用武之地了,可以放开手脚洗啊涮啊。在山涧洗衣服人不觉累,水清啊,一把清,人的干劲也足。不过,到家后才觉得人累得快散架了。如果二道街女人赖床了,大多是上山洗衣服累的。
衣服洗好后的二道街女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顺手扒拉开石块,一汪胖胖的水,瞬间瘦了下去,瘦得连一块青石也包不住。
在二道街,因为满眼都是山,满地都是石头,有一块地不易。如果有人煞有介事地把你领到他开垦的地前,你一定要绷住,不要笑,因为那块地超出你的想象,可能比脸盆大不了多少。为了向大山讨点地,二道街人是卑微的,扛着镢头,弯腰一下一下地刨,有的用錾子一寸一寸地錾。
二道街人家的地,形状奇怪,有方方正正的,有细细长的,有三角形的,有月牙形的……我觉得二道街山上人家的地囊括了世上所有的形状。二道街的地大小不一,有的有脸盆大,有的有桌面大,有的有凉席大,如果有两三块凉席大,主人就开始飘了,理想就肥了,地里舍不得种瓜种菜,愣是撒上小麦。平原地带的小麦地是一望无际的,麦子成熟时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成气候。二道街山上的小麦地是浓缩版,像从海洋中捞出的一个泡沫。尽管地盘小,它也得按节气走,多一步不行,少一步也不行。麦收时节,漫步二道街山上人家,你会看到手工放倒的麦子,看到打下来的麦粒,用盆,也只能用盆装。这微薄的收获丝毫不影响二道街人,从土地中获得喜悦。
有人说,中国人依恋土地,看到地,不能让它闲着,总是渴望它长点什么。土地不多的二道街人,对土地是疼爱的,从拥有它的那一天,就开始虔诚地侍候。
也许你会说,啰唆了半天,这些和石头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呢?
二道街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地,从高处到低处,是一层层的梯田,每一块地都有碎石镶边,若没有碎石镶边,那点可怜的土经不住山风的几次搜刮,经不住风雨的几次扑打。地与地之间,有差高,差高怎么办?二道街人用碎石砌成的墙撑着。山坡上梯田与梯田之间,都是用碎石勾的边。二道街山上人家的菜蔬,像是长在石头砌的盆景里。不要说吃,你就是看一眼,心里也美得不行。
在北云台山,有多少条大大小小的山涧通向大海呢?有人统计过,数字让人咂舌。山涧里除流淌着清亮亮的溪水,最多的就是碎石。
大山深处,山涧里的碎石是乱的,尤其是雨后,乱七八糟,满山涧都是。离人近的山涧就不一样,人会巧妙地利用碎石。在山涧两边用碎石砌一条通道,任山水在里面撒了欢似的跑,跑向山下的大海。
来连云港的二道街,你可以看海,可以看云,你也可以看看这里的人,是如何把一块块不起眼的碎石,稳妥地镶进自己的生活的。
一枚小石子,长在别处也许会自卑,觉得自己没有用。长在二道街不会,睿智的二道街人,总会为它寻得一个好去处。即便没有人用它,任它躺在大山深处,也蛮好,因为可以顺势吹吹山风,闻闻花香,听听鸟叫。一块石头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连白云也会妒忌的。
在二道街的路边,如果你看到一枚小石块,千万不要童心大发,大脚一抡,把它踢飞。因为坡子大,停车的司机,说不定正勾着头找它呢!石块塞在车轮下防滑,不然,车就成淘气的孩子,自己溜下山了。
山 洞
二道街西面的山脚下有山洞,好几个。
夏天,知了的叫声,密密匝匝,溅得满山都是,连草缝里都落满知了声。天热啊,这时从山洞前经过,凉气似水滑的绸,袅娜着身子从洞里飘出。洞口清爽凉快,但少有人驻足蹭凉。年幼时的我,从洞前经过,更是恨不得多长出一条腿才好。
和父亲一起从山洞前经过,我会玩花式法,首先我会矫情地飞奔,然后矫情地尖叫,以示害怕。个子不高的父亲,此时会云淡风轻地咧嘴一笑,脱口一句,有什么好怕的!他是聪明的,他应该读懂我的心思,我所有的矫情,其实是想博得他的关注。一个孩子只有笃定一个人爱自己,他才会矫情起来。
年龄大了,胆子也跟着长。我终于能勇敢地站到洞前,细细地看它,尤其是冬天。冬天一到,山洞就变样了。夏天,洞外的青石上,水流长出无数的脚,在石壁上爬,你只有走近才能发现它的踪迹。冬天,水流的手脚被捆住,结成了冰,洞口白花花的,从上到下都是。洞顶滴下的水,成为晶莹剔透的冰挂,一根根悬挂下来,长短不一。严寒成为艺术大师,在洞前大展身手,山洞成了艺术品。
南方的山洞因为是喀斯特地貌,洞里有形态各异的石钟乳,有大小不一的广场,甚至有暗河,可以划船,经过灯光的打扮,洞里成为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
我哥哥小时候和二道街的许多小孩一样,对山洞好奇。有一天,他急匆匆地回到家,样子十分兴奋,连话都快激动得说不出来了。原来他和几个要好的小朋友到洞里探险了,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准备了手电筒、火把、火柴、水、食物,甚至还在家里隐蔽处留了字条,以便大人寻找。他们决定早晨进洞,午饭在洞内解决。几个小孩,拨开洞前的杂草进了洞,洞里的地面上都是水,手电筒的微光,灼开了前行的路。很快,他们出了山洞,因为洞压根就没有想象的那么长。
离二道街较远的一座山头,有山洞,那个山洞深,洞口非常隐蔽,洞里开凿出房间的模样,穿过山洞,要花十多分钟的时间。看过一个军事题材的小说,讲一支队伍神秘地屯住在一个深山老林里,任务就是开山洞,为战争作准备。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流了血,流了汗,流了泪,甚至有人把命留在洞里,工程快竣工时,接到上级命令,工程停止,部队撤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啊!
二道街山洞的开凿也该有故事,问谁呢?
有一天天刚亮,我满脑子都是二道街的事,我又一次想到了山洞。那里究竟有几个山洞?是四个,五个,还是六个,我真是拿不定主意。有时最熟悉的地方,往往是最陌生的。
我曾经专门去数过山洞,数着数着,我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因为从这个洞到那个洞之间有段距离,距离之间有风景。这些风景有的是龇出的山岩,形态各异,分明是大自然雕刻出的石像;有的是长在石缝里的树,一棵树对生命的热爱,远远超出人的想象;有的是开在路边的各色野花,花朵不大但气势旺……它们不光抢走我的视线,还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当又一个山洞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已经把前面有几个山洞的事忘了。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有这样镜头,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拖着受伤的腿在山路上爬,每爬一步,身后就是一道血痕。这还不打紧,要命的是敌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后面追,马蹄声“嗒嗒”地传来,重重地敲在我心上,我两手攥紧,眼泪唰唰往下掉,我一时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转机出现,在山道边出现一个不大的山洞,他拖着受伤的腿躲了进去。不一会儿,敌人骑着战马从洞前飞过。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我曾想当年的战士是从二道街山洞前爬过的吗?当然不是。但这个镜头在我脑海中一直是鲜活的。
人就是一根木头,走着走着就老了,就朽了,就走不动了。
我父亲最后坐上了轮椅,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有多少硬汉都被时间整趴下了,何况他?一个普通人。
二道街是细长的,我们会把坐在轮椅上的父亲,顺手推到西边的山路上。西边山洞前的野路已经铺成了水泥路。我们从山洞前来来回回地走。那时,我已经不怕山洞,我怕父亲会离开我们。
在时间面前,一个人的害怕是渺小的。我的父亲并没有因为我的害怕,而留在这个世上。
父亲走后的日子,我常像一只悲伤的狗,拖着尾巴在山道上走。为了分散悲伤的情绪,我开始数山洞。山风夹带着寒意在弯弯的山路上跑,我数着山洞,数着数着我就忘记了,也不想数了。因为我脑子乱了,满脑子都是过去的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像得了一个怪病,脑海中常常出现,父亲坐着轮椅从山洞前经过的画面。那一刻,我又在想,山洞有几个呢?
然而当我真的走在山道上,我又不务正业地开始胡思乱想。我会想,当年开凿这些防空洞的军人,他们去了哪里;我会想,那时这座山就是荒山,他们开凿时一定遭了不少罪;我会想,当年开凿山洞的人,怎么也想不到山脚下的大海边,会长出码头,长出港口……
父亲不在后,当我从漆黑的山洞前经过,很想矫情地尖叫,但我没有,尽管山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想叫。因为我知道,最疼爱我的父亲死了,我的矫情没人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