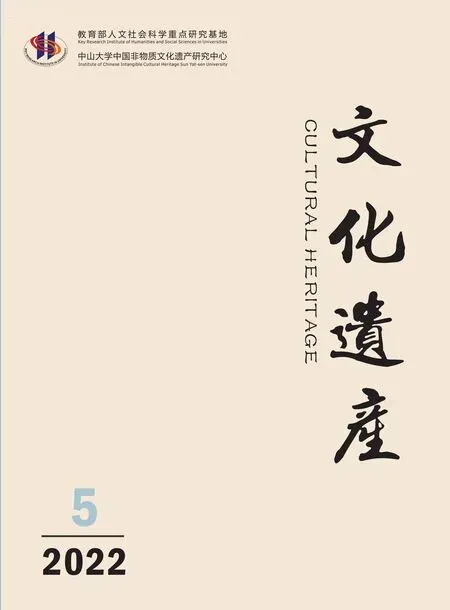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之“改”与“留”考辨
薛 雪
明人编纂的元杂剧选集,作为探析早期戏剧表演的重要文献材料,一直是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而李开先(1502-1568)有感于“元词鲜有见之者”而编订的《改定元贤传奇》,既以“元贤”为题,力图存元杂剧之旧貌;又经精挑细选、审慎改订,无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作品。同时,作为明代最早刊行的元杂剧选集,近人傅惜华曾评价:“此书实为《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后,时代最早之元人杂剧选集,重要异常”,亦充分肯定了《改定元贤传奇》的文献价值。
《改定元贤传奇》对于后来的选本,亦有着参考借鉴的意义,之前学者的研究中,已有人着眼于李开先的戏剧理论及相关戏曲活动,进行综合性的讨论,也有学者从文献校勘、选本比较等方式切入,屡屡提及后来选本在版式体制、改动内容上对其的继承性,如张倩倩曾评价此书“开启了文人选编元杂剧的先河,对万历时期的元杂剧选本影响很大”;孙书磊亦认为“《改定元贤传奇》在元明时期的元杂剧传播中发挥着轴心与中介作用,它促进了元杂剧体制的演进。”可以看到,此书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
《改定元贤传奇》的研究虽已有不少成果,但少有人注目编选者的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李开先在其间的平衡、取舍之道亦尚待考究。故本文以李开先的编选观念切入,结合具体的文献考证和文本分析,阐释编选者在 “观念”与“实践”之关系上的平衡与选择;尤其重点关注该选本“改”与“留”之辨证关系,以期考究李开先对待元杂剧的真实态度,进而深入探讨《改定元贤传奇》所承载的文本体制之典范性、编选观念之示范性,以及随之衍生出的戏剧史意义。
一
关于编选该书的工作和意图,李开先在前序中进行了细致的说明:
予尝病焉,欲世之人得见元词,并知元词之所以得名也,乃尽发所藏千余本,付之门人诚庵张自慎选取,止得五十种,力又不能全刻,就中又精选十六种,删繁归约,改韵正音,调有不协,句有不稳,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订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为“改定元贤传奇”。
他自称因有感于当时选集良莠不齐、杂乱参差,故自选藏本中的五十种准备予以刊行,又困于现实因素,精而又减,最后出品只有十六种。且从剧作题材类型、思想内容到改动的方式、规范,俱给出了详细的要求准则。不难发现,该书的编选原因和意图,一言以蔽之,即“欲世人之得见元词”;所据宗旨,乃不求其“全”而求其“善”,重在发掘元杂剧的文学价值,而“改定”之谓,亦不乏希冀后人效法准则之意。
同时,李开先在编选《改定元贤传奇》的观念上,还包含着很强的辨体意识。《改定元贤传奇》专门收录元杂剧,又言“俟有余力,当再刻套及小令。”明确对同为“曲文学”的杂剧、散曲进行了区分,正如李昌集所言:“《西野春游词》是散曲集,李开先提到的曲家皆是散曲家,均是证明,李开先对‘词’与‘传奇’的分界还是清晰的。”很显然,《〈西野春游词〉序》是针对散曲而言,《〈改定元贤传奇〉序》则专就剧曲而论,“散曲”和“剧曲”在体制形式上互相依存,却又是相对独立的。如此,在“以‘曲文学’的眼光视戏曲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之时,《改定元贤传奇》于“剧曲”文体上,标举元杂剧为典型,就含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有既定观念于前,其后的实践情况就颇值得考究,而元杂剧的整理审定,其重点必在对原有文本的“改”与“留”上。正如李开先在前序中所表露的那样,留存元曲旧貌的同时,还得有所规整、改进。由是,李开先在实际的操作中,如何处理、平衡各种矛盾,“改”与“留”之间又呈现出怎样的问题和关系,恰是焦点所在。
二
《改定元贤传奇》标明了“改”字,其中的“改动”部分,自然不可忽视。相关的标准要则,序言中就已明确点出:“删繁归约,改韵正音,调有不协,句有不稳,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订正之”,于曲词、宾白上皆有涉及。不过,李开先对于曲词部分的改动,虽在理念表述上以“改韵正音”为准要,讲究北曲声韵的格律轨范,实际操作却不尽然如此,故不少学者认为他对曲词的改订实不算多。反而是其中独具个性的改笔,更值得关注,且足以昭显他对元杂剧的态度和个人观念。
该选本所收《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杂剧第一折中的【混江龙】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此曲对扬州之美景极尽描摹:
a.江山如旧,忆昔歌舞古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红楼。绿水朱阑品玉箫,珠帘绣幕上金钩。淮南无比景,天下最高楼。
b.江山如旧,竹西歌吹古扬州。三分明月,十里红楼。人倚雕阑品玉箫,手卷珠帘上玉钩。维扬风月景,天下最为头。
c.江山如旧,竹西歌吹古扬州。三分明月,十里红楼。绿水芳塘浮玉榜,珠帘绣幕上金钩。维扬风月景,天下最为头。
这支曲在李开先《词谑》中亦有收录,与《改定元贤传奇》除个别字有出入外,基本无二。通过比较后可知,其他版本似在《改定元贤传奇》的基础上,进一步润色而成,且继志斋刊《元明杂剧》本中,该曲上方有批注:“此一折杨升庵重订”;同时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崇祯刊本中,亦有注文“此折系杨升庵重订,故后人混收入升庵《黄夫人集》内。其中间有异同,则出吴兴臧晋叔本也。”两条批语证实,曲中的异文部分确系再经后人改动所致。
在《改定元贤传奇》编撰前即已刊行的《雍熙乐府》,恰也收录了此折,可作为更早出的版本以供参证:
江山如旧,竹西歌吹古扬州。三分明月,十里红楼。人倚雕阑品玉箫,手卷珠帘上金钩。淮南风月景,天下最为头。
后出于《改定元贤传奇》的《元明杂剧》本,反而与《雍熙乐府》本所录最为相近,整体比较之下,“忆昔歌舞”“二分明月”“绿水朱阑”“无比景”及“最高楼”几处,当为《改定元贤传奇》本所独出的改笔。值得思考的是,这段曲文用韵上并无差缪,却被编选者们反复修订,既没有非改不可的缘由,也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选取一段溢美景色之词操笔,反是展露文采的空间大了许多。由此可知,几版的改动,乃是文人出于自我理解、表达自我感受的改笔。特别是“三分明月”一句,显然化用自唐人徐凝《忆扬州》名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独李开先取“扬州独占二分明月”之意,改作“二分明月”,虽然意义上更为贴切,且更具有文学性,但这番改动却无视杂剧作者的原本意图,编者难掩文人气质。
至于宾白部分,“删繁归约”“不切太泛”的标准皆可适用。通过比勘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出,在宾白的改动层面,李开先也投入了不少个人意志,如《青衫泪》第三折,借裴兴奴之口念出白居易的《琵琶行》:
a.门前冷落鞍马稀,慈亲逼作商人妇。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况是曾相识……满坐闻人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泪。
b.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满坐闻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古杂剧》本、脉望馆本及《柳枝集》本,基本是遵照《琵琶行》原诗搬用,不过逐一梳理下来,则能发现李开先的改动更合情理。首先,将“老大改嫁”改为“慈亲逼嫁”,对应前文老虔婆贪图重金,逼迫裴兴奴嫁人的情节;其次,裴兴奴所嫁的茶商刘一郎,当晚是因外出吃酒离船,而非为做生意出走,删去“浮梁买茶”一句,有效避免了剧情上的自相矛盾,相较于《元曲选》大段的删节,李氏选择性的减句,更贴近原作;再者,“相逢况是曾相识”紧密联系全文,剧中二人不仅并非初见,反而情意甚笃,“不相识”显然不合逻辑,更与该剧“悲欢离合”之主题相悖;最后,将“江州司马青衫湿”改为“青衫泪”,与题目相切,颇有画龙点睛之妙用。
从上述两个例子不难看出,李开先对剧本的改动,尽管附着了浓厚的文人习气,对剧本原有形态却影响不大。同时,他所判定的可改之处,多出于语言曲辞层面,关注辞藻修饰,虽难免有卖弄成分,倒也开启了从文辞角度整理元杂剧的先河。
三
戏曲剧本不仅具有文学性,其特有的舞台性更不可忽视。改动之外,李开先对于元杂剧剧本旧貌的留存,正体现出他对戏剧文体特殊性的深刻认识。赤松纪彦视《改定元贤传奇》在折、楔子、题目正名等体制上的不甚规范,为“元杂剧的古老特征”,与此同时,“……上开”“……住”等元刊本的常见用语,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保留下来,亦是值得考究之处:
(一)“……开”
元杂剧的“开”,孙楷第认为乃“脚色初上场时开端之语”,康保成指出“是戏曲演出时的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仪式”,昭示着脚色出场需要自报家门。在刘晓明《杂剧形成史》中曾论及:“ ‘开呵’一语在元剧中的使用目前可考者仅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明息机子辑《杂剧选》,其他元杂剧选本皆未见。”事实上,除上述两个版本,“……开”的句式于《改定元贤传奇》中也能得见,在《阳春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里,亦被部分使用。
整理相关剧作,“……开”在《改定元贤传奇》中出现共计8处,其出现的位置,一是位于全剧或每折起始之处,有引戏开场的功用,如《陈抟高卧》第一折开场处:“(冲末扮赵大舍引郑恩上开)”;二是在主要人物在全剧中初次登场或每折首次上场之处,即“人物上场时自我表白的按语”,用以自我介绍和叙述剧情。不仅如此,这时“开”出现的前文中,往往还包含其他人物下场的舞台提示,表明前面的故事已交待完毕,自此人物交替、虚拟的故事空间有所变动,故而“开”或许还兼具“转场”的作用,表示场面的转换并暗示剧情的推进,如《两世姻缘》第三折:“(酸戎装上开)……蒙圣恩除为翰林院编修。……自得官至于今日,早已十有八年……”,酸回顾过去经历的同时,故事时间也推进到十八年之后。
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没有明显标志,但《改定元贤传奇》中还存在类似于“开”,起到情节叙述功能的文字,借此交待出舞台上不便表演的情节,例如《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四折开场:
(小驾一行上云)寡人唐肃宗是也。自安禄山构乱,父皇幸蜀,驾至灵武,因父老之请,传位于朕,征天下兵马,东还破贼。安禄山被李猪儿赐死,郭子仪、李光弼等擒灭安庆绪、史思明等,余党尽除,廓清海宇,重立唐朝天下。百官大臣立朕为肃宗皇帝,迎父皇还宫,居于西内。今早问安回来无甚事,还后宫去来。(下)
这段描述明显与《玉箫女两世姻缘》第三折相似,皆是借角色之口讲述剧中人物的过去经历,却在后出的《元曲选》和《古今名剧合选》版本中被整段删去。由此可见,元杂剧版本的流变过程中,“开”的提示是在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的,正如陈容富所指出,从“开”字的保留,约略可以窥见《改定元贤传奇》相较于其他版本的古老性,而“开”作为元杂剧特定的表演形式,它的从有到无,也折射出编选者元剧观念的变化,但至少对于李开先而言,他是认可且重视此旧制形态的。
(二)“……住”
黄天骥曾关注到元杂剧中特有的“开住”一词:“初时不知所谓,及见杨梓《霍光鬼谏》始知‘开住’即开呵之后继续呆在场上”,以此类推,诸如“做……住”的句式,或也暗含着要求人物停留台上的指示意味。在《改定元贤传奇》中,“……住”的句式共出现5次,分布比较零散,没有相对固定的位置。
1.《西华山陈抟高卧》第三折:
(驾上科,)(末作入内科)
2.《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一折:
(卒报)(冲云)着他进来。
3.《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二折:
(做報)(正云)引他进来。
4.《玉箫女两世姻缘》第四折:
(驾云)宣来。(作唤旦上科)(云)妾身张玉箫……(入见驾科)
5.《玉箫女两世姻缘》全剧结尾处:
(帝君上队子)(云)(指旦末科)
其余版本中,或是改“住”为“科”“介”,如《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一折,卒子报告安禄山求见:“(卒报住)(冲云)着他进来。”脉望馆本、《古杂剧》本及《元曲选》本作“(卒报科)”,《元明杂剧》和《古今名剧合选》作“(卒报介)”。然后文仍有“(押净下)”的指示,表明在安禄山与张守珪对话时,卒子一直在场上,因此“住”仍是表达了停留之意。
或是直接删去,如《玉箫女两世姻缘》第四折,张玉箫被宣见驾:
(驾云)宣来。(作唤旦上科)(云)妾身张玉箫……(入见驾跪住科)
《元曲选》作“(驾云)宣来。(内侍唤旦科)(正旦上云)妾身张玉箫……(入见驾科)”,就直接删去了“跪住”的指示。但臧懋循的改法,实为不妥,因后文中驾令玉箫指认韦皋,仍有“(旦起认酸科)”的科介,表明此前旦的表演,都是跪着进行的,此处才会有起身的指示;另,后文中复有“(旦跪云)”“(旦扶酸背,做谢驾科)”等科介提示,因此旦的跪立与否,一系列动作提示都是清晰明了的,陡然删去反而不利于演出效果。
统观下来,早出的版本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原始舞台本的痕迹,尤以《元刊杂剧三十种》《改定元贤传奇》为典型,而比较晚出的版本,特别是《元曲选》中,几乎看不到这类句式的存在,可以说,剧本体制在逐步整饬的同时,与之相随的旧有形态,却也在不断消歇式微。
(三)收场下断
除上述两种舞台指示词,《改定元贤传奇》在剧本结尾也有不同面貌。顾学颉曾讨论元杂剧的收场情况:“元杂剧在全剧将结束的时候,照例由一个地位较高的人出场作断,对剧情作最后处理;然后念一首诗,或七字句的顺口溜,也偶有念词的。诗的内容是概括剧中重要情节,并含有褒贬判断的意义,很像判词,元刊本中叫做‘断出’或‘断了’”。正如其所言,“下断”的形式早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就可查得,《遇上皇》《东窗事犯》和《博望烧屯》三剧结尾处,即出现了“驾断出”、“断出了”和“驾断出(散场)”的提示语,因该版本中宾白大量省略,所以具体的文辞样式难以考证。不过在内府本杂剧中,同样保留了这一形式,可供参考。
着眼《改定元贤传奇》中,两剧“断”的呈现也并不统一,总结起来有两类:
一是没有明显标示的,即《江州司马青衫泪》结尾,众人拜谢完皇恩,正旦唱罢,题目和正名前有一段总结性的念白:
迁客那堪送客行,梧桐霜老楚江清。串头兰棹翻云影,帆尾秋风剪月明。邻画艇,近沙汀,琵琶谁拨断肠声。声声偏入愁人耳,道是无情却有情。
这一部分在其他几个版本中,都有所保留,但《元曲选》中却被完全删去,唱词之后直接就是题目正名,显然是编者有意为之。从内容上看,此部分除“邻画艇,近沙汀”一句,余皆为七言韵文,且内容基本涵盖了该剧的中心剧情,又全剧中皆未出现人物下场诗,因此是“下断”的概率更大。相似的情况,可参照脉望馆钞本《司马相如题桥记》中【尾声】之后出现的“下断词”:
杂剧卷终也。(外云)道甚。(众答云)瀛洲开宴列嘉宾,祝赞吾皇万万春。武将提刀扶社稷,文官把笔佐丝纶。
《题桥记》在结尾表达了对圣上的赞颂之词,或许是因为前文中已有“一起齐的拜谢君王”的部分,所以《改定元贤传奇》中并未在收场处继续“颂圣”。因剧本中并未给出明确的指示,故而不能断定是由哪个角色来完成。根据上文的内容,当有两种可能:其一是“驾”,既是内府本杂剧中较常用来“下断”的角色,又前文“驾”念白结束后,没有下场的标识,或许还留在场上进行这最后的表演;其二是“正旦”,在唱完【随煞】之后,脱离出剧情,作为局外人来完成这段表演。仍需注意的是,么书仪称《题桥记》结尾部分作“打散词”,参考孙楷第先生的观点,“打散词”可简略地解释为“表演结束后的总结散场之语”,又上述两剧文中皆缺乏“断”这一明显标志,称之为打散词或更为接近,此处还有待商榷。
二是借剧中开场担当冲末这一角色的人物之口,总结陈词,言语中有提及“断”,如《刘晨阮肇误入天台》的结尾:
(太白云)众仙近前,听我明断:紫霄仙谪来尘世,修真在桃源洞内。有刘阮心慕清虚,厌尘劳踪迹韬晦。当暮春采药入山,与二女夙有仙契。化白云迷其归途,指引他二人相会,成就了两姓姻缘。……再来时路径全无,何处认旧游之地。吾指引复入洞中,使仙眷依然匹配。三年后行满功成,忽一朝同还仙位。
这段话最明显的特征即是借剧中地位较高、身份尊贵的非主角人物之口,总结陈词、臧否人物,且言语中有提及“断”字。《元曲选》本将“明断”改为“嘱咐”,并增加提示语“词云”,明显忽视了“断”所暗含的特殊意义。参照脉望馆钞校本杂剧,则与《改定元贤传奇》有相似的情况,例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一剧结尾,也用到了非主角的人物汉钟离,同时文中有“断”字出现:
(钟离云)梅柳你二人今日成仙得道也,听吾下断:你本是人间土木之物,差洞宾将你引度,今日个行满功成,跨苍鸾同朝玉帝。
同样与《元曲选》做比较,臧懋循不仅将“听吾下断”改为“听吾指示”,更将这一段文字放到了【收尾】之前,完全忽视了“下断”的内涵。对比上述两例可以发现,两处“下断”的言辞形式和表现内容相似度颇高,又日本学者小松谦曾总结到“内府本中,全剧的最后,剧中身份最高的人物要念七言韵文(多为三四节奏)以终场,此称‘断’或‘断出’,为演剧的定型。”据此可以推断,《改定元贤传奇》中保留的正是“下断”这一体式。虽为旧制,但基于“下断”的特殊性,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改定元贤传奇》所用底本与内府藏本的渊源颇深。可以见得,保留杂剧结尾之打散词或下断词,用以梗概全剧,总结全文,一来留存了元杂剧的原始形态,二又可看作该版本源出于内府的佐证之一。
从整体来看,《改定元贤传奇》中多处保留“……开”“……住”及打散词等“古老”特性,实则意图保留剧本更为原始的形态,这是李开先元剧观念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它们既反映于剧本体制上,又可视作舞台表演的遗存,尤其《两世姻缘》第一折结尾出现的“吊下”指示,应是提示此处穿插了“吊场”的表演,作为意义较为明确、且当时仍被演出使用的戏剧术语,它们在后来的选本中基本都得到保留。而李开先的存旧之举是否表明这些旧制仍在当时的舞台上演,还有待考证。
四
如前所述,《改定元贤传奇》编选中的“改”与“留”,并非对立或割裂的存在,反而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它们作为有效可行的方式和手段,共同服务于《改定元贤传奇》的“定型”,使其可以成为李开先心目中理想、规范的元杂剧选本,并最终作为一种创作范式,呈现于世人面前。
其实,李开先作为编选者在“观念”与“实践”上有着平衡与选择的综合考虑,这也反映出他对待元杂剧的真实态度:语言文辞的层面,不合乎剧情、不利于排场的部分,是可以执笔添改,倾注个性情感的。编选工作本就是对剧本的“二度创作”,文人参与元杂剧的整理,也是他们个人意志介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改定元贤传奇》的剧本内容更加充实、体例渐趋整饬,虽然附着浓厚的文人参与感,却不失为一种推进,更是元杂剧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从“曲无定本”到“曲有定本”的必然趋势。
至于体制形态的层面,尤其是有涉舞台表演的部分,则是需要保留和遵循的。元杂剧实乃“舞台艺术积淀”的文本,这些被留存的“古老特征”,突出了戏曲兼具案头场上的文体特性,也是它与散曲分界最著之处。由此,愈加凸显了李开先的“辨体”意识,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剧”的本质。对元杂剧旧制的重视,也正是《改定元贤传奇》这一版本的价值所在,可以说,它就是继《元刊杂剧三十种》之后,比较能反映出元杂剧旧有形态面貌的选本。
还需注意的是,作为明人最早刊行的元杂剧选集,《改定元贤传奇》的编者在力图存旧的同时,还会有意识地对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在此过程中又难免掺杂上个人的情感偏好和思想观念,更会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化风气所困囿;虽于体制上有所精进,仍然疏漏多出、不甚完善,所以它并非元杂剧在不断改造后的“完成形态”,而是此过渡进程中的一环,上承《元刊杂剧三十种》所代表的旧制,下启文人改本的“个性”与“兼容”,它所反映的,恰也是元杂剧体制不断演进完善的轨迹。
与此同时,《改定元贤传奇》对后来的编选者多有影响之处,而这番影响不限于体制、内容上,还兼及编选观念和对戏曲尊体的认知上。纵观后来的元杂剧选本,在选剧上多关乎教化,凡有序者,常以悉数历代文体起笔,至元则尊倡词曲,此式正肇始于《改定元贤传奇》;在编选的目的上,息机子称“词曲不有独收其功者乎,焉得小之,刻之以传可也。”王骥德则感慨“而独元之曲,类多散逸,而世不尽见。”同样在突出元杂剧之重要性,又皆对李开先“欲世人之得见元词”有所映射;而黄正位《凡例》中所述“是编也,俱选金元名家,镌之梨枣”、“曲中折白等语是皆金元习音,不必求其洞烛。若以己意强解,至或妄易佳句,反失其真矣。今尽依旧本改定”,亦是承继于李开先对“金元之旧”的重视;而后的选本,则在李开先的基础上深入阐发,臧懋循《元曲选序》中的“名家”“行家”之辩,孟称舜提出的“学戏者,不置身于场上,则不能为戏;而撰曲者,不化其身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此曲之所以难于诗与辞也。”这些切乎舞台的表述,于观念层面,反映了一种从“曲本位”到“剧本位”的演进趋势,凡此种种,也正不断推动着元杂剧的经典化。
总而言之,《改定元贤传奇》的编选,无疑体现出李开先对元杂剧的认识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他能在思潮并起、各家争鸣的环境中先声夺人提出“词必元声”、重乎“本色”等重要观念;又率先认识到“元杂剧”重要的文献和艺术价值,编订《改定元贤传奇》一书作为轨范。而选本之“选”,本就附着了文人的意志,此般精心的编辑工作堪称开风气之行为。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既以“本色当行”为标尺,维护元杂剧文本形态之旧制;又通过种种选定、删改,渗透出文人“个性”,对后来的元杂剧选本皆有深刻的影响并,最终奠定了《改定元贤传奇》在元杂剧经典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