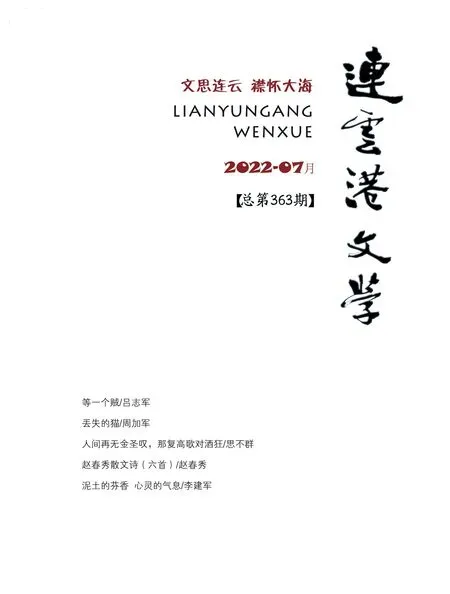人间再无金圣叹,那复高歌对酒狂
思不群
“才名千古不沉沦”
有次与一位诗人聊起海子,我问他对海子了解多少,他答道:“不就是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卧轨自杀的那个诗人吗?”我不禁哑然。海子短暂的一生写有精纯短诗三百多首、长诗数部,但人们匆匆略过这些,只记住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一个把他带向惨烈毁灭的悲剧。我想起金圣叹曾说过:“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这便如品尝佳肴,满盘珍馐,但在颟顸之徒嘴里,狼吞虎咽之后,最后只落得几块形状奇特的骨头和鱼刺而已。而这几块骨头和鱼刺,就是他们一直所津津乐道时向人说起的,他们愣是把一个悲剧看成了喜剧。命运之乖谬无常如此。
金圣叹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命运乖谬无常之人。
“先王礼法,千秋万代不可毁弃”这是金圣叹,而任情肆志、跣足上床纵酒狂也是金圣叹。
“受父母身,读圣贤书,上承圣君,下寄苍生”这是金圣叹,而“高才负气人以身世为儿戏”也是金圣叹。
“生平唯服浣花堂”这是金圣叹,“千金散尽还复来”也是金圣叹。
虽然距今才三百多年,但他的面目已然模糊。当我们深入他一生在世俗功名和自由放诞之间的挣扎、犹疑,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真身:前世原是李杜身。他的生活仿佛同时有两个副本,对位着一李一杜的人生遭遇。
“子美篇篇老,陶潜顿顿饥。”金圣叹素所服膺者是杜甫,自少年时起就醉心于杜诗,并以毕生之力评点批阅,但并未完成。他的族兄金昌说:“余尝反复杜少陵诗,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经(即金圣叹,其堂号名唱经堂——引者注)不能批也。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万倔漩陀罗尼三昧,唱经亦如之。”所谓隔代知音,千年一遇,大约便是如此。金氏对于杜诗的爱好几至痴迷:“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日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两颗高贵的心灵一经相遇,便须臾不可分离,反复其间,可谓至乐。
金圣叹从杜甫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忠而恕的典型文人形象,实际上随着人生遭遇的展开,他发现自己的身影渐渐与杜甫叠合,仿佛是在杜甫身上生活,这从金氏所作《妇病》《忆舍弟》《乙酉又病一首》《宿野庙》等诗题即可想见一斑。而且为了能与文朋诗友日夜谈宴,中年以后金圣叹也想仿杜甫造一草堂。杜甫建草堂乃是“集腋成裘”,东家借花西家求树,而草堂得以建成,还得感谢他的表弟王十五的资助,为此他专门写下一首《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屋赀》。巧的是金圣叹他也有一表弟,名叫崔由甲,听说此事后慷慨解囊,玉成其美,沉吟楼遂得成。为了答谢表弟的高情厚谊,金圣叹以同题仿杜作诗一首以为志谢:
生涯丁此日,吾道在江边。
直为林塘好,非求卜筑偏。
城中盛冠盖,表弟独哀怜。
不特存衰老,兼能割俸钱。
不仅如此,金圣叹越读杜诗,越感觉杜甫后期贫病交加的悲惨命运,仿佛从杜诗中度过漫长的时间之河游了过来,在自己身上重现。而立之后,金氏大多时候都陷入困窘之境,不时为衣食之忧所掌握。屋破家贫,缺薪少炊,妇愁儿啼之中,他除了抚膺浩叹,又能如何?当然,可以稍感宽慰的是,不时有三五知己送来少许生活之需,《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辛巳大饥无动惠米志谢》等诗作,生动记录了家无米炊时,对朋友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然而,生活悲愁、没有出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些苦闷一直折磨着他,以致他在《庚子秋感》一诗中写道:“乱世黄泉应有路,愁人孤枕总无情。起来掻首忽长叹,一院霜华太瘦生。”寒屋清冷,孤枕难眠,前路难寻,一种绝望、悲凉之情,如霜华月冷,满院而生。
在悲愁的另一面,是金圣叹在文学世界里的自由腾挪,指点星辰。以一己之力评点天下六才子书,虽未完成,但其才情,其胆识,其风骨,其眼光,已经展露无遗。然而,用笔挣来的才名不仅没给他带来荣耀和官位,相反,世人争相贬责,甚至斥骂,视其为荒谬不经之徒。甫一转过身,金圣叹忽然从镜子里发现自己由杜甫变成了李白:“才名千古不沉沦”有之,“拔剑四顾心茫然”有之,“人生在世不称意”亦有之。“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一十八地之下而后已。”在金圣叹死后,与他同时代的归庄仍撰《诛邪鬼》一篇,指斥金圣叹,并称“但恨杀之不以其罪”,仿佛金圣叹一死仍不能一泄其恨。这岂止是“世人皆欲杀”,其文恨不得要掘坟鞭尸,方解其恨。正所谓“才高造物忌,行僻俗人嗤。”在那些正人君子之流看来,金圣叹不入正道,惑乱世人。所以金圣叹身后除了在三五知己诗文中留下些许痕迹,在官方记载、史传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他的文字。这是一个被主流官场、文坛遗忘的人。而金圣叹也掉头而去,自觉地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把自己放到那自由世界里去。世传金氏被黜之时笑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有人问:“自由身”出自何处?金答:酒边多见自由身,张籍诗也;忙闲皆是自由身,司空图诗也;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诗也;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诗也。即是说广大世界,人间百事,但无公事羁绊,无处不得自由身。李白高唱:“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而金圣叹也在《水浒传》第十三回总评中写道:
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
任你是文曲星下凡,任你是笔底夏花开,而终究一切都是幻梦一场。于是李太白睥睨权贵,侮辱佞臣,贵妃磨墨、力士脱靴是其化用;而金圣叹设学社、立讲席,“遇贵人嬉笑怒骂以为快”,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则殊可叹惋。
“一样疏狂两个身”
西晋张翰羁縻官宦中,忽忆家乡莼菜和鲈鱼之鲜美,他想“人生贵得适意尔”,于是毅然弃官归乡。“适意”在苏州话中表达的是一种自在自乐的生活状态。作为吴人,金圣叹一生同样努力追求一种适意的生活。
一日,金圣叹与好友王斫山在客舍中闲来无事,各自斜倚卧榻,说及人生苦短,殊少乐事,不由感叹。好作怪谈的金圣叹却提议道:“我俩何不苦中作乐,寻出点人生快意之事?”王斫山欣然同意。金圣叹张口即来:
“於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王斫山却也毫不示弱:“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箧中无意忽检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还债毕,不亦快哉!”
“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刚说完,王斫山仿佛忆起什么,问道:“斫山曾以三千金与先生,以大钱生小钱,大钱仍归我,小钱与先生做灯火费。如今,一月有余,灯火费攒得几个?三千金该还我了吧。”
“三千金早已送与酒家掌柜了。此物在君家,只是平添一个守财奴的名声而已,我已代你把它处理掉了。”王斫山先是一愣,听他说完,二人一起大笑,齐声道:“不亦快哉!”
金圣叹一生好作“不轨之论”,言谈荒诞不经,不入绳轨,显露出他个性中疏狂怪诞的一面。他在《西厢记》评点中一气写下的“三十三不亦快哉”,可谓是真性情,有大趣味,以自由狂狷的无间之思,入愁闷无绪的现实之身,于是“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神游万仞,而自由神在。这“三十三快哉”于己有何用?无用。于世有何益?无益。这就像夏夜中闷热无绪于是去捉萤火虫,一只一只捉来,也无甚用处,但在暗夜中,荧光亮闪,便觉这夜晚不一样,睡梦不一样。他在《杜诗解》中曾说:“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唯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可见,他的狂与怪,不过是要在憋闷的“铁屋子”中,以放诞自适之古怪,打开一窗扇,以供自己自由呼吸,聊以慰己,直言之:一种精神性的突围而已。据说比金圣叹早生十四年的“铁笔”王铎曾在一书作中连写三个“不服”,这是他用笔底的墨汁纵逸而出的纸上呐喊。金圣叹亦善行草书,但其书迹流传甚少。清人评其一纸本楹帖“字大如斗,气势惊人”,今已不传。从其现存仅见的“雨入花心自成其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墨迹来看,似乎规矩笼罩住了他的个性,放逸之气仅显露出一二分。而与王铎所为颇可相比附的,是在一次以“吾四十而不动心”为题的科举考试中,金圣叹连书三十九个“动心”,考官不明所以,金圣叹曰:“孟子曰四十不动心,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不循常理的思路,不行常道的作为,其实无非是要寻找一个解脱的出口,逸出传统的轨道,偏向个性之境。尤其是明清鼎革之后,他更加绝意仕进,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被一种一切皆虚妄和人生无常的意识所捉住,幻灭感总如夏蚊在帐,不远不近,时时来袭。他在《水浒传》第五回借题发挥说道:
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
此语实在沉痛,悲凉,正如“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而一切最终都化作梦幻泡影。
要走出这梦幻泡影,只能向内求,自求解脱,得其自在。好友徐增说他“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当狂与怪都被现实碾平,他便向酒寻求安慰。酒的好处是,它能从冰凉如水,化作炽热如火,它并不把那些无处宽解之情封闭在体内,而是以热力将它蒸发出去。“先生饮酒,辄三四昼夜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高谈,戏谑,酒精燃烧尽胸中之不满和压抑,那些脱离束缚的诗句、话语,便得了大自由,大快活,如群羊出圈,小鸡出笼,在自由广阔的大地上生龙活虎地奔跑,金圣叹是其中最领头的一只。
在郁闷又释放之后,他便抵达纵浪大化之境,池边林下,或批书,或高卧,浑然无我,弃绝执着。他化作了黄昏时分天上的晚霞,他是万物,但又不是万物。人见金圣叹,如见晚霞。好友徐增有一段话说金圣叹:
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迎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者,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
即是说,金圣叹有了佛性,广大无边,你见如来,所见皆自己,人见金圣叹亦如此。是木讷无言,是啼笑宛然,是剑舞随风,他都为你照见,为你一一映透出来。
“一生惯作惊人句”
金圣叹曾把儿子金雍称为“读书种子”,其实他本人更是天生一粒读书种子,它拼命伸展开千万根触须,深入泥土,吸着雨露,知热知冷,知雨知雪。春之花,夏之风,秋之叶,冬之雪,无一不成为营养,无一不助其丽词妙语,随笔而出。十岁入乡塾读书,也曾发愤努力,以功名为念,他曾回忆:“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诗书读毕,红日沉落,窗前一片苍茫,时间的恍惚和匆忙,内心的充实与沉迷,浑融于夕光之中。虽寥寥数语,但意境悠远而情味深厚,让人瞬间闪回年幼时的旧梦之中,既温暖又怅惘,既怀想又嗟叹。
唐诗人中,杜甫之外,金氏对李商隐颇有会心,晚年他在评点义山《曲池》一诗时,突感一阵怅惘之情、伤感之绪袭上心来,瞬间掉入追忆之中:
某尝忆七岁时,眼窥深井,手持片瓦,欲竟掷下,则念其永无出理,欲且已之,则又笑便无此事。既而循环摩挲,久之久之,瞥地投入,归而大哭!
怜惜一片瓦,以同怀视之,不能不说是痴;而久久徘徊踌躇于扔与不扔之间,乃至“归而大哭”,显现出内心的柔软与脆弱,也颇让人惊异。这不仅仅是早慧,其间有一种超群的感受力。当这种突出的审美感受力与文章相遇,如金石相击,于是火花四射,青天白日之当午,一记闪光照出白纸黑字之灿烂、丰赡。而感觉敏锐之人,往往怀有旷世之深情。这深情如舞台上之灯光,照彻一片,人物之内心,细微之表情,无不纤毫毕现。因此,其感觉皆异于常人,见他人所未见,悟他人所未悟,往往先人一步,直取真谛。
在《水浒传》第六十一回“燕青说道:‘……故此忍这残喘,在这里候见主人一面’”下金圣叹夹批道:
只二下余字,已抵一篇豫让列传矣!读此语时,正值寒冬深更,灯昏酒尽,无可如何,因拍桌立起,浩叹一声,开门视天,云墨如磨也。
刺客豫让誓死报恩于智伯,不惜毁尽形貌,拔剑自刎;燕青虽为浪子,但对主人卢俊义忠心不二,即使卢已家破人亡,也追随左右。金圣叹感这二人之侠肝义胆,高情厚谊,心里灼热感叹,可惜手边无酒,胸中之感叹无从抒发,于是不由拍桌浩叹,浩叹之不足,更要“开门视天”,畅其胸怀,让灵府内的涌动之气息与天地交相往还,彼此应答。然而,“云墨如磨”,黑暗深厚,一笔下去,拖也拖不动,又不胜其悲。一面对天浩叹,一面又悲愤莫名,此情此景,真如他自己所说的“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者也。”文学之魅力即在于此,欲死欲生,方死方生,死死生生,其间痛苦与至乐,迷思与竦悟,该会在敏感的心灵上掀起多少波涛,让一颗心经历多少上下起伏。如此,真可说金圣叹是前人知音。
但他不仅仅有感受力,体会得到,而且他还说得出。他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己,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质而言之,诗是真性情的流露,是“血的蒸汽”,老妇之痛哭,幼儿之欢笑,本质上都是诗的。而对待这些内心的真情抒发,便不可轻慢,而应以知音的方式去靠近、体会、感悟。但人们往往只挑出一二可笑可乐之事,口口相传,实难称得上是知音之赏。所以他在评点《水浒传》时:“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比金圣叹晚出生约一个半世纪的歌德有一段话与此相类:“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明珠暗投,天才埋没,这是最令人痛心之事。浩瀚无穷的文艺作品和作家如同天上的繁星,气象万千,时移事易,只有伟大的星相家才能凭借智慧和识见敏锐地识读出那些“恒星”,确定他们的位置,让他们在人类精神的夜空上永远闪耀。对于七言律诗,他曾指出:“律诗在八句五十六字中间空道中。若止看其八句五十六字,则只得八句五十六字。”这并非重弹“意在言外”的老调,实际上它还触及到了诗歌的建行和分节问题。强调律诗在“中间空道中”,即是说诗歌之建筑形式是诗意产生之一部分,它同时是一种表达,会实质性影响到诗意的生成。这是完全现代的诗歌观。
金圣叹的这些奇思妙想,常常是兴到之物,灵光一闪,很多就写在书页背面、空白处,唱经堂墙壁,贯华堂柱上,还好他的儿子金雍把它们整理出来,没有散佚,这真是后人的福分。金圣叹用一枝长锋湖笔,日夜批阅,时时拂拭,扫去沉积在那些珠玉之词上的灰尘,让它们散发出原有的光彩,照亮那些浑浊、灰暗的世人之眼,让他们看到花纹之美、音节之响,感到心中有东西在蠢蠢欲动。关于《水浒传》武松打虎一节,常人只看武松拳脚的精彩,惊喜于老虎死而英雄生的快意,金圣叹却越过这些表面热闹,深入文本之中:
我尝思:画虎有处看,真虎无处看;真虎死有处看,真虎活无处看;活虎正走,或犹偶得一看,活虎正搏人,是断断必无处得看者也。乃今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副活虎搏人图来,今而后要看虎者,其尽到《水浒传》中景阳冈上定睛饱看,又不吃惊,真乃此恩不小也。
这段话,说尽了文学和世界的关系,文学是一种创造,作家以自由的创造精神为众人造出一世界,而这世界之真实与否,实乃作家对于世界的一个莫大馈赠,它超越时空,超越真假,让人在一个绝对自由的世界里漫游,耽于美的享受。接着他又说:
耐庵何由得知踢虎都必踢其眼,又何由得知虎被人踢便爬起一个泥坑?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奇绝,妙绝!
圣叹真了解文学,真了解作家,在许多人还在争执作品之似与不似之时,他却高屋建瓴,一脚迈过,直接进入现代人关于文学的一个共识:文学写的是未必实有、但却应有之事,即是说它写的是理想世界,而并非现实世界,它是精神引领之物,而并非仅仅摹写现实。这就把文学拉到了理想的高度,远远超越了话本小说、白话小说只是供人娱乐的定位。金圣叹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先锋性,远远超越同时代人,跨入了近现代的大门。这种境界,这份识见,甚至当今一些作家、读者都未必比得上。
“广陵孤客不胜悲”
1661 年,因参与苏州哭庙抗粮事件,金圣叹被清廷杀害。同死者共十七人,多为吴中士子。金圣叹之被杀,原因很多,既有当时清廷为杀一儆百杜绝吴中读书人妄议朝廷的原因,也与金圣叹平时率性臧否人物、褒贬权臣有莫大关系。而究其更深远的背景,则是前述金氏为人为文之狂与怪,不入俗流,为正统人士所不容,从而将他一步步推至危险境地。不仅仅金氏,有明一代,徐渭、李贽等等的命运大抵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圣叹之死与嵇康有一定相似之处,死于文章,死于言谈,而其理由在嵇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在金圣叹则是冲撞惊扰了先帝之灵。金氏亦善抚琴,当他洒然挥手,并吟出“四壁众山通夜响,广陵孤客不胜悲”之诗时,他是否有过嵇康的命运会重临自身的预感?其悲剧命运,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非才之难,处才之难。”在被捕后,金圣叹曾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可见金氏于文学是火眼金睛,于政治则是懵懂无知,或者说太天真,直到此时他还认为自己是“无意得之”,不知道自己在才名显露的同时,也早已被清廷盯上,视为目中之刺。
同年,7 月13 日,哭庙案犯在南京被斩。清代顾公燮所撰《哭庙纪略》对刑场有如下描述:
是时,四面皆披甲围定,抚臣亲自监斩。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一人皆毕命。披甲乱驰,群官惊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一百余字,而刑场上那种紧张、血腥与悲郁之气恍然可感。那一摊热血化作一种坚定的意志,肆意横流,深入大地和山河,并隐隐汇入了几百年后民国志士的铁血之中,最终将清王朝的铁桶江山瓦解。我想起了在此一百多年后,同样是在古老的俄罗斯也有一次著名的行刑。那是1849 年4 月俄罗斯彼得拉舍夫小组成员因反对农奴制度、要求进行改革而被逮捕,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8 个月后,他们被带往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第一批囚犯已经绑在了行刑柱上,当射击队抬枪瞄准的时候,虽然明知自己是下一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切地感觉到那些枪口的黑洞正对着自己,越变越大,巨大的吸力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吸进去。然而,奇迹发生了,在行刑前一刻,有人传达了沙皇特赦的赦免令。虽然尼古拉一世一生劣迹斑斑,但至少这一次多少为他在历史上挣回了几分。没有他的赦免,也就没有后来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神殿,就缺少了最厚重、最有价值的那根石柱。同为古老的帝国,同为多灾多难的大地,然而因了文化遗传基因的不同,在古老的东方没有这种幸运,我们也就至今没有产生属于本民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时至今日,在苏州已经很难找到与金圣叹有关的遗迹了。相传其故居为古城内马医科巷北海红坊六号。清代广东人廖燕慕其名,曾“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今年初,笔者往访其地,则已成为姑苏区特殊教育学校,并未留下任何与金圣叹相关的提示。巷子已经粉刷一新,但仍掩不住清寂之感。这是对的,如金圣叹那般的灿烂文章,锦绣文才,只能在寂寞中产生,有大寂寞才有大欢喜、大悲痛,才有“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自古皆然。这是一个非常逼仄的小巷,与此类似的巷子在苏州古城内有数百个,它们大都幽暗、狭窄、深藏,除了该处的住户,少有人至。而就是在这样的小巷子里,在那木格窗下,孕育了金圣叹这样的才情之士。他们的幽愤、心思和命运也如这些巷子一般暗魅、深长、曲折,常人难以看清,也少有人愿意去探寻。
金圣叹现存唯一的遗迹,是位于苏州五峰山下西山坞的墓碑,深陷在乱木杂草之中。据民国时期李根源所著《吴郡西山访古记》,碑上原有清代吴荫培书“清文学金人瑞墓”七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毁,今已不存。李根源还写道:“时坞中杜鹃盛开,有红、紫、黄、白四种,灿烂悦目”,想来当时此地乃是一清幽之地,而花之灿烂正如金氏之锦绣文章,开时灿烂鲜美,谢时落英缤纷。现墓碑为1986 年所立,上仅书“金圣叹墓”四字。四周灌木丛生,草莽纵横,方圆数里俱为苍郁所覆盖。藏在这么幽静的地方,可谓大隐。金圣叹当年赠诗给友人曾写道“爱君便欲同君去”,而他最爱之“君”无疑是诗文,是他的评点,如今他真正随这些文字而去,他可以坐在山脚下,心无旁骛地去批他的才子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