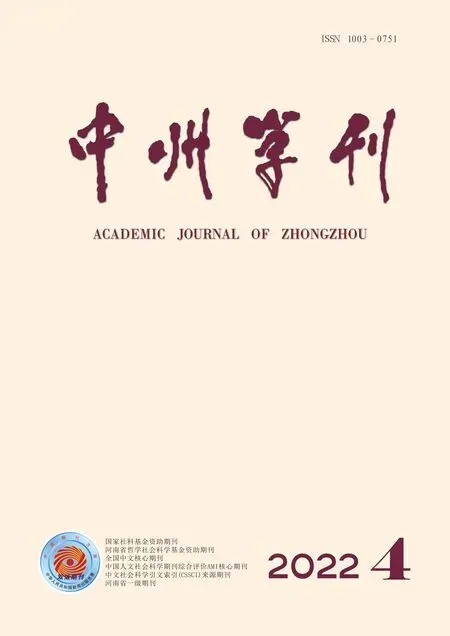共同富裕与税收公平*
——亚当·斯密与罗尔斯税制理论的当代启示
李 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目标。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将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的试点,计划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会议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些政策决定表明,共同富裕不仅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分配模式,也是现阶段国家发展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与税收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如何设计出优良的税收制度,在市场分配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是我们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聚焦于税收制度的公平性问题,讨论在税制设计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我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提出具体的建议。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税收公平
我们说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么,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共同富裕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一张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安全网。在这张安全网中,无论人们如何不幸,都不会落入忍饥挨饿的境地,都不会没有学上,都不会没有房住,也不会没有钱看病。第二,一个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存在贫困的代际传递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人们出生的起点就决定了其竞争之终点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没有上升空间、没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而要保证社会的流动性,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使得出生在社会中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能够有大致相同的机会去竞争社会中的较优位置(较好的教育机会、晋升机会、较优的工作岗位等)。而保证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机会平等的基本条件是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尤其是覆盖发展程度不同地区(例如农村和城市)的优质的公立教育。机会平等的维护显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化的私立教育。因为,私立教育是付费教育,只会拉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缩小这一差距。第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因此,自由市场一定要发挥其核心作用,主导资源的配置。然而,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尤其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由此看来,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并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
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么,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税收和慈善是两种不同的再分配机制,分别被称为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税收是强制性的再分配,而慈善则是自愿的再分配。当然,大部分公民都是自愿交税的。所谓税收的“强制性”指的是,如果某人不交税的话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我们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要同时借助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但主要依赖于二次分配。原因有三点:第一,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慈善取决于捐助者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关企业的营业状况等因素,大多是一次性或短期行为,很难保证持续的捐赠。相比之下,税收由于是强制性的,通常能够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第二,慈善捐助者并不一定能够将财物捐赠给最需要的人,捐赠者可能为了名誉而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例如,英美最知名的高校也是接受慈善捐赠最多的高校,但这些高校并不比其他高校更需要这些资金。与慈善不同,税款的使用则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支出统筹安排,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公立教育的建构。第三,慈善是由资本主导的,捐赠者捐助的财物越多,对社会的影响力越大。但资本的意志并不一定能够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慈善业过于发达可能会左右政府的决策,有将政府演变为富人政府的危险。相反,税收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能够更好地限制资本,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基于上述三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税收公平、加强税制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建设。
税收制度是国家的核心政治制度之一。税收不仅是一个国家之政府维持运转的资金来源,也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全民的优质公立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个公平而有效的税收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对于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来说,公平是不可或缺的价值。无论一种税收制度如何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如何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如果这种税收制度是不公平的,人在相应的税收安排中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那么这种税收制度就是需要改进的。正是由于公平对于税收制度的重要意义,在税收理论建构之初,税收公平问题就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野。下面,笔者结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和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对公平问题的讨论,探讨“税收公平”的确切含义,并揭示“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
二、亚当·斯密论税收公平
17世纪中叶,在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人们就已经开始探讨税收公平的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等著作中阐述了自己对税收公平的看法。威廉·配第认为,所谓“公平”就是税收要对任何人、任何东西“无所偏袒”,应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能力征收数量不同的税,而且税负也不能过量。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思想,在《国富论》中进一步阐发了税收公平的含义。在亚当·斯密看来,税收应该由所有国民共同承担,他反对贵族的免税特权。而且,税收应该由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个人收入共同负担。在具体的税收额度上,应该按照自然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同比例税率征税。亚当·斯密将自己关于税收公平的理论总结为平等原则,并将其作为四种税收原则的第一种原则。他论述道:“一国的国民,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一个大国的各个人必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商所收益的比例提供他的管理费用一样。所谓的税负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
亚当·斯密对税收平等原则的规定一直延续到当代讨论之中。当代学者将亚当·斯密的税收公平思想总结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指的是:条件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的是:条件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然而,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说法是含混不清的,这两条公平原则只是大概指出了支付能力强、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优势的公民应该承担较多的税负,而支付能力弱、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劣势的公民应承担较少的税负。至于这种多、少是绝对差值还是比例差值,收入极低社会成员是否可以不承担税负等具体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然而,这些细节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都将成为有关税收是否公平的焦点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回到亚当·斯密,探究他是否对税收公平给出了具体的、可量化的规定。
亚当·斯密在讨论税收的平等原则时,对于何谓“公平”进行了确切地规定:在具体的税收额度上,应该按照自然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同比例税率征税。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规定。依据这一论述,税收制度应该在搞清楚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即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财产)的前提下,按照同样的比例对所有人征税。例如,如果A所拥有的财富总量是1万元,而B所拥有的财富总量是100万元,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征税,假设税率为3%,A就应缴纳300元税款,而B则应缴纳30000元税款。
亚当·斯密如此设计税收公平原则,有两个论证理由。第一,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国家和政府,所有人都从这一政治结构中获益,所以人们有义务共同承担维持这一政府的各种费用。在亚当·斯密著书立说的时代,社会契约论正流行于西欧各国,亚当·斯密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因此,他对税收公平的讨论与社会契约论对国家和政府的理解是一致的。依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缔结契约组成国家,其目的就是要获得国家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不仅包括对人们生命的保护,还包括对人们财产的保护。同时,对人们生命的保护意味着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以集体之力为人们生命的延续提供各种必需品。正是为了筹集资金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保护和必需的生活条件,税收制度才成为一种必要的、合法的政治制度。依据这一推理,在确定谁应该缴纳多少税款的问题上,公民从国家获得的保护越多、受益越多,应该缴纳的税款就越多;而公民的财产越多得到的保护就越大。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应该按照财富的自然分布状况,向所有公民同比例地收取税款。这种对税收的解释也被称为税收制度的“利益说”,与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一脉相承,霍布斯、亚当·斯密、卢梭等思想家都曾阐述过这种理论。第二,税收平等原则依据人们所占有的财富征收同比例的税收,这一原则没有偏袒任何社会成员,是一个中立原则。人们通常认为,一种规则如果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参与者,那么它就是一种公平的规则。亚当·斯密给出的税收方案正是这样,这一方案将依据人们的财富状况以同等比例收取税款,无论人们财富的是多还是少,都缴纳同样比例的税收。从绝对数值来看,富裕者缴纳的税款多,贫穷者缴纳的税款少,但比例是一样的,这就是一视同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税收方案不会改变社会财富的自然分配状况以及贫富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同比例税收的方案是最尊重自由市场的税收方案,同时也就是最尊重人们自由的税收方案。可以说,在亚当·斯密建议的税收方案中“平等”和“自由”两种政治价值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从上述两方面看,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确实有平等待人的“公平”特征。然而,出于两个方面原因,亚当·斯密最初给出的税收公平方案却是欠公平的。下面,我将结合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具体分析亚当·斯密的税收公平理论的两个问题。
三、约翰·罗尔斯论公平合作
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要求依据社会财富的自然分配情况,同比例地征税。出于下述两个原因,这一原则有可能偏离真正的公平:一是对于非常穷困的社会成员来说,缴纳税款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二是中立的税收制度是否公平依赖于市场的初次分配是否公平,而后者的公平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保证。
第一,如果对所有公民依据其所拥有的财富(收入+财产)同比例地征税,那么,对于一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公民来说,这样的税收就会危及他们生命的延续。假设,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非熟练工人,其每月收入都必须用于养家糊口,这时如果政府还要从其微薄的收入中收取一部分税款,那他就会被逼到崩溃的边缘。依据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如果一个人通过一份全职的工作,其税后收入还不足以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那么这就违背了人们最初缔结社会契约的初衷。保证每个公民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不应该被看作完全是公民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下去的必需品,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缔结社会契约进入社会,也就不再对他人和社会负有任何义务;相应地,也就不应再缴纳任何税收。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le Walzer)所说,对于社会契约的准确解释是:“它是一个对成员的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协议,它依据的是成员们对其需要的共识,随具体的政治决定而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契约是一个关于如何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约定。在共同体成员对何谓“需要”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社会分配必须首先满足每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因此,如果一种税收制度危及某些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丧失了合法性,就是不道德的。
实际上,所谓同比例的税收对于财富量不等的社会成员来说,其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对于拥有的财富量越少的社会成员,其影响越大。例如,对于一个月收入10万元的白领来说,上缴其收入的10%作为税款,并不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工人来说,上缴其收入的10%的税收就将对其生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由此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税收平等原则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税收制度不能危及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获取,不能毁掉穷苦者的生活。因此,在亚当·斯密所说的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至少应该加上一个“起征点”的限制;亦即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收入+财产)在某一起征点之下的社会成员应该免除税负。而且,从税收对于财富拥有量不同的社会成员的福利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角度来看,真正公平的税收应该是累进性质的,而不是同比例的。
第二,亚当·斯密的税收公平理论的显著特征“中立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平性。税收制度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保持中立,这是亚当·斯密对公平性的阐释,体现了他对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尊重。然而,将“中立性”等同于“公平性”的必要前提是:自由市场对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公平的”。因为,只有当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公平的,按照社会财富的自然分配同比例征税才可能是公平的。如果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本身就混入了不公平的因素,那么对自由市场的尊重并不能维护社会合作的“公平性”。然而,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却往往并非公平。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对社会合作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罗尔斯将包括生产、销售、分配等各个环节在内的自由市场看作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合作形式。在这种合作中一些人获利多,一些人获利少。罗尔斯将获利较多的一方称为“禀赋较好者”,这些人通常有较多的财富、权力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好的“禀赋”使得他们在社会合作的议价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能迫使社会合作的条件偏向自己一方。相反,在社会合作中一些人获利较少,这源于他们较低的议价能力,这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少、权力小,社会地位不高,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劣势。事实上,亚当·斯密对于自由市场中广泛存在的议价能力不对等的问题也有论述。在讨论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博弈时,亚当·斯密写道:“在一般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有许多议会的法令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但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佣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主由于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在议价过程中占有相对的优势,能够将付给工人的工资压得足够低。因此,从不对等的议价能力来看,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最初分配并不总是公平的。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总是倾向于议价能力较强的一方,其结果总是将更多的社会财富分配给既有财富较多的人。从罗尔斯关于公平合作的观点来看,亚当·斯密的平等原则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保持中立,这并不意味着税收“公平”,真正的公平应该是站在穷人(禀赋较差者)一方,向富人(禀赋较好者)一方提出合作的条件,而这种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就是罗尔斯正义学说中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为我们讨论税收公平提供了新的思路。按照罗尔斯的理解,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并不能保证公平,因此,可以借助税收等政府手段主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就是进行“再分配”。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其最终的目的是使得社会合作中的“最小受惠者”的期望达到最大值。具体说来,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主张对禀赋不同的社会成员收取不同比例的税款。相比于禀赋较差者,禀赋较好者应承担更多税负,这样才能矫正自由市场的初次分配所带来的不公平。所以,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将支持“累进”性质的税收制度而不是等比例的税收制度。
对比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和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平等原则所规定的税收制度只具有为社会的公共部门筹集资金的功能,而以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为基础的税收体制则具备了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改变禀赋较好者和禀赋较差者之间的博弈格局。亦即通过税收制度增进社会中最小受惠者利益的期望值,调节自由市场中“禀赋较好者”和“禀赋较差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保证在强者与弱者的合作中,弱者的利益达到可能的最大值。
四、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看到,依据效率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税收制度应该减少“投资税”而增加“消费税”。然而,这样的税收制度显然是与税收公平背道而驰的。人们拥有的财富量不同,财富较多者的财富用于投资的比例必然大于财富较少者。因为,对于财富较少者来说,其大部分财富都必须用于维持基本生活,都必须用于购买必需品。特别是对于较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或许倾其所有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根本没有“闲钱”来投资。因此,如果一种税收制度减少“投资税”而增加“消费税”,那么就是间接地减少针对富人的税收而增大对穷人的税收。这种“累退”性质的税收违背了税收公平的基本理念。对于税收制度的设计,要追求公平就应增加“投资税”,而要追求效率就应减少“投资税”;那么,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应如何取舍呢?用于投资的财富与用于消费的财富之间应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呢?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具体的答案。




对于不同的商品,人们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生活必需品,人们的需求弹性非常小,可以说是“刚性需求”。也就是说,无论其价格多高,生活必需品都是要购买的。因此,如果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并不会使得人们对必需品的需求减少。相反,对于奢侈品,人们的需求弹性很大,如果对奢侈品征税,则很有可能导致需求减少,扭曲原有的市场结构,产生税收超额负担。因此,从提高税收效率的角度考虑,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应该对奢侈品减税而对必需品增税。显而易见,上述针对消费品的税收方案是不公平的。生活必需品是每个人都要消费的,而奢侈品则仅仅是少数富人的消费品。而且,对于财富总量较少的人来说,对必需品的消费占其消费总量的比例远远大于奢侈品消费所占的比例。于是,再一次,一种有效率的对消费品征税的方案是“累退”性质的穷人多交税而富人少交税,这完全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为了增大社会财富的总量,一种旨在提高效率的税收制度主张对人们用于消费的财富收税,而不是对人们用于投资的财富收税;并且主张对需求弹性较低的必需品征税,而不是对需求弹性较高的奢侈品征税。在这样的税收制度中,税负将完全由财富拥有量较少的社会成员承担。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财富,而且也没有用于购买奢侈品的财富。他们的财富大部分用于购买必需品,以及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而这部分商品则是主要的税源。由此看来,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中,效率原则往往与公平原则背道而驰,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在维护公平还是提高效率的问题上,正如罗尔斯所说,公平是优先于效率的,只有在保证公平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考虑效率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效率而保证公平。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的税制改革一定要优先考虑公平性问题,加大资源税、房产税、资本税等直接税的征收力度,同时避免向必需品征税,并努力将财产和收入都纳入征税的范围。另外,除了如何收税的问题之外,税款怎么使用的问题也与税收制度的公平性息息相关。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来说,税款的使用除了维持政府运转所需的必要资金外,其余的资金应该主要用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只有当税款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促进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平等,这样的税收制度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才可能体现公平原则,并成为人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