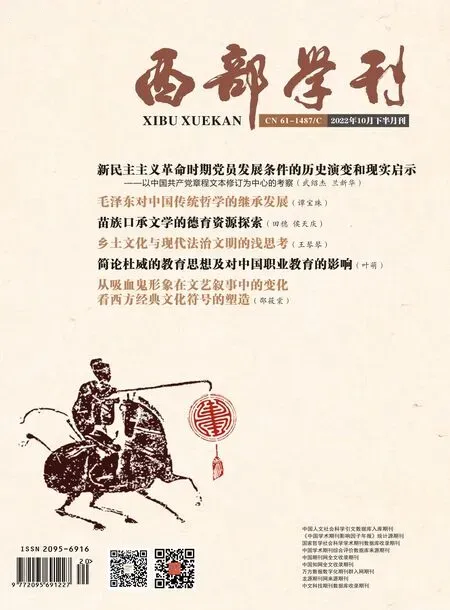小林健志的“填词和译”与“志延舍文库”
杨嘉琛 朱 龙
引言
“填词”这一中国古典文学样式在日本“除少部分人以外,几乎无人问津”①[1],其传播与接受程度远不及汉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1950年开始,仍出现了一批“业余译者”尝试“填词和译”,为填词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所谓“业余译者”之“业余”,指的是与汉学家、词学家之对应的概念。日本近代以降出现了如神田喜一郎(1897—1984)、中田勇次郎(1905—1998)等词学家,作为词学研究的一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译注填词作品,但其重心仍是学术研究。而作为业余译者代表的小林健志(1915—1997),虽不专攻词学,却在闲暇之余热衷于填词这一中国古典文学样式,努力突破“汉文训读”的桎梏,尝试“填词和译”,即翻译为真正的日语。并且,他的译词活动并非是孤立的,文献中有他与日夏耿之介(1890—1971)、花崎采琰(1903—1998)等业余译者的交游记载。这些业余译者的译词活动,推动了填词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为日本词学史及填词译介史增添了一抹绮色。
汪超[2]、刘宏辉[3]等国内学者,及日本学者嘉瀬達男[4]均关注到了填词和译的业余译者群体,明确了这一特殊群体的译词活动是填词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重要特征,但在译者个案方面则语焉不详,有待进一步探究。
小林有关填词的著作共11部,他将这些著作命名为“志延舍文库”(下称“文库”)自行刊印。这些“私家版”著作虽未公开出版且数量不多,但在词学研究并不兴盛的日本,是研究填词和译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此外,由于这些著作刊印较少,多数研究者未能一睹其原貌,因此笔者通过走访日本两处藏馆——长野县饭田市立中央图书馆“日夏文库”及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实地调查后撰写此文,在考察小林填词和译特点与影响的同时,还原“文库”原貌。
一、“志延舍文库”的刊印
小林并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而是一名机械工学的工程师,通过零星记载可窥知“他还有精通汉诗的风流雅士一面”[5]。笔者通过整理“文库”著作中的序跋,还原出其刊印“文库”的经历。
小林1915年出生于埼玉县大宫市大门町,193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工学部机械工学科,“二战”期间在千叶县的国产精机公司工作,“文库”中的部分原稿,就是这期间在通勤电车中所译。1946年起担任芝浦工业大学机械工学教师,1951年刊印其一《二十四詩品》,此后六年间共刊印了15部著作收录于“文库”。1957年刊印其十五《テヘランの唄》,同年转任至通产省工业技术院机械试验所,刊印也随之暂停。1969年转任至宫野铁工所,1977年“文库”再次开始刊印,从其十六《こぼればなし》开始,到1984年其三十二《続十六字令》为止,共刊印了17部著作,之后是否还有“文库”新著,暂未发现相关资料,1997年去世。
(一)“志延舍文库”的基本情况
小林在他与其夫人名字中各取一字,为其家宅和“文库”命名:“志延舍文库可读作‘Shiensya Bunko’或‘ShinobuyaFuminoKura’,‘志延舍’是健志和延子所居住的房子,有一个漂亮的的阁楼”。《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中记载了小林有关填词的文献,调查得知这些文献的原典仅在饭田市立中央图书馆“日夏文库”和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中有馆藏。其中,“日夏文库”是英国文学学者日夏耿之介的旧藏书(如表1△所示),日夏于1971年去世,因此未收藏其后出版的“文库”著作。“词学文库”是词学家中田勇次郎的旧藏书(如表1○所示),收藏了“文库”中的17部著作。笔者走访两处藏馆,在实物调查的基础上,将已知信息总结为表1:

表1 “志延舍文库”书籍情况表
(二)书籍形态及著书理念
“文库”均为私家版的册子形式,一部分著作除正文外还有题词或插图。书籍形态方面,其九《詞品附靈芬館詞抄》为正方形,其三十二《続十六字令》为线装本,用20列*20行的四百字竖版原稿用纸向外对折制成。其余有豆本(袖珍本)也有B5判,或为横开本或为竖开本。装订方式根据页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排版也根据内容有横竖版两种,书籍形态各异。
其十五《テヘランの唄》及以前均为油印本,印刷数量仅为几十至一百册。其十六《こばればなし》开始,变为电子排版,印刷数增至千余册。关于“文库”书籍形态各异、纸张选材不一的问题,小林解释为:“刊印这些书籍仅是为了兴趣,并非要商业出版,因而采用与内容最相适应的简单形式”。同时,小林借用佐藤一斋《言志晚录》中“著书只要自怡悦,不要初有示人之念”,来阐释他“仅为愉悦自身,而后馈赠好友的著书理念”。
(三)“文库”中填词相关书籍
目前已见的“文库”著作中有11部和填词有关,其中包含多部中国词的唯一日语译本,结合序跋中的信息总结其底本及主要内容如下:
1.其六《宋代の抒情詩詞》及《宋代の抒情詩詞(追補)》:胡适《词选》的“转译本”,以英国汉学家克拉拉·凯德林·扬(CLARA M.CANDLIN YOUNG)的译著TheHeraldWind:TranslationsofSungDynastyPomes,LyricsandSongs为底本,是一本英、汉、日三语对应的词选,刘宏辉对此译本的成书经历及翻译策略进行了详细考证;
2.其七《二十四女品花 附美人十二咏》:清冯云鹏《红雪词》“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和译本。“美人十二咏”为况周颐编《蕙风词》的和译本;
3.其八《続詞選》:清董毅《续词选》的全译本,序中介绍采用“文语体散文译”的和译策略;
4.其九《詞品 附靈芬館詞抄》:以清郭麐所著《灵芬馆杂著》二卷为底本,选取其中将填词风格分为“幽秀”“名隽”等12类的词话进行翻译。此外,“灵芬馆词抄”选取清郭麐所著《灵芬馆词》中的30首,按照词调分类并进行和译;
5.其十《単調の詞》:以清夏秉衡《清绮轩词选》卷一刊载的“单调词”为主,并补充其他单调词,是一部限定调体的填词选译本。除中国词以外,还选入了日本词人田能村竹田的一首十六字令;
6.其十一《漁夫の詞 附散曲》:以歌咏“渔夫”为主题的选译本。主要内容为填词,此外还有两首渔夫诗代表作——柳宗元《渔翁》《江雪》及部分散曲;
7.其十二《物語の詞》:底本为清徐釚的《词苑丛谈》,以文学故事为主题,翻译其中收录的词作及词话;
8.其十三《続詞品 附過雲精舎詞抄》:底本为清杨夔生的《续词品》,并摘录杨夔生《过云精舍词》中的12首。此书仅为摘录,无翻译;
9.其十四《李後主詞集 附小傳》:以杨荫深著《李后主》为底本的词人别集译本,并撰写词人小传,详细介绍了李煜的生涯与词作风格;
10.其十九《十六字令》:以十六字令为限定调体的选译本,除中国词外,还选入了田能村竹田、塚本嘉寿、花崎采琰三位日本人的作品。解说中阐述译文采用“7775”音数律——“都都逸调”的和译策略;
11.其三十二《続十六字令》:与其十九同为十六字令的限定调体的选译本,补充了近人毛泽东、陈掌谔、刘德兴及日本人马嶋春树、花崎采琰的作品。
可以发现,小林对填词的关注并未局限于五代和两宋,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明清及民国,甚至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的词作。同时可以看出,小林生活的时代能够接触到不少词学文献,历史上中国文献以不同渠道东传至日本。但客观地说,词学文献并不多见,这种现实与填词规则复杂、鉴赏与创作难度较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正因这一点,更可以说明“文库”著作之珍贵。
二、小林健志的“填词和译”策略
小林努力摆脱“汉文训读”的束缚,尝试多种和译策略。在其早期的译著中,采用了“文语体散文译”的策略,此处举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下阙为例: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小林在其八《続詞選》中的译文为:
对比中田勇次郎《歴代名詞選》中的“现代口语译”:
多情の人はむかしから別離をかなしいものとおもう。さらにそのうえ、うらさびしい秋の季節にどうしてたえられようか。こよい、酒のさめるところはどこであろうか。それは、楊柳のしげる川の岸辺、暁の風ふき、ありあけの月のかたむくところであろう。これよりのち年をへては、どんなよい時もどんなよい景色もなにもならないであろう。たといかずしれぬほど多くの風情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いったいだれといっしょにかた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か。
可以看出,小林的译文选择了风韵古朴、语言简洁的“文语”,而中田的“现代口语译”其本质是逐字逐句的现代日语口语译。当然,这两种译文的不同与其二人的译词身份——业余译者与词学研究者,以及两本著作的著书目的——自得其乐与词学研究,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正因为业余译者这一身份,使小林不必过多顾虑专业性,从而作出更为自由大胆的尝试。
其后,小林提出了使用日本诗歌采用的“音数律”——五七调、七五调或“都都逸调”进行和译的策略,反对使用“现代口语译”。他认为“无论是用纪记万叶的古语还是用都都逸调,都应是译者的自由。但口语译则与唐宋诗词意境不合,元散曲或民国后的白话诗才适合用口语译”。
小林在后期的填词和译实践中较为成熟地实践了如上译词观。例如,在其三十二《続十六字令》中翻译十六字令,就采用了都都逸调“7775”音数律的填词和译策略,此处举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及其译文为例:

使用“都都逸调”这种“音数律”的和译策略固然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期待,但填词文体形式复杂,并非所有调体都适合用“都都逸调”和译。关于这一点,小林并非没有考虑,而是他作为业余译者无需做过多专业性的考量,仅需满足他自得其乐、文学交游的目的即可。
三、小林健志与填词和译者的交游
小林的填词和译著作影响了花崎、日夏等业余译者,同时也对中田等词学研究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围绕填词和译沟通交流、互赠书籍,维持着亲密的交游关系,构成了独特的交际圈。中田和日夏二人旧藏有多部“文库”书籍,即为他们交游之佐证。同时,翻阅他们的著作亦可发现颇为丰富的交游记载。
日夏在《唐山感情集》中记载了他接触填词的契机,“工艺大学小林健志教授将其油印本新作——《单调的词》馈赠与我,这是一部关于‘词’的注解本,对我来说也是一本原创的教材,我随后立刻尝试翻译了一部分。(略)得益于小林的这本译注,让我领略了‘词’语句长短变化、文体错落参差、极富变化的魅力,我又向他借阅了多部词学文献”。此外,花崎在自传中,记述了向《東方文芸》杂志投稿的文人学者名单,其中有小林、日夏等业余译者,也有神田、中田等词学家。
日本词学在这一时期百花盛开,表现为译者、学者集会交游,创刊著书的繁荣景象。但不得不承认,这一群体人数不多,影响力也终究有限,虽取得了一定的填词和译成果及词学研究进展,但始终未能达到如汉诗一般的成就。
结语
填词在日本虽远不及汉诗影响深远、受众广泛,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之一,研究其“走出去”的路径和其在世界上的影响都具有深远意义。业余译者的广泛参与,是这一时期日本词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历史上的汉文热潮和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汉文素养。就填词和译来说,小林对其他译者,甚至对填词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日本词学的推进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著作的学术与文献价值不可忽视。当然,小林之外的译者们也在不断尝试各种译词策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的成书经历、译作风格,以及译者之间的交游活动等都值得进一步关注。此外,笔者还认为今后对填词和译的考察不能是孤立进行的,在挖掘相关文献的同时,要将填词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联系起来综合探究,要用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行分析。这些都是研究填词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填词译介史和日本词学史的重要课题。
注 释:
①本文中引文原文为日语的均为笔者译。
②所示数据为“左右规格*上下规格”,单位为mm,手工测量存在误差。
③其二、以及其二十至其三十二共14部书籍在日夏文库和词学文库中均未收录。根据其十七《西洋マンガ》后附载的《志延舎文庫既刊目録》可知其二是名为《ホックリポックリどこにいるの》的32页小册,1951年6月刊印,其余信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