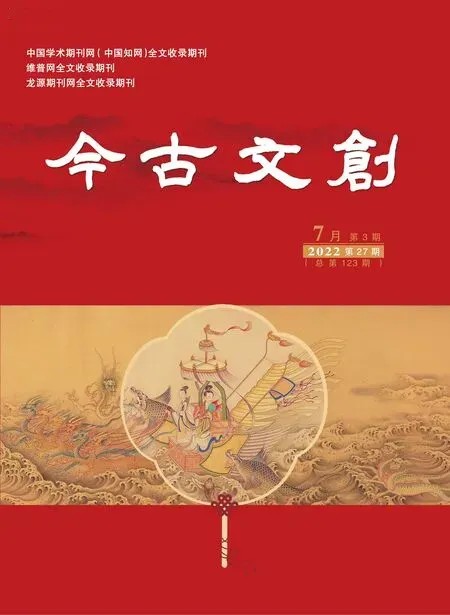比较视域下徐坤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以小说集《厨房》为中心
◎夏慧玲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伴随20世纪80年代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重写文学史风尚的盛行,女性作家的文本大多被批评家群体以个性解放一以贯之,相对忽略了女性的性别价值。这一情况为众多学者注意,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便反对鲁迅、茅盾等男性批评家们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出发来审视萧红作品的行为,赞成孟悦、戴锦华从女性自我体验的角度切入文本批评的方式。实质上,90年代的女性文本已愈加关注女性这一群体的独特感受,可见女性作家们正试图以多样的文学形式使女性摆脱时代的束缚,成为纯粹的人。徐坤在《双调夜行船》中曾言:“那么90年代,则是随着多元文化历史现实的到来,有更多的一直在文化边缘默默行走的女作家,更注重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女人’的自我发现。”徐坤的写作跳脱出女性为政治斗争献身或服务的传统模式,转向对个人写作的践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女性的“第三次解放”这一概念。徐坤认为“第三次解放”即是“90年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放……不会有体制上的压力和公共道德舆论上的指涉。”90年代以来,较为宽松的时代环境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存在的可能性,这与80年代女性写作举步维艰的现状形成对比,青年女作家徐坤也在良好的时代氛围中孕育而生。
徐坤竭力将“第三次解放”的观点内化于小说,刻意以女性身体或心灵的“越轨”彰显其对女性自我感受的关心,且力图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消解女性可能面对的道德、舆论压力,是对传统女性革命题材的背离、转身。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切入写作,为读者全面、深入地感受文本中女性人物的悲欢离合提供便捷,徐坤的写作能力可见一斑。从文本内部来看,小说中女性生活的场所在悄然变化,且女性不再以时代“客体”的形象出现,这是徐坤对女性社会地位及时代处境的大胆拨动。徐坤善用先锋姿态深究女性所遭遇的身体疼痛和精神困境,以饱含讽刺的话语揭露女性面临的窘境,并以此反思社会与时代的病症,这是徐坤有关“第二性”写作的旨归。
一、人物状态的转变:“向上”与“向下”
与《青春之歌》等革命题材中的女性形象不同,徐坤小说中的女性褪去了为理想事业奋不顾身的果敢、勇气,终日颓靡、慵懒。贺桂梅在《“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直言:“小说(也包括电影)《青春之歌》的主要文本特征,在于以女性故事来表征知识分子革命道路这一政治主题。”她认为“可见”的女性由于革命题材的现实性而被50年代的主流阐释及90年代的“再解读”归依为“空洞的能指”,努力地寻求能够“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体制中阐释女性主体形态的可能性”。《青春之歌》由于其女性人物的阅历饱含“向上”的成分而被批评家们反复与时代或革命关联,失去了对性别意识的关注。徐坤则极力避免其小说中的女性以洋溢的热血奉献时代,而是以其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无视,瓦解其被政治话语裹挟的可能性,完成对传统女性题材小说的转变与革新。
小说集《厨房》的主要篇目便是《厨房》这一短篇小说,其女主人公枝子的“欲望”因第三人称视角的介入而被毫无遗漏地披露,生动地描摹出了一位“颓废”的女性。《厨房》中反复出现自由间接引语“她”,这为读者感知枝子真实的心理状态提供捷径:“她的身子这会儿全软了,软得一塌糊涂,怎么也动不了……这会儿她想,她只想,我爱这个男人,我爱。跟我爱的男人在一起,这就行了。行了。”枝子的私密想法使该文本远离宏达的政治主题,将读者的视野凝聚于女性的个体体验。并且小说结尾枝子重返厨房的决心与毅力,更是瓦解了其与主流话语关联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枝子对厨房的执意回归与倡导女性解放的浪潮相斥,但这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行为反倒引起读者的反思。
收纳于小说集中的另一篇《一个老外在北京》,则更为直接得展现出女性的自私、贪欲,使女性的形象无限“向下”,将其塑造成光怪陆离时代下的傀儡。外教尼尔斯的生活境况因一位女孩而日渐惨淡:“女孩子坚决要求跟尼尔斯出国。不出国,嫁你干什么……两年后,女孩跟有一个老外去了美国。”尼尔斯的悲惨境遇源于女孩对爱情的亵渎,使读者在怜悯尼尔斯的同时,深思女性心理变化的原因,这是徐坤使其女性人物远离革命话语的方式,其目的在于激发读者对女性心理的在意。《遭遇爱情》则因女性对身体的玩弄,使其人物彻底地摆脱与乐观的生活方式产生关联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明作者对“第三次解放”的践行,另一方面悄然地引导读者关注女性作为“人”的感官体验,实现作者个人化写作的真实意图。
徐坤对女性心理状态的大胆、肆意描写,并不仅是为了鼓励女性放浪形骸,深层目的是希图以违背道德伦理的故事情节激发社会或时代对女性心理的重视,如同酒井直树在揭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共谋时所指:“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为了隐蔽自己的毛病而互相认可对方的毛病,恰似两个同谋犯的狼狈为奸。”依酒井的看法,作者对特殊性的寻找其实在为普遍性探求光明出口。徐坤对女性的刻意贬低或对其丑陋心理的揭露,与革命题材的女性小说的最终目的具有同一性,旨在为女性的“可见”寻求可行性策略,反映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美好愿景。
二、场所的变更:“向内”至“向外”
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场所的变动并不仅指地理位置上的调动,即女性走出厨房。“向外”也暗指女性心理的逐渐外放,主动且善于与人交流、释放自我。“向内”至“向外”的转换折射出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与提高,显示出女性群体的魅力。徐坤小说中人物的“向外”,或徐坤自身对“向外”的期盼,都是徐坤小说中亟待被赞扬的“华丽转身”。但“向内”与“向外”的写作方式都以激发社会对女性感受的关注为热忱,这是徐坤小说一脉相承的写作态度。
徐坤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厨房》与21世纪之初刊发的《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暗含场所的变更。《厨房》的女主人公枝子出走后又回归的举动,曲折地表明女性解放的失败,枝子对静谧的厨房生活的狂热极易引起读者的不适。且《厨房》的结尾为枝子手提着从松泽家里带出的垃圾这一情节,暗喻女性犹如男性低劣的附属品,允许被随意舍弃。小说在开头写道:“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厨房对女性的约束力成为作者的困扰,她以小说开头的话语答复了鲁迅关于“娜拉出走后怎样”的疑问,呈现出一位女性作家低沉的写作心态。而《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在场所的设置及女性人物内心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上都与《厨房》大相径庭。《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将女性活动的场所由狭隘的室内厨房转换至辽阔的广场,说明女性执有大胆地向异性表达爱意及主动融入社会的魄力。作者不再将象征女性存在感的厨房作为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而是以能够充分展现女性才艺的广场设置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场所的“向外”暗喻作者对女性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女性“能否走出厨房”,而是在于女性能否提高思想、融入社会,也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更迭。徐坤在《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的结局写道:“多尴尬!多丢人!两个大活人,活生生压在一起……女人的起立比较艰难、迟缓……先是缓缓蜷起双腿,坐起,表情痛楚,龇牙咧嘴……瞬间就收敛了回去,做出一副平静状。”女人在广场的狼狈姿态极其冷静的处理方式,与枝子在结尾时极力克制自我情感不得而流泪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表示女性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心理承受能力的提高。女性面临社会舆论展现的抗压能力,来源于其与社会的频繁接触后的自我调适,反映了新世纪女性由“向内”至“向外”的华丽转变。
而《狗日的足球》的文本内部已实现“向内”至“向外”的过渡,且其结局以“向外”的失败,彰显作者对“向外”的渴望与追寻。留校任教的青年女教师柳莺本极度厌恶每逢世界杯时,未婚夫杨刚将家里作为免费的放映厅,招来众多看客的行为。在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马拉多纳矮小的身躯与坚韧的品格吸引了柳莺为其驻足,柳莺对其心生怜悯并逐渐欣赏、爱慕这位足球运动员。柳莺对足球的态度由排斥至接纳表明女性已主动参与并融入男性聚集的场所。正如徐坤在小说中写道:“完全被球场辐射出来的‘场’所辖服,一个巨大的、解放了的‘场’,在辖服所有人的行为,撺掇着人们去与禁锢已久的文明作对。”球场被作者抽象化,成为女性“向外”的象征物,暗示女性对顽固思想的挣脱。但作者清晰地认知到,女性“向外”并不会一蹴而就。因足球场上反复涌现污秽女人身体的语言,柳莺逐渐反抗球场且痛斥这群球迷的无知,这表明作者对女性“向外”可能会遭遇的阻碍的担忧,及对提高男性思想觉悟的强烈号召。
小说“向内”至“向外”的发展是女性社会地位及思想意识进步的剪影,是新世纪女性的一次华丽转身。女性主体意识的提高,是女性重拾话语权的不二法门。女性的思想和眼界若一味地固执与短浅,其境遇也会较为困厄。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也应积极调动其思维的能动性,对时代环境做出认真的考量。徐坤曾言:“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人被爱情和婚姻剩下,大概还是要有相当压力,男女双双钻进人间烟火气的厨房和婚姻围城才是老道理。”她以诗集《厨房》来逃离时代给予婚姻的围城,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仍能以冷静的思考使其文本脱颖而出,这是其将思维的活力注入灵魂深处的结果。
三、主客体的消解:影响与支配
在徐坤的小说中,女性的行为干扰着男性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或支配着男性的命运,这是对传统女性压抑地位的反拨,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征。徐坤赋予女性人物以主体地位,且有意淡化男性的社会价值,有利于削弱父权社会的力量,并引导女性读者逐渐提高自我意识并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为当代女性的出走提供精神支撑。
女性对男性的压迫在《厨房》中主要表现为松泽对枝子的惧怕。传统男性大都享受女性对其的依附与忠诚,且并不害怕女性的多情与细腻,而松泽却被枝子的热情与豪迈劝退,这证明女性对男性生活的影响。小说中写道:“男人脑子里还在先惊后怕地想,不得了,真不得了,这个女人,不要命的女人,简直要把我玩死了。”松泽的真实心理因叙述者的存在而真实地呈现。且松泽拒绝枝子情感的方式十分委婉和含蓄,表明枝子具备改善其生活水平的能力。男性无法再无视女性的感受,而是与女性平等对话,是女性“可见”的重要环节。徐坤故意将男性塑造成仰视女性的姿态,是其针对“当下此时”不平等现象的刻意倾斜,这极易引起读者对其的误读。读者在细读文本时,需耐心地体味作者的用心,而不是浅尝辄止。同时,小说中的枝子作为一位出走后的成功女性,也悄然地支配着松泽的行为。艺术家松泽需依靠枝子获得提升职场地位的机会,于是不惜出卖身体与灵魂:“可现在他的身体里分明缺乏这种感觉……他并不明了,一旦有了身份和功利的意念,一切就都不好玩了,连一点点肉体的冲动都不容易发生。”松泽需刻意掩埋其对枝子的厌恶,假意地迎合枝子的纵情行为,这体现女性对男性的控制力与支配程度。小说中的艺术家松泽与枝子的逢场作戏,暗示传统社会中男性主体地位的瓦解,以及女性逐渐拥有话语权的现状,是新时期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彻底分割,对落后文化的坚定转身。
与《厨房》相似,《狗日的足球》《一个老外在北京》《遭遇爱情》《早安,北京》都为女性角色赋予影响或支配男性的力量。《狗日的足球》中未婚夫杨刚召集朋友看球需征求女友的同意,这是与传统男性背道而驰的行为,体现女友对其的重要性。而《一个老外在北京》则以女孩对尼尔斯生活方向的随意支配,证实作者对解放女性思想与提高女性主体地位的努力。《遭遇爱情》虽以梅的惨淡退场为结局,却不能以此消减梅对岛村的干扰程度。在梅与岛村的业务洽谈以岛村的退步为结果后,小说中写道:“这一夜岛村彻底失眠了,带着失意和惆怅辗转反侧,对自己和这个世界都没有了把握,仿佛又陷入孤独冷漠里兀自漂浮着。”岛村对这个世界的不适来源于梅对其的挑逗与谋划,显示女性力量的不可小觑。《早安,北京》未直接涉及都市女性的描写,但泽源却害怕亲戚的邋遢与土气会使妻子烦心与困扰,表明其对妻子想法与见解的在意。
徐坤以女性对男性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支配来暗指小说中主客体的销声匿迹,并以此表达其内心对性别平等的渴望。小说中女性获得的身份认同感,有益于启示当下部分思想仍旧较为保守、顽固的女性提高对自我的认可度,并由此引导她们不再效仿传统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相处模式,这是徐坤寄托于小说中的良苦用心。与此同时,男性是女性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推动力,其思想观念的转变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且不容小觑。男性对女性的呵护与疼惜,为女性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推波助澜。
四、结语
徐坤的小说并不拘囿于对女性心理活动的揭示,而是从整个时代的现实情况出发,以此来布局小说集的内容、框架,显示了一位女性作家思考问题的向度。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发展的想象,为当代女性的举止提供了参考、警示,因而具备现实意义。文本需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才能维持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只能被大众闲置。吴晓东等学者从诗学角度研讨中国现代小说的思路时就曾写道:“这意味着,文本世界不再具有稳定性,它需要在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寻求定位。”由于文本张力的存在,小说的蕴意需与深重的历史乃至源远的文化需发生关联,以此具备厚重的时代价值,这样才能避免被时间或读者遗忘。徐坤的构思水平与长远的写作眼光可被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