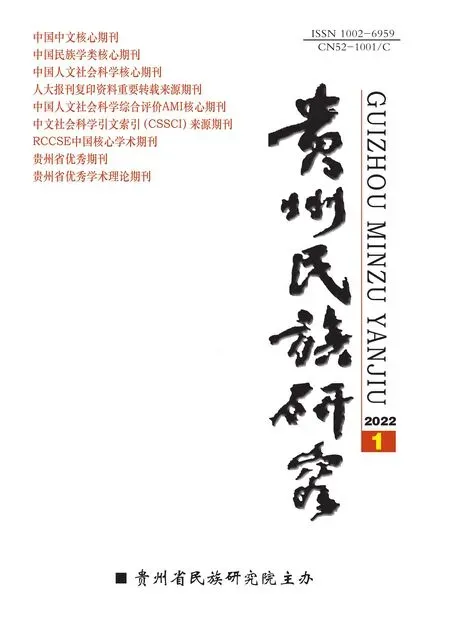从符号学角度谈方南苗族服饰中苗龙的文化表达
胡瑞波 董建辉 杜沂倩
(1.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贵阳 550001;2.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3.贵州黔南科技学院,贵州·惠水 550699)
引言
从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成熟来看,龙符号伴随中华文明的始终。从龙符号的造型形态上来看,不仅有着自然界各类生物的原型,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表达、观念传达、符号创造,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中国龙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勇敢、不屈不挠和大胆创造的民族精神。龙符号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对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和唤起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苗龙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主体的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起源,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动,它与主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方南苗族历史上共经历了五次大迁徙,由于蚩尤部落战败于炎黄部落,被迫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历史。在迁徙的途中经历了黄河和长江,来到了清水江沿岸后逐渐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回顾迁徙的历程,不难发现,这些共享的集体记忆被勤劳智慧的方南苗族女性和银匠们制作在服饰中。苗龙符号作为方南苗族服饰主要的创作题材,苗龙符号的摆放位置不同和组合的方式不同,所表达的文化符号也不同。苗龙符号的产生与中华主体文化的龙符号的产生同源,后经方南苗族不断迁徙且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苗龙符号高度生活化色彩的形制。分析苗龙符号的造型、色彩和隐含的文化价值,并与主体中华文化符号的龙崇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苗龙符号与主体中华文化的龙崇拜的区别与联系,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挖掘苗龙符号背后厚重的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引入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方南苗龙背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符号学相关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关于符号的记载层出不穷,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老子在其论著中表述的“名”与“实”的关系正是符号(表示万物的思想)与指涉及物之间的关系。早在《易传》中就有“拟诸形容,像其物宜”的记载,其中的“像”就是指“符号”的意思,“观物取像”正是符号创制的最初过程。庄子的“象罔”说、《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毛诗大序》的“比兴说”都有符号学的影子。在方南苗族社会中,万事万物都可以变成龙,如牛龙、蜈蚣龙、鱼龙等。龙符号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纵观西方符号学的发展历程,瑞士学者索绪尔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提出了四种区分:“历史性和共时性”“语言和言语”“横组合和联想”“符号能指和符号所指”,表明了“语言是一种表观念的符号系统”。通常将“一事物代表另外一事物(如A代表B,A即B的符号)”。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传达的意思是感官可以感知的对象,所指传达的意思是能指表达的意义。从上述观点来看,方南苗族服饰中的龙崇拜被赋予了不同的符号意义,而且不同的符号表达其内涵也不一样。在部落社会时期,龙符号的造型成为部落权利的象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龙符号又被赋予了新的符号内涵。但无论如何,方南苗族龙图腾图案怎么变化以及如何变化,其内部都存在符号学的意义,都存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具有一物代一物的文化符号意义,其内部的文化和信息都可以使用上述四种区分来解析。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拓者C·S·皮尔斯提出了“皮尔斯的符号三角形”。他认为:“符号学总是一种带有三个(而不是两个)词项的关系:一个符号是一种事物,它在某个方面与第二个符号及其对象相联系,以便与第三种事物即对于这一对象的解释建立关系,以此类推,以至无穷”。皮尔斯认为符号结构由符号“代表性项”“对象”和“解释项”构成。在研究方南苗族中龙符号的符号意义时,也可以采用如上三种方式对其加以研究和解释,对于解析龙符号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皮尔斯进一步认为,符号学的源头是逻辑学,涉及到三种范畴即感觉质、经验和思维。同时,又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联,后将符号划分为:图像符号、标志符号和象征符号。方南苗族服饰中龙符号隐含着图像、标志和象征符号。采用符号学的理论,研究方南苗族服饰图案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其目的是理解图案背后厚重的文化信息及图案反映的祖先崇拜、生产生活轨迹、文化准则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为方南苗族服饰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二、龙舟节实地调查及其龙符号的符号化表达
瑞士学者索绪尔提出了符号具有“历史性和共时性”“语言和言语”“横组合和联想”“能指和所指”的功能。龙舟节及其符号化形成的过程可采用该理论进行解释。例如,方南苗族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到二十七以施洞为中心举行独木龙舟节的故事。“相传在清水江边上住着一位宝公的方南苗族老人,经常带着孙子九宝到江上去打鱼。当宝公专注捞鱼时,突然一条恶龙从江里跃出来把九宝抓进了龙洞,咬死九宝并放在自己的床上当枕头,从而引起宝公愤怒,于是有了宝公拿着火炬烧死恶龙的传说。当恶龙被烧死后,浓浓的烟雾遮蔽了天空,加之接连下了九天九夜的倾盆大雨,使得秧苗无法种植,牲畜无法寻找食物。此时,有位妇女到河边洗衣服,淘气的孩子就拿着棒槌在水里搅来搅去,嘴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使得天上出现了一道奇观,一条花花绿绿的巨龙横卧在江上丝毫不动。由于恶龙引发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此后就产生了分龙肉的故事。基于此,平兆村分到龙头,龙塘分到龙身,平寨分到龙尾。尽管关于分龙肉的说法众说纷纭,但分龙肉的故事题材已普遍流传于当地。当人们吃完龙肉后,恶龙托梦给当地人,表达自己杀死了九宝后自己也得到了惩罚,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要求大家制作一条木龙舟,相当于跟它活着一样,如此一来,它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多子多福,保佑大家。”结合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来分析,独木龙舟最初的所指是消灾祈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龙舟节的能指和所指的内容不断地丰富了。从能指角度上来看,首先是制作独木舟的方式更加复杂了,制作的形式也拓展了。从纵向上来看,当地需按照方南苗族宗教的方式,经过复杂的仪式过程后,才开始制作独木龙舟。在造龙舟的过程中,树木需经过严格的选择,且树木须是挺直和合抱之木方可制作独木龙舟。制作前需请有威望的鬼师烧香祈祷,祈求树木的原谅,之后用斧头砍倒树木,砍倒后要在树桩上敬酒和祭祀以便树重新发芽,寓意着人和树木一样生生不息,表明了方南苗族万事万物平等的宇宙观念。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符号的能指方面,也存在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其符号由单一的指示性符号向更加复杂的符号系统发展。同时,由于清水江水流比较湍急,龙舟制作时需要将其制作成母子舟,主要目的是适应环境的需要。总而言之,独木舟制作能指方面的内涵也伴随着巫术、仪式性活动和适应环境的需要,其能指方面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大和丰富。从横向上来看,关于龙符号被创作在服饰上,通过苗族女性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码,提升了方南苗族对本支系的身份认同。从所指角度上来看,起初的独木龙舟主要的目的是消灾祈福,此后由于能指内涵的不断拓展,所指的内涵也逐渐地扩大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健康长寿、多子多福等美好的寓意。截至目前,独木龙舟的内涵还在不断地扩大,表现为向原生论、工具论和多元论的所指方向发展。
三、苗绣苗锦实地调查及其龙符号的符号化表达
苗龙符号中的异形同构和同形异构能指内涵丰富。从同形异构来看,方南苗族能够将两个截然不同的生物进行组合,体现了方南苗族女性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造型上来看,最为常见的能指题材有双头共身龙和双身共头龙。事实上,方南苗族在能指题材的运用中也存在抽象化表达,与青铜器中饕餮纹样有些相似之处。由此,从双头共身龙的所指分析来看,当地人强调对龙头部的表达,通过双头的造型,增强了人们对龙头的观看效果。通过五彩缤纷的色彩搭配和多样化形式表达,增强了双头共身龙的视觉形象。同时,利用中国古典散点透视将两个不同视角形态平面化地展现在同一维度上,这加强了人们对其图案观看的视觉效果。从双身共头龙的能指角度来看,发挥了方南苗族女性独特的创造力。从所指的角度上来看,方南苗族人认为,两个身体一边为灵魂,一边为肉体,这类的创作体现了方南苗族社会中的生命哲学。从构图上来看,也源于方南苗族女性平面化的造型语言的应用,在形体观看过程中,无论从左边看还是从右边看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体现了方南苗族社会对宇宙万物和生命哲学的看法。从异形同构能指方面来看,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牛龙、鱼龙、蜈蚣龙、水龙、射龙、人头龙、鸡头龙、泥鳅龙、飞龙、虾龙、狮龙”,等等。从龙的所指角度上来看,方南苗族人普遍认为龙是吉祥物,既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也能够作为当地的守护神。龙符号的形象在方南苗族社会中非常普遍,且万事万物都能与龙对接,构成龙的不同形态。从设计手法的所指上来看,动物形态与龙共身的造型彰显了方南苗族妇女高超的表现手法和真实的生活场景。从造型上来看,方南苗族龙符号的创造体现了万事万物和谐平等共生的文化场景。从创作题材的能指方面来看,能够将人、蚂蚱、青蛙、蝴蝶和龙的造型异形同构,体现了方南苗族与万物平等和谐相处的思维模式。从牛龙的能指和所指分析来看,牛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力气大逐渐成为方南苗族耕种的生产资料。因此,人们对牛加以崇拜似乎合理,并以此为基础,牛的能指和所指内涵不断地外延。起初在蝴蝶妈妈生12个蛋的故事中,牛跟姜央是兄弟,是平等关系,后来姜央和雷公分家产,牛分给了雷公,后来便有了姜央借雷公的牛犁田的故事和杀牛偷吃的故事,也为雷公引发大水“洪水滔天”的故事作了伏笔。从方南苗族龙舟造型上来看,方南苗族的独木龙舟前有龙头后无龙尾,龙头部位有木制的大水牛角,也被称为水龙牛,不难看出,内涵又被进一步地延伸。由此,要解析牛龙背后丰富的文化信息,需要对其进行分层次地解析,牛龙所处不同层次,其能指和所指的内涵也不一。从鱼龙的能指和所指来看,从能指上来看是鱼和龙的组合,其所指表达的是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寓意。从方南苗族织锦中央的龙符号的能指来看,既绣有盘龙符号,也绣有卧龙的图案,其所指的符号意义是想表达出方南苗族经历了长期的迁徙。在田野调查当中,在方南苗族织锦正中央的龙符号,潘玉真解释为盘龙或卧龙,符号意义为定居,盘龙或卧龙实际上是表达他们定居于此,体现出方南苗族对故土家园的热爱。
四、方南苗族银饰实地调查及其龙符号的符号化表达
方南苗族银饰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苗汉交流交往交融的因素更多,主要体现为双龙戏珠、龙凤呈祥、鲤鱼跳龙门、麒麟送子等元素和符号的使用。从创作题材上来看,既体现了主体中华文化的元素符号,又体现了工匠们勤劳智慧的创作能力,即在有限的题材中创作寓意丰富的作品。方南苗族银饰的创作体现了主体中华文化符号和银匠们就地取材的创作能力。从银项圈的形制上来看,一种是拉丝扭曲成型的银项圈,其独特的工艺造型,成为方南苗族银饰最具特色的工艺品种。另外一种为月牙形的银饰项圈,上面装饰多吊坠,其图案有蝴蝶、瓜子等,具有多子多福的象征意义。而该类银饰项圈上面的龙符号成为了最为耀眼的符号,其中,龙符号盘旋在月牙形的项圈内,同上方拉丝工艺制作的银项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符号象征意义上来看,拉丝成型的银饰项圈更强调曲线之美,而月牙形银饰项圈更强调图案背后丰富的文化信息。从造型符号上来看,银饰上面绘有双龙戏珠的图案,其主题设计具有高度的地域化和生活化色彩。从文化寓意上来看,依然与中华主体文化符号有关,其中双龙戏珠既具有地域化和生活化色彩又源于中华文化符号。从刺绣上来看,方南苗族刺绣有各式各样的龙符号,例如,双身共头龙、双头共身龙、牛龙、水龙、蜈蚣龙、鱼龙、鸟龙等,其造型夸张,形态各异。从制作工艺上来看,方南苗族银饰的制作工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工艺创作主体上来看,苗绣主要是由女性制作,体现了阴柔之美,而银饰基本上是男性制作,体现了阳刚之美。从龙符号形制上来看,女性绘制和刺绣的龙符号更能反映生活化色彩,体现了方南苗族社会内部的生产生活特征和朴素的生活哲理,而男性制作的龙符号则更具苗汉文化的交融性。事实上,方南苗族男性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更多。对于女性而言,其图案创作受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创作实体中有鱼和龙、牛和龙、鸟和龙等的创作。从形式上来看,增添了苗龙的趣味性,表现了人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的关系。从龙符号的政治和权威上来看,苗龙更具生活气息,汉龙与权力和权威联系更为紧密。从双身共头龙和双头共身龙形制上来看,图案造型大多为适合纹样,粗细对比繁而不乱且设计感强。苗龙符号能够将多维空间的人物造型展现在同一画面中,将人与龙和谐展现,使其构成了多点透视关系,这符合中国人的创作方式和审美方式。苗龙符号的创作与西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相互矛盾,它更强调多点透视关系,展现了人物造型和龙形态刻画的核心关系,形成主体和非主体强烈的对比关系,体现了方南苗族妇女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创造形成虚实对比的图案布局,彰显了方南苗族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苗龙被方南苗族妇女发挥得淋漓尽致,各式各样造型夸张的龙图案极具生活性和美学价值。通过对龙符号深入研究和分析,发现苗汉两个民族对龙的崇拜有着共同的起源,对其深入研究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护民族之间和谐共生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结语
通过对苗龙符号的调查研究发现,苗龙符号的形成经历了反复的变迁,从图案的形制上来看,苗龙符号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犷到精美的过程。方南苗族女性通过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制作了形式多样的服饰。基于此,苗龙作为方南苗族女性制作服饰的主体创作元素,虽然造型上与中华主体龙符号中的权威和社会等级有关,但其主体象征更具生活化和自然化的文化表达,体现了社会民众对图腾和神灵的崇拜,对幸福和祥瑞的期盼。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夸张变形且始终围绕适合的纹样进行创造,集中表现了规则与不规则的高度统一,表达了方南苗族特殊的审美方式和审美需求。龙符号的符号化表达形式有鱼龙、牛龙、蜈蚣龙、水龙、人头龙、鸡头龙、泥鳅龙、飞龙、虾龙、狮龙等,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不同形体的符号组合,其表达的文化内涵不同,共同构成了方南苗族服饰符号功能。苗龙作为方南苗族服饰创作的主要元素,从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图腾信仰、仪式活动和节庆活动中,可以发现方南苗族集体对龙崇拜具有共享的成分。从《方南苗族古歌》所唱的内容来看,也有龙题材的创作,这些题材的运用反映了其迁徙历史,且集中地体现了方南苗族妇女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正因如此,方南苗族服饰对于维系方南苗族社会集体的凝聚力,建构方南苗族人对族群历史共有的集体记忆发挥了纽带作用。基于此,便形成了共同观念信仰、社会组织和物质生产与生活等方面的有机整体,描绘出了方南苗族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通过对方南苗族服饰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发现,苗龙符号是其服饰创作的重要题材。研究苗龙符号象征性功能对于理解方南苗族女性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解析苗龙符号背后丰富的文化符号及挖掘苗汉两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助力民族团结发挥着重要作用。苗龙符号的产生与主体中华文化符号既有同源,又存在着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于方南苗族而言,方南苗族女性在相对封闭的社区中,根据区域独特的生产生活、礼仪节庆和人生各类礼仪,发挥她们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符号。从符号象征功能来看,体现了勤劳智慧的方南苗族女性文化和生活化题材苗龙符号的象征性功能。因此,解析苗龙符号背后丰富的文化信息,有助于挖掘该类符号与中华主体文化符号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动,也进一步表明了苗龙符号存在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解析方南苗族女性集体的心智、丰富的文化符号表达及方南苗族女性对待生活和家庭的态度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