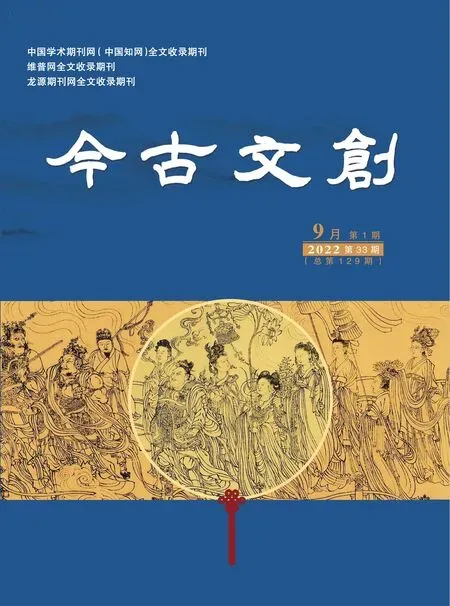论纳兰词中的忧患意识
◎赵士城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纳兰性德,自幼聪慧过人,诗词兼善,素有“国初第一词手”之称。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词349阙。翻开纳兰词,凄清悲凉之感扑面而来,俊爽飘逸的笔锋下透出的却是沉重的哀婉之感。词集中的“泪” “恨” “愁” “断肠” “凄凉”“伤心”“憔悴”“惆怅”等语,满目皆是,“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 。后人读其诗词颇有哀婉之感,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
一、忧患意识的成因
(一)外因
1.政治环境。康熙初期,为了巩固帝位,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抑制党争,惩戒贪污之徒。纳兰身为皇帝机密侍从,亲历皇帝对“市恩通贿”的父亲的屡次提醒。虽然明珠被罢免丞相一职是在纳兰死后三年,他生前不难发现其父败亡的命运。作为皇帝近侍、宰相长子,面对父亲渐渐失去皇帝宠眷却无法规劝其悬崖勒马,内心不免忧伤和惶恐,在其词作中常有表达“临履之忧”的词句,如“西风乍起峭寒生,惊雁避移营。千里暮云平,休回首、长亭短亭”。所描绘的图景之中,“西风乍起”“惊雁”和“千里暮云”等一系列形象,可以说是将词人惴惴不安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纳兰虽外表强作尊严,小心侍奉君主,但内心的忧愁却是无穷无尽的了,面对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宦生活,不禁感慨涕零。
“信道痴儿多厚服,谁谴天生明慧。”清醒的纳兰看到了其父将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命运,但现实的境遇却使他有心无力,只能自吞恶果,暗自忧虑。这无法言说的愁苦与惶恐不安无处排解,就只能化作愁肠,在漫漫长夜中“愁似湘江日夜潮”。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牵连其中的家世成为纳兰词忧患意识的成因之一。
2.文化环境。纳兰虽为相府长公子,但并不沾染豪门子弟的风流习气,喜与诗书为友。公元1672年,年仅十八岁的纳兰参加顺天府乡试,得到当时知识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徐乾学的赞誉。自此,他师从徐乾学,“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以读书六要,及经史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在纳兰心目中,徐乾学俨然已经成为教师的楷模。不料,公元1673年,因上一年中壬子科顺天府乡试副榜未取汉卷的疏误,其师被贬回江苏故乡。眼见有才学之人反被小人陷害,自己却束手无策。
此时的纳兰还和当时颇有声望的文士,如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朱彝尊、吴兆骞等结为忘年挚友,在诸多友人中,不得意者甚多,且多为明朝遗少。一边受统治者怀柔政策的牵制,一边与才学挚友惺惺相惜,当污言秽语诋毁中伤致使友人落魄之时,用情至深的纳兰倍感悲哀。虽然彼此之间时常通过诗词文字聊以自慰,但眼见一个个友人落难而去,“眼看鸡犬上天梯”,怕是“眼前冷暖,多少人难语。”想到自己,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二)内因
1.仕途才学。纳兰自幼天资聪颖,其在世不过三十一年便著作等身,且其中不乏卷帙浩繁之作,这其中的心血付出与其过人的才华怎能不令人心生叹服!他的生前好友严绳孙曾惊叹道:“吾不知成子何以能成就其才若此!”
公元1676年,纳兰荣获殿试二甲七名,赐进士出身,此时纳兰年仅二十二岁,少年郎的踌躇满志、为国建功立业之心在九年如一日的侍从之旅中并未得到满足,权力倾轧的黑暗官场也令他厌恶至极,在这个诗酒趁年华的年纪里,纳兰非但不可尽兴而有所归,反倒终日处于君臣之事之间而惶惶不安,这使得本就不喜功名利禄的纳兰只可郁郁于心,满腹诗书才气既然不能使自己的山泽鱼鸟之思如愿,能够借此抒怀也罢。纳兰师长徐乾学曾有云:“及被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行,而后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作为侍卫,同时也是康熙亲信的近臣,纳兰跟随康熙出巡了多处边关要塞,行役途中除饱受相思之苦外,其身体也备受折磨,路途奔波加之身心俱疲足以使一个人的心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种种不情愿既无处言说,更无力转变,只能在惶惶之中度日如年,以词代言,长歌当哭。
2.自身性格。纳兰作为当朝权臣明珠之子,身处岌岌可危的高位之上,内心细腻敏感的纳兰不会一无所知,毫无察觉,再加上仕途人生所遇种种,其心境以及性格便不会不无变化。严绳孙在《成容若遗稿序》中也曾提及这种朝臣常有的心态:“及官侍从,值上巡幸,时时在钩沉豹尾之间,无事则平旦而入,日晡未退,以为常。且观其意惴惴有临履之忧,视凡谓近臣者有甚焉。”可见纳兰身处帝王之畔、豹尾之间,不时心有惴惴之感,临履之忧颇重。
最初,纳兰的词集被命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饮水词》。佛家典籍《五灯会元》中道明禅师有答庐行者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意为心语相通,自明其意。人生的经历与体验日渐增长的纳兰,再也不是那个在丞相府长大的不谙世事的少年了,现实世界冰冷的规则像枷锁一般束缚着纳兰的身体言行,但纵然生活如此世故,纳兰的内心中依然保持着一份至纯至真。面对友人,纳兰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以真诚相待。诗品如人品,纳兰之词之所以如此“真纯”,张任政在《纳兰性德年谱·自序》里说得好:“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为词,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所谓情真则文至耳。以文观其人,可见纳兰之至情至性、至真至纯。但所遇并非皆是所求,心中理想与现实境遇的截然不同致使纳兰内心矛盾重重,这种独特的生活际遇便形成了他多愁善感的个性,且将这种独有的心灵悲歌跃然纸上,直言不讳,这便形成了其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3.爱情婚姻。爱情之于纳兰,更多的是悲戚伤感,幽怨苦多,是一段灰色的回忆。相传,纳兰有一位才貌双全的表妹令他钟情不已,但那名女子后来被选入宫中,两人有缘无分,此情终成梦一场,这给纳兰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尽管旧事惊心,纳兰的婚姻也总算是幸运,其妻卢氏为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兴祖之女,知书达理的妻子与纳兰情谊甚是相投,心意相通,两人情笃意切,幸福温馨。可惜,好景不长,身为皇帝近身侍卫,纳兰不得不时常入值宫廷、扈从出巡,在远离爱妻之时饱受相思之苦。更为不幸的是,成婚三年后,卢氏不幸逝世。生离的无奈就已令人哀愁,突如其来的死别更是令纳兰肠断。
在卢氏亡故后半月便做出了令人哀痛欲绝的悼亡悲歌,且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卢氏的亡故之日、生辰之时,在纳兰身处塞上荒芜之地,还是梦醒时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对亡妻的思念,哀婉的悼亡之音便也从未停歇。早知世事无常,“一生一代一双人”(《画堂春》)的美好愿景也最终落空,面对不称心得意的仕途种种,纳兰心中唯一的慰藉便也无处可寻,这人世于他而言终已是毫无滋味可寻,心灰意冷之中所抒之情便更是充满着对昔日美好的追忆,忧愁之感也便愈加深重。
二、忧患意识在词作中的体现
(一)情思之忧
悼亡词是纳兰性德词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并获得了卓越的成就。纳兰的悼亡之作共有三四十首,且首首情真意切,足以见得痛失爱妻、红颜知己给本就心力交瘁的纳兰增添了多少忧虑苦楚,其心中的不舍与无奈旁人又怎能感同身受。
这是纳兰悼亡之作中的典型一首,词的上片由问句而起,渲染之下凄清之感乍起。紧接着萧萧黄叶、疏窗、斜阳这些意象勾画出了一幅深秋残景图,词人触景生情,凄凉萧瑟之感油然而生,在落日的余晖中独立沉思。下片描写了沉思中追忆起的寻常往事。赌书句以李清照与其夫的甜蜜往事为喻,然这往日的“寻常”乐事已随亡妻的逝去而无处寻觅,心灵的创痛也永无平复之日,纳兰心中的愁绪怕是再也无人问津。
“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浣溪沙》)、“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闲教玉笼鹦鹉念郎诗。”(《相见欢》)、“唱罢秋坟愁未歇, 春丛认取双栖蝶。”(《 蝶恋花》)。类似于此的诛心之句在纳兰的爱情词中随处可见,感受到词人痛失爱妻、爱而不得的悲痛之余,这字字句句中的情真意切更令人为之动容。自此“天咫尺,人南北”(《天仙子》),鸳鸯戏水又与其何干,从此唯有愁思相伴。
(二)家国之患
清初,清王朝政权建立前期并不牢固,边塞之地战乱频发,经过较长时间的战乱纷争,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在几年的侍卫生涯中,纳兰一直奔忙在康熙左右,不时随驾出巡,所到之处大多耕地荒芜,田园废弃,百姓民不聊生。王朝迭代,兴亡之间于平民百姓而言是毁灭性的灾难,于达官显贵而言也是不可预测、不可违背的,那么自己眼前的将相豪门、荣华富贵都只是顷刻间就可灰飞烟灭的虚幻之物,对比之下,一种空幻的兴亡之感便涌上心头,也因此,他写下了不少抒发兴亡之感的词作。
这首词作于公元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春,那年纳兰随康熙帝向东巡视至松花江一代的满族发祥地。七十年前的这里,满洲族在战火纷争中孕育并发展壮大。七十年后,纳兰来到这血战之处,想必当年这里也是极尽辉煌的城池,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今却只剩军垒遗迹,兴废之间,又有几人能够言说明了呢?
面对古戍、荒城野雉、残灰、碧血等凄惨悲凉的大漠荒芜之景,纳兰内心不禁悲戚感慨,悲观宿命论跃然心头,往日的英雄、玉帐皆已成非,天命不可违背,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世间的纷争又与我何干,兴亡之间早已成定数。
想必如今盛极一时的清王朝若干年之后是否会“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满庭芳·堠雪翻鸦》)。
随着人生经历日渐丰富,纳兰明白人生之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成了纳兰心中极对抗的矛盾感,这种无法化解的冲突与对立只能演变为其内心的忧虑,忧国忧民,忧心不已。
(三)忧友患己
古来颇有才学之人多高洁傲岸,知音难觅,但难觅不等同说毫无可觅之人,如高山流水一般。因此,一旦彼此双方意气相投便会更加的心心相惜,这种相投和相合之处往往无关年龄、家世、地位等客观因素,大半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契合,多表现为才学上的相互器重、内心思想层面的相互理解等。纳兰与其友人便是如此,思想的高度契合,人生境遇的类似使纳兰与其众多友人一见如故,自此便互为彼此心灵的慰藉。
纳兰极其看中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尤其是在爱妻亡故之后,其心多寄托于友情之间。无奈天不遂人愿,这些江南才士时时漂泊,或南归奔丧,或走马上任,奔赴他乡,或被贬一方,难得相会。种种人生无奈常使他患得患失,惆怅不已,抒发此间情感的赠别之作也不少,如《菊花新·用韵送张见阳令江华》:
虚实相生之间将纳兰对见阳的不舍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既然我不能随你而去,如若“有几个征鸿”为伴,想必也能为你解闷,也是极好的。
友人的境遇使礼贤下士的纳兰郁郁不平,在词作中纳兰多处提及劝慰友人之言语如“且由他、娥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且以此句为安慰,“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化用杜诗之意,慰藉友人彼此之间青眼相对,在大有可为之年不必悲伤,应振奋精神。然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劝慰之余,于纳兰自身而言更多的却是忧患与懊悔。
提及自己的境遇,纳兰便是万般忧愁,此般无奈也只能与友倾诉。面对多才之士大都沉沦下僚,鸡犬却多得道升天,便写出了“御沟深、不似天河浅”“空省识,画图展。高才自古难通显。”“冰霜摧折,壮怀都废”等词句。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词人在愤慨之余,只能走上消极遁世的道路。纳兰不喜官场琐事,然“一身还被浮名束”,侍卫之职看似光鲜,其中冷暖却无人知晓,对“倚柳题笺,当花侧帽”安闲自适生活的渴望也只能与词一起呈寄友人一叙深隐的衷肠。
综上所述,荣华富贵、车马轻裘于纳兰而言就像是一副无形的枷锁,将纳兰与其向往的以山泽鱼鸟为伴的逍遥自得的生活生硬的割裂开来。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为仕途忧心不已的纳兰本以为妻女与友人能够为自己一解心头的苦闷,但造化弄人,相伴不久爱妻便撒手人寰,所恋之人也了然无果。雪上加霜的是知己友人也大都遭遇不顺,有心却无力的纳兰只能借助文字抒发心迹。将而立之年的纳兰便已看尽人间冷暖,坎坷的人生际遇将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少年心志消磨殆尽。内心对于向往生活的美好愿景与残酷冷漠的现实之间形成的矛盾感成为了纳兰心中一粒石块,无法消解。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识》中曾有云:“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正是这内与外的矛盾冲突致使纳兰的性情与往日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也是其词作中满目凄清,充满对于家国、友人、自身等方面的忧患之感的原因。
①方红心:《试论纳兰性德的感伤词》,《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1期,第56-60页。
②寇宗基:《纳兰性德对中国华夏文化的倾慕和求索》,《晋阳学刊》1998第5期,第77-81页。
③(清)纳兰性德撰,张秉戍笺注:《纳兰词笺注》,文津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