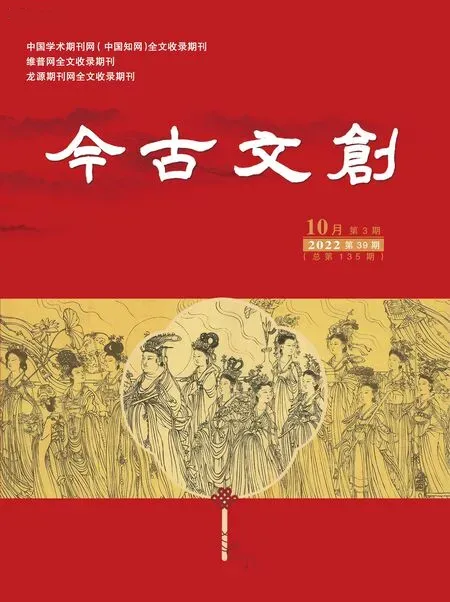本真性时代的两条退路 : 《庄子》哲学研究
◎施浩东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世界赤裸地横亘在眼前,事物亦坦然地展示着自己,人居其中,却不免茫然——存在无言,人当如何处之?不知道正确答案,不知道游戏规则,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迎来终点,但哪怕如此,当人第一次发出此问,第一次试图为世界寻求解读之时,世界已为人而变。价值的齿轮轰然旋转,将整体的世界分割为人文的世界,朴素的生存转化为多彩的生活,寂静的时间流转为属人的历史——自然变成了一场找不到规则和尽头的人生游戏。
有人试图为自然、为社会建立绝对律令,他们相信自己知道规律是什么,相信自己的理论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最优解,并开始为自己的学说公然辩护,要求他人服从于既定的规则。不同的人建立了不同的价值与规则,于是产生对抗与争端,是非与真伪。又有后来者,由此是非对抗代代无穷,周而复始。
对于这一类玩家,我们不妨将他们归纳为对永恒与必然性的追求者。但此外,还存在另一类玩家,他们坚持一种“零视角”,反对这样或那样的律令,拒绝忠于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认为矛盾与偶然是这场“人生游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又以庄子哲学尤为典型。
长期以来,前者都在我们的历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都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解释世界的一切,相信世界确实存有一种真实。但时至今日,科学与社会的发展正让这个观念似乎变得越来越可疑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的物理学大厦,基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我们永远无法同时测量到电子的动量和位置,甚至能量E和时间T也是此起彼伏对我们永远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事物的深层状态,如量子层面的微观状态,总是呈现出一种不符合逻辑的不确定状态——对于必然的追寻似乎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只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世界。更值得怀疑的是,生活世界变化万殊,基于一定时间条件的律令永远无法穷尽生活的变化从而暴露了其局限性所在。在智能时代的背景下,随着信息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个体的话语权被前所未有的放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来自外界强加于人的社会模式——通过政治权威、长辈教诲、宗教等方式所强加于人——扼杀了人的独特性、独立性与创造性。他们要求从强加的社会角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回归或者说创造出真实的自我意识。如查尔斯·泰勒所宣称的,对传统社会角色及伦理的反抗引导向了一个彻底的“本真性时代”。在本真性时代,政治和权力不再高悬于苍穹之上主宰一切,人类对自由的向往,正是庄子哲学新的生命力所在。
因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重新讨论庄子哲学不仅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以其恢宏奇诡的文字深刻地批判了对绝对律令、绝对价值的一味强求所带来的恶果,并为身处于本真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两条退路。
一、超然本性的丧失
在庄子看来,在人之初,人的本性是与道为一的,人类之初的至德之世是最理想的和平治世,此时的人类亦不必纠结于自身的意义问题。其后,随着成心的形成,世人将完整的世界区分成了彼我、始末、是非、尊卑、胜败等等分界,于是终日争辩不休,钩心斗角,劳心疲神地沉溺于无用之辩中,人也就背离了道,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沦落为有待的对象了。
对于成心,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这里的“成心”陈鼓应先生将之解读为成见之心,但笔者认为韩林合先生的解释更为恰当—— “完成了或成熟了的心,即有了完整的心里官能(认识、感受和意欲等)的心,而非特指成见之心”。韩林合先生进一步指出,“成心”正是是非之分的基础,因此也可以称为“是非之心”。正是在这种是非之心中,“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显然,在这一段文字中,庄子将批判的笔锋直指儒墨二家。正如前文所言,如果将庄子视为道家“零视角”玩家的代表,那么在这场人生游戏中,儒墨二家显然是信奉律令并视自家之言为唯一真理的玩家代表。在庄子看来,儒门也好,墨家也罢,他们的理论都是不具有绝对性的,二家之争辩皆不过是成心而已。换而言之,这种对人生游戏规则的寻求与辩护是无意义的,其结果只是成心四起,人沦入是非的无谓争端中。
在《应帝王》的结尾,庄子用“倏忽凿窍,七日浑沌死”的寓言的方式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来自成心的异化对人的本性的摧残,庄子将这个故事放在七篇《内篇》等末尾,可见其重要性。如憨山德清所指出的:“此倏忽一章,不独结《应帝王》一篇,其实总结内七篇之大意。”对浑沌的解读颇丰,一般认为浑沌指向混同、自然的原初状态。庄子将其尊为中央之帝,亦是彰显了庄子对这种状态的推崇。原初的浑沌无有七窍,亦无须视听,此时的浑沌是完满的。但倏与忽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七窍视听是人皆有之的,出于一种报恩的善意,倏忽为浑沌日凿一窍,结果就是浑沌七日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杀死浑沌的过程并非是凶恶的魔鬼与刀兵,而是一种仁慈的善意。开凿七窍的过程并非一日之短,而是用时七日,可见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化过程。简单地说,原初的浑沌不具有七窍,因此也不具有人的种种是非区分,不具有属文明人的社会性,而倏忽的目标就是把浑沌改造成一个社会性的成员——一如以儒墨为代表的规则寻求者将社会角色与规范强加于本真的人。当浑沌的改造被完成的那一刻起,原本的非社会性的浑沌就已经死亡了,同理,当社会改造完成之时,人也就与完满的道相分离了。
《浑沌之死》作为一个悲剧神话,不言而喻的,庄子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原初状态无可避免地丧失的失落。从寓言的角度来看,这个丧失的过程正是人不可避免地走向文明的过程——对规则与智识的追寻让人的单纯被剥夺了,人的天真被扼杀了,人因规则而产生种种是非区分、步入文明社会,但代价就是完满状态的消失。显然,庄子把这个过程视作是人的不断堕落的过程,而面对这种堕落,如何消解也就成了《庄子》全书的主题之一。
在《齐物论》的一节中,庄子对这种丧失了本然之性的状态做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在庄子的视野里,丧失了本然之性而圄于成心之中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整日钩心斗角、形体不宁,沉溺在是非与所为所构成的牢笼之中,种种情态日夜交侵却又不知所以。他们的生命失去了生机与意义,他们的心灵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更可悲的是,大多数的人津津有味地过着麻木不仁的、丧己于物的生活,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是缺乏意义的。
那么,既然对规则的寻求、对是非的执迷、对经验的迷信等种种成心造就了人生的种种困境,从庄子的视角出发,我们又当如何超越成心,复归于道而得到解脱呢?
二、退路其一:齐“物论”
如前文所言,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人类愈发感觉主流的思维模式造就了种种人生困境,以儒墨二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永恒的追求,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绝对律令的向往反而使社会危机常常发生;相反,肯定相对,以一种“零视角”游心于人世间的庄学反而在这个本真时代为人类打破主客樊笼提供了一盏明灯。在《庄子》一文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两条退路,以使人消解成心,从而复归于道。
庄子向我们阐释的第一条退路就是齐“物论”。既然人心中的物我、是非、真伪、善恶、贵贱、生死等种种成心造就了人与道的分离,使人的本真被异化了,那么,要回归于道,首先要做的就是齐“物论”,也就是放弃被社会规则所蔽的种种是非俗见,从规则的建立者给人强加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庄子看来,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绝对是非区分界限可言。
在《齐物论》中,庄子对齐“物论”做了详细的说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在庄子的论证中,人首先将彼此绝对地区分了开来,在彼此之上建立起来是非之别,并以此之是来否定彼物之非。但是,这些是非彼此都是相对的,彼此都是相对而生,彼此随起随灭,方可方不可。庄子得出结论,彼与此实际上是相同的,彼就是此,是就是非。为此,庄子要求从这种是非区别中超脱出去,将这些都看作是相对的甚至虚假的。若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达到了“明”的境界。
对此,劳思光先生的阐释颇为精彩,“一切理论系统相依相映而生,又互为消长,永远循环;如此,则理论系统之追求,永是‘形与影竞走’,自溺于概念之游戏中。倘若心灵超越此种执着、而一体平看,则一切理论系统皆为一概念下之封闭系统,彼此实无价值之分别。”
正是因为封闭系统的概念实际上没有价值分别,因此,在庄子看来,以儒墨二家为代表的规则建立者把自己的理论视作唯一的是非标准并在此之上建立道德体系、社会规范的做法是极其危险与有害的。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忘掉是非分界,自然就会把社会名声看作是桎梏而已,更不会陷于对其的追求而丧失本真了。也就是“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
通过齐物论,庄子成功地消解掉了规则建立者们的塑造的理论基础,打开了种种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对人的自我的禁锢,为人的心灵找到了一个通往逍遥的避风港。
但对外部规则的禁锢下解放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的,一方面,这种解放让人的本性得以舒展,人的自我得以张扬,但另一方面,这种解放的副赠品往往是对自我的沉迷。一如德安博对反讽主义者的阐释,当他们看透了规则、是非中的偶然性与相对性,从社会约束和道德律令中抽身而去,将自身与社会角色相分离,他们将怀疑一切的合法性,其结果就是从社会领域退回到个人领域。从正面来说,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带来的是强烈的自我创造的需求与实践,这种力量对于一个现代的、成熟的民主政治团体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从负面来说,这种过度高昂的自我意识往往将他们推向社会规则的对立面。显然,这种尝试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对于庄子所处的年代而言,战乱频繁,社会体制尚未成熟,对自我意识的过度渴望并不利于个体的生存,更难以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保持开朗与从容。
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研究者认为庄子式的角色是作为乌托邦式的反讽主义者,如德安博语,“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种道家的模范是一种‘承受外部压力、只对自己真实、专注永久自我探索’的角色,它强大到足以在可能异化的社会中形成一种身份,从而实现‘自我创造’。”
但显然,庄子笔下的人物并非是如此的“强者”,一如他在《德充符》中塑造的诸多形不全之人、在《人间世》中塑造的“无用之木”,恰恰相反,庄子笔下的道家圣贤往往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种矛盾形象的塑造正是庄子向我们展现的第二条退路——对自我的消解。
三、退路其二:吾“丧我”
在庄子的笔下,有许多寓言的内容都是与个体面对残暴的、险恶的社会权力的危险性相关的。如在《人间世》中,庄子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颜回向孔子辞行,他准备访问卫国,以自己所学去改造卫国的残暴君主。此时的颜回可以说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他并非被上级指派,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力图去改造世界。但这种尝试是危险的,面对颜回的请行,孔子的答复是“若殆往而刑尔!”从庄子的角度来看,颜回显然已经被儒家的规则道路所束缚,通过对“善”对追求来肯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力图以儒家礼义去改变卫君的做法本就已经落入了是非取舍的有待境界。但这个问题在这里并非是我们的首要关心对象,我们更关心的是,即使是那些看透了是非规则的相对性,从而从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的人,当他们从外反内,专注于自我,以自我对抗外部压力之时,他们面对的困境实际上和出使卫国的颜回是相似的——个体的脆弱让他们面对社会权力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借孔子之口,庄子给出的答案是“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首先,孔子要求放弃听之以耳,而是听之以气。对于这个气,陈鼓应先生将之解释为“心灵活动到达极精纯的境地。换而言之,‘气’即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通过这种境界,最终产生一种“虚”的心境。
对此,颜回问道,“未始有回也”的状态是否就是“虚”的境界。对此,孔子予以了肯定。也就是是说,对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而言,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招致的危险境地,他们的答案是对主体自我的主动消解,可谓是自我的“虚”。
然后孔子进一步解释了一个完成了心斋的,或者说虚己的人是如何行动的,“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适应任意一种社会境况,扮演任意一种社会角色,他们随环境而采取适当的行动,而不被危险所萦绕。通过“心斋”的虚己,他们能够从容地游心于这个世界。
在《齐物论》中,庄子将这种虚己的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也就是开篇所提到的“丧我”—— “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对于“吾丧我”,陈鼓应先生将之概括为“摒弃我见”,也即是要通过将成心之我、偏见之我的摒弃,来达到忘我、与万物同为一体的本真状态。
在这里,“吾丧我”之“我”实为主体之自我,亦即自我中心的观念,所谓“丧我”也就是要取消自我中心主义,消解掉主体之自我,从而避免以己之所是为是,以彼之所是为非,自以为是地将自己与他者隔绝开来的做法。
自我中心消解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自我与社会角色间矛盾的消解——他们不再为了自我创造而对抗社会,而是从容地悠游于社会角色、社会规则之中。我们不能因此而斥责他们虚伪,事实上,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其本身可以说是空无一物,却又真实地、不加修饰地反映出他所面对的一切。
更准确地说,通过“丧我”,庄子建立了一种颇为“空虚”的角色,他们不追求功名利禄与是非规范,忘我地如水面一般随风而动,悠然自得在社会规范中穿行,洒脱地在各个社会角色与规则间切换。德安博将这类角色称之为“真实假装者”,即与真实自我无关的、完全偶然的社会角色扮演者。对这个观点,笔者保持认同。
事实上,对于这种“丧我”者对于不同社会角色的扮演、适应能力,《庄子》书中多有暗示,如《大宗师》中,“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庄子以夸张、吊诡的手法隐喻了“丧我”者在面对环境变化而切换社会角色的能力——若化为鸡,就打鸣报晓,若化为弹弓,就打鸟捕猎,若化为车马,就乘它而去。所谓“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入火不热,沉水不溺”,正是庄子对这种境界的艺术性描述。
四、总结
总的来说,庄子通过“齐‘物论’”与“吾‘丧我’”两条退路,帮助我们在这个本真时代保留了复归于道的可能。两条退路又互为递进,从而构成了这种理想人格的多维性。可以说,庄子将人分成了三种,我们可以将之分为“成心者”“齐物者”和“丧我者”三个境界。
“成心者”,也就是常态意义上的大众、凡人,他们被种种外界强加的是非、真伪、彼我规则所束缚,终身籍籍于成心之中,迫切地把外在社会人格内化于自身却不知自身早已与道背离,在被异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这种人在庄子看来最为可悲。
“齐物者”,也就是能达到齐“物论”境界的人,他们以相对性消解了外界是非界限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往往转而追求自我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从而从种种社会桎梏中超脱出去。其结果常常是自我意识的高扬,这种人面对强势的社会权力是危险的。
“丧我者”,这种人建立在“齐物者”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只有“齐物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丧我者”。他们既凭虚己以遨游于世,从容地游走在权利的刀锋之间,又能从成心桎梏中解脱而去,他们无为而又自然,是真正的圣人、真人与至人。
不同于我们历史上的先辈们,身处于“本真性时代”,时人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外在强加的主流价值观、文化环境、社会要求等所带给人之本真的种种异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发展,个体的话语权在空间上被空前放大,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虚拟空间里充当信息的造物主形态,其所带来的诸如狂妄自大、执迷不悟、肆意地以一己之见对他人口诛笔伐等等不良后果更是屡见不鲜。那么,庄子通过文中的两条退路像我展示了一种“关于如何以没有目的的方式巧妙地漫游于世间的哲学”。
一方面,这种哲学帮助我们从狂轰滥炸的信息狂潮中暂时抽身而去,避免我们的本真被其裹挟而死亡。另一方面,这种哲学也至少告诉了我们,如何周旋于社会处境中——如同一面镜子——从而免受伤害。
①⑫⑬㉑汉斯·格奥尔格·梅勒、德安博:《游心之路:庄子与西方现代哲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5页,第50页,第190页,第193页。
②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36页。
③⑥⑧⑨⑪⑭⑮⑰⑱⑲㉒㉓㉔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页,第34页,第27页,第35页,第113页,第73页,第80页,第81页,第81页,第24页,第143页,第126页,第290页。
④⑤翰林合:《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第22页。
⑦憨山德清:《庄子内篇注》,香港佛经流通处1997年版,第299页。
⑩劳斯光:《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216页。
⑯⑳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0页,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