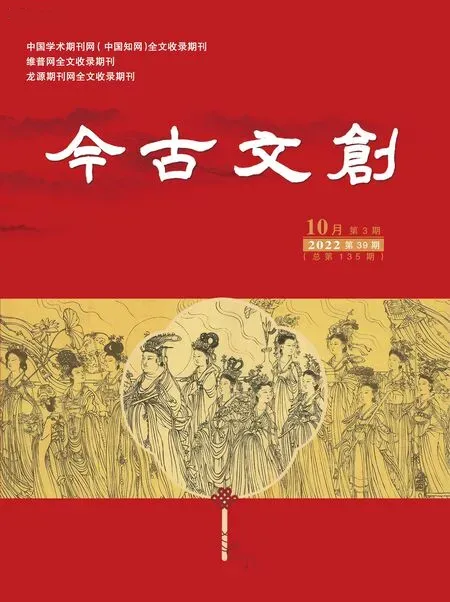论《茶花女》与《羊脂球》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来源
◎楼玲妤
(浙江树人学院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小说《茶花女》讲述了巴黎上流社会一位有名的交际花玛格丽特与贵族公子阿尔芒从相识、相恋,最后被迫分开的一段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羊脂球》讲述了妓女羊脂球与一行与她社会地位差距悬殊的人乘坐同一辆马车从敌占区逃亡途中发生的故事。本文将从两位女主人公所处的父系社会、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理想追求这三个方面比较分析她们悲剧命运的来源。
一、父系社会
(一)外表出众
在父系社会里,女性是否美丽取决于男性的审美愉悦程度,男性力图把女性美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中,女性之于他们,只是生理层面的物品,是性对象,因而女性的容貌与身材成了美丽的基础条件。
《茶花女》中,以男性视角对玛格丽特进行的外貌描述正反映了这一点,“她身材颀长,窈窕得有点过度……”“在一张艳若桃李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黑眼睛,黛眉弯弯,活像画就一般……由于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鼻翼有点向外张开……皮肤上有一层绒毛而显出颜色,犹如未经人的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一样。”处女般纯真的面孔、性感的身姿,完全符合当时男性对女性美的创造要求,也是玛格丽特能成为巴黎名妓最基本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她悲剧的最初来源。
而《羊脂球》中也有类似对伊丽莎白的描写,“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说明羊脂球的美丽是天然的,并不是通过精心打扮而显示出来的,正因如此,她才被普鲁士军官看上而最后不得已委身于他。
(二)特殊职业
父系社会几乎将女性极端地划分成了“贞女”和“荡妇”两种类型。
《茶花女》中,阿尔芒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已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玛格丽特,转而带着对妓女的固有偏见,要求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的前途以及他们整个家族的声誉着想而主动离开阿尔芒,“您爱阿尔芒,您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向他证明您的爱情,即牺牲您的爱情,成全他的前途”,并且以重操旧业为借口让阿尔芒误以为她是由于放不下钱财,贪恋原先巴黎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生活才离开的,最终导致玛格丽特在阿尔芒不明原因的谩骂和诋毁声中含泪而死。这体现了在父系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阿尔芒父亲的出现打破了玛格丽特因被阿尔芒打动而想要重新开始平凡生活的梦;男性还以自己的偏好衡量女性的贵贱,而划分的标准往往依赖于表面现象而不是女性身上更加深刻的品质,阿尔芒父亲否定的不单是玛格丽特个人,而是妓女这一群体,他固执地认为,“上等人和情妇之间只能是买卖关系,绝不能产生真正的感情,不然就会玷辱门楣,断送前程。”
《羊脂球》中对当时社会看不起妓女的现象更是通过几位贵族太太的言行举止表现得淋漓尽致,“好像她们觉得,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卖淫妇面前,她们必须团结一致,把她们做妻子的尊严显示出来才行,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高于放纵的私情的”,她们不但看低羊脂球,还联合起来在私下里辱骂她,认为她是婊子,是社会耻辱。如果说前面《茶花女》的部分展现的是父系社会下男性对女性意志和行为的绝对操控,那么从这里人们看到了那些依附于男性存在的上流女性身上的自私和冷漠,她们用“男性的语言、观点和思想概念、评判标准来攻击或诋毁女性。”
(三)抗争的不彻底性
起初的玛格丽特由于长期在公爵的包养下生活,听惯了花言巧语、看尽了人间冷暖,潜意识里早已默认自己是男性随时可以抛弃的玩物,本身放弃了自己作为女性在男权控制下的抵抗。而阿尔芒深情地告白和无微不至地照顾唤醒了她心中对真爱的憧憬和向往,她为了爱情背上沉重的债务,不惜变卖贵重物品离开巴黎跟随阿尔芒到乡下重新开始生活,勇敢追求生活与爱情自由的行为,体现出玛格丽特身上的抗争性。但在后来面对阿尔芒父亲无理的要求时,她并没有显示出顽强的抵抗,而是以舍弃自己的幸福为唯一选择,最终维护了阿尔芒的前途及其家族的声誉。这些情节反映出在父系社会下“母系氏族因没有形成女性可以传承的文化系统,没有形成完整的意识形态,即使有部分象征性标记存在,也只能以零星的或者是隐形的方式散落在父权文化系统中的边角,被后来者忽视。”玛格丽特不但肉体不受自己掌控,在精神上也显示出了屈从于男性意识的倾向,可以说她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有余,但坚决抗争的战斗信念不足,因此,在阿尔芒父亲的威权话语面前,只表现出了短暂的、不彻底的抗争。
与茶花女相比,羊脂球的抗争精神则多了些坚决性,不仅体现在她伟大的爱国情怀与高贵的民族气节上,也表露于她面对他人辱骂以及拒绝男性时的态度。羊脂球的反抗在文中第一次出现于听到贵族太太对她的谩骂后,“她以大胆而极富挑衅的目光扫视了她的这些邻座”,她的行为随即就取得了效果,“于是车厢内马上肃静下来”。
与马车上的其他人不同,她是由于反抗普鲁士士兵的蹂躏,几乎掐断了那人的脖子,为了避免被捕才选择逃亡,而当民主党人高尼岱之后的痛骂伤及了她崇拜的拿破仑皇帝时,她“面色变得比野樱桃还红,气得说话也结巴了”,毫无畏惧地予以了反击。
当高尼岱趁着夜色想要猥亵羊脂球时,他被她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拳;当得知普鲁士军官想要占有她后,她坚决地拒绝了,回到车上“脸涨得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然而作为本身就缺乏话语权的女性,加上妓女的身份,在面对男性的绝对权威与众人的压迫时,羊脂球的反抗又显得单薄无力,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
二、性格
(一)善良
玛格丽特虽然因现实所迫从一个美丽纯真的农村少女沦为了权贵们的玩物,但她身上“来自下层人民的纯朴善良的精神光辉始终未被泯灭。”玛格丽特看着阿尔芒为了报复自己故意牵起另一个漂亮妓女的手而感到伤心欲绝,但却始终都没有告知阿尔芒实情,任由他误会。玛格丽特不愿知道实情的阿尔芒会又一次不顾一切地要和她在一起而误了自己的前途,也不愿让他记恨于父亲。病痛的折磨,相思的苦楚,难言的委屈,她把一切难熬的苦难都留给了自己。
玛格丽特的善良还体现在她典当首饰支付她和阿尔芒的生活费却不准别人告诉他;又像文本最后写到,“看见哥哥回来,她笑容满面,这个纯洁的姑娘一点也不知道,仅仅为了维护她的姓氏,一个远方的妓女就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玛格丽特在自己和阿尔芒妹妹的幸福之间,成全了后者。
与羊脂球坐在一辆车里的都是体面的上层人士,相比之下她只是一个身处底层、受人歧视的妓女。途中马车因风雪耽误了行程,附近又没有饭馆和小店,没有事先准备食物的人那时都已饥肠辘辘,开始惺惺作态搭讪和暗示羊脂球。羊脂球面对一车看不起她的人依然表现出了她善良的本性,慷慨地拿出了自己本来预备用作三天旅途中吃的食物和大家分享,以德报怨。然而这只换取了其他人短暂的和善,随着食物逐渐被瓜分殆尽,很快人们对她又恢复了之前的冷淡。
当普鲁士军官以过境为要挟提出要羊脂球陪自己过夜的条件时,她成了所有人平安离开的关键,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让马车上的人愤愤不已,因为大家都很自私,害怕她这种行为会引起灾难,并利用她单纯赤忱的爱国之心以种种伟大的理由规劝她前去。然而众多女英雄的感人事迹都没能使羊脂球动摇,直到修女以着急前去救助生天花的法国士兵为理由打动了善良的她,最终应了普鲁士军官的要求。此外,过程中车上的其他妇女在心里暗自嫉妒和较量为什么被叫的人不是自己的心理,体现出她们“披在身上的那层薄薄的羞耻布只能掩盖她们的外表”,在身份地位和现场表现的反差对比下,更凸显出羊脂球的坦荡和上流人士的虚假。
善良的羊脂球不愿一行人遭难,更不忍心让众多的法国士兵得不到救治,强压着自尊把自己献给了普鲁士军官,可当她第二天回来时,那些说过不会忘记她的人们全然换了一副模样,所有人都装作不认识她,就算是她主动打招呼也无人回应,甚至像躲避灾祸似的避开她。到中午大家都拿出了从旅馆中带出来的食物开始享用,根本没人顾及由于匆忙上车什么都没有准备而饿着肚子的羊脂球。
羊脂球的两次牺牲并没有得到上流人士的感谢,也没能唤醒他们泯灭的良知或拯救他们自私的本性。羊脂球最动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因为自己被伤害而反过去伤害别人,她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一次又一次地怪自己傻而感到气愤和羞愧,她并不是不知道与自己同车的是怎样一群丑陋、虚假的人,但当选择再次来临之时,依然坚定地选择站在良善与奉献的那一方。
(二)软弱
玛格丽特的软弱在“抗争的不彻底性”的部分中已经可见一斑,至于羊脂球,她此前已经慷慨地与大家分享过食物,但当自己饥肠辘辘却没有人理睬她时,她理应可以要求其他人和她分享食物,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在车厢中悲愤地哭泣,从这点上看,羊脂球的性格中也存在着软弱的一面。
(三)自卑
玛格丽特是由于出身贫苦,流落巴黎而被逼为娼,并非真的喜欢性带来的热烈与快感,但在小说里她的话语却处处透露出她对自己身份低贱、只能任人摆布的观点的认同,“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他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所以在选择面前,玛格丽特自动放弃了她作为女性天然拥有的选择爱、追求爱和享受爱的权利而成全了别人。另外,也正是自卑导致了她的软弱,也许从根本上玛格丽特就不认为她与其他所谓的正常女性一样可以去竞争以守护自己想要的东西。
羊脂球愿意相信“只要动机纯洁,行为总是可以被原谅的”这一说法,根本原因是她内心有因妓女这一职业形成的罪恶感,她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渴望通过善举使上帝宽恕她的过错,进行自我救赎,这点从她在旅途被困时还要去参观婴儿洗礼的行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三、理想追求
茶花女追求两性关系的自由与平等,这是她对于真正美好爱情的基本诉求。长期依靠出卖肉体获得公爵的钱财来维持生活的玛格丽特清醒地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悬殊差距,她把男性当作自己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提款机,而她也只是男性释放性欲、满足虚荣心的工具,知道自己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被无尽物化却无力改变。因此在过去的时间里,玛格丽特认为“如果要我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反而会死去,现在支撑着我的,就是我现在过的这种充满狂热的生活”,所以她肆意挥霍着法郎,用各种名贵物品来逃避和填补自己精神世界的空虚。
而阿尔芒的出现——一个会真心爱护她的人,他善良体贴,会悄悄打探她的病情;看到咳嗽不止的她会用乞求的语气希望她保重身体;甚至会因为她的病痛落泪。这让玛格丽特拥有了抛弃过去,走到物质生活的对立面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勇气,并向阿尔芒提出要“信任我,听我的话,而且不多嘴”这样的要求,说明她认为双方地位平等、互相尊重是开展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的基础。
羊脂球则有着与茶花女全然不同的理想追求,爱国主义情怀是她行动的底色。小说的创作背景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法国军队在遭到普鲁士士兵的强力打击后,不久便宣布投降,很多人由于看不到希望而选择弃城逃跑。羊脂球因为无法忍受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及此带来的耻辱,差点掐死了一个进驻她家的士兵,无法在当地继续生活而被迫逃走,相反,与她同行的九个人则都是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而离开。为世俗社会所不堪的妓女,却是马车上唯一一个因为与侵略者抗争而不得不离开敌占区的人,这使那些表面上风光无限的上流人士黯然失色。
此外,羊脂球认为自己多少代表着祖国而在普鲁士人面前显露出严肃高傲的气概,也显示出她强烈、自觉的爱国意识。她拒绝民主党人高尼岱的求欢,气愤于普鲁士军官的无理要求,体现了一个普通的法国人真挚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茶花女与羊脂球都生活在畸形的环境里,由于妓女身份而不受人尊重,不同的是前者在绝望中追求爱情自由,后者则在毁灭中坚守民族大义。
四、结语
正如《茶花女》里所说:“人世间的这些悲剧,却往往又是在维护某种道德规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茶花女和羊脂球都生活在男性具有绝对权威的社会下,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因为身份的特殊性而处处受人歧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又由于她们内心始终坚守着美好的人生理想,表现出的善良、软弱、自卑的性格最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朱立元先生曾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他不仅指出了悲剧对于人的灵魂的净化作用,而且抓住了人们在欣赏悲剧时所经历的由消极情感(怜悯与恐惧)到积极情感的转化过程。”茶花女和羊脂球所遭受的痛苦的根源并非她们的罪恶,而主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身份,这两部作品在创作时间上虽然相隔了32年,却同样展现了在父系社会下性格相似的两个妓女心中的理想被残酷现实反复打磨以致破灭的悲剧性遭遇,不仅使人产生了对她们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黑暗现实的痛恨之情,与此同时,更激发起了与邪恶势力抗争的勇气,因此它们才能在时间的长河里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