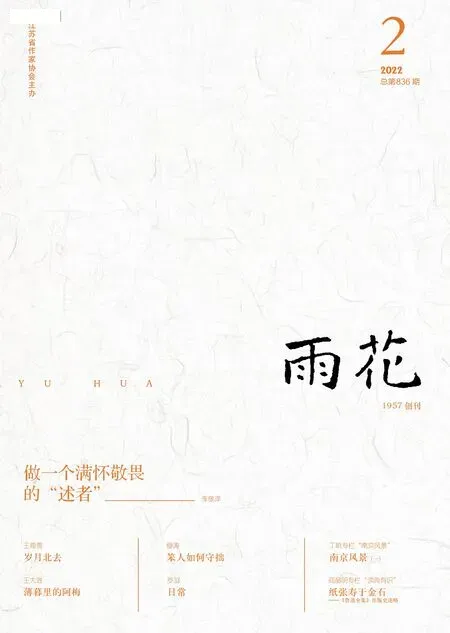阳台上的菜
施 勇
沈汉文醒来时,窗玻璃正泛着暗蓝色。迷糊间,有一声鸟鸣响起,“接哥接姑去”,沈汉文竖起耳朵用,那鸟鸣却没了下文,这使得天地间显得越发空寂。他叹了口气,起来将洒水壶接了水,去阳台。
这儿并不是沈汉文自己的房子。他的房子原本在乡下。年前,政府规划几个建设项目,选址落在了他们村。拆迁手续办完之后,各家揣着补偿款开始搬家。因为安置房尚未建成,村里年轻一点的,便都到城里租房子。老人呢,大多要投靠子女。按理,沈汉文也应去城里,跟儿子儿媳一块儿住。早几年,老伴刚去世那会儿,儿子沛林就说要接他去城里,他不肯。一是儿子家在五楼,爬上爬下的嫌麻烦。二来两辈人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处,难免磕磕碰碰。多年来他与儿子一家,尤其与儿媳之间,一直客客气气和和睦睦,这当中除了相互尊重,还因为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儿子儿媳平日工作忙,只有周末的时候,带点水果和肉菜过来,一起吃顿饭,热热闹闹,这样挺好。沈汉文认定,但凡生活可以自理,还是一个人单独住来得自在。
如此,只有另外租房子。一开始,儿子物色的是车库。城里的房子,底层大多是车库,车库上面才是第一层。一般情况,楼上有一户人家,楼下就会配一间车库。除了停车,更多的是作为储藏室或厨房。很多老年人图生活便利,平时吃住都在车库。一间车库,一分为二。前半部分作厨房兼客厅,里面的一半摆张床,装个卫生间,就可以了。二三十平米的面积,虽不大,但不用爬楼,进出方便。儿子的意思不言自明,既然自己家的楼房不愿意爬,那肯定是住车库咯。
这样看了几家,都不能令他满意,说不上来哪儿出了问题,就是感觉不合适。
孙女琳琳打电话来,关心他的健康,说等放假了回来看他。沈汉文回应着,忽然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他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
他跟儿子说:“不要车库,租个套房吧,要有一间单独的房间。”
儿子眼中闪过一丝不解,接着回答:“好。”于是带他去看套房,新的,他嫌租金贵。转而选旧房,有一套位于老城区的旧房。一楼,五十平米,有厨房、卫生间,一个客厅、一个房间。他很满意,便住下来。
为什么非要租套房,他没有解释,不知道儿子怎么想,会不会把他当成《都挺好》里边那个尽给儿女添堵的苏大强?好在找房租房的过程,虽有一些曲折,但还算顺利。他也没有从儿子儿媳脸上看出任何不快。
搬进来后,沈汉文将客厅的沙发和茶几挪到窗边,空出来的位置,靠墙放了一张床。这样客厅也成了房间。他在另一个房间也摆了一张床,铺了被子。
他睡客厅的床,斜对着那台三十二寸的液晶电视。每晚靠在床头看电视,看苏大强住在小儿子苏明成家,上完厕所不冲水,身上有味儿也不洗澡。沈汉成不由得闻闻自己身上有没有味儿,心想:这位老哥的做派,不讨儿女嫌才怪。
沈汉文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到半夜里醒来,苏大强早已走了。他起来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才将电视关掉。继续睡,到五更又醒了。这次醒来就睡不着了,开了电视继续看,直到天光微明。
沈汉文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去阳台浇水。这套旧房有个开放式阳台,就在客厅门外,靠着南墙。在这个约摸四五平米的阳台上排列着五个没有盖子的泡沫箱,借助幽微的天光,可以看到箱子里种着绿叶蔬菜。肥厚的叶片填满了箱内空间。沈汉文摆动水壶,让细雨在几个泡沫箱之间来回均匀地洒过。那些菜立马鲜亮起来,叶面上汇聚的水珠参差滚落。
刚搬来那会儿,沈汉文挺忙碌。乡下房子在签约的第二天就拆了,当时菜地里扁豆、青菜、茄子长得正旺,人虽进了城,这些菜却舍不得浪费。好在离城区不远,电动车充满电,刚好能走一个来回。他便隔三岔五地去采摘。将菜带回来,给儿子送去一点,自己也留一点。项目开工后,地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此后吃菜就得上菜场买。拆迁前,几个老哥在一块儿闲聊,都说去城里开销大。如今,这说法正逐步被现实所印证。
用泡沫箱子种菜,是受了蔡老师的启发。沈汉文住过来才两个多月,认识的人不多,第一个就是蔡老师。那天搬完家,儿子和搬家公司的卡车都走了。沈汉文找了一块毛巾,给刚刚就位的桌子、柜子、茶几擦拭灰尘,这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头发灰白的清瘦老太站在门前,老太冷着脸说:“师傅,你们搬东西踩坏我的葱了。”
“哪里的葱?”
“就在楼下。”楼前是停车场,再外侧是草坪。老太领着他来到草坪前:“喏,就这儿!”
沈汉文一看,靠着停车场有一小块葱地,面积不大,长一米,宽半米的样子。这块地原本应该是草坪,铲平后被利用起来,种了三行小葱。小葱长得茂盛,看上去与旁边的麦冬草一样高。其中一行却被压烂了,上面的车轮印清晰可辨。沈汉文的脸立马烫起来,刚才卡车就在这儿卸的货。
“你们怎么开的车?”老太埋怨道,“素质这么差!”她的声音不高,却有一股令沈汉文无从辩驳的气势,让他想起了苏大强的老婆赵美兰。
沈汉文挠了挠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赔你嘛。”
第二天,沈汉文就从菜场买了一把葱,补种了进去。不想一周后,物业公司派人将小区绿化地中所有的菜清除,补上了麦冬草,说小区绿地是不允许种菜的。
沈汉文有些遗憾。“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赔了。”那时,他与蔡老师已经熟悉了。知道她退休前是城区小学的语文老师,老伴去世后,她将楼上的房子租了出去,自己住车库。
“犯了错误就得改正,这不是赔不赔的事。”蔡老师永远这么正义凛然。
当然,蔡老师也改正了,她改正的方式是将小葱种进了泡沫箱。泡沫箱中的小葱虽不及地里长得肥,可蔡老师打理得好,看起来倒也翠绿壮实。
沈汉文从中受到了启发,从外面捡回来五个泡沫箱子,填了土,沿着阳台由东至西高高低低摆上一队。四五平米的空间就成了小菜园,青菜、菠菜、韭菜、生菜、大蒜,一个箱子一个品种。撒下菜籽,定期浇水、施肥,三五天,星星点点地有嫩芽冒出,不到一个月,已经绿旺旺一大摊子了。
今天,沈汉文起了个大早。想好了要去看望老郭,他就睡不着了。带点什么呢?一箱纯牛奶,上回儿子拎来的。儿媳晓莹总说“牛奶补钙,老年人要多喝”。可他不喜欢那个奶腥味,跟他们提过多次,不要再送来了。以前送来的,他也暂时存着,回头遇到亲戚朋友有个什么事,就转送出去。
再摘些菜吧。如今,菜场上蔬菜要比猪肉贵。听说,这两天菠菜都卖到了十三块钱一斤。浇完水,沈汉文在心里已将这五箱水灵灵的菜分好了,其中一份给老郭。
刚开始,老郭是住在儿子家的。他与沈汉文的想法不同,和儿子儿媳住一块,可以省下一个人的房租钱。老郭有两个儿子。房子拆迁时,大儿子家刚添了孙子,大儿媳要去儿子家带孙子。兄弟俩一合计,让老爷子先住小儿子家。老郭没多想,跟着就在小儿子家住下了。
没承想,住了一个星期,小儿媳就有了意见。这意见涉及吃饭的声响、睡觉的习惯、如厕的细节……琐琐碎碎,总之一句话,老爷子在家里,生活诸多不便。要么老郭搬出去,要么她搬出去。老郭一气之下,另外租了个车库,独自生活。
这件事让老郭的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他终于认可了沈汉文的想法。老哥们凑一块儿时,提起老郭的遭遇,大家长吁短叹,都认识到养儿防老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么顺理成章。好在各人手里都攥着补偿款和房子呢,不怕。
等老郭缓过了劲,沈汉文调侃他:“咋样?房租钱省下不少?”
“反正比你的套房省钱。”老郭接过沈汉文的烟,边点火边怼道,“一个车库管够了,我说你干吗要租套房?”
顿了一顿,老郭又说:“莫不是看上哪个城里老太了?”
沈汉文白了他一眼,说:“哪能告诉你啊?怕被你抢走了。”
“抢不走,抢不走。”老郭摇摇头,“你看我这车库,比得上你那个一室一厅的套房么?”
老郭嘴快,两个人聊天,总是老郭占着话头。可他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还钱的事。那五百块钱,沈汉文一直记着。三年前老郭向他借的。这次房子拆迁,拿到了补偿款,沈汉文想他总该还钱了吧,这样拖着算个什么事呢?每次遇见老郭,沈汉文总想当面提一提,却又抹不开面子。
现在倒好,老郭摔了一跤躺床上了,这事就更不好提了。
沈汉文停好车,从踏板上拎起牛奶和一把菠菜。看车库门虚掩着,推开。一只猫从饭桌上“嗖”地跳下,惊慌失措般蹿了出去。里边电视机亮着,苏大强正接听大儿子苏明哲的电话,儿子听说暂时不让去美国了,很失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干嚎。看电视的人半躺在床上没声息。沈汉文凑近叫了一声:“老郭。”
睁眼看见了沈汉文,老郭的一张脸立马生动起来,抹了一把下巴上的口水,摆手说:“坐、坐。”
沈汉文找了张椅子坐下,问道:“怎么样啊?”
“就一条腿不能动。”老郭的话不太清晰,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似的,又苦笑着解释,“不知怎么的,说话也不利索了。”
“谁照顾你?”
“两个儿子,轮流来。”老郭望了望门口,“今天大儿子,许是买菜去了。”
沈汉文看着老郭,感觉心里堵着什么。躺在床上的老郭,让沈汉文想起庄稼地里一根根枯黄灰瘪的玉米秆。被掰去了玉米棒子的秸秆,立在初冬的田野里,岁月的风吹走它们身上最后一丝水分。沈汉文甚至能听到玉米秆由内至外碎裂风化的声音。
“怎么摔的?”
“那天,半夜里上厕所,站起来太猛了,眼一黑,就摔地上了。”老郭缓缓说道,“后来,冻醒了。要爬起来,一条腿使不上力。抓着床沿硬是挪到了床上。”
“没去医院?”
“去了,那晚腿一直痛,熬到了天亮,打电话叫儿子过来。去医院拍了张片子,骨折了。”老郭掀开被子,指着被纱布层层缠绕、像树根一样粗肿的右腿膝盖,“这地方断了。”
沈汉文临走时,老郭黯然道:“下次你来,我恐怕不在这儿了。”
“不住这儿,去哪里啊?”
“房东看我这样子,说要收回房子,不租给我了。”老郭说,“我儿子说,实在不行,就去养老院,那儿服务好。”
“嗯嗯,孩子们也忙,各有各的事,还是去养老院好,那儿有人照顾。”沈汉文点点头。
“要是像朱美玉那样就好了。”老郭幽幽说道。
沈汉文无言以对。拆迁前,朱美玉的屋子就在沈汉文家后面。老太太八十三岁了,还能自个儿耕地收种,看上去身体健朗。谁也没料到,在签完拆迁协议后不到一周突然走了。老哥们谈起她,都说老太太聪明,早不走晚不走,签到了补偿款和安置房才走,一没给子女添麻烦,二还为子女涨了财。
回到租住的地方,沈汉文呆坐了好长时间。到了中午也没心思做饭,和衣靠着床头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沈汉文做了个梦,梦里他回到小时候,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父亲带着他去镇上赶集。这雾真大,连父亲的脸都看不清,只觉得一只大手牵着他跌跌撞撞地向前。集市地摊沿着街道两侧摆开,绵延向前,总走不到底。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在雾中若隐若现。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在他眼前一晃而过,又迅速隐去。在一个售卖竹编小动物的摊位前,他忍不住停了下来,摊主正用草绳缠绕竹幂,缓慢地编织一件东西。那东西逐渐成形,身体、脚、头部、脸,是一只长着人脸的羊。那脸赫然就是老郭的脸!沈汉文害怕得转身就要走,回头已不见了父亲,他一下子慌了神。摩肩接踵的人群如一堵厚实的高墙,屏蔽了他与父亲的联系……
老年机的铃声特别嘹亮,把他从惊惶中解脱出来的是儿子沛林的来电。说晚上过来吃饭,让他多煮点饭,菜就不要准备了,他们带过来。虽然乡下的院子没有了,儿子儿媳还是保持着周末陪他吃顿饭的惯例。
沈汉文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到了四点半再淘米煮饭也不迟。多出来的这一段空当,他准备摘些菜给蔡老师。蔡老师的女儿在美国。前些天中秋节,女儿给她寄来了两盒月饼。那天,沈汉文和小区里的几个老年朋友坐在蔡老师的车库门前闲聊。蔡老师拿出了月饼,给他们一人一个。笑着自嘲:“我丫头真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特产,还非得从美国买了寄过来。”大家都说,这可不一样,是丫头的孝心啊。
沈汉文知道,蔡老师就一个女儿,十五年前留学美国,毕业后在那儿安家落户了。这十几年,就回来过两次。一次是结婚办宴席,一次是她爸爸去世。住在104 的梁老太有次说,蔡老师这女儿算是白养了,这么远,老了还能靠得上么?
这一点,蔡老师倒是看得通透,说,只要丫头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她不求什么。
“以后会去美国养老吗?”沈汉文问。
“干吗去美国?在这儿不是挺好?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不要总想着靠他们。”蔡老师说。
不靠他们,那靠谁呢?蔡老师没有说下去。
生菜的叶片很嫩,像一嘟噜碧绿的花朵,轻轻一拔就握在了沈汉文手中。它有一种特有的清香。老伴在的时候,经常用它烧汤,生菜叶鸡蛋汤,再加一小把虾米,既有菜的香味,也有汤的鲜味。沈汉文一个人生活后,却从未这样做过。他更喜欢炒着吃,也不像一般人家不切就炒,而是先将生菜叶切碎,揉去绿色的汁水,再与鸡蛋一起炒,吃起来清新爽口。
沈汉文在阳台一边摘菜,一边关心蔡老师车库门前的人。蔡老师的车库就在他斜对面的楼下,她的门前经常有人坐着聊天。几把生菜就这样送过去,被人看到了怕是要生出闲话来。
太阳转过对面楼房的屋角,从西面墙头那棵高大香樟的树顶缓慢地滑下。几个老太各自回去了,沈汉文才将生菜放入塑料袋下楼去。
蔡老师在拣扁豆,戴着老花镜,将扁豆荚一个一个地对着灯光照。沈汉文拎着生菜进来,说:“蔡老师,做什么菜呢?”
“扁豆米饭,有没有吃过?”
“扁豆米饭?第一次听说呢。”沈汉文将生菜放在桌子上,“这几棵生菜,我在阳台上种的,你尝尝鲜。”
“老沈,你太客气了。”
从蔡老师那儿回来,沈汉文的心情轻快了许多,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来到客厅,沈汉文摁开了电视,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将频道转换了一圈,也没能让他静下心来。忽然想起饭还没煮,急匆匆地去淘米。将米倒进电饭锅时,他想起蔡老师说的扁豆米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晚饭时,沛林又拎来一箱牛奶。他有些生气,儿子好像缺根筋,不晓得他的喜好,也从不询问他需要什么。有一回拿来两个凤梨,他这老牙能咬得动吗?只得先冷藏着,时间一长,最后还是烂在了冰箱里。这事令他好长时间不痛快,他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了,诸如此类的小事,本不应该放在心上,现在却会耿耿于怀。
“爷爷。”孙女琳琳也来了。看到琳琳,他心里的不快一下子烟消云散。孙女小时候一直由他们老两口带着。稍大一点,去城里上幼儿园,遇上感冒咳嗽,儿子儿媳没时间照顾,就送到乡下来。神奇的是,一到乡下鼻涕就不流了,咳嗽也自然好了。老伴说,乡下的孩子皮实。他觉得,是乡下的空气好。
琳琳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了工作。可是不稳定,五年换了三个单位。这些,都是儿媳晓莹在饭桌上数落出来的。他懂得晓莹的意思,女孩子家家,与其在上海辛苦拼搏,不如回小县城来,找个安稳的工作。
今天饭桌上,晓莹又提起这事。说在上海工作,表面上风光体面,实际上呢,工作压力大,生活成本又高得离谱,不要说买房子,就是买一斤青菜萝卜都不知道贵多少倍。
“呼吸的空气都要比这儿浑浊。”晓莹用胳膊肘蹭了一下沛林说,“哎,你说是吧?”
沛林闷声不响,自顾自吃饭。
其实,沈汉文对上海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这一生曾去过上海两次。第一次在他三十五岁时,家里准备添置一台电视机。当时时兴上海产的“金星”牌,而这个牌子的电视机,本地百货商店没有。他便想着去上海买。这儿去上海,要乘船过江,来回得三五天。出发之前,他做了功课。姑妈家在上海,晚上可以投宿在那儿。那天,当他扛着土特产敲开姑妈家门时,姑妈的反应很冷淡,好像对待一个平常串门的邻居。这让他倍感失望。既然不受待见,又何必赖在那儿呢?稍稍坐了会儿,他就撒了个谎出来了。事后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再踏进姑妈家半步。上海人的傲慢将他心底蕴藏的浓厚亲情击得七零八落。
第二次是老伴生病。老太婆生的是“一个字(癌)”,儿子知道后,急吼吼地联系了上海的医院,安排她住了进去。其实,那时病已经是晚期了,即便后来动了手术,也没起多大作用,反而让老太婆多受了不少罪。他在心里埋怨过儿子,可儿子这样做错在哪里,他又说不上来。老伴手术后,他去陪护了几天,看着她难受痛苦的样子,他心里也难受极了。
姑妈的冷漠和老伴痛苦的表情构成了沈汉文记忆中的上海,它的高楼大厦、流光溢彩,在沈汉文看来都是冰冷而坚硬的。谁知道大城市光鲜表面的背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想到这儿,他忍不住插了一句:“上海有什么好的。”
“爷爷。”琳琳说,“下次带您去上海玩玩,让您亲身感受感受啥叫‘魔都’。”
晓莹放下筷子夹着的排骨,对琳琳正色道:“沈嘉琳,我劝你一句,在上海没有好的出路。”
“怎么没有好的出路?”
“这几年,你跳来跳去的,找到理想的单位了吗?”
“不是一直在找吗?”琳琳噘了噘嘴。
“还不如回来考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什么的安稳下来。”
“不要。”琳琳回答得很干脆。
谈话陷入了僵局。沈汉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后悔说了那一句“上海有什么好的”。他觉得是这句为儿媳帮腔的话,直接引发了母女间的争执。老了老了,越来越不会说话了。他真想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好了,好了,吃完了早点回去。”沛林放下筷子,抽了张面巾纸抹嘴。
不出所料,孙女没有跟儿子儿媳回去,说要陪陪爷爷。沈汉文知道,其实她是不想再听她妈妈的唠叨和数落。
上一回在乡下,为减肥的事,母女俩也闹得挺僵。那天,一家三口来吃饭。琳琳只夹了几筷子素菜,饭也不吃。说是这两天又胖了两斤,要节食。晓莹呢,担心女儿的身体,偏要劝她吃饭。跟她讲节食的危害,会导致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胃黏膜损伤,甚至重大疾病,等。琳琳不爱听这些说教,转身进了房间,把房门关得砰砰响。她当晚就留在了乡下。
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脾气比爹妈还要大。沈汉文想起儿子的青春期,倒不是十分叛逆。最严重的一次是言语中顶撞他妈,沈汉文知道后,用烧火棍狠狠抽了几下儿子的屁股。那时候教育子女,除了棍棒,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现在想来,不知道儿子是不是还记得,有没有记恨他。
隔壁房间的被子前两天刚晒过。沈汉文不放心,又找了一条新的羽绒被垫上。以前,孙女和父母怄气之后,总是留在他那儿过夜。沈汉文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好是坏。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给孙女留一点缓和情绪的空间和时间。
睡之前,沈汉文将自己房间的电视机音量调小了。电视里,苏大强在保姆小蔡的照顾下活得滋滋润润,居然还梦想着出一本诗集。沈汉文看着心里发笑,这位老哥幸福得都不晓得自己是什么货色了。转而想起了蔡老师,将来她女儿会不会也给她请个保姆?
再一次见到老郭,是在他的葬礼上。老郭走得很突然,据说是因为脑溢血。沈汉文这才想起来,上次看望老郭时,他说话含糊不清,应该是发病的前兆。真后悔没有提醒一下老郭。
老郭住进养老院才半个多月,还没适应就走了。沈汉文听说过这个养老院,是一个私营机构,在一座小镇边上,里面住着三十多个老年人。一条宽阔的运河从大门外流淌而过。沈汉文想象过,夕照之下,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河边悠闲地散步,芦苇苍茫,微微摇曳,远处的水面碎金闪烁。这是傍晚时候最美的风景。
到了地方才发现并非如此。养老院的大门旁建了一排平房,竟然是用作灵堂的。这排刺目的建筑直白而残酷地昭示着进来之人的最终归宿,将沈汉文心中“养老”这个词,涂成了惨白的颜色。
此刻,老郭就躺在其中一间灵堂中。他的两个儿子儿媳蹲在水晶棺前烧黄纸。沈汉文坐了会儿就走出了灵堂。
灵堂的不远处就是那些老人的房间。三个老头正坐在屋檐下晒太阳。阳光很暖和,晒得人犯困。其中一个像只老猫蜷缩在椅子里,似乎睡着了。沈汉文上前打听老郭原来住哪个房间。一个精瘦的黑脸老头朝睡着的那个努努嘴:“跟他住一间。”
“老倪,老倪。”另一个老头很热心,叫醒了睡着的那个。
沈汉文说想去看看老郭的房间。老倪眯着眼说:“没啥好看的,东西都被他儿子清理走了。”
“你带他看看去,说不定看上了也要住进来的。”热心的老头转而又对沈汉文说,“是吧?”
这是一个双人间,三十平米的空间放着两张床。沈汉文猜想,外边靠窗的那张是老倪的。因为里侧那张没有被褥,只剩灰色的床垫。老郭生活过的痕迹已荡然无存。
阳光穿过窗玻璃投射进来,落到地上,变成了古铜色。似乎房间里有某种魔力,让一切变老,包括光线。对面墙上挂着一台液晶电视,往里走是卫生间,地面挺干净。老倪倒了一杯茶给沈汉文:“看看,每天有人来送水、打扫卫生。”
沈汉文接过茶杯,在床垫上坐下。心底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儿的条件比车库要好,还有人说说话,老郭本来又是个话痨,在这儿他应该不会感到孤独。可是孤独这种东西,不是阳台上的菜,一眼就能看到它冒出的嫩芽和伸展的叶片。它埋在各人的心里,独一而隐秘。他人既难以觉察,也很难预料它会在什么时候发芽、抽枝、展叶。凭什么认定老郭就不会孤独呢?
老郭最后两天一直在迷糊中。老倪告诉沈汉文:“怎么喊都喊不醒,却时不时地说胡话。”那两天,他像孩子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者又回到母亲的子宫里,乐不思蜀。岁月驶了个大回环,在老郭身上流逝而过,接近终点,也回到起点。
灵堂那边传来绵延的诵经声。“这人啊,就像坐着公交车,一站一站的,都要走过。”老倪说,“老郭的这一站,就是我的下一站喽。”
送完了老郭回到家,天已擦黑。泡沫箱中还有两排青菜,这些菜哪怕长在这样狭窄的空间中,依然尽情地伸展叶子。沈汉文准备摘下来烧一碗汤。透过阳台的栏杆,他看到蔡老师正在灶台边,从电饭锅里盛饭。沈汉文突然有一股冲动,待会儿做好了汤端过去,他想尝一尝扁豆米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