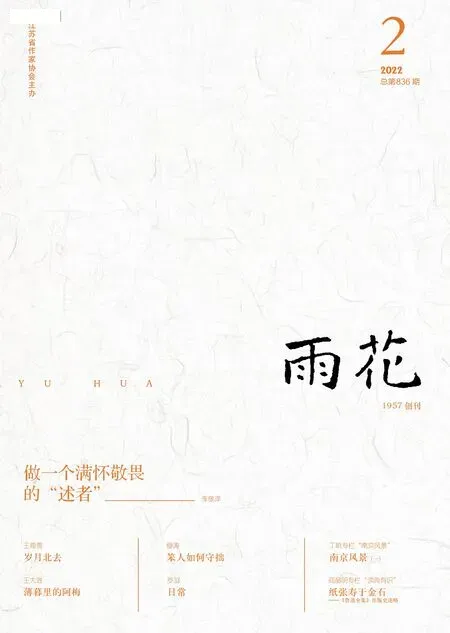克劳斯
了一容
说起这个克劳斯,我实际上跟他不熟,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深。
前段时间,老家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1920年大地震百年纪念筹备组”的微信群,主要用来收集与民国时期1920年大地震相关的人文资料,不知是谁把我也拉进了这个群,我嫌群太多,想退出来,但又怕薄了拉我入群者的情面。既已有那么多群了,再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索性没再管,只设置了一个免打扰状态。
可是,有一天我看见那个拉我入群的小伙子发微信邀我去一所大学参加地震纪念相关活动的第一次筹备会,希望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说实话,对这类话题我不怎么热衷,加上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只是一个亲历者的后裔,仅此而已。这都已经过去几代人了,我也并没有听到太多与之相关的人文故事,即使听说了,也都是零零碎碎,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兴高采烈地搞这么一个活动不容易,真不应该叫我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凑数。有没有我,我去不去参加,其实都是无足轻重和无关痛痒的。但是,他们一再邀请,我还是去了,因为那天正好有一个新营玉皇沟的文学爱好者找我玩,我不知道带他上哪儿去玩,就提起有这么个活动,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结果他显得异常兴奋,说:“去、去。”还一个劲儿说,“这是个好事情、这是个好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文学爱好者老何先生所谓的“这是个好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能够和那些大学教授、高等学府的研究生们一起共话地震,并深入浅出地探讨一个重大的社会性话题而感到自豪荣幸呢,还是觉得这件事情真有那么重要。但老何态度积极,好像他在这里面能淘到宝似的。
那天是个星期六,我们顺道还接了一位年轻的油画家小马,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
要说这民国大地震方面的事情,我听我们村子里的马江元老人讲过,我的几位太爷也都曾是亲历者。太爷弟兄几个同河州那里的一帮年轻人成群结伙来到了沙沟满寺堡。这里的地形地貌同甘肃老家差不多,也是个苦寒之地,从西到东出来走走看看,或许比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强。
地震那天,这些河州人恰好在满寺大河滩的老油坊里榨油。那时候榨油用的是水车,一架水车,还有一个石碾,用水车的动力带动石碾,将炒干的胡麻放到石碾上碾成粉末,再放到锅里蒸熟,然后用麦草垫底,将其填入一个圆型的铁箍内,做成油坯饼,再将油坯饼放入木头的油槽里,槽子的一侧装上木头楔子,启动悬空的撞锤,这样就可以把油硬生生地压榨出来。榨油坊一般都是建在村中水源充沛、绿树掩映、青草茂盛的河岸边,每年立冬后即开始榨油了。满寺堡的老油坊旁边有条大河,河水特别大,但水是从上游的臭水河流下来的一股子苦水,又苦又咸,还带有一丝煤油一样的臭味。人是吃不成的,连牲口也不爱喝,灌溉浇田就更不行,若浇一两年田,田里肯定盐碱泛滥,就无法再种庄稼了。大家都说,可惜了这一河的水,哗啦啦地流着,跟江南水乡的水似的,很欢实,人却用不成。这里的人吃的都是井水和窖水。
然而,这条河里的水却让满寺大河滩的这个老油坊得了济,成为榨油不竭的动力源泉。毕竟水吃不成,能够因之而吃上世界上少有的胡麻清油,那也是不得了的大事,这水也算是功德无量,用到了正途,没有白白浪费。
这些跟地震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地震那晚住在油坊里的河州人都没有睡觉,救了一村子能够救活的人。当晚他们睡不着,那干啥呢?由于他们精力过于旺盛,榨油都没有把他们的力气榨干,多余的精力没地方发泄,大家就聚在大河滩油坊旁边的那片苜蓿地里借着月色摔跤呢。他们较量和切磋跤术,同时也在消耗公牛犊子一样的过剩力气。也正是因为大家都在这片野滩地里汗下如流地跌绊着摔跤,所以尽管地震来得特别突然,大家也只像是在一面抬起来的地毯上来回颠簸了几下,除了头有点眩晕之外,竟都毫发无损,存活下来了。接下来,这些震后余生的河州人开始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大家找了几把铁锹和镢头,就去村里倒塌的房屋和窑洞的废墟里救人,有些地方他们不敢用镢头和铁锹,怕伤着里面的人,就只能用自己的双手刨,手指甲都在刨挖的过程中掰掉了,他们拼命刨开废墟和倒塌的窑洞,把里面的人救出来。满寺堡的马江元老人回忆说,那一村子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你们河州人救出来的。河州人骁勇善战,能工巧匠者多,心也齐,是最讲义气的。
这就是地震跟我相关的内容,再就是听到的、在书本里读到的一点与地震相关的零星的故事,但这都不足为外人道。因而,让我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确是勉为其难,我只有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听众的份儿,抑或为大家捧场,做一个生活中的群众演员,也壮壮人气。
那所大学环境还是挺不错的,绿树弄影,湖泊环绕,各种假山和名人塑像,以及碑刻书法,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我们一直走到后面的一栋楼,在楼梯口打电话,有人把我们接了上去,走进了会议室。这间会议室也不是特别大,好像是老师堆放杂物的地方,也可能是一间大点的办公室,抑或是研究生的实验室,里面摆放了一圈桌椅,桌上有一次性杯子,里面倒上了水,每张桌子上还放了几个橘子。
有一位年长的老师模样的人和一个主持人,坐在上首的位置。首先,主持人介绍与会人员。我发现,除了那位年长的五六十岁上下的老师和我带去的文学爱好者老何之外,数我的年龄最大,其余不是研究生就是大学生,当然还有几个网络媒体的记者,也都是这个学校近两年来的毕业生。大家介绍完之后,我大致有了一个概念性的了解,但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一个都没有听清,也不好意思再问。
有几个女孩子讲得特别动情,就像是在读一篇描述苦难的散文,而且把自己都讲感动了,竟然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似乎不哭不足以证明苦难究竟有多深重,不哭不足以说明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究竟有多持久,一代一代,这些苦难至今还在影响着大家。有人甚至愤慨地说,究竟是谁把我们迁移到这么个烂地方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吃不上,喝不上,这也就罢了,竟然还这么容易发生地震,而且都不是小地震。尽管哭了,反思了,委婉地诅咒了,但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深入到我的心里去,只记住了那个女孩子流泪的一点细节,以及声音哽咽的可怜样子。
轮到了我,大家让我说。我说的啥也忘记了,大概是胡乱应付了几句,意思是地震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苦难,但现在也未尝不是一种可开掘的矿藏,有很多人都在这里面寻找机遇和矿脉,包括旅游文化,拿苦难做文章做成功的也都大有人在,大家都可以好好在里面做点文章。
我的话说完,主办方的人高兴地带头鼓掌,让大家赶快集思广益,想办法拉资源,包括故事撰写,到筹资金、拉赞助,再到立项目,拍电影和拍摄纪录片等都说到了,大家众说纷纭,好像这里面真的能抓几个金娃娃似的。我听着,觉得这件事情酝酿发酵到后面,还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响。
我觉得研究过往的地震,把那些尘封的记忆和苦难再翻寻出来,一遍一遍地复述,翻来覆去热残汤剩饭似的来书写来研究,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没有意义才是最大的意义吧!
最后,大家隆重推出了两位发言人,一位是从我们村子里出来的,就是马江元老人亲房侄子某某某的孙子,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学教授。老教授让我们村子的这个长得白净清秀的娃娃先说。这个娃娃的爷爷曾是我儿时学习本民族语言的一位启蒙老师,人品非常好,对我和我的家人都相当亲近。实际上,我也很想听听这个娃娃的高见,也盼望他能像他爷爷那样优秀。这个娃娃过去也曾找过我,但几次都阴差阳错,没有见到。只听家人说他是从外面的一所有名的大学毕业的,现在又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大学里读研究生。书是越念越多、越念越好了。大家和我都把他视作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对他的表现相当期待。
小马开门见山地讲起来了,毫不客气,也没有打官腔的开头,这倒是我所喜欢的个性。他大致讲了两件事,其中一件他说到大地震的时候有两个人,如何预测到地震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成为我们那里老百姓津津乐道和显示自己博闻强记、通晓人文典故的资本,好像他们这样一讲,就像是跟这些先知先觉者们沾亲带故,亦或是跟随在先知们身边时常能够聆听他们的教诲、接受他们的指点似的。讲完这个故事,他又接着谈起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说他要写一系列关于地震的调研报告或者笔记体的文献等作品,要发在某些权威性的人文社科期刊上。他的口吻,仿佛这些作品已经在脑子里写好了,只需往电脑上一传输,很快就可以见刊。我和在座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后来我们在活动结束后回来的路上,老何幽默地笑着对我说:“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你们那里尽出大人物,就像马步芳、马鸿逵、马思义,还有我今天遇上的这一位少年天才,也许是能写出《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的天才。”他语言中夹枪带棒地把我的原籍和生我养我的两个地方都讥讽了一通。
我说:“世事难料,人只要有远大志向,剩下的不就是成功了?”
老何说:“他哪里是要准备去写,他的口气,好像都已经发表出来了!”
画家双手拍着大腿,忍俊不禁地说:“我听着他咋那么能耐啊?真的感觉又是一位转世灵童!”就在我们下楼的时候,那个娃娃给我们三个来了一句:“我今天特别忙,不送你们几个下去了,我马上还要接见一位重要的外宾呢!”我当时对这个娃娃的话没太在意,因为我的脑子里可能想着别的事情,可是跟我一起来的老何和小马,等不到进电梯,就已经笑得稀里哗啦的,边笑边说你们村子里咋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啊。我在惭愧的同时,又有些说不出来的难过和五味杂陈的感觉。但我又一想,河州那么大,我们那个村子沙沟就有成千上万口人呢,谁也无法代表谁,谁又能代表和承担什么呢?
后来,那个小马画家猜测说:“那个娃娃可能是说他要去见学校聘请的某个外教吧,他却硬说成是去接见一位重要的外宾!”
那个娃娃发言结束之后,主办方给我们隆重推出了这次活动的幕后主角,也就是这所大学最杰出的老教授,我不太清楚,大学有没有关于地震的课程,但我感觉他可能是专门研究地震的专家。我始终没有听清楚这位教授姓什么,我一直以为他姓柯,因为那个主持人反复讲到“柯老师、柯老师”,我以为说的就是这位教授先生本人。我们暂且就把他称呼为柯老师吧。但是这位柯老师在他的发言里始终都离不开“柯老师”三个字,似乎他自己在震后不久就赶到了震中,在近四十多天的余震中,踩着废墟调研、采访,并拍摄了许多无比珍贵的照片。这一次,他让我无比讶异,他好像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穿越了时空隧道,在给我们讲授和还原当时的一个个场景。后来,他让学生用投影仪在墙壁上播放那些民国时期拍摄的照片时,我才看到照片中时时出现的一个外国人。教授指着那个外国人说:“他就是克劳斯。”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此“柯老师”非彼“克劳斯”。但是教授给我们转述的时候,好像他和克劳斯两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曾经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他们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从这个窑门口走到那个窑门口,后来好像转累了,他们俩在一个塌陷的崖窑前较僻背的地上一人撒了一泡尿。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气息贯穿于整个发言中,甚至那种地震后的气味都被他活灵活现地传达给我们,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后来,他讲着讲着,便化身为克劳斯本人了,回国之后的克劳斯,再一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这所大学给我们现身说法,讲当年地震后不久他就不辞辛苦来到中国,讲述那些曾经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看到的那些震后的难民们缺吃少穿的苦难历程。
这位在他们看来非常伟大的克劳斯究竟是干什么的,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我猜测,克劳斯可能是一位从国外来到中国的旅行家,或者是一位摄影师,再或者是一位地质学家,再或者是专门研究和调查民国大地震的外国记者,还可以明着是一个从欧美来亚洲的传教士,暗中却是一个间谍。他无非就是这样一些人中的某一种人。可是这位老教授,却讲得头头是道,好像他对克劳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似乎当年地震刚结束,他们两个就一道结伴而行,在那片地震后的废墟上鬼魅一样走来走去,转着拍照片,留下了许多现在的人赖以研究地震的珍贵资料。这是何其震撼人心啊!
实在太奇妙了,世界也太小了,这位化身克劳斯的教授竟然与我同住在一个小区,而且住在相邻的一座楼里,这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观察。
有几次,我和画家小马晚上在小区外面的草坪上散步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克劳斯”,他跟我们擦肩而过,我赶紧把头低下,装作没有看见,他可能也装作没有看见我,我们心照不宣。他长着一张大窝瓜似的吊脸,头发黄白相间,稀稀疏疏的,穿一件淡绿色的T 恤、一条土黄色短裤,下半截腿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脚上是一双球鞋,里面穿的像是女式的丝袜,十分另类。“克劳斯”的个头比较高,走起路来弓腰马爬,虽然没有残疾,却一颠一簸的。他好像跟小区的这些俗人不咋交往,保持着特立独行的生活状态。再回想,“克劳斯”那天在大学里挥舞着拳头,高声大嗓地大讲特讲克劳斯的情形,不由得让人忍俊不禁。我开始观察他,就时常能看见这位“克劳斯”晚上一个人独自散步,一个人走到一家小饭馆去下馆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夫人,家里有没有人做饭。
后来有一天地震了,把我吓坏了,我忘了“地震须知”里拿着绵软的东西顶在头上钻到坚固的桌子底下的建议,竟赶紧脱下睡衣,准备把衣服穿好跑下楼去,可还没等我把裤子穿上,地震就已经过去了。我趴在窗台上一看,竟然看见了“克劳斯”先生。他像一只十分狡猾的有先见之明的老鼠,第一个窜出了窝,在院子里转着圈儿走来走去,又坐在小区花园里供人休息的木椅上,在灯光下鼓捣手机,也许是在看有关地震的消息吧。他作为这方面的教授,可能又在收集资料。
我对“克劳斯”突然有些佩服,我自己在地震后打算往外跑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可是裤子还没来得及穿上,“克劳斯”就已经在院子里观察和活动开了,你说他的速度何其了得啊!我感觉他对地震有着天生的、特殊的警觉和敏感,就像大自然中的老鼠、青蛙等小动物一样,对地震有着先知先觉的能力;地震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时,他就已经跑出了危险区域,这不能不叫人仰视啊!
我把这件事情跟画家小马说了,他差点把肚子笑破了。他对我说:“‘克劳斯’可能晚上都不脱裤子,时刻都在准备着,只要有一点震动和摇晃的端倪,就会像兔子一样窜出来。”
我听着,想了想,难道这就是那些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博士们的生活状态吗?风轻轻地在窗台上吹着,我脱了衣服,重新穿上睡衣,躺在床上再一次想起了“克劳斯”们,竟有些辗转反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