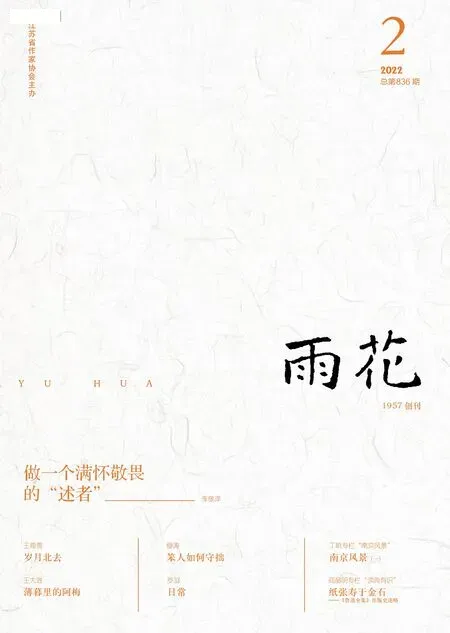纸张寿于金石
——《鲁迅全集》出版史述略
阎晶明
2021年9月25日,为纪念鲁迅诞辰140 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人文社与鲁迅作品出版暨纪念鲁迅诞辰140 周年座谈会”。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话题。人民文学出版社是《鲁迅全集》的出版机构,其权威性不仅因为其出版历史长,更因其编辑、注释等一系列工作在专业性上的不可替代。多位鲁迅研究界的专家,参加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的资深编辑参加了当天的座谈会。
我在会上作了个简短发言。我的发言既是向长期以来为鲁迅作品出版作出贡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资深专家、前辈编辑致敬,也表达了对鲁迅作品出版再出发的期待。我在发言中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希望鲁迅研究界的专家们在研究、总结鲁迅著作的出版史时,不要忘记阐述中国共产党在《鲁迅全集》出版史上最原初的、始终如一的作用,不要忘记研究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一直以来对《鲁迅全集》出版的重视、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鲁迅全集》的出版史,它的发生、发展,很大程度上早已超出了文学的出版的范畴,本身就是一部值得书写的历史。我想就此梳理一下,并突出政治力量对《鲁迅全集》的推动作用。
一、鲁迅逝世与《鲁迅全集》的启动
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在上海逝世。由于鲁迅在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这一悲痛的消息激起了各方反响。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得到鲁迅逝世的电讯后,于10月20日即鲁迅逝世的次日,给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和许广平发去了唁电,并同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其中有这样的要求:
其中的第五条就发出了完整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呼吁。这也是以上诸条中实现最早的愿望。另一条就是第四条,设立鲁迅文学奖,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作家协会始设鲁迅文学奖。其他诸项,事实上应为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的“过度”要求,以迫使其积极对待鲁迅身后事宜,具体事项均因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而未获实施。
对于一位文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为后世人留下作品,像鲁迅这样在世时已注定属经典之列的作家,其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就显得格外迫切。鲁迅逝世后,他的亲人、学生、战友,几乎是共同意识到出版《鲁迅全集》意义的重大和迫切性。正如许广平所言,“溯自先生逝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而这些要求归纳起来,又有以下一致:“望早日出版”“希收集齐备”“冀售价低廉”(《〈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编辑出版完整的鲁迅作品,甚至是鲁迅本人在世时的愿望,书名也已定好:《三十年集》,而且他自己已经构思出了两种编辑方案。其中第一种,将所有著述分为“人海杂言”“荆开丛草”“说林偶得”三大类。目录之外未作说明,所以连许广平本人都不明白鲁迅目录里所写“起信三书”具体所指是什么。第二种则按体裁分类并以创作为序。许广平曾经记述道:“记得先生大病前,曾经说到过:他自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中止学医而在东京从事文艺起,迄今刚刚三十年,只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余万言,拟将截至最近的辑成十大本,做一记念,名曰《三十年集》。当时出版界闻讯,不胜欣忭,纷请发行。使先生不病且死,必能亲自整理,力臻完善。”《三十年集》于1941年9月出版,编辑者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出版者为鲁迅全集出版社,加上原初的编辑、目录的确定者是鲁迅本人,所以这套多达30 册的文集,倒是“通体”都是“鲁迅”元素了。《三十年集》是鲁迅所有创作和学术的集成,未收鲁迅的任何译著。这既是因为要尊重鲁迅本人意愿,也是考虑到读者购买的承受力。
虽说《三十年集》“启动”在前,但实现出版方面,倒是先有《鲁迅全集》。正如许广平谈到《三十年集》时所说:“无奈愿与事违,先生竟病且死,死后行将二年,始将全集印行,捧诵遗著,弥念往昔,不胜痛悼。”如果印行《三十年集》是为了实现鲁迅本人的愿望,那《鲁迅全集》的出版则更充分体现了各界有识之士对鲁迅的尊崇和对鲁迅作品的热爱。
1937年7月18日,由宋庆龄、蔡元培、许广平、沈钧儒、许寿裳等72 人组成的鲁迅纪念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当天的成立大会上,由许广平报告了《鲁迅全集》的运行进程:“鲁迅遗著共三十余种,大都已经中央审查通过,现正整理版税权之收回,以便全集从速出书。全集编辑各先生,为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等七人。”而北京的《北平新报》则指出:“关于《鲁迅全集》审查事已有部批,除《二心集》《南腔北调集》《毁灭》《伪自由书》四种,全部禁止;《华盖集》《坏孩子及其他》《而已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三闲集》《鲁迅杂感选集》《壁下译丛》八种,部分删去。”其余倒“均通过”;而“关于被禁部分,现正从事疏通,有无其他办法另行出版,则尚不可知云”。事实的确如此,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与专制统治下,完整地、公开地出版《鲁迅全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鲁迅全集》的出版很自然落到了许广平、许寿裳等亲人,以及革命、进步人士身上。1937年10月,“文艺界救亡协会”在上海成立,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巴金、郑振铎、许广平等人参加,会议提议:“前与商务印书馆商定出版之《鲁迅全集》,因战事关系,延期出版,决由今日出席者签名,请商务从速进行出版。”(《学习鲁迅精神,文艺家大团结》,见《鲁迅研究资料汇编》(2),P872)鲁迅纪念委员会在1938年5月16日发表于汉口《文艺阵地》的上《〈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一文中,特别说明了全集与鲁迅《三十年集》的关系,“幸而鲁迅先生去世之前,曾手拟《三十年集》总目,生平著作及述作,依照年代先后,分作十卷。这次纪念委员会刊印全集,是以这一目录作为基础,再加上翻译作品,依照翻译年代先后,分作十卷。”文章强调了《鲁迅全集》出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意义。“这是一个火炬,照耀着中国未来的伟大前途;也是一个指针,指示着我们怎样向着这前途走去。在这个民族抗争的期间内,这全集的出版,将发生怎样的作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二、初版《鲁迅全集》的曲折过程
《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注定要载入中国出版史册的大事,众多重要人物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这里可以就胡愈之的努力做一介绍,略知其中之艰辛和感人之处。关于胡愈之为推动《鲁迅全集》出版所做的工作,郑振铎在《忆愈之》一文中曾写道:“《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手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胡愈之,浙江上虞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参与创办《公理日报》《团结》《东方杂志》等报刊,参与组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复社”等团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传播抗日救国主张,与侵略者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949年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胡愈之是鲁迅的同乡,青年时期在绍兴府中学堂上学时就受到过鲁迅的教育,对鲁迅的尊崇无疑是真切的。能够为《鲁迅全集》出版尽力,于公于私,他都十分愿意全情投入。
2018年10月15日《文汇报》发表署名周铁钧的文章《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集〉出版》,透露以下细节:“1936年11月,胡愈之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了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想法,党的负责人刘少文等商议后表示: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迫切需要用鲁迅精神来唤起民众,支持抗战,要动员、利用一切力量,尽快组织出版《鲁迅全集》。”文中还写道:
其中的细节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进行精确化讨论,但毫无疑问,《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分不开。
《档案春秋》2017年第2 期发表金洪远的文章《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其中谈道:
经过多方努力,《鲁迅全集》于1938年6月始逐步出版印行。出版方由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承担。“复社”作为一家并不正式的“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却出手不凡。在《鲁迅全集》之前出版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又曾出版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由于参与其中的各方人士日以继夜地工作,加上胡愈之特殊的运作方式,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不但在出版速度上快得惊人,而且在出版经费上也提前得到了保证。受《西行漫记》出版、发行方式的启发,《鲁迅全集》从印制规格到营销模式,都具有创新特色。
印制方面,为了既要实现普及鲁迅作品、达到唤醒民众的作用,又能够为出版印制筹集到足够资金,“主创团队”成员胡愈之、王任叔等将全集设计为甲、乙、丙三种不同规格。正如胡愈之的弟弟,也是“团队”成员之一的胡仲持所说:“不到四个月,《鲁迅全集》的三种版本都出齐了,甲种纪念本重磅道林纸印,封面皮脊烫金装楠木箱,预约价每部国币一百元。乙种纪念本重磅道林纸印,封面红布烫金,预约价每部国币五十元。普及本白报纸印,封面红纸布脊,预约价每部国币八元。”(《〈鲁迅全集〉出世的回忆》)甲、乙两种纪念本总共只印了200 套,并作1-200 编号。其中楠木箱上刻印了蔡元培题写的“鲁迅全集”四字。销售方面,充分利用各种人脉预约出售。每到一地,就举行茶话会,邀请各界人士购买预售书券。比如在武汉,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自费花1000 元钱订购了10 部。当时在武汉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对《鲁迅全集》出版极为关心。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而普及本也是通过预订发售,情况十分乐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上时有一种声音,认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得益于国民党高层的认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以一天时间审查批准、又亲自出钱预购即是证明。我们说,国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给予过帮助是事实,但邵力子却未必应算在其中。因为,邵力子支持《鲁迅全集》出版,一是因为他与鲁迅同为绍兴人,二是邵的成长道路中对鲁迅的崇拜早已铭刻在心,三是邵本人1920年就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党员,邵力子一生从未动摇过革命立场。
《鲁迅全集》就这样在国家危难和国民党公开禁止的情形下奇迹般地神速出版了。全集在广大的解放区产生了影响。当然,综合各种条件,在延安还很难见到《鲁迅全集》。有记述称,是胡愈之把编号为058 的一套纪念本《鲁迅全集》交上海党组织转延安的党中央(周铁钧《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集〉出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照片上,确可见到有三本《鲁迅全集》置于案头。而延安“解放社”于1940年鲁迅逝世4 周年之际,曾根据全集编选了一套《鲁迅论文选集》(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行)。1941年纪念鲁迅逝世5 周年之际,又出版由刘雪韦编选、张闻天主持并作序的《鲁迅小说选集》。1948年,东北解放区在大连翻印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版权页注明“东北版初版发行三千五百部”,同时注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初版”。这些举措都可以见出鲁迅作品在解放区的广泛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鲁迅全集》出版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非常关心鲁迅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很快就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正式出版了十卷本《鲁迅全集》。这其中,冯雪峰功不可没。
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整理鲁迅作品出版最重要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为了更好地整理鲁迅著作,当时的出版总署决定在上海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专事校订出版鲁迅著作,并聘请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冯雪峰担任总编辑。1951年,冯雪峰又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刊社于是迁移到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鲁迅著作编辑室。人文社自建社起就致力于鲁迅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1951年秋,《呐喊》《彷徨》等二十余种单行本相继问世,接着又出版《鲁迅小说集》《鲁迅选集》两卷本,以及许广平、冯雪峰、许寿裳等回忆鲁迅的专著十余种。1958年底,推出十卷本《鲁迅全集》,之后又编印了十卷本《鲁迅译文集》,这是继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之后,全面系统整理出版鲁迅著作的第一个注释本,成为新中国出版史上的盛举。这一版的《鲁迅全集》与1938年版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注释。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大大增强,也因此奠定了人文社出版鲁迅著作的专业权威地位。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正是人文社从一开始就确立的原则。正如现任社长臧永清在2021年9月25日纪念座谈会上所说:
“从积极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校对工作的王任叔先生,到主持鲁迅著作编刊社、起草《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方案》,调集王士菁、孙用、杨霁云、林辰等鲁迅研究专家,主持与领导完成195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的冯雪峰,以及后来的几代文人,都是一代又一代接着前辈的接力棒全身心投入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传播鲁迅精神之火。自1950年10月19日起,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尤其是《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始终是一项国家工程。”
1958年版之后,人文社又先后出版了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可以说,历次版本的《鲁迅全集》,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直接领导下完成的。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版,是迄今仍然被学界广泛公认的版本。注释的专业水准和客观程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实属不易。事实上,这一版的《鲁迅全集》,早在“文革”结束前,在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央的批准下就启动了。
1972年2月11日,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口头通知出版口负责人,说:“中央领导同志要看《鲁迅全集》。现在的本子太小,想用中国古装本的形式,用线装,字大点,每本不要太厚,一本一本出,出一本送一本。”15日、16日,他又对出版口写的报告作答复:《鲁迅全集》用解放后的版本排,内容和注释全不动,并说“要集中力量突击这套书,其他任务往后拖一拖,这是主席交的任务”。
1975年11月1日,毛泽东阅邓小平10月31日报送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关于鲁迅著作的研究和出版问题的来信。周海婴信中提出:
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年谱》第6 卷)毛泽东主席逝世前,为鲁迅及鲁迅研究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促成启动了《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就是这次批示的直接结果。那次编辑工作的启动,拯救了全国很多相关的文化人士,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可以说,这种改变是早于粉碎“四人帮”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就有相关的回忆,谈到这次编注工作对他个人的影响:“那时也是‘四人帮’倒台前夕,我们学校参与了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查找史料,采访前辈作家,和前辈学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也正是这个经历,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前辈作家、学者,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他们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做学问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9年第10 期)
四、毛泽东、周恩来与《鲁迅全集》
中共领导人中,有多位表达过鲁迅精神、鲁迅著作对他们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就是突出代表。
毛泽东向往鲁迅,也向往拥有《鲁迅全集》。1938年1月12日,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当时《鲁迅全集》还未出版。同年8月,二十卷《鲁迅全集》出版后,毛泽东通过上海地下党辗转得到了一套纪念本。也有说毛泽东得到的是从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一套精装本。1942年7月2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当然,限于条件,延安没有印行《鲁迅全集》。
周恩来则视自己是鲁迅的同乡同族,对鲁迅有着特殊感情,同样也对鲁迅作品十分热爱,对《鲁迅全集》的出版十分关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而周恩来赠送尼克松的礼物,就是一套《鲁迅全集》。为此,他曾派人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设法解决。几经周折,最后还是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库存中找到一套1938年版的纪念本赠送。此事引出的后续故事,则是1973年实施了根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简体、横排版重印。
可以说,《鲁迅全集》从启动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出版行动。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对《鲁迅全集》的出版形态产生过很多直接、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尤其是注释力量的组织,也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心和领导下开展的。过程中也有教训和改正的过程,但很多方面不但具有历史时期的超前性,而且具有作家著作出版的超规格性。《鲁迅全集》的校勘、校对、注释之谨严,收集作品之全面和甄别之慎重也是文学出版中最具典范性的例证。
《鲁迅全集》是中国文学出版史上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家工程。在八十多年的历史中,《鲁迅全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启迪人心的重要作用。是火炬,是指针,关乎中国的未来前途,彰显着文学的伟大力量。正如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所说,出版《鲁迅全集》的迫切性在于:“而先生以一生心血,从事于民族解放的业绩,又岂忍其久久搁置,失所楷模。”
鲁迅作品的永恒价值,有力地证明许广平所强调的观点:纸张寿于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