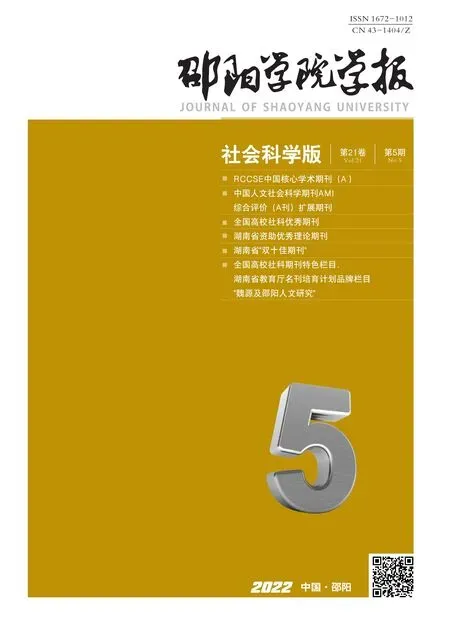“雄直”“清劲”:岭南近代诗学的进路
李姣玲, 马国华
(1.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2. 广州航海学院 党委宣传部, 广东 广州 510725)
岭南近代诗学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雄直”与“清劲”风尚的并立与融通。从古典诗学传承的层面看,“雄直”与“清劲”风尚不但渊源有自,而且互有高下;从近代创作新变的层面看,“雄直”与“清劲”风尚又百川归海,先后汇入同光诗学阵营。不论立足传承还是拓展新变,岭南“雄直”与“清劲”缠绕共生的诗学生态最终在传统诗学现代性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从合流走向了消解。从“雄直”“清劲”入手,我们不但可以明晰岭南近代诗学发展演进的源流与脉络,更可由此探索诗学发展内部地域与时代的深层意涵。
一、岭南近代诗学的源流与脉络
自班固《汉书》首开风气,将文学与地域联系起来,古典诗文论中便有梳理建构南北文学谱系的传统,“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1]1730一度成为江左清绮、河朔贞刚的具体表现。刘师培写就《南北文学不同论》,将考察时段从上古延续至清代,总结南北文学为“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571。着眼诗学,刘氏更拈出崇声律、尚修辞与矜风调等源流各异的清代南方诗学谱系:“若夫诗歌一体,或崇声律,或尚修辞,或矜风调,派别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2]577岭南偏处南疆,文教不昌,关山阻隔在地域上奠定了其与北方乃至中原文学弱势联系的局面。从班固到刘师培,在南北不同的文论背景之下,南方的地域意涵从江左而至湖湘,并未涵盖岭南。明清之际,屈大均曾说道:“吾粤诗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开风气,千余年以来,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户汉魏,皆谨守曲江之规矩,无敢以新声野体而伤大雅。”[3]1-2以《感遇诗》为代表的曲江体绍承汉魏风骨而又融合楚骚情韵,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谨守汉魏三唐,延续曲江风尚,一以雅正为鹄的,足以说明岭南诗坛接受、回应中原的诗学姿态。从清代到近代,随着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起,岭南对北方的诗学接受也愈多,“自朱彝尊后,其他文人学者联翩而至,如王士祯、翁方纲、钱大昕、赵翼、袁枚……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令人目眩”[4]16,程中山称此为清代岭南对北方诗学的“情意结”[5]。如果说迟至道光年间岭南诗坛依旧对“南来学者”有所崇拜,及至晚清民国,岭南诗家便成为中原诗坛的异军苍头,影响辐射全国的诗家诗论诗作颇多。
岭南诗学源流有二。其一自唐代张九龄,其诗雅正冲淡,张氏之后又有邵谒,其诗朴实无华。二人诗作或雅正,或真朴,而其共通之处,则在雄直的气象。自此而下至清初的岭南三大家,诗作气象雄浑远追汉魏,总体都表现出骨梗刚健的岭南地域诗学风尚。至清末,康有为、黄遵宪诸家亦多绍承此风,“其体以雄浑为归,其用以开济为鹄”[6]40。而随着时代风会的转移,康、黄等人的雄直逐渐趋向新异,到梁启超诗界革命,求新求异诗风已颇为壮观。从康、黄到梁,雄直与新异或有变化,但究其绍承乡贤、尊奉典范,亦有内在的一致性。其二自民间的粤讴。粤讴为岭南民歌,源出楚歌,从战国时期的《楚辞》到清中叶的《粤讴》诗集,清劲自然、回环往复的特点始终如一。曲江体的雅正冲淡同样包含岭南民歌清劲自然的审美特质。风尚所及,明初的南园五子诗在气象雄浑之外复有清圆流丽的一面,道咸之交的黎简更“由山谷入杜……取幽于长吉,取艳于玉溪”[7]308,转换雄浑刚健为晚唐五代的风情绵缈。楚辞、粤讴与岭南诗学的长期混融,实为近代梁鼎芬、曾习经等人清劲诗风发展衍流的地域文化诱因。
斟酌王闿运、陈衍等诗坛领袖的诗学体系,汪辟疆细化了地域文化与近代诗坛的深度关联,他将诗坛分为六派,虽然诸家皆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6]18,但地位却又不同:湖湘派蕲向汉魏六朝风尚,为诗坛旧派;闽赣派借径宋诗,或生涩奥衍,或清苍幽峭,流风所及,群起响应,由此而夺帜湖湘,跃居诗坛主流;其他诸如西蜀、岭南等流派则以地域风土见长,为诗坛别体。呼应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进的大背景,岭南与中原长久以来的弱势联系开始被打破,原本单向度的接受转而演变成为双向度的互动。
综合文学南北不同的源流传统、岭南近代诗学“雄直”“清劲”并立的发展脉络,汪辟疆认为:“近六十年间诗派,闽赣尚元祐,河北宗杜苏,江左主清丽,惟岭南颇尚雄奇,如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尤其著者。惟梁鼎芬、曾习经与晦闻三家,敛激昂于悱恻,寓秾郁于老澹,有惘惘不甘之情,与粤中诗人,迥然异趣。”[6]264在诗分六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岭南诗家析为两支,一支以康有为、黄遵宪为领袖,梁启超、何藻翔等为羽翼,诸人究心国计民生,经世风尚发为歌诗,沉郁顿挫亦不乏讽喻箴规,是为雄直一派;一支以梁鼎芬、曾习经等岭南四家为中心,潘博、黄孝觉等为后劲,诸人学行宦游与闽赣诗家渊源甚深,诗文风尚亦近乎清苍幽峭,是为清劲一派。

二、从激进到保守,岭南近代雄直诗风的转向
在近代岭南诗坛中,康有为、黄遵宪皆有转移风气之功。康氏传衍宗师朱次琦的经世致用之学,致力于维新变法,发而为诗,如“海涵地负”,似“巨刃摩天”[6]40,雄峻浑肆。其诗虽兼采异域风物,“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9]331,但神理结构皆推本杜甫,有着岭南传统诗学中的雄直气象。康氏弟子遍及天下,政教诗学亦多有响应者。黄遵宪早年即主张通经致用,后以外交官身份游历欧美多年,谙熟泰西学术政教的源流本末,其诗作溯源乐府,旁采民谣俗谚,用骈句散行、伸缩离合之法[10]3,“惟陈言之务去,斯精义以入神”[6]41,代表作《今别离》虽以欧西新事物发凡起兴,表现出强烈的近代思想与精神,但诗作风格与主题却又谨守传统诗教的范畴,被时人目为新派诗。以康、黄为肇端,岭南风尚逐渐由雄直趋向新异,以欧西史实名词入诗的手法蔚然成风。
自1894年起,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开始创作“新学诗”,新学之诗最初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11]49,路径偏狭,难以索解,“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12]250云云,其所依赖的思想文化资源大多来自西学,迥异于传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海外,随着见闻的增广,他融汇黄遵宪等人的新派诗与谭、夏诸人的新学诗,明确“诗界革命”的口号,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学范式,并标举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魁首[13]325。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从异域风光到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现新思想新理念开始的,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倡导尚武精神、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界革命’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14]。这种向外拓展的诗学姿态与此前维新变法援引西学的策略如出一辙,成为康梁诸家政治意识在诗学领域的映射。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的诗歌专栏为阵地,梁启超掀起了风雷激荡的诗歌变革思潮,肇始于岭南一隅的新异诗学也由此而风行海内。
然而,从1910年的《国风报》开始,梁启超所鼓吹的诗界革命运动逐渐退潮,到了《庸言》时期,“文苑”更悄然转换为京师同光体诗人群的诗词园地。梁氏一改往日诗界革命的面目,转而回归传统,他一度学诗于巴蜀赵熙,又请赵氏与陈衍为其删诗。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曾如此描述梁氏的诗学转向:
可知启超归国以来,则亦时时喜治所谓诗古文辞者;盖其时在京师投简札而过从者,大率治诗古文辞者多也……此四五年中,厥为启超文学之复古时期焉。[15]353-355
从诗界革命的外向拓展转向同光体诗派的复古开新,可看出梁氏晚年对旧体诗学现代性转换的重新认识。同样裹挟风雷之气,“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陈义虽高,却难以弥缝近代诗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紧张对立;与此相对应,以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为首的同光体诗派,延续传统,化旧为新,转而给人惘惘不甘的文思情韵,意境浑成,更为契合清末朝野士绅对传统政教体系的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如果说梁启超的诗学转向更多是回应民国思想文化的时代浪潮,那么,同光体诗论家陈衍的论说则是立足于古典诗学发展的内部律动来体察诗界革命派的演进逻辑:
诗有六义,兴居一焉,兴、观、群、怨皆是也。后世谓之“诗情”。其邻与乐者曰“兴趣”、曰“兴会”;邻与哀者曰“感触”,故工诗者多不能忘情之人也。任公有《腊不尽二日遣怀》云“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对?常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以上十首,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苏子卿之《河梁》耶?蔡文姬之《笳拍》耶?沈初明《通天台》之表耶?庾子山《哀江南》之赋耶?同时善作悲吟语者,尚有太夷……可以把臂共怀抱者。[16]51-53
“远托异国”云云,正是对梁启超早年诗学外向姿态的描述,将“不能忘情”推本六义之“兴观群怨”,转而接续传统诗教,用维新党人的不能忘情来呼应同光体诗家郑孝胥、陈三立的惘惘不甘,有意无意间,两种貌同而实异的诗情诗思就“把臂共怀抱”了。陈衍在此拈出“不能忘情”与“兴观群怨”的关联,纵横推演之际,就完成了对梁氏诗学转向的文化解读。
梁启超回归同光风尚并非维新诗家的个案,严复、林纾等新派学人也都有此种倾向。严复濡染西学甚深,以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名噪一时,诗作却“树骨浣花,取径介甫,偶一命笔,思深味永”[6]114。在汪辟疆的近代诗学体系中,严复属于闽赣派诗学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其《瘉懋堂诗集》中,酬赠叠唱郑孝胥、沈瑜庆、陈宝琛者屡屡有见,“劬学甚笃,诗工最深”[6]114。在他看来,诗歌首先要发愤而作,展示士绅的远见卓识,形式须抑扬顿挫,格律须排戛妥帖[17]243-244。林纾早年诗作以1897年刊行的《闽中新乐府》、1913年前后刊行的《讽喻新乐府》为代表,他曾说:“畏庐子曰:儿童初学……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18]89不论取法白居易的讽喻诗还是欧西民俗谣谚,诗歌风味中都充斥着维新与现代的一面,与分唐界宋的清末诗坛大异其趣。但在庚戌、辛亥间,严复悄然转向,“雅步媚行,力戒甚嚣尘上矣”[16]56。林纾《畏庐诗存》亦以此时为发端。在陈衍看来,林纾“少年所作,蕲向吴梅村、黄仲则、黄莘田诸家,久而尽予弃斥。中年以来,长学东坡、简斋二家”[18]304,有如此诗学渊源,故钱基博论定林氏诗作风格为清疏淡远,“旷如奥如,尚清遒而不贵绮错”[15]304。
回溯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维新诗家的诗学选择,最初他们试图通过形式、内容的局部变异来提振传统诗学,但却无法克服随之而来的诗体分裂。这种分裂深刻而精确地展示了清末民初政教与诗学背离的片段与细节。可见,诗学的发展毕竟有其稳定的文化传承,相较于求新求异的外向姿态,立足传统的复古开新更显圆融稳健,由此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运动也就为传统的同光体诗学所消解。
三、由唐转宋——近代岭南四家清劲诗风的转向
岭南近代诗学,康梁等人为代表的雄直诗风当然雄踞主流。求新求异、排戛动荡的诗界革命派与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思潮相呼应,昭示着时代的新风。盘点岭南近代诗家,在雄直风尚之外,也有不少人受道咸宋诗运动的影响,以清劲幽峭为宗尚,自具面目。此类诗家中最著名的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黄节并称“近代岭南四家”。
梁鼎芬少入词林,声望清华,因在中法战争中越级言事而被贬黜,后入张之洞幕府,与同光体诗家郑孝胥、陈三立相往还。梁氏寝馈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甚深,其诗佳处多在悲慨、超逸两种。盖其早年诗学韩偓,多凄艳绵缈之音,中年以还,为家国身世激荡,惘惘不甘之情时时形诸笔墨,如“芳菲时节竟谁知?燕燕莺莺各护持。一水饮人分冷暖,众花经雨有安危。冒寒翠袖凭栏暂,向晚疏钟出树迟。傥是无端感春序,樊川未老鬓如丝”[19]65。陈声聪盛称此诗“俊逸高警”[20]34,可见其声情绵缈、哀感顽艳早为诗坛所共知。
曾习经早年从梁氏问学,诗作风尚颇为相似,“早年近体宗玉溪,古体宗大谢,峻洁遒丽,芳馨悱恻……中年以降,取径宛陵,摩垒后山……腴思中含,劲气潜注……及其晚岁,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入陶、柳圣处”[21]4926。徐世昌则说曾习经“辛亥后,寄寓宣南,却聘课耕,贫悴以殁。诗托意深微,而出以淡雅,温厚清远,在都官、后山间,光宣之际,自名一家”[22]528。
自1907年起,同光体诗论家陈衍赴京师学部任职,他一方面与陈宝琛、樊增祥、赵熙等诗坛名宿广通声气,另一方面以京师大学堂—小秀野堂为中心,向巴蜀、岭南诗人群输出同光风尚,在陈衍的大力鼓荡之下,京师诗坛逐渐为同光风尚所牢笼。岭南四家中,曾习经、罗惇曧、黄节早先均蕲向中晚唐,及至入京,诗风随即转向。在陆胤看来,从《国风》到《庸言》,以曾、罗等人为代表的岭南诗家有着比梁启超等维新诗家更为纯粹的诗艺转折。如果说此前维新诗家雄直诗风的转向体现了从政治向文学本位的过渡,那么,以曾、罗为代表的岭南四家更多地表现为诗学旨趣与眼界识力等内在思想文化的群体认同。罗惇曧曾任京官多年,性喜交游,与诗坛名流俊彦广通声气,在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中,罗氏多次出现在庚戌、戊午的都下雅集中,“计余居都门五年,相从为五七言诗者,无虑数十人。讨论之契,无如赵尧生(熙)、陈仁先(曾寿);进学之猛,无如罗掞东(惇曧)、梁众异(鸿志)、黄秋岳(濬)”[16]36。此时,他正担任《庸言》诗文录的采编,左右逢源之际,诗风早已由唐转宋。其诗曰:“工诗固多穷,人自穷非诗。力与文字远,未必富贵随……落落二三子,遐蹰勤摹追。”[23]正如叶恭绰所说,罗氏“殆入北京,与当代贤俊游,切磋洗伐,意蕴深迥,复浸淫于宋之梅、苏、王、陈间”[24]。
燕志华评定黄节的《蒹葭楼诗》,曾说“黄节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思想是南社的,而其诗则得力于‘同光体’。二者在其身上得到了复杂而又和谐的统一”[25]240。汪辟疆则评“晦闻晚岁以世变乱亟,人心日坏……幽忧所感,悉发于诗。其诗由晋宋以入唐宋诸贤,惟不落前人窠臼,沉厚悱恻,使人读之,有惘惘不甘之情”[6]262,所谓惘惘不甘,正是同光体诗家郑孝胥清苍幽峭的美学风格。
四家之外,诸如潘博、黄孝觉等岭南诗家在清末也与京师同光体诗人群多有唱和往来,风化所及,诗亦近于清苍幽峭。回溯清末民初的京师诗坛,以《庸言·诗录》为载体,事实上岭南两派诗风已经呈现出合流的趋势,共同汇聚在同光风尚之下。以《庸言·诗录》第9期为例,在全部20位诗家中,罗惇曧、黄节、潘博为清劲诗派,麦孟华、何藻翔为雄直诗派,诸人与赵熙、杨增荦、王闿运等人一道附翼于同光体核心诗家陈衍、郑孝胥、陈三立等人周围,共同成就了岭南近代诗坛的具体面貌。
四、从“雄直”“清劲”合流看近代诗学的走向
若是着眼南北不同的诗学源流,近代岭南诗学自树一帜,在诗分六派的总体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岭南对中原诗坛的辐射与影响也日渐增强,以康、梁为代表的岭南诗家甚至一度成为风行海内的时代最强音。若是立足雄直、清劲的脉络演进,不论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诗家还是以曾、罗为代表的传统诗家,均有汇入宋诗派同光体诗学阵营的趋向。传统诗学现代性转换下的岭南现象由此产生:一方面岭南诗学异军突起,成为近代诗坛的重要流派之一;另一方面岭南诗派又逐渐为同光风尚所牢笼,最终完全消解。总结前文可知,近代岭南诗学发展贯穿着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时代的双重意涵。
首先,不论溯源诗坛流派的谱系建构还是着眼“雄直”“清劲”的内生逻辑,岭南诗学的发展都印证着从别体到附庸的总体态势。在此诗学格局背后,呈现出南方与北方、中央与地方等二元政教模式。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裹挟着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意涵,由政治而艺文,在诗学逻辑上便会形成附庸与主流的互动共生关系。从明初的“南园五先生”到清初的“岭南三大家”,岭南地域流派风格的萌生、高涨与彼时中央政权、主流诗坛均存在强弱对立的总体态势。自近代以来,中央与地方的传统政教模式逐渐瓦解,民国间军阀割据更进一步弱化乃至消弭了北方作为政教文化中心的象征意义。因此,身处晚清的陈衍在诗坛标举同光诗学风尚,未尝没有维系传统政教文化的心理。汪辟疆进一步论证诗分六派,诗坛的分裂割据必然也呼应着民国政坛的割据态势。也正是民初南北政治思想文化的强弱互易,推动了民初岭南诗学的繁荣兴盛。
其次,如果说“雄直”“清劲”诗风长期以来对立共存的流衍成就了岭南地域诗派,那么,随着传统诗学现代性转换的推进,两派诗风的合流也就宣告了岭南地域诗学的消解。自近代以来,岭南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窗口,以此为契机,岭南诗学也呈现出传统与新变共存的态势。“雄直”诗风原本溯源传统,但在康、梁等维新士绅的推动下,逐渐转向新异;与之相对,“清劲”诗风则偏重认同复古开新的同光风尚。经历短暂的分流之后,两派诗学又共同汇聚于传统诗学的大旗之下。只是,合流之后的岭南诗学成了同光风尚的附庸,而同光体诗派也在白话新诗运动的冲击之下日渐没落。以传统诗学的现代性转换为背景,溯源于雄直风尚的诗界革命运动无疑是白话新诗运动的先驱,康、梁等人对传统诗作内容与形式的探索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有着相同的路径,只是后者更彻底、更激进。徘徊于传统现代之间的梁、黄诗界革命最终难以舍弃传统,胡、陈白话新诗由此而全面趋向西化,并且颠覆了整个旧诗体系。蕲向传统促进了岭南两派诗风的合流,应对现代则完成了岭南地域诗学的消解。
综上所述,近代岭南“雄直”“清劲”诗风的流衍与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转向密切相关,甚至岭南诗派存在与否都取决于参照何种诗学体系。同光体诗派发展到清末,与时代精神已经渐行渐远,亟待变革。然而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冲击之下,同光风尚转而成为传统诗学乃至传统文化的象征,成为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此风潮之下,趋向新异的诗界革命派选择了回归传统。新文化运动通过白话新诗体系的建构看似消解了新旧诗学的对立,实际上以新诗为主导的体系依旧需要应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转换。胡适在1922年就宣布白话新诗取得了胜利,可时至今日,立足于传统的旧体诗词写作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诗学范畴内部这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现象回应着清末保守主义的诗学路径,我们固然不需要回归同光体诗派的复古开新,但一空依傍的全面创新显然又是一种偏颇。
在近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从新月派到现代派,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通过对晚唐五代情韵藻采的传承实现了融汇中西的审美理想;从国统区的中国诗歌会到解放区的新民歌运动,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又尝试着回应传统诗学对民谣俗谚的吸收借鉴。世纪之交,九叶派诗人郑敏接连著文质疑新诗的西化路径,提倡重新挖掘传统诗学在新诗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背景,汪辟疆提出的岭南悖论也就得到了化解,岭南诗派在近代虽然为同光风尚所消解,但随着现代诗学的进一步拓展,它所保留的新变因素必定会被重新激活,为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转向提供新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