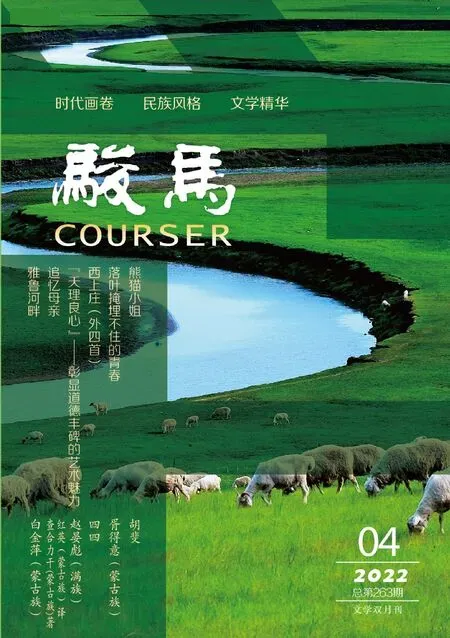庭院美丽
■韩高琦
一
抽枝开花前,紫薇的主干被漠视,
皮肤罩着一层泥色。
枯燥,不加微笑和运动系数,
如坚持着的自我放逐,
如初冬的一次远足却从未抵达。
皂花雀偶尔停栖,
爪趾绯红,细小,分享边缘生活的支点,
惹人怜爱的构图。
叫声依旧,我的布衣口袋依旧。
竹屋一角,立着一个土陶坛子,
装得下五斤黄酒,
热血的年龄离开我很久了。
我捡到它时,有一根羽毛
落在里面,空虚显得很具体。
拿小石子轻叩几下,
如是我闻:回音雄浑
二
独门独院。
法国冬青抬高篱笆墙的倔强头颅,
二哥说:不修不剪——
随心所欲的样子,难得一见,
无为哲学,人身上的隐形翅膀,
忘了飞翔,始于何时?
它们从未歇息,
警觉,如猫鼬直立,
一年四季说着同一种护卫的语言。
我的安心纯属审美疲劳。
西厢的那丛芭蕉,可以听雨。
虚拟者,切开一个柠檬,
清凉的阴影下,
可以抚琴,可以吟啸,
可以入梦——
冉冉之姿与午后的怔忡相匹配。
再远的薄荷知音,也在眼前。
三
大树有三:一棵沙朴,一棵香樟,
另一棵也是香樟。
我不想细写:它们太显眼,
占据东、南、西三面。
东方既白,紫气笼罩的翠竹,
俨然韩星圆的身姿,
脱俗,爱理不理,闺阁幽闭。
一贯的格调,洁癖和距离,
拔节的清风呵,早晚摩挲,
家族最高的颜值,对着朗月吟哦。
墙角边散落着数株竹柏,
明显营养不良,
伞状的造型始终没有达标。
沿阶的忘忧草却是不依不饶。
孪生的一对玉兰树被分开移栽,
十几年下来,
变成一大一小的搭档,
深喉中的怨怼,不被我理睬。
四
当然,石榴的寓意纯属本地特色,
与爱琴海的吟唱无关。
我栽下她的那一刻,
没有多想——
眼下,灯笼花齐发,
梧桐韩家的虎纹基因被彻夜照亮。
耕读传统不变,
从泥土到草根,到蛹,
从胚胎字母到蒲公英的鹅黄发音,
从风铃到雄黄,到香囊,
阳光芬芳,燕子斜飞,
报春的消息来自出门打拼的后辈们,
年迈的母亲眼神清澈,
双耳拒绝尘世间的噪音,
她坐在竹屋的廊檐下,诵经。
五
屋宇深藏大海的寓意,
正阳门,两侧八字排开,
分别侍立着一棵铁树——
哦,两米高的铠甲武士,
雌雄一对,威势旗鼓相当:
全身的剑戟怒张,未曾一刻懈怠。
“请止步,”左边发话,
“进门前要安检。”右边补充。
假想敌又是谁呢?
一个巨婴时代,怎样学会自处和拒绝?
独门独院。天地留白处,
分明就是陶潜三分地,
父母替我在打理,
那里种植着葱蒜,星月和五行数学题,
答案留待宫叔回归的秋季,
留待寂茶室打造完工的那一天。
漫不经心,移步到庭院中央,
我牵手椭圆形的花坛,
沿着顺时针方向走一圈,
接着,又逆时针走一圈。
如此反复往还,
一如七星瓢虫牵手奥特曼,
一如红花檵木牵手毛叶丁香的执着,
一如乡愁牵手诗人半生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