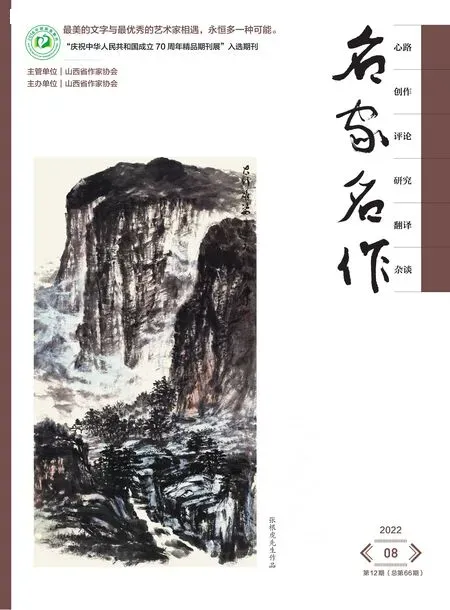精神生态视角下《长日留痕》男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重建
窦龙昕 马秀鹏
一、引言
《长日留痕》一经出版便立刻受到各国学者、评论家的高度关注,研究主要围绕人物角色、后殖民语境、回忆主题以及叙事风格与叙事策略等角度进行。国内对石黑一雄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不如国外成熟,但已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位国际作家。该小说刻画了一位对达林顿勋爵唯命是从,不顾个人情感的英国管家形象,体现了石黑一雄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细致入微的刻画及对人性的敏锐洞悉。从精神生态视角窥探史蒂文斯的心理状态及情感波动有助于我们寻找到导致精神失衡的原因并在实践中总结出实现精神救赎的方法与路径,尤其是为现实所累以及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们指明方向。因此,深入探究主人公史蒂文斯的精神救赎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著名学者鲁枢元将生态划分为自然、社会和精神三种。自然生态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相对独立的自然界,社会生态主要研究范围是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行为,精神生态主要研究人类内在的情感与精神生活。他还提出了“精神圈”概念,他认为:“把地球生态系统划分为水圈、大气圈、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五大系统是不全面的。在这五大系统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由人类的操守、信仰、冥想、想象构成的‘精神圈’,它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精神圈”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第六大系统,肯定了人作为个体的精神性存在,也突出了人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生态文艺学》中,他概括了现代人的五种精神病症,即“精神上存在的‘真空化’、行为上表现的‘无能化’、生活风格中出现的‘齐一化’、存在展现出的‘疏离化’,以及心灵上凸显的‘拜物化’”,这样的精神生态折射出现代社会发展的困境。
二、主人公精神生态的失衡
(一)人与自然的疏离
“疏离化”这种病症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内心世界这三方面的疏离。鲁枢元提到以往的人随时都在与充满生机的自然进行着对话和交流,现代人却很少直接亲近自然,而只与自己制造的工业产品,做着单向度的独白。“人们不但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感受不到自然的阳光,甚至也已经失去了对于‘春、夏、秋、冬’的季节的体验。”史蒂文斯服务于达林顿府长达35年之久,但从未踏出过府邸;当他面对来自美国的新主人刘易斯提出的驱车前往英格兰西部旅行的建议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是心中自言自语道:“……去美丽如画的风景名胜观光这个角度……了解甚少;……但身处英格兰名流显贵常常聚集的豪宅里。”由此可见,史蒂文斯对于是否了解本国的自然风光与风景名胜并不在意,他真正看重的仅是为英国名流及政要提供服务。当肯顿小姐好心将一只满插鲜花的大花瓶放在史蒂文斯办公室以为其阴暗冰冷的休息室增添活力时,他表达感谢后却直言道:“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但这不是一间娱乐室。我很乐意将消遣保持到最低限度。”并迅速将话题转移到工作上。鲜花既象征着大自然的生命力和活力,又象征着肯顿小姐对史蒂文斯爱意的吐露。但史蒂文斯冷漠的回应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等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事物丝毫不感兴趣,他拒“自然”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既加速了鲜花的凋谢,同时也再一次浇灭他与肯顿小姐之间爱情的火苗。
(二)人与人的疏离
“人与人的疏离,是由社会对‘竞争’的鼓励开始的。”在这种社会气氛中,关爱、同情、帮助难以出现。书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提到了“海斯协会”。入会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申请入会者须具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史蒂文斯对其标准所述的尊严奉为圭臬,同时与其他府邸的男管家进行交流与竞争。这种孤注一掷的拼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史蒂文斯对周围环境及关系的疏离与麻木。最具表现性的是肯顿小姐执意要过问史蒂文斯正在阅读的书籍,但史蒂文斯所持的态度却是:“我务必请你别打扰我……这是完全不能让人忍受的。”史蒂文斯对个人情感进行极致克制:肢体与眼神的躲避以及冒犯的言语都在无形中拉远了与肯顿小姐的距离。
然而,肯顿小姐并不是史蒂文斯 “疏离化”的唯一“受害者”,他的父亲老史蒂文斯先生也不例外。1932年于达林顿府召开会议期间,他的父亲老史蒂文斯彻底病倒,史蒂文斯却无暇安守病榻,只在父亲的卧榻旁做过三次简短的逗留。面对其父鲜有的情感袒露,他局促不安,无言以对,一遍遍地重复“希望父亲现在感觉好些了……我很高兴父亲感觉好些了……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直至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他仍忙于侍奉从而痛失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而当迪纳尔先生问起史蒂文斯的精神状况时,他却用借口“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痕迹”搪塞过去。由此可见,史蒂文斯不愿流露真实情感是一种自我欺骗的精神麻痹,对情感的极致压抑使得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疏离。
(三) 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
鲁枢元认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更多的是精神的丧失,即表现在信仰的丧失、理想的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丧失。精神的丧失,引起自我肯定的坍塌。在他的这部类似日记般的回忆录的叙述中,读者很快发现,他对自己所处的困境遮遮掩掩,不敢袒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叙述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时,叙述者往往做出错误的道德判断且隐含与作者价值取向不一致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可靠叙述”。修辞性手法将不可靠叙述定义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上,在阐述叙述距离时,布斯指出:“当叙述者所说所做与作品的规范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小说中村民与韦克菲尔德夫人等人询问史蒂文斯是否为达林顿勋爵工作过时,为府邸服务35年之久的他回答道:“我没有,夫人,绝对没有。”二战结束,时过境迁,达林顿勋爵已经成为举国唾弃的对象,史蒂文斯出于对“尊严”的考虑,羞于承认事情的真相,却在心中默默坚持认为“我们这一行的人……手中掌管着文明”,坚持相信他服务的主人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由此可见,史蒂文斯经历了二战任人摆布的命运后,还未彻底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已经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在他看来,承认事实莫过于将自己35年尽心效力的心血付诸一炬,将自己一生秉持的“尊严”摒弃,从而他整个人生的意义也就土崩瓦解了。因此,与内心世界刻意保持疏离,与残酷的现实保持距离,他才能直面痛苦。
三、精神失衡的原因
(一)母亲角色的缺失
史蒂文斯虽是整部小说的叙述者,但却从未提及自己的母亲。石黑一雄说:“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什么是他要逃避的……他为什么要在特定的时间说特定的事件,这些都不是随意的。”主人公回忆早年时的工作经历时,他的话题总是避不开自己的父亲,十分自豪地向读者夸赞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如何完美得到了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尊严”。甚至在提到兄长伦纳德死于战争这一残酷事件时,也竟未提及自己的母亲对于丧子之痛做何反应。史蒂文斯对于父亲的过多着墨同时也暗示着史蒂文斯内心不愿意袒露有关母亲的任何事情。从史蒂文斯与其父亲的职业经历来看,父子关系的重要程度远远高于母子关系。母亲角色的缺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史蒂文斯日后在处理亲密关系时的无能化。长期以来,史蒂文斯一直浸泡在父亲的严格的职业操守中,并将此奉为圭臬,由此史蒂文斯对于与工作无关的亲密关系尤其是男女之爱的抵触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异化的职业伦理观念
史蒂文斯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职业素养的男管家,维护着达林顿府各个方面的运作,不容许有一丁点儿的差错与不规范。虽然他不能像雇主达林顿勋爵那样对人类的和平事业有所推动,但他却坚定地相信 “他也曾为服务于全人类而施展过其才华”。令人可悲的是,史蒂文斯对于雇主的绝对服从、盲目服从使他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事实真相的勇气,遮蔽了内心的情感需求,并将“尊严”渗透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彻底模糊了生活与工作的边界,两者混淆不清。按照其近乎异化的职业理念,他将工作视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与幸福擦肩而过。比如,当肯顿小姐告知史蒂文斯她已经接受了朋友的求婚,他仍强掩内心悲伤并反复强调着“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的事件正在楼上发生”,他必须立刻返回楼上工作。在肯顿小姐强烈的暗示下,仍然不做出任何挽留,仅仅表达祝贺后借工作之故离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泯灭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基本情感需求,与内心自我愈来愈疏离,最终沦为阶级和制度的奴隶与牺牲品。
四、 实现精神救赎的途径
关于“精神生态”,鲁枢元认为:“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中,每两者都是双向动态的关系。精神生态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类生存的现实物质世界之间的桥梁,起着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对于史蒂文斯而言,历时六天的西部之旅无疑是一条精神疗愈之路,是构建精神平衡的绝佳契机。
(一)回归自然
在史蒂文斯为期六天的旅途中,他经常会因为沿途的壮丽风光而大为惊叹。首先,他为自己规划的行车路线十分满意:“它引导我穿过了农田,使我置身于牧草地散发的怡人芬芳中……以便可以更好地欣赏所经过的小溪或是山谷。”如此温柔的言语无不透露出史蒂文斯对于自然的热爱。当第一晚到达索尔兹伯时,史蒂文斯回忆起白天所见美景,直呼道:“那鳞次栉比、延绵不断的英格兰乡村土地,那场面是多么的壮观啊。”旅行的第二天,史蒂文斯偶然救了一只横穿马路的母鸡,面对农舍主人的感激时,史蒂文斯笑着说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经历。你看,我正驾着车寻求这种乐趣呢。”而当女主人和史蒂文斯分享前些日子乌龟被压死在路上的悲痛心情时,他便也忧郁地感慨道:“真是太悲惨了。”不知不觉中,史蒂文斯逐渐卸去了自己坚硬的外壳,人性的温暖慢慢复苏。再次上路之后,史蒂文斯也收获了内心的安宁,袒露道:“这次小小的遭遇……使我对未来几天里将面对的整个旅行计划感到特别的振奋。”构建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景。
(二)自我反思
第三天晚上,史蒂文斯由于汽油耗尽而在一个小村庄意外停留时,素不相识的泰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家里暂住,并吸引了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谈论的话语对史蒂文斯的观点造成很大的冲击。史蒂文斯所认为的只有贵族才有“尊严”与邻居哈里·史密斯先生认为的“尊严是这个国家每一位男女都可以为之奋斗而获得的”起了冲突。在与邻居们争论后,史蒂文斯坚定地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和理论化了”,“并不值得尊重”。但紧接着又承认道“无疑是有几分道理”,这自相矛盾的说辞反映出了史蒂文斯内心对“尊严”定义的动摇。最后,史蒂文斯幡然悔悟,意识到任何自以为是的人想要给“尊严”下定义都是“荒谬可笑的”。在小说的结尾,当史蒂文斯得知肯顿小姐不会和他一起重返达林顿府时,他勇敢承认道:“我的心行将破碎。”在与陌生人打开心扉,流泪倾诉后,史蒂文斯终于能够正视自己:“我应该停止过多地回顾过去,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而且应尽力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在无休止地回顾往事和责备我们自己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能获得什么呢?”终于他看穿了过去生活的虚妄,决定走出昔日的阴影,重燃希望,过好剩余的宝贵人生。尽管这种改变与成长伴随着极大的阵痛,但这是实现精神生态平衡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彻底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实现伟大的精神上的涅槃。
五、结论
石黑一雄小说中男主人公精神生态失衡的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书中,更是全人类都要面临的危机。人类在大步向前迈进的过程中更要看清自我的状态,学会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史蒂文斯在同样是管家的父亲的影响下,在异化的职业伦理观念指引下,舍去了最美好的亲情、爱情,丢失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岁月流逝,二战结束,事实证明他追求的目标只是虚幻的泡影。在感受人性美、自然美的旅途中,史蒂文斯重新找回迷失的自我,明确自己的人生价值,搭建人类健康的精神生态家园,最终建构了精神生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