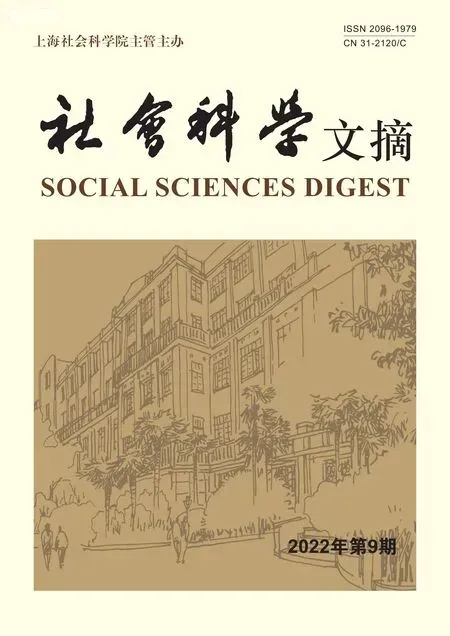现象学与中国哲学
——兼论中国现象学建构的可能性
文/蔡祥元
现象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尤其在人文精神方面有独特贡献。近二三十年来,现象学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研究不断深入,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话也在全方位展开,涉及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乃至文艺理论等领域。可以说,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界的一个“现象”。本文在相关讨论的基础上,对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关系再做一些新的考量。在思想方法上,笔者将对现象学的“事情本身”进行提炼,表明它具有原初给予性、居间构成性以及直观明见性三个基本特征,然后将它与中国哲学的工夫论做对比。接下来,结合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背景来突显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亲缘关系,并借助学界有关中国哲学的现象学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的“事情本身”有某种哲理上的特质性。以此表明,我们有理由期待和展望,未来可能出现一种有别于德、法现象学,可以名之为“中国现象学”的思想流派。
什么是现象学
现象学的开创者是胡塞尔,广义的现象学包括海德格尔、舍勒、伽达默尔、罗姆巴赫、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现象学家各有其思想领域,他们以现象学方法为指引,围绕意识现象、生存体验、存在领会、伦理价值、知觉感受、文本阐释等专题,打开了一个个独特的思想视角。就现象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思想方法。这个方法或态度通常被总结为“朝向事情本身”。要把握现象学的“事情本身”,首先需要将对待事物的日常态度和理论态度悬置起来,这就是现象学的悬搁判断,也是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
由于“事情本身”是通过现象学还原揭示出来的,如此获得的“事情本身”首先具有原初给予性的特征。胡塞尔将它确定为“一切原则的原则”。不同现象学家关注不同的“事情”,但它们都具有这种“原初给予”的基本特征。舍勒称之为“自身被给予性”,并认为它是现象学实事领域得以统一的共同性所在。海德格尔通过词源学考察表明“现象”一词在古希腊那里的原本含义是“显示着自身的东西”,并据此将现象学的“现象”解读为“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此种原初给予性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事物的直接显现,它不同于现象主义、实证主义所号称的那种只以眼前直接感知到的东西为实在。与它们相比,现象学所揭示的“事情本身”甚至具有某种先验的、先天的特征。但是,现象学并不因此走向柏拉图的先天理念论和康德的先验论。此种“先天结构”,不同于先验形式,它不是以使经验现象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的方式存在,而是经验现象得以构造出自身的那个构造性活动本身。
为此我们把“事情本身”的第二个特点称为居间构成性。西方传统哲学一直以来受两大对立的思想方式支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现象学原则是要在哲学层面“解构”这些对立。当然,这不是对它们的简单否定或拒斥,而是深入到对立双方各自思想的根子处,然后再往前推进。由于现象学所揭示的“事情本身”总是处于这两大对立的思想方式中间,因此具有“居间性”。现代西方哲学中具有此特征的哲学流派并不少,詹姆士的意识流、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等。但是,他们主要只是描述了一种还未理论化的、处于主客对立之前的原本的“生活经验”(生命冲动或生存意志),并把它作为世界现象的“根据”,而对此类“居间物”何以能够成为世界现象的“根据”,这方面的展示整体而言还是“笼统”的,会成为某种单纯的“先天论”。这就涉及现象学的“事情本身”的构成性特征,张祥龙称之为现象学的“构成识度”。
“事情本身”的第三个特征是直观明见性。现象学的直观明见性不同于逻辑的自明性,后者是纯形式化的、客观化的。这涉及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自然主义的区别。在对事情本身的考察方面,它们是当代西方哲学两大主要的哲学流派,在思想方法以及在问题本身的考察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哲学的理路,都反对宏大叙事,而甘于“打零工”。但是,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的推进,在我看来,有一种将“经验”平面化、单一化的趋势,正如科学将自然现象均等化为数理模型那样。它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也经常引入逻辑符号来进行“逻辑推演”。这一特征使其相比于现象学,看起来更有科学精神,也更加严密。而这种做法,在现象学文本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原因就在于现象学所打开的视野不是“平面的”,现象学理路地展开不是基于“概念”的逻辑推演。
“事情本身”上述三个基本特征之间充满张力,要恰当把握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并不容易。要把握现象学的“事情本身”需要某种工夫。我这里参考中国哲学,把这个特点称之为现象学方法的工夫论特征。将现象学方法称为“工夫”,不只是表明掌握现象学方法需要全身心参与,同时也是借助中国古代道论传统中的工夫论来彰显现象学“方法”与现象学的“事情本身”之间的内在关系。
现象学之于中国哲学
自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以来,如何会通中西哲学是中国学人的头等大事。清代的训诂考据中断了宋明哲学活泼的思想对话传统,本身不能再产生出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的全方位“入侵”,从自然认知到社会制度各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传统观念的思想构架在现代人看来缺少明见性,与主流的“世界观”难以圆融。现代人做中国哲学,如果不满足于“寻章摘句”,而希望在思想本身方面有所突破,那么融合、吸收西方哲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都深谙西方哲学。他们对儒家义理的重新阐释,都参考、借鉴乃至融合了西方哲学的某些视角。他们因此对儒家义理有所新的发明。但是,整体而言,这些“发明”并不算成功。他们所倚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跟中国古代哲学的哲理差距甚远,不能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生存论关切充分展现出来。哪怕是现当代的生命哲学、意志主义、过程哲学等,它们尽管也注重生命体验,但仍与中国哲学“貌合神离”,因为中国哲学不是满足于单纯的生命体验,而是体验其内部所具有的某种“超越性”价值。在这方面,只有牟宗三借助西方哲学而对中国哲学的义理有所推进。他的思想创新主要借助康德批判哲学,并因此找到了中西哲学传统的“对接点”,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限制,他并没有把这个“对接点”打开。牟宗三、唐君毅都曾关注过现象学。唐君毅将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的对象作为一种“纯相”的世界,与柏拉图哲学归为一类,这个归类并没有看到胡塞尔与柏拉图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牟宗三从康德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现象学进行过直接评判。如倪梁康所指出的,牟宗三对现象学的评价是“偏误”的,他没有看到,其“智性直观”的理路在许多方面与现象学方法有相一致的地方,尤其是没有看到,现象学方法跟人生哲学的紧密联系。
对一种“先天”的东西的把握和展示如何不陷入空洞的概念思辨,正是现象学超出康德哲学乃至超出西方整个传统哲学的得力之处。现象学“朝向事情本身”的思想方法,具有一种立足前概念、前反思的实际生活经验来阐发精微洞见的思想旨趣。张祥龙把现象学方法的这个特点称之为“热思”,强调它具有不离开实际经验的源发性、时机构成性的基本特征。现象学这种思想特点,相比于其他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传统更为契合,后者同样是一种不离人伦日常又不滞于人伦日常的思想经验。
除了思想方法的契合以外,现象学所关注的“事情”本身很多地方与中国哲学也是相合的。比如,像倪梁康所指出的,胡塞尔对意识现象的分析跟佛教的唯识学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可能建立起紧密联系。着眼于我们前面指出的广义的现象学,那么,这种相合的主题有很多。例如,海德格尔着眼于人与世界的内在关联来思考“人之为人”,相合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舍勒对情感与价值关系的考察,相合于儒家在情感的发用中指点价值之根源的思想特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梅洛·庞蒂有关身体主体性的揭示,与中国哲学“身心一如”的思想传统遥相呼应。
虽然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存在亲缘关系,但要真正从现象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哲学并不容易。很多时候这种解读往往停留在从外部对中国哲学的义理扣上一个“现象学”的帽子,而对相关文本的阐释依然停留在传统哲学框架之中。哪怕将相关文本摘取出来与现象学文本进行直接比较,这也只是对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它们跟中国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乃至与实用主义等的比较研究,并无实质区分。对于此类比较研究的现状,正如倪梁康与方向红所评述的,还不是真正的“会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代哲理虽然也具有现象学的“双非”特征,但它们只是“隐含”在文本之中。如何在古代文本中“剥离”出它所具有的现象学洞见,这需要现象学的“工夫”。这跟一般的现象学研究一样,此种“洞见”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现成存在物,它需要研究者进入文本空间以后进行“重构”。在中国古代文本中找到的现成的思想观念,尤其是那些基本哲学观念,大都已经积淀了太多的“想当然”,都不是现象学的。它们都是首先需要放在括弧里的“大概念”,可以说,都是现象学需要悬置的“自然态度”或“传统观点”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之于现象学
自胡塞尔开创现象学以来,现象学在欧洲大陆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象学运动,不仅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胡塞尔的思想大家,在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美学、诠释学等领域打开了新的视野,甚至成为一般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现象学大家的相继离世,现象学也进入某种衰微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方法本身有问题,而是说,它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在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中已经穷尽了它的可能性。
与欧洲大陆不同,现象学在中国哲学界整体上还处在引介阶段。这几年随着胡塞尔全集(倪梁康主持)、海德格尔全集(孙周兴主持)、伽达默尔全集(洪汉鼎主持)、舍勒全集(张任之主持)和列维纳斯全集(朱刚主持)等现象学经典文集的系统翻译与研究的展开,现象学在中国大陆的研究会出现一番新的势头。在中国现象学的研究方面,目前有两个主要方面的突破:一个是张祥龙前后期的天道和孝道现象学;一个是耿宁和倪梁康的心性现象学。
张祥龙在其早期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背景,吸取并借鉴其对存在的现象学展示,从时间性、境域性、构成性等维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的天道观进行了现象学的阐释。他所展示出来的天道,既具有现象学视野的基本特征,又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质,由此在德法现象学之外打开了新的现象学视野。之后,张祥龙转向对儒家哲学的现象学研究,其代表性作品有《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和《儒家哲学史讲演录》。这些研究可以称之为孝道现象学,它们主要围绕亲子之爱及其背后的意义生成机制而展开。在张祥龙眼里,这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心印”。孝道现象学对儒家哲理的重新阐发有别于新儒家直接从心性之体入手去接续宋明理学,而是彰显了儒学一个更为古朴的维度。但它并不古老,因为它采取了现象学的视角,有别于学界对孝道文化采取的一般性的文献疏证或义理研究。作者的这番“复古”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耿宁与倪梁康的心性现象学研究,参考并借鉴胡塞尔意识结构的现象学分析,对唯识学和儒学中的心性结构进行了类似的现象学分析。相关的研究著作有:倪梁康的《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缘起与实相:唯识现象学十二讲》等文章和论著,以及耿宁的《心的现象学》《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虽然倪梁康、耿宁主要参照胡塞尔的思想方式来研究唯识学、儒家心性之学,但他们由此展现出来的具有现象学意谓的心性结构与胡塞尔的意识结构有着根本的区别。耿宁从中国哲学视角出发向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来突显两者的区别。这些问题突显出中国哲学语境下的心性现象学对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超越。可以设想,就像海德格尔、舍勒做的那样,心性现象学也将在诸多现象学领地中展现出自己独有的“事情本身”。
此外,陈立胜从身体性维度出发对阳明心学的重新阐释、张再林的中国古代身道研究、孙向晨有关家哲学的系统性建构也依托和借鉴了现象学的视角,柯小刚对书法和《诗经》的现象学阐释与实践、方向红对中医和《易经》的现象学研究、朱刚依托列维纳斯展开的有关家的现象学研究、张任之依托舍勒对儒家心性与体知问题的现象学研究等,也都是在此思路下展开的。而王俊从罗姆巴赫的跨文化现象学视角出发,指出现象学内在地就有一个跨文化而生的维度。这一切都预示着现象学在中国大陆将有一个新的开端。
——专栏导语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