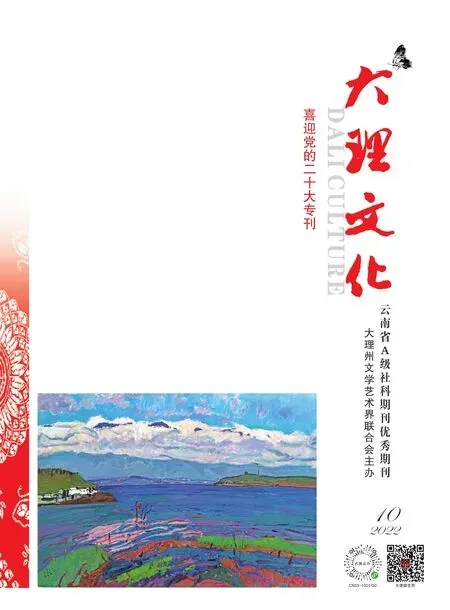宁静光明
●段成仁
光明村。
这个名字进入耳朵,应该是在十几年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个藏在苍山西坡褶皱里的村子,因其让人费解的“光明”之名,在我心头产下一颗卵,并孵化出一只不安分的蠕虫。十多年来,这蠕虫一直在心里爬爬停停。都说时间会让人淡忘一切,可这些年来,蠕虫却在心里头越长越壮实,其长久的生命力让人惊讶——那个小村庄究竟有何魔力,让我一直挂牵,这么多年都放不下?
念叨的时间久了,竟有所发现。
其一,在经验中,一个村子的命名,大多是用名词来完成吧,如某某庄、某某屯、某某寨。这“某某”的位置,往往由名词盘踞着。这名词一般是最能彰显这村子特质的某种事物的名称,听者一听,大略能从村名中了解这个村子的特征,村子的内质基本可以确定了。比如,某个村庄叫“赵庄”,或是因为这个庄子里的绝大部分人家都姓“赵”,或是庄子上有过一户姓赵的大户人家,这庄子在赵姓人家的提携护佑下,得以生存、绵延并发扬光大,其命运与一户人家相随相融。人们一说“赵庄”,听者脑海中浮现的,就是那个坐落在某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姓赵的村庄,或者就是那个被一户赵姓人家“统治”了多年的村庄。除了由房屋、道路、街巷等组成的具体化的村庄外,还有笼罩在这个村庄上空的赵姓人家的影响力,以及赵姓人家用岁月和统治力酝酿而成的气场,成为这个村庄的特质,这种特质从这个“赵”字里面散发出来,铺天盖地,排不开,抹不去,褪不掉,烙印在与之相关的事物的骨髓里。
而光明村,以形容词性较重的“光明”一词来命名,耐人寻味。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愣住了那么一瞬间。
光明,最为浅见的意思是光亮、明亮。“光明”一词最为常见的用法是用作形容词。此外,光明一词还有“照耀、辉映”“光大、显扬”“荣耀、光彩”“昌明盛大”“磊落、坦白”“正义的、有希望的”等意思。另外,人体有一穴位名为“光明”,位于踝上五寸处,但我估计,一个人体穴位应该与一个村子的命名没多大关系——所以,各种符合逻辑的或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推理不断地在脑海中出现——难道,那是一个散发着光明的村庄?难道那个村庄时常被亮光照耀?还是那个村庄发展前景好,前途一片光明?……各种揣测、各种猜想,时时充斥在我的脑海里,都因为不能亲自到现场了解而得不到确切的答案。
这样的猜测与向往,是蠕虫的生命力的源头之一。
其二,传闻说,光明村核桃多。我出生的村庄也出产核桃,不乏核桃年收入逾十万元的大户。对于核桃的多,我已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所以,暗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叫做“攀比”的人类的天性时时在作怪:光明村核桃多到何种程度,有我老家那么多吗?这是我一直都想弄明白的。
除却不好的东西,好的事物在数量上表现出“多”的特性,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上天赋予云南出产核桃的优秀天赋,全省有16个州市124个县市区出产核桃,其中,漾濞是优秀当中的优秀。多年来,漾濞核桃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若论功劳,光明村的贡献应该排在首位。近几年来,漾濞县每年都在核桃成熟的季节举办“核桃节”,邀请八方宾客共同体验和分享核桃丰收的喜悦。光明村的鸡茨坪是“核桃节”的重头戏——“祭树神”的举办地,所以,我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关注光明村了吧:那里的居民因为有了核桃,一定很富足吧?家家户户都有大片大片的核桃林吧?每到秋天,家家户户都仓满库盈了吧?居民们家家户户都住着宽敞明亮的小洋楼吧?真想亲眼见见。
这样的猜测与向往,是蠕虫生命力的源头之二。
幸好,后来终于有机会去光明了。
那是在2015年深秋。去的缘由是,漾濞县文联邀请州文联的作家老师到漾濞县,为漾濞、永平、巍山三县的写作爱好者上写作课,上课地点就在光明村的核心区——鸡茨坪。而我有幸参加上课,所以,多年的光明之期终得成行。
路上的激动自不必说。培训课上,一心只想赶快寻到一个答案的我,竟然对珍贵的学习机会都不管不顾了。州文联的老师们侃侃而谈,来自三个县的作家们也在班上交流心得,可我总是分心。在我到达鸡茨坪之后,心中那只蠕虫变得异常活跃,不停地在胸口乱窜。身处光明村内部的我,心痒难耐,鸡茨坪的核桃树、民居、石墙、竹丛织成一张细密的网,罩住我,隔绝我对更远处的探查。在圆桌式的课堂上,我东张西望,目光多次穿透砖墙的孔洞,穿透院门,越过屋顶,四处搜索,以期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填筑我这么多年来对光明村无尽想象而开拓的那个空间。
终于下课,来不及多想,就一头扎进鸡茨坪的内部。
但凡对某件事情太过期待,当知晓其结果、面对其真相的时候,往往会有遗憾。光明村就是这样。沿着鸡茨坪的村内道路绕了半天,沸腾了十余年的热情,被眼前的平凡一度一度地降下来,雕塑了十多年的希冀,被脚下的普通一刀一刀削走。平平常常的水泥路上,散落着核桃树叶。路两旁,是高高低低的石墙。石墙外,是我最熟悉的核桃树。核桃树林里,数十户人家的普通民居零散地安放在核桃树下,一声不响。
光明村何以以“光明”为名?“光明”之名何以远播四方?我在村子里转悠半天,却始终没有遇到答案。
茫然地沿着村内水泥路走了一圈,茫然地回到上课的地方,心不在焉地听作家老师们聊天。我确实没能迅速地从希冀到失落的巨大反差中回过神来。
“光明这地方好,安静!”在杂乱的聊天中,突然有一句从中跳脱出来,清晰可闻。
抬头搜寻了一圈,未能确认是哪位说的,内心却被这略带慵懒的声音中的“安静”二字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我才想起,刚才在村子里走了半天,仅仅遇到了两个六七岁左右的小孩子,还有一位用竹耙扫核桃落叶的老大妈。另外,在一个有一排木栅栏的农家院子外,停着一辆越野车,院子里,似有三五个外来之人在喝茶、说话。
细细回想一下,鸡茨坪确实是太安静了。
忽然意识到,自己注意的方向可能偏了。我一定是错过什么了。
我错过了什么呢?思绪回到刚才走过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信息汇聚过来,全都指向了两个字:安静。
顿悟似的,我立马起身,独自一人又往村子深处走去。我想再去看看,自己刚刚是遗漏了什么,或者说,我想再去验证一下,那种我之前没注意到的,以及那位不知名的老师说的“安静”。
经验证明,当人的意识特别地注意某种事物的某方面特性时,这种特性就会被放大。当我再次走在鸡茨坪的水泥路上时,安静就从无处不在的安静中渐渐现出原形来,实质化,包围着我,阻止我的脚步,让它慢下来,捋顺我的呼吸,让它平静下来。
核桃树是安静的。
当时没有风,我走过去的时候,衣袖似乎带起了几缕风,但又轻易地凝固在周围的安静里了。核桃树站在农家院子外、石墙根、空地上,一株接一株,一排接一排,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覆盖着整个鸡茨坪。每一株看上去都是上百年的年纪,甚至数百年,体型巨大,主干遒劲而老成,周身千疮百孔,枝杈懒懒散散。老气横秋的老树桩上,顶着几个老气横秋的枝杈,仿佛有无数段时光被禁锢在里面,不想动弹,看不出树枝有再往外延伸和生长的想法。
那时已是深秋,核桃树们刚刚生产完毕,我没有听见它们因阵痛而呻吟的余音,也没有听见它们诉说生产的艰辛,它们只是静静地看着树根旁被主人遗漏了的核桃果,以及满地的核桃树叶,听任它们的命运,不发一言。就像它们给鸡茨坪的居民们提供了数百年的核桃果,却从未宣扬自己的功劳一样。
密密匝匝的枝杈间,除了残留的一些褐色的树叶,仅剩几声梦游般的蝉鸣,没传出多远,就被深秋锁住了喉咙,此外,就只剩下无尽的寥落。树枝外面,是深秋的苍山和湛蓝的天,天上不时有白色云朵飘过,核桃树看见了这些,但它们仍然一动不动,任云流霞长。
鸡茨坪里的那些古老的核桃树,是公认的光明村的标签,它们安静下来,整个光明村就能安静下来。
与核桃树相比,路边的石墙更是如雕塑一般安静。
矮矮的,两三尺高,时断时续,顺着路边,曲曲折折,向下一个看不见的拐弯处延伸而去。农家随意堆砌,齐整与凹凸不平都是随意的,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竟造出了上等艺术品。青苔也来凑热闹,颜色刚好,潮湿度刚好,茂盛的程度也刚好,和石墙的苍老与沉默、随意与随性高度契合,将艺术的意境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猜了半天,也猜不透主人的心思,砌这些石墙,是设置人家与人家之间的界限吗?不像,有几处石墙完全坍塌,消失许多年了,却看不出主人有修复的打算,有不知名的爬藤密密地覆盖在石墙坍塌处,又是一件天然的艺术品。是用来防范牲畜的吗?也不像,一两尺的高度也拦不住大牲畜们。石墙里头的空地上,零散地有几头黄牛在那里啃秋草。周边有一群鸡在觅食,悄无声息地,偶尔有公鸡一声打鸣,时不时把鸡茨坪的安静撕开一道道巨大的口子。
鸡茨坪的石墙,是安静的琴弦,以安静为拨片,弹奏出的,也是一道道安静的音符,这一道道安静的音符,组成了宁静的华章。
宁静的鸡茨坪,温养了宁静的居民。
那两个六七岁的小家伙出现的时候,我正在用手机对着一堵附满青苔以及细小蕨类植物的石墙拍照。两个小家伙一前一后,从一扇大门里面冒出来,慢悠悠地向我这边摇过来。我将手机对准两个小家伙乱拍一通。看见我拍照,小家伙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我。见我放下手机,小家伙们又继续前进,走到路边的竹丛旁,从草丛中采摘一些叶子,采好后,又往回走,消失在大门后。自始至终,两个小家伙没有言语,没有笑声,没有沟通与交流。
拿出手机翻看刚拍的照片,稍大一点的女孩留着笔直的中分齐肩发,上穿红色夹克,上面印有“米”字旗,下着黑白横格子齐膝筒裙,裙脚印有一只白兔,脚杆纤细,脚上是一双白色胶鞋。最显眼的,是那双直视着镜头的眼睛,平静而幽深,像是藏在石缝中的两小汪干净而清澈的水。另一个是小男孩,稍稍靠后,从小女孩肩头后露出大半个头,单眼皮,眼神跟小女孩的一般无二,也是两小汪干净而清澈的水。他们身后,有青翠的竹丛,有长满青苔的石墙,有乳白色的枯竹叶。
这样的孩童让人感到陌生。
我所熟悉的孩童是欢笑着的,蹦跳着的,撒着娇的,哭闹着的,酣睡着的,而照片里的这两个小家伙,与周围的石墙、草丛、落叶融为一体,安安静静,无声无息。
用竹耙扫核桃树叶的大妈也是不声不响。看见大妈时,我问大妈:“收集落叶是用来生火,还是垫牛圈?”大妈说:“不是,就堆在树根,做肥料。”大妈说话时,手中的竹耙并没有停下来。仅仅就一句,说完这一句,大妈抿起了嘴,嘴角有着淡淡的微笑。我就站在旁边看,竹耙所过之处,枯叶沙沙作响,厚厚的一层叶子就被捋成一堆又一堆,堆在树根周围。被核桃树枝筛过的阳光斑斑点点,落在地上,也落在大妈覆有一层油汗的脸上,古铜色的脸忽明时暗,但那淡淡的笑容却一直是明亮的,如雕刻一般,不惊不变。
村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是什么促成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莫非就是养育、护佑着他们的光明村本身?难道是光明村将自己的亿万年来一贯的宁静,充分地融入到了山水草木之中,又在村民们的血液中埋下了宁静的种子,经天长日久的酝酿,培育出了宁静的果实,让宁静的气质得以代代传承?所以,就连孩子们的童年,在她宁静的怀抱的温养下,也是如此宁静?
我想,这样的猜测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了。不然,山脚的城市里,有无数休闲之地,无数装修精致的好去处,坐在农家乐院子里的那几个外来之人何必大费周章,舍近求远,来到这藏在苍山西坡褶皱中的鸡茨坪喝茶?
或许,在城市里,在那些精致的地方,刚好少了一种叫“宁静”的东西,而光明村,刚好有。
我为之前的浮在表面感到羞愧,也为自己能迅速觉悟而感到庆幸。光明村,它的安静,它的沉默不言,不仅不是某种性格的极端,反而是最接近人类精神的最佳存在状态——宁静。
外部世界,大多因喧嚣而混沌,因混沌而蒙蔽,因蒙蔽而暗淡。而光明村,因宁静而清澈,因清澈而透亮,因透亮而光明。
至此,我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只蠕虫也终于消停了。光明之名,是准确的,是实诚的。没有牵强与附会,没有雕琢,更没有修饰,名与实,已为一体,无分无别。
自那以后,或陪家人出行,或跟随调研组考察调研,我又曾数次去到光明村,去到鸡茨坪。虽然去的缘由五花八门,但其实我内心是澄明的,知道自己是冲着什么去的。
追求身心的宁静,一直都是浮躁空虚的现代人的一种理想。哪怕是能让身心暂时得到放松一刻、安静一刻的地方,便蜂拥而去。
一传十,十传百。近年来,发现鸡茨坪是个安静的好去处的人越来越多,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发现光明村的潜力后,便将光明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试点来打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改善光明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去了的朋友回来都说,光明村的鸡茨坪变化很大。我心中挂记,便思量着挤时间去一趟。
2019年6月,愿望达成了,我又去了一次鸡茨坪。以往数次去鸡茨坪,大都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回。这次去鸡茨坪,我足足在鸡茨坪待了两天。这样的际遇,让我有了宽松的时间,来感受鸡茨坪。
鸡茨坪果然变了,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而且,它还拥有了另一个名字:云上村庄。
准确地说,是鸡茨坪一下子多出了很多东西:高档的酒店、独具特色的民宿、修剪齐整的草坪以及草坪上的帐篷营地、精心砌成的石头墙、青色的石板路、开满各种鲜花的花圃、别致的咖啡屋,外形做成核桃树根和核桃果模样的内部装修高档的卫生间……很显然,为了打造乡村振兴试点,自然基础条件优厚的鸡茨坪迎来了商业开发的机遇。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为鸡茨坪的居民们感到高兴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有些担忧。
在商业开发的铁蹄下,鸡茨坪还能像往日一样安静?扫落叶的大妈的笑容还会不会像雕塑一样,平淡而宁静?孩子们的眼神会不会一直那么干净而清澈?公鸡的打鸣声会不会还是那样清亮而悠长?牛儿们还能不能悠闲地在空地上啃草?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鸡茨坪的安静是一株把根扎得很深的大树,安静是鸡茨坪的天性,不轻易移改。最近多出来的那些东西,只是它的外衣,我能感受到,它的内心依然一片安宁。
特别是在雨季,鸡茨坪,越发安静。
刚到达的时候,看到村庄入口上有一个牌匾,上面有“云上村庄”四个字。当时,我只是看到四个字,但在后面的两天两夜里,我领会到了这四个字里含有的重重的分量。在雨中,鸡茨坪那如梦如幻的世界、如诗如画的情景告诉我,“云上村庄”这个名字不但没有给人突兀的感觉,而且很贴切,甚至让人觉得“此名本天成,妙口偶得之”。
两天两夜里,我在核桃神树下,听它缓慢的心跳和呼吸,在修整一新的草坪上看孩童嬉戏、追逐,在花圃里的花丛中看花和蝴蝶,在石墙根看青苔生长,看蜗牛爬过一片核桃树的枯叶,在咖啡屋喝苦咖啡,看窗外的青草疯长,在老查家的院子里呆坐,在景漾别院的游泳池边拍白云、拍鸽子、拍彩虹,在静夜里听窗下那只蛐蛐的低吟,在高处看雨雾飘过来抱住鸡茨坪又离开鸡茨坪,在玉皇阁的悬崖边上淋雨、看流云……整个村庄或云蒸雾裹,封锁喧嚣入侵,或云带飘飘,似有神仙眷顾。晨光中,稀稀落落的三五游客偶尔出现在石墙一端,随意散漫地遛达,又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消失在石墙的另一头。树荫下,一张桌子,一壶茶,有三五人,边喝茶,边说话,边打盹。暮霞里,那几户农家乐的主人惬意地忙碌着,在准备满是泥土味的农家菜,还收拾好了干净的客房,迎接游逛的客人归来。
还好,两天两夜的接触后,光明还是心中的光明,鸡茨坪还是心中的鸡茨坪。那些孩童的笑声还在,那位老大妈的笑容还在,石墙、鸡鸣声依然还在,核桃树神还在,鸡茨坪的宁静,一直还在。
这一次我离开鸡茨坪,也是在黄昏时分。跟以往一样,我又感到从鸡茨坪深处传来的那种动静,我知道,那是村里的那株核桃神树,又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开始守护夜幕下的鸡茨坪了。
编辑手记:
铁栗把对家乡、民族、国家的诸多复杂感情,隐藏在对巍山的“村庄、稻田、阳光、人情”等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中,如同西河水,缓缓流过每一个人的心田,不经意间就拓开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作者细腻、节制、隐忍的抒情,深远、旷达、广阔的心境,智性、清晰、透彻的思考,让这篇仅六千字的散文内涵深厚。文章以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为起点,讲述了红河孕育的巍山文化。作为一个汉、彝、回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巍山各民族不仅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习俗,并且相互融合、交流,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地区。巍山人的生命意识已渗入到日常生活中,不逆时令、天人合一、感恩自然……处处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作者也写到“乡村振兴”的春天里,巍山人依靠勤劳的双手、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村庄更美好,让生活更富足。个人在历史、文明面前,犹如沧海一粟,但作者仍以一己之力给予一方土地人文关怀,描述亲身经历、见闻,让人感受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并由此看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一个小地方的文明已如此绚丽,历史已如此厚重,更何况一个泱泱大国呢?
张新冬退伍后被分配到家乡一个叫枧田街的地方,负责收取当地的三轮车养路费。在当地工作多年的他,不仅感受着当地人勤劳、善良的天性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活,也见证着枧田街的发展变化——从依赖三轮车出行到交通便利、道路遍及。远方从故乡开始,只有脚下这片土地的道路足够平坦、宽阔、便捷,才能有通向远方的无数可能。
多次寻访漾濞县光明村的段成仁,亲历着这个小山村的变化。他笔下的光明村,拥有着许多“宁静”的特质:光明村远离都市喧嚣的村庄环境、村民宁静平和的心态与朴素的生活状态。光明村的宁静也吸引着许多渴望宁静的到访者。当地政府抓住机遇,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支持和带动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其旅游资源。再次到访光明村的作者,也欣喜地发现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光明村仍旧保持着宁静的特质,真正做到了“因宁静而清澈,因清澈而透亮,因透亮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