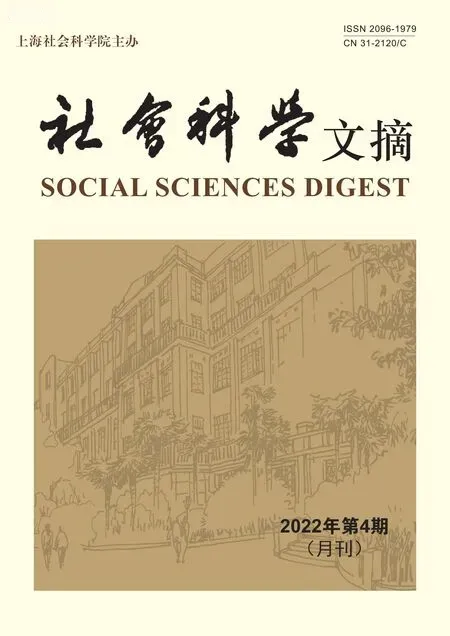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典型”在现代中国的百年旅行
文/王一川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摘自《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原题为《“典型”在现代中国的百年旅行——外来理论本土化的范例》)
从鲁迅于1921年9月发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并在其中首度使用“文学典型”时起到2021年,来自西方的现代典型理论在我国文论界旅行时长已一百年整。现在回头对典型的百年旅行轨迹作简要追踪,应有助于冷静而全面地梳理外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及其对自身古典理论传统的传承作新的反思和建树。
典型之转型和构型
典型理论在现代中国先后经历过不同旅行驿站或景观,可以大致概括出转型、构型、定型、变型以及再构型五个时段。
1921年起的十年为文学典型在中国登陆、发生或转型期。鲁迅在从德译本转译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后,为这篇译作写了序言《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指出“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需要注意鲁迅从德译本转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并为其撰写该篇译序时的具体做法和特定背景:第一,他此时已明确认识到“典型”及“文学典型”是一个有用的文学理论概念;第二,“文学典型”既可以是颓废者,也可以是工人,具有多重可能性;第三,“文学典型”与“写实主义”流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第四,“文学典型”“写实主义”可以抵达文学的“表现的深刻”的“极致”或高峰;第五,从他对“文学典型”的理性认识和价值推崇,有助于回头理解他此时段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构思和文学理论探索,特别是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典型”“写实主义”的自觉的美学追求。有理由推测,鲁迅的以阿Q形象为代表的文学典型化创造,是有意识地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如上小说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典型”和“写实派”等文学理论中吸取了养分的。此后,围绕鲁迅创作的阿Q等新型人物形象的批评,成仿吾、沈雁冰、郑振铎等紧紧抓住来自西方的“典型”新说,在论争中使其正式顺利登陆中国文坛。可见西方现代“典型”理论登陆中国时的第一个文学“港口”便是鲁迅和他的创作。这标志着“典型”自此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典型在中国的构型期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深入和成功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五封书信等著述中表述的“典型”理论迅速传布、影响日盛。许多人为典型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努力,但首功应属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与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学运动的过程中,大力译介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在推动典型范畴在中国文艺界的广泛运用和普及方面有突出建树。他同胡风、周扬、冯雪峰等文艺理论家一道共同开创出中国化典型理论的道路。
典型之定型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化典型理论进入成熟、定型及主导时期,在我国现代文学界树立起一种无可争辩的美学权威性。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中国化典型理论获得了系统表述并拥有主流地位。毛泽东出于让文艺作品承担感染和动员群众的目的,要求文艺作品注重“典型性”,走“典型化”的创作道路,因为他认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继毛泽东之后,蔡仪在美学体系中有机地输入了“典型”范畴,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整个美学体系的基石。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前期,逐步中国化的典型理论被推向成熟、定型及主导的时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和批评著述中主张一种积极的和革命性的典型观基础上,毛泽东把典型范畴根本性地转变成全国文艺界的一整套实实在在的体制化举措,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运动等体制运作过程。
20世纪50年代属于来自苏联的典型范畴在中国的吸收和转化时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典型终于上升成为中国主流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其鲜明的和权威的标志之一就是正式进入由国家主导而由学者集体编撰的高校教材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中的基本或核心范畴之一。高校统编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出现如下中国化文学典型观:“作家进行典型形象的创造,总是力求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生动、鲜明的个别的艺术形象表现一定社会集团的本质特征,通过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和具体的矛盾冲突,反映特定时代的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人物的共同本质。”另一统编教材《文学概论》也主张创造既有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文学“典型”,并把“典型性”作为文学形象的一个基本规定。文学形象当其“有可能描写出鲜明而生动的现象、个别性以充分地表现它的本质、普遍性,使它具有突出的特征而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时,就具有了“典型性”。典型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前期进入成熟、定型及主导时期,根本上是由于这个时期文学创作在上一个时期基础之上,出现了更加丰富多样的需要以这种理论来加以概括和推广的典型现象,例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财主底儿女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等中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
典型之变型和再构型
典型理论在中国走向流散或变型期,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竞相告别和走出“文革”浩劫的年代里,曾经位居主流的“典型”理论暂时被冷落,不得不向边缘移位直到出现某种衰落情形。
典型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呈现出流散中回归或重聚势头,可称为再构型期。这主要是指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他艺术创作中再度出现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形象,例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白灵、田小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必达、陈墨涵、朱预道、张普景、高秋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圣天门口》中的杭九枫和阿彩,《大江东去》中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宋运萍、梁思申。这些新出现的文学典型人物,既是对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生活新变化的有力的审美回应,本身又发出重新寻求“典型”理论去阐释的呼吁,而它们又是其他文学理论范畴所无法解释到位的。这就使得文学典型理论的重新构型成为一种必然。
反思典型之变迁
典型理论在现代中国百年旅行期间赖以兴盛和发生多次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这里不妨尝试就其中部分问题作初步及简要讨论,以便由此特定案例对外来理论本土化问题作必要反思。
典型理论在现代中国兴盛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出于那时期正日益高涨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在新的文学形象阐释上的特殊的美学需要:对内力充满失望而对外力满怀期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敏锐地捕捉到来自俄苏的典型理论有助于阐释现代文学中的以阿Q为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新型人物现象,于是大胆加以借鉴,从而才有力地促成典型范畴东渐的成功。正是依靠来自西方的新范畴典型,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找到了借以洞悉中国现代文艺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束强光。另一方面,那时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本身也给予中国革命以“照耀”和“援助”,而典型理论不过是那时水到渠成地输入我国的种种革命理论和实践武器中的一种罢了。总的来说,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学界出于把握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形象创作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是典型这一富有理论威力的西方理论的及时输入,这两方面的合力才终于确保典型在现代中国文艺界平稳着陆,直到取得主流地位。
还有一个似乎被遗忘的原因需要补充进来:正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的“性格”及其他相关理论传统,为中国现代作家和文论家倾心接受来自西方的典型理论,提供了属于本土传统的无意识基础。假如没有这种已深潜入无意识之中的心理基础作为内应,人们对外来典型理论的接受就不会如此容易,而会变得更加艰难。伴随明清之际以白话长篇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式叙事文学的兴盛,中国自身的性格理论已经生长起来,并且已开创出自身的理性思维的勃勃生机。只是在清末民初以来全力告别古代传统而师法西方的过程中,这种传统被我们自己所遗忘。
对于典型走向流散或变型的原因,也需作多方面分析。第一,典型走向流散或变型其实是它在定型后的自我膨胀中走向自我解构的一种必然后果。随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及其标举的“三突出”“高大全”等理论对典型论的过度滥用,典型在“文革”十年终于走向恶性膨胀的极端,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重新觉醒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对它的激烈质疑和冷酷抛弃,这就把它推向自我解构的绝境。第二,这种流散或变型更是出于改革开放时期创作出现新变化、并由此发出新挑战的结果。“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一再对“典型”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镜子”的权威性,以及对“典型化”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法则的权威性构成严峻的挑战,从而迫使文学批评家们无法再充满自信地运用“典型”武器了,转而探索“朦胧”“积淀”“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等新理论。第三,需要同时看到来自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合力作用: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再是苏俄而是来自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文论思潮,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先后抢滩中国,竭力迫使典型让出主流或王座;另一方面,我国文学理论家们面对以“语言论转向”“文化论转向”“视觉转向”等为标志的新的欧风美雨而展开新的回应,尝试借机加紧耕种自己的文论园地,包括寻求自身文论传统的积极的现代性变革。这两方面的汇合,促使典型一度让出理论原野的中心而退居边缘。而同样需要补充的一点,正是由于忽视了从中国本土“性格”等相关理论传统中寻求支撑,来自西方的典型理论才如此轻易地被更新的西方文学理论所替换或者被排挤到边缘。
向西方求索的原因
当现代中国文学界急切需要求助于外来典型理论的本土化时,为什么没有从自身的古代“性格”等相关理论传统中寻找,反而跨越文化的界限向西方异文化去求索?
在鲁迅开始自己的现代白话小说创作的“五四”年代,整个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多元文化共时化汇聚时刻。当晚清至“五四”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急剧衰落、西方文化强势介入之时,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仁人志士愤激地认为本土文化传统已经衰落和堕落到对中国现代变革和复兴更多地只能起到一种阻碍作用了,因此决绝地把改造中国国民性、建设新型现代中国文化的希望转而投寄到对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等现代文化及其相关理论的借鉴上,特别是对苏联“十月革命”以来传来的新型理论的“拿来”上。当此之际,中国自身的古代“性格”等相关理论传统难免会暂时遭到忽视乃至抑制。
有意思的是,当鲁迅等在明晰的意识层面高举“反传统”大旗时,其内心对于传统的偏爱或维护却依然故我地在隐晦的无意识潜流层面默默运行,起到一种隐秘而又不可或缺的筛选作用。鲁迅等之所以从来自西方的大量文学理论进口产品中选择“典型”理论而不是其他理论,或许正由于潜隐在他们内心的本土“性格”理论在面对来自西方的“典型”理论时,于无意识中产生了一种更近的亲缘关系,在选择时起到了隐秘而重要的导向性作用。这一点可以为接下来借助中国古典“性格”等相关理论传统而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典型”理论的重新构型,提供一种合理化的理论缘由。通向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许可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性格”等相关理论传统与西方文学典型理论的对话及交融之间,以及在新的文学创作现象及其问题与相应的新的文学理论建构的结合之间,寻求新的理论旅行的可能性。在如此情形下,在包容外来理论过程中持续地建构自主、自强并体现传统风貌的中国文学理论,想必已然是水到渠成之事。
现代中国本文化之所以大方地接纳来自西方异文化的典型理论资源,根本上还是出于自身的文化现代性变革需要:当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理论及批评界急需新理论资源去填补阿Q等新型艺术形象的理论阐释空白时,典型理论恰好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由此可见,“内需”才是典型理论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一个关键原因。其次,典型理论在中国旅行过程中不得不在本文化与异文化的激烈较量中经历种种变迁。典型理论能够在现代中国真正实现本土化,并且长时间地成为现代中国主流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核心范畴,恰是由于它契合了现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内需”。本文化中生成的“内需”及其具体诉求方式,实际上规定着外来理论本土化的具体方式及其结果。典型理论在过去百年间经历多次变迁,主要是由于现代中国本文化自身承受多重压力或影响而需要实施持续变革的缘故。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界重新呼唤典型形象的再生,推动典型理论呈现再构型景致,也势出必然,这需要紧密结合21世纪以来文学及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其他艺术门类现象去另行展开具体而深入的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