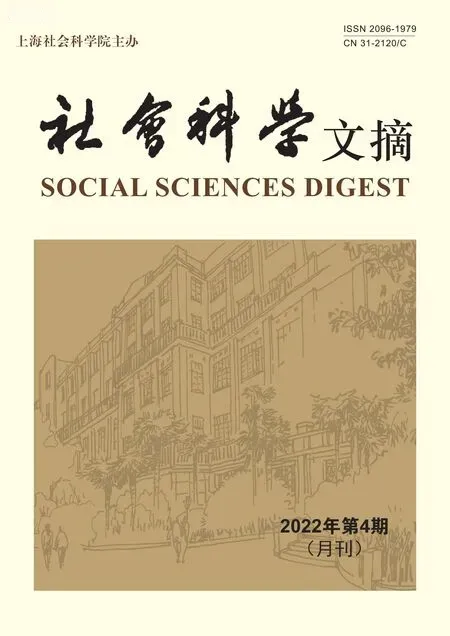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文/王中江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题为《 “自我”与“他者”的相与之道:儒家关系伦理学的多重图像》】
认识历史深厚、谱系广大的儒家学说,需要我们采取非线性和复杂性思维,需要我们在认知它的一个维度时,不能忘记它的其他维度;在看到它的一种叙事和论说时,不能忽略另外的叙事和论说。一种对儒家的归结说,认为儒家建立的人伦秩序整体上是一种差序格局,引申这一看法,即对儒家伦理学提出质疑,认为它无法适应现代陌生人的社会。对此我们能够给予的回答是,这类看法就只是识别了儒家的部分特性,而遮蔽了它的其他特性;其受限于儒家伦理学中的部分东西,而没有关注它的更多维度。儒家有特殊的血缘亲情伦理观,主张“礼”的差异性安排和秩序,这是事实;但儒家也强调人性平等,强调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自我发展;儒家还有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伦理观等,这也是事实。
儒家的普遍伦理是相与之道,是交往之道,它建立在天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与人等一般的关系世界中。儒家为此建立的伦理话语和学说,能够面对除了亲人、友人和熟人之外的一切陌生人,能够广泛适用人与人、自我与他者的各种关系。儒家的关系伦理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孔子对同一伦理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论说,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提出的同一论题的不同回答,都证明了儒家伦理的多义性和多重性。这就意味着探讨儒家的伦理,不能让它的血缘亲情伦理和差异性“礼”的伦理遮蔽住它的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伦理。
“我”与“他”:人应该如何相互对待
儒家伦理学可以概括为关系伦理(相与之道)。它的一种论说方式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化为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特殊关系,并以“有亲”“有义”“有别”“有序”和“有信”来加以规范。但儒家一开始就没有将伦理的空间单一设置在人群的小圈子内或者熟人关系中,它的伦理学还有另一种叙说方式,它是在人与人、我与他等自我与他者的普遍关系中建立伦理价值和规范,它同儒家的四海一家和天下大同的共同体信念相呼应。
有两个过去我们关注不够的语境和文本很适合作为讨论这一论题的切入点。其中一个文本被保存在《韩诗外传》卷九中: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子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言,蛮貊之言也;赐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亲属之言也。”
以上孔门伦理故事呈现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与之道是多重性的,它包含着四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互惠模式,二是惩罚模式,三是宽容模式,四是至善模式。用传统的术语表述就是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
“互惠模式”或“以德报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的伦理学传统中,它的通俗表达是人家对我好,我也对人家好。故事中,孔子三位弟子一致回答的“人善我,我亦善之”,可简称为“以善报善论”,这就是互惠模式。它的意思很清楚,别人善待我,我也要善待别人。从道德理性来说,善的施与者一般对我有一个预期,而回报者的我也会给予回报。而我如果确实以善回报了,他者与我的互惠伦理价值就实现了。如果善的施与者是我,接受者和回报者是他人,情况同样。这是“若想要别人如何,那自己就‘必须’先如何”的一个推断。儒家以修己、自律为先,更多的是先要求自己要善待别人,然后再期待得到别人的回报。即使我的期望落空,我也不要轻易指责别人,而是再回来反省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善待别人。
被孔子批评为“蛮貊之言”的子路的说法(“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人”),可以叫做“以不善报不善说”,用隐喻表述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善施与不善的还报,这实际上是对不善者施加的惩罚,是让加害者为他的加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这是维护伦理规范和修复社会秩序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伦理上是正当的。孔子严厉批评子路的惩罚模式,一则因为子贡和颜渊的回答更动人,二则因为他主张“以直报怨”。但实际上孔子又没有完全排斥惩罚模式,对孔子来说,一位仁者又是会“厌恶人”的人。仁者为什么要厌恶人,孔子给出的理由是他“不仁”。
对他人施加给自己的不善不去报复,子贡的这种主张是宽容模式,大体上属于孔子说的“以直报怨论”。对孔子来说,“以直报怨”的施与模式,在伦理价值上要高于“以怨报怨”的惩罚模式,而低于“以德报怨”的善良模式,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方式,类似于子贡的“引之进退”。子贡的“引之进退”,可解释为合乎“礼”和谨慎从事。对于不善待或加害自己的人产生不满、愤怒和惩罚,很合乎人的一般心理和价值观。反之,我有很强的自制力,不加惩罚,加以忍受和承受,敬而远之,这是宽容;不仅如此,我更友好地劝告他者(引之进退),“化敌为友”,这需要更高一级的伦理价值观,这更是宽容。
颜渊主张善待不善待自己的人(“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这是“以德报怨”的善良模式,比子贡的宽容模式还要高,是理想化程度最高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将它评价为“亲属之言”。孔子赞美颜渊的立场,说明孔子还有“以德报怨”的立场,而不是只主张“以直报怨”。对不善待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和惩罚,而是承受、宽容,甚至更善待之,当然也会更难。在亲人、朋友之间不容易做到,在陌生人之间可想而知。但它作为人类伦理价值之一有它适用的地方。
孔门的四种相与之道,从伦理价值等级上说,至善模式最高,其次是宽容模式,再其次是互惠模式,最后是惩罚模式。从实践上说,等级不同,人们履行起来的难度自然不同,越高的越难做到。幸运的是,社会越健全,互惠模式的运用就越普遍,而惩罚模式、宽容模式和至善模式的运用机会就越稀少。社会越不健全,才越需要惩罚、宽容和至善模式来面对大量的不善者。互惠模式是建设性的,是建立和保持良好秩序的最有效模式;后三种模式是消耗性的,是弥补缺陷的补救模式。惩罚主要是对互惠缺失的补充,宽容和至善是用充足的善意和能量救助害己害人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四种模式都是需要的,但需要的程度则取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智者”的“相知之道”:认识自己与认识他者
孔门伦理语境和文本中的第二个故事是,孔子询问他的三位弟子做一个明智的人是怎样的(“智者若何”),做一个爱人的人是怎样的(“仁者若何”):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这一故事中孔门以“智者”和“仁者”身份呈现出的相与之道,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之道和相爱之道。三位弟子对何谓智者、何谓仁者的三种回答和孔子的三种评价,就塑造出了三种不同的智者和仁者,也塑造出了三种不同的相与之道。
什么是智者或做一位智者应该怎样?在知人与知己的关系中,子路心目的智者是能做到使别人知道自己的人。人希望被人知道和受到肯定,不能说子路是追求虚名的人,他认为智者是让人认识自己和受人称赞,包含着通过自己的美德而实现它的含义,否则孔子也不会肯定他的答案达到了“士人”的标准。只是,子路的“使人知己”的表述,没有立足于孔子的先求诸于己、后求诸人的立场,直观上将让人知道自己变成了首要的事情,带有气盛的意味,孔子对他的评价没有子贡高,缘由也许就在这里。
智者的相知之道,在子贡那里是认识他者(“知人”),孔子对其评价更高。子贡的“智者知人说”,有可能就是接受了孔子的说法。《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知”,子曰“知人”。这是明确以“知人”为“智”。但为什么我要“知人”呢?一般来说,“知人”隐含着两个前提:一是人与人、我与他有所不同,譬如人的性情、好恶、心志、价值观等;二是人不能不生活于群体中,自我与他者不能不交往和相处。因此,要跟不同于我的“他者”进行良好的交往和相处,自我就离不开对他者的认识和了解。我的特性不是他人的特性,我的可欲和偏好不等于他人的所欲和偏好。只有认识他者,我们才能按照别人所希望的方式对待之。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当代社会就更应如此。
颜渊的“智者自知”是孔门的又一种相知之道,它受到孔子的最高评价,证明在人们的相知之中,“认识自己”是首要的。在很多事情上,人容易将目光首先投向别人,“认识自己”是将目光首先转向自身,要反观自己。孔门以修身完善自我为志业,在道德上反观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不足。反观自己的不足是为升华自己,是为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无知才能获得知。对孟子来说,认识自我首先是认识自己的善心和善端,扩充和实现自己的良知和良能。
人类的相与和交往基于人们的相知。故事中的这三种相知之道,也是人们的相与之道。让他人认识自己,注重使他者见证自己,这是让他者眼中有一个我;认识他者注重对他者的尊重,这是让我的眼中有一个他;认识自己注重自己对他者的自主性,这是让我的眼中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自己。这都是我们交往中需要的。
“仁者”的“相爱之道”:自爱、爱他和被爱
上述故事中的“仁者”集中体现在“相爱之道”上。它是三种不同的仁者类型,也是三种不同的相爱之道。子贡心目中的仁者和相爱之道,是孔门中的标准性答案,儒家围绕仁的大量论说,都指向如何去爱人,但孔子给他的评价是中等。子路的(“仁者使人爱己”)和颜渊的(“仁者自爱”)的模式都是稀有的,孔子的评价为最低一等和最高一等。
孔门的“自爱”和“为己”当然同贬义的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没有关系。它是纯粹善良意义上的“自爱”和“为己”,是为了最好地爱自己而又最大限度地爱他人的自爱。颜回心目中的“自爱”是孔子心目中的“自爱”,也是孔子“为己之学”意义上的“为己”。同孔子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为人”相反,它是指人内在的自我道德发展和自我实现,是形之于内施之于外的统一。对孔子来说,修身养性、成就自我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将之作为谋取和获得其他东西的手段。如果将其工具化和手段化,那就是“为人之学”,那就不是同自己性命攸关的生命的学问。颜回的“自爱论”是孔子“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儒家“仁”(身心合一)字的构成,是从一个人对自己身心的关心和爱引申出来的。儒家“忠恕之道”,恰恰又是“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己不欲”不施人和“己欲”而“施人”的“推己及人”。一个人能够懂得爱人,首先是知道自己需要爱,应该爱自己。从人的同类相似性出发,他就能够推论别人也需要爱,别人也应该受到爱。从这种“共情”出发,他既会爱自己,也会爱别人;他能够珍惜自己,也会珍惜他人。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子路的“仁者使人爱己说”。这种模式看上去不是说自己先爱别人,然后赢得别人的爱。但实际上它说的是,一个人能够使别人爱己,是他自己善良和爱人的结果。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个人如果不爱人,他怎能得到别人的爱呢?完全可以设想,一个能够被别人爱的人,不正是因为自己的友好、自己与人为善而赢得的吗?这很符合儒家的要“使”别人如何(如“爱己”)、自己先要如何(“爱人”)的相与之道(“仁爱之道”)。通过自己的美德赢得他者的共鸣,对他人是善,对自己也是善,是“成人”,也是“成己”。
结语
东西方有许多不同的伦理学及其谱系,其中一部分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和深远,儒家的伦理学及谱系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这样的伦理学只是为人的身份做出差序性安排,让人受到等级性的差别待遇,说这样的伦理学不能面对和适应陌生人社会,这怎么可能呢?莫非这种伦理学真的存在着严重的乃至致命的缺陷,莫非我们整体上弄错了,再或者是它确实存在着某种缺陷,这种缺陷被我们夸大了,以至于它的很重要的其他方面被我们遮蔽和否定了。我认为是第三种可能性。儒家的伦理学有礼的差序性,儒家也确实重视来自血缘亲情的孝和从五伦来设定人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规范。但这只是儒家伦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儒家伦理学的整体。儒家还存在着广大的地带,这就是它围绕着人与人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普遍伦理语言和主义。从过去使用不多的孔门的两个文本和故事入手,结合孔门的大量伦理的话语和叙事,儒家五伦关系之外的另一个普遍性的人与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伦理、相与之道、交往理性世界和图像的多重性就呈现出来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遗忘,更不能被否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以及它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影响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