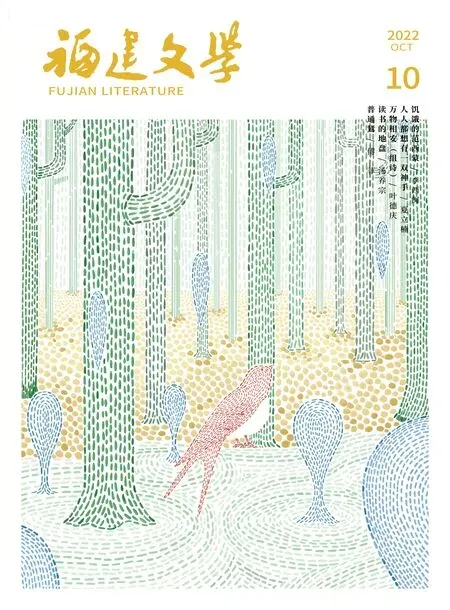在魔幻和荒诞中思考
——评陈树民的小说新作
邱景华

陈树民写小说已经30 多年了。继小说集《忐忑人生》之后,又奉献出中短篇小说集《天云村》,还有一些未收入集子的新作。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些新作,是以魔幻和荒诞的手法为主,不同于以前写实为主的小说。一个老作家能不断焕发出艺术青春和创作激情,犹如老树开新花,而且是开出一树奇异的花朵。
1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是“出于幻域,顿入人间”。换言之,就是借狐仙女鬼,来写人间悲欢。在严肃作家的笔下,不管是魔幻还是荒诞,都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深藏着作家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以卡夫卡为例,他具有德语民族特有的思辨性,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理性,他擅长“以逻辑表现荒诞”(加缪语)。写过一批世界闻名的想象小说的美国作家爱伦·坡,深有体会地说:想象力就是分析力。魔幻和荒诞,就是奇诡的想象力。用古人的话来说,是“其奇崛诡秘非常人之思路所及”。其实,这奇诡想象力的内核就是理性分析力和推理能力,但又不是说理,而是借助于主人公的“变形”来寓意,并要虚构为一个个具有奇特魅力的故事:卡夫卡把人变成甲虫;蒲松龄把狐狸变成少女,想象出人鬼之恋……
陈树民的新作也是通过“变形”来展示他的奇诡想象力。在《大鱼》中,把人变成鱼,鱼又再变回人;《吠犬镇》里是把人变成狗,狗又再变成人。而《天云村》中,大人可以变小,变成儿童;人还可以停止长大,保持儿童模样。在变来变去中拓展故事,深化主题。对作家而言,这种“诡变”的想象力,不是单一的,必须有“三十六变”。陈树民的想象力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宋女》写的是宋祠圣母殿里的彩塑侍女,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宋女”,即泥塑像变成真人;《父亲归来》中死去的父亲,复活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了一系列逝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的神奇融合;《栗色马》写一匹来历不明的栗色马突然来到小城,引发了种种不可理喻的事件……
这种奇诡想象力的奇妙,还在于要把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魔幻或荒诞的“假”的故事,用写实的细节叙述出来,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爱伦·坡与幻想型作家霍夫曼相比较,认为爱伦·坡的小说具有一种想象的细节真实。卢卡奇也将卡夫卡与霍夫曼相区别,他说:“只要想一想卡夫卡就够了,在他笔下,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最不真实的事情,由于细节所诱迫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也就是说,幻想型作家的小说,缺少细节的真实,只能给读者一种艺术的假定性;而卡夫卡却能将“艺术的谎言”变成艺术的真实。
在陈树民的小说中,既有奇诡的想象力,又有能赋予魔幻和荒诞的想象以写实细节的才华。比如,在《月光岛》中,就有能诱发人性恶的神奇月光,这是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奇迹;但人性恶在某种外在因素的诱发下,能从人体内释放出来,却又是事实。在小说中,为了把现实中的“不可能”变成艺术的“可能”,作者采用了一系列写实的手法。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即主人公“我”,回到故乡的月光岛,给读者以真实感。“我”划着一只小船,回到月光岛,看到古堡城墙里的老街,回到老家,看到父母,遇到儿时的伙伴阿钟和他的黑狗,这些都是用写实的细节和场景来叙述。通过这些必要的写实铺垫,把读者引入具有魔力的月光,诱发体内人性恶发作的狂欢而惊悚的场景。紧接着就是相互吵架,最后发展为两派的冲突和武斗。耐人深思的是:这诱发人性恶的,不是丑恶和可怕的东西,而是自然美好的月光,它先是让人愉悦、兴奋,最后令人发狂——疯狂,把人们引向可怕的灾难。
在这本小说集中,不管是魔幻还是荒诞的故事,作者都借助写实的细节和场景的叙述,将不可能的事变成了艺术的可能和真实。在一些小说的开篇里,作者笔下的写实呈现出一些游离和令人可疑的细节和场景,这种不同于纯粹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运用,往往深藏着一些暗示,形成一种悬念,逐渐让读者产生一些疑惑,慢慢被引向超现实的联想,然后出现非现实的魔幻或荒诞的人物或故事,使得整篇小说笼罩着魔幻和荒诞小说所特有的神秘感。
2
从小说艺术的层面讲,陈树民的新作中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魔幻,一是荒诞。
汪曾祺说:“中国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角度。”鲁迅称赞《聊斋志异》:“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中国小说史略》)孙犁说:“蒲松龄刻画了众多的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关于〈聊斋志异〉》)
陈树民笔下的魔幻手法,主要是继承了《聊斋志异》的传统,精心创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神奇女性。比如,《可儿》中的可儿,是由鸟儿变的女孩,会飞,纯洁可爱。《天云村》里的秀、《妻变》中的童瞳、《宋女》中的彩塑侍女雪儿,都具有传统美德和文化修养,或者说是具有古典美的女性,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当然,作者也没有把传统美德的内涵简单化,在《宋女》中,与雪儿同是宋祠圣母殿的宫女们变成真人后,来到现实中的泰城,最后却都被大款们包养。耐人寻味的是,圣母殿的这些泥塑的宫女,原来是光彩夺目,历千年而色不褪;但后来因泥塑的精魂逃到泰城,化为肉身的真人,没了精魂,就没有了神气和色彩,现出原胎的泥土本色。这个魔幻手法,有着深刻的含义。
陈树民除了借鉴《聊斋志异》的传统,还吸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即把魔幻的人物和情节及超现实的想象,融入现实生活中,形成一种新的超现实,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创造“神奇现实”。像《妻变》中老卫的妻子童瞳本是一个远离世俗的佳人,有一天突然变成儿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种种新的人生问题产生了,于是就有了新的故事。又如,《可儿》中那个会飞的可儿,本来是鸟,后来变成人,她来到人间,教会许多人在空中飞翔,由此诱发出种种超现实的故事。再如《宋女》,圣母殿里的泥塑侍女,寂寞千年之后,被真情所感动,动了凡心,来到现实生活中,与喜欢她的主人公悠然,发生相恋的奇遇。
简言之,如果说陈树民的新作用魔幻手法创造了人性美,让读者向往和追求,那么荒诞手法的使用,则揭示人性恶,令我们警醒。
他用荒诞的手法,创造出一个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独特而令人心悸的故事。比如,虚构中的吠犬镇规定:如果乱说话、讲错话,黑脸镇长会念咒语,把说错话的人变成哑巴的狗。外来者夏为看到这种可怖的现状,便带领被变成狗的人,与镇长抗争。虽然他也被镇长变成狗,但他想出各种办法,最后打败了镇长,也让他变成一条黑狗。小说的深刻处在后半部:因为镇长死了,他念的咒语也失效了,那些“狗”又重新变成人,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但放肆地乱说话,又引发了小镇人群的互相攻击,最后发展为集体武斗。外来者夏为梦见死去的镇长对他说:这就是让小镇人放开说话的后果。镇长还把人变成狗的咒语教给夏为。后来,小镇人越闹越厉害,气急的夏为念起咒语,也把小镇人变成狗。但他看到很多变成狗的人哀哀地叫着,流着眼泪,围着求他,后悔了。后来夏为又梦见镇长,他问镇长有什么办法解除咒语,让变成狗的人再变回人。镇长神秘一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梦醒后,夏为明白只有施咒的人死了,咒语才会失去法力。无奈中,为了解救小镇上变成狗的人群,他毅然自杀。于是,狗群又集体变成人群……
这是一篇寓意深广的力作,其对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性作了层层深入的揭示,达到力透纸背的深度。其凝重和沉痛的笔力,令人联想起鲁迅的某些小说。这篇力作,是作者对自己创作水平的有力超越和升华。
这类荒诞小说,表面上看接近于西方现代派的“荒诞文学”,但所借鉴的主要是荒诞手法,并没有荒诞的内涵。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荒诞是世界和人生存处境的本质,人被一种不可知的异己力量所控制,无力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在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充满恐惧地活着。而在陈树民的小说中,荒诞只是一种艺术手法,或者说荒诞是一种可以克服、也必须克服的暂时现象,人在世界活着,必须认识和克服人与生俱来的人性恶,防止它被唤醒和喷发,警惕人为灾难的发生,必须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3
在陈树民的新作中常有一个近似于作者精神面貌的人物作为叙述者。如《天云村》中的来兮,《栗色马》中的“我”,《可儿》中的子庄,《里村三变》中的亦男等,这些人物因为坚持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受挫,他们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和相当的距离……
其实,这些叙述者就是作者。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作家,成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他所接受的理想主义的教育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滋养,共同奠定了他的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底色。作者对现实的观照,从本质上看还是理想主义。于是,作者借助魔幻和荒诞的手法,在小说中表达他的思考和态度:面对巨变,他显然无能为力,只能让大人变小或停止长大,保持儿童的天真和纯洁;或者远离城市,回到想象中的古朴山村,并且随着城里人的到来,越搬越远,在天云的深山里,去建立自己的“世外桃源”……
很显然,陈树民的新作对社会转型和巨变所带来的历史进步意义的思考还不够,对商品经济、对城市还带着一种简单化的否定。作者关注并想告诉读者:在社会的转型和巨变中,对人的复杂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警惕和避免人性恶的泛滥;要保持对理想的追求,对美的向往,对人的美好情感的珍惜和守成;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包括中外世界名著、古典音乐和艺术等)。要言之,不管社会怎样变化,巨变中有不变——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总会继承和发扬下去,不管有多少的曲折和反复,这个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不可改变的。而正因汇入了人类优秀文化不可阻挡的前进河流,陈树民的新作也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