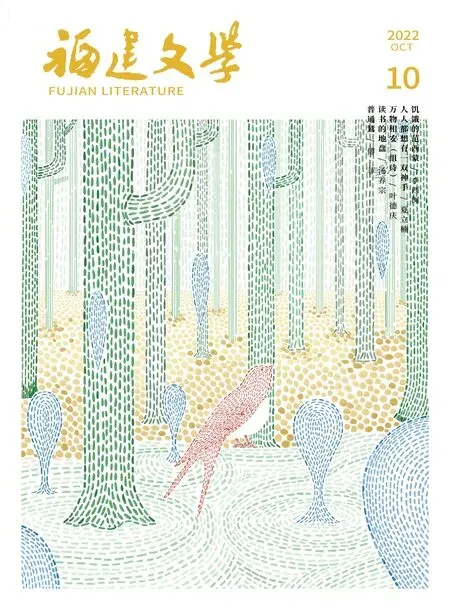去无顶山
王清海
我第十八次去无顶山的时候,认识了小景。
秋风微凉,石缝里的青草,野花,还有些小树,仍然蓬勃,并没有觉出萧瑟。
我站在悬崖边,白雾缭绕在脚下,像是踩在云里。无顶山就是这样,雾经常有,丝丝缕缕的,并不影响视线,还总是能看到远处的森森林木。
很多人在这里选择悬崖跳伞或者翼装飞行,就是迷恋这种与白雾一起缥缈的感觉。那天有三个人穿着翼装,站在我和小景的旁边,他们走向悬崖,跳下去,如鸟一样展开翅膀飞,在云与雾里,在林与山间。
小景和我背着伞包,站在那里。很多围观的人以为我们是一起的,各种手机和照相机都对着我们,期待地看着我们。
小景也一直看着我,看了很久才说,叔叔,你怎么不跳?
我说,感觉今天身体不太好,不跳了,你呢?怎么不跳?他说,我不敢。
我笑了,说,开玩笑的吧,都站在这里了,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小景,风景的景。我说,我姓王,你叫我王哥吧。我记下你的名字了,你跳吧。他说,我想跳,可是真不敢,看见你不敢,我就更不敢了。我说,一起下山?他说,好。
小景有些紧张,不知道该怎么逃避围观的目光。我很自如地向前探了探身子,伸手感受了一下风向,然后若无其事拉着小景离开了悬崖。
两个背着伞包戴着头盔,系紧胸带腿带的人,来到悬崖边,站在那看了看,没有跳,然后一起又坐着索道下山了。
每次来无顶山我都做着同样的事情,背着伞包站在悬崖边,从没有向下跳过。
我看到了很多跳下的人,每一张面孔在跳下时的表情都不一样,他们的表情如同相片一样在我眼睛里划过,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回不来的人,我也记不得他的样子。回来的人,再相遇,在他们眼里,我不如一个看客。看客只在外围看看,而我是背着伞包的,站在他们身边,冒充了他们,但又不是他们。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他们眼里的怪人,但我觉得自己是。我有时候想,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我。这些感觉,不过还是自己的感觉。
不过有一个人一定记得我,瘦高,黑,连续遇上过两次。其实飞行的人,大多数都瘦,黑。做极限运动的人,怎么能把多余的脂肪带到身上?他比来这里跳伞或者翼装飞行的人,都略显高些,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就冲我微微点头,轻笑。第二次仍然是。在这之前,站在悬崖边的人从没有对我笑过,他的笑容让我如沐春风,似是得到了认同。
他没有跟我说过话,我也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我跟景区的服务人员打听过他的名字,张云生,竟然是这行里的翘楚。
认识小景的那天,我没有看到他。
我和小景住宿时,特意避开了那些飞行的人,避开了那些看飞行的游客,找了一个偏僻的农家乐。老板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我第一次住这里的时候,她的儿子还在读小学,腼腆可爱,见到有客人,会主动回避。后来又去,他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带小景去的那年,老板娘迎上来,主动告诉我,她的儿子去北京读大学两年了。第一遍声音有点小,我没反应过来,然后老板娘扯着喉咙给我说了一声。
住下以后,小景跟我说,老板娘儿子读的大学,离他的母校不远,他上学的时候,无数次从那个学校门口经过,看见老板娘提起儿子的学校这么激动,他忽然想起来,自己也曾是家里的骄傲,村子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没多久,很多亲戚都到家里来祝贺,言谈之间,不断有人提及很多领导都是他们那个学校毕业的,好像小景的将来,也会成为某某大领导甚至会超越。还没踏进大学校门的小景,被那些话激动得踌躇满志。
虽然跟小景一见如故,但在住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打算住在一个房间。毕竟两个陌生的身体,挤在一个房间里,还是有些别扭。只是这些年无顶山游客量大,农家小旅馆虽然偏僻些,也只有一间房了。我们只好住在一个房间。拿到房卡后,小景看了我一眼,神色有些不自然。
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分开摆放,中间只隔了伞包大小的一条缝。窗台上摆着几盆不知名的野花,淡紫色的小花开得很典雅。在房间内向外望,能看到披满绿藤的小院子。
小旅馆建在半山腰,走出院子,就是一个很深的山沟。几年前,曾有一个跳伞的,偏离了方向,在崖壁上撞了几下,最后就摔死在这个沟底。
进了房间后,我和小景开始卸身上的伞包。小景脱下后,开始检查,手柄,胸带,腿带,引伞,主伞,备伞,ADD,检查得很仔细,他一边检查还一边问我,王哥,你看我还缺什么?我说,什么都不缺。他看我将伞包往柜子里一放就不再管了,问我,王哥,你是不是跳前才检查?我说,我没有跳过,也不准备往下跳。
看小景一脸的疑惑,我跟他讲起那个摔在沟底的跳伞人,他说他听说过,他在来这里之前,在网上查询了很多相关的事情,网上有这个跳伞失败运动员的生平,他的微博,每到祭日,都会有很多人留言哀悼。
我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了解得少了。小景说,王哥,死了的人,特别容易被人记住,这是不是这项运动最独特的地方?我说,死了的人,被记住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死了,不如活着的时候被人忘了,也是在活着。
小景说,也许他一辈子都没有做过能让人记住的事情,用一个不平庸的死来做个终结,也是很不错的。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寻死,所以从来也没敢跳下去,不过无顶山悬崖跳过那么多人,也就死了一个,安全系数还是可以的。小景说,要不明天咱们跳一次,我做了很多准备了。我说,让我再想一夜。
脱下身上的伞包,一身是汗,冲了澡,顿觉浑身轻松。我洗完后出来,小景穿戴整齐地进去洗了澡,然后穿戴整齐地出来,躺在床上。
别人这么整齐地睡觉,本来裸着上身的我也只好重新穿好衣服睡觉。
屋子里关了灯后,比外面黑,能模糊听到小景的呼吸声,几乎看不到人。
他说,王哥,人在黑夜里会不会忽然长出翅膀?我说,不会,不过人在黑夜里会乱想。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以为自己的命运从此就会改变,每个黑夜里都有很多幻想,醒来后还是昨天的样子继续活着,从来没有因为夜晚的想法改变自己。一直到毕业,我还是我原来的样子,身边的同学们,有的已经写出了很棒的论文,有的去了国外,有的继续读研读博,而我,毕业就是毕业了,很辛苦地找到工作,然后开始在工作里挣扎,想要领导满意,想要升职加薪,纠缠在一个又一个目标里。我说,大家都差不多,这是生存和生活啊,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他说,身边的同事们也在工作,可是他们很轻松,他们干着各种各样的事,到最后,有的自己成了老板,有的继承了家里的拆迁款或者别的钱吃喝玩乐去了,有的跟公司高层是亲戚,很轻松地当了我的上司,就连一个我觉得神经不正常的小余,竟然在业余时间写诗得了一个大奖,辞职当专业诗人去了。只有我在挣扎,我不想就这样挣扎一辈子。我说,那你来跳伞,是想一跳成名,然后拿这个当职业?他说,王哥,别逗我了,这行当里,怎么一跳成名?跳成功了,活着,跳失败了,死了。我连跳都不敢跳。就是想转行,也绝对不敢拿这个当职业的。我说,那就睡吧,天亮了回去,上班,下班,那才是真实的生活。
他“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我也闭上了眼睛。一夜都是半梦半醒,总觉得伸手就能碰到的那张床上,小景一直睁着眼睛。
山中的早晨,伴着若有若无的鸡啼声醒来。
我拉开窗帘,昨夜模糊的景色一下子清晰起来,连墙角处的一坨狗屎都看得清楚。
随着帘子拉开,小景睁开了眼睛,说,王哥,早。
我说,早。
他说,王哥,我昨夜又有了想法,我要跳一次,你有没有跳伞经验丰富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下?我说,我没有加群,平时也不关心这个,每次都是一个人来去匆匆的,没有什么朋友。他说,我今天不想回去了,昨天夜里,我仿佛又坐索道上了山,站在悬崖边,向下纵身一跳,拉开引伞,打开主伞,缓慢地飘落在一片草地上。我反复想过很多次,我都成功了,我要去试一次。
他说得很坚定,我觉得他这次一定会跳。安静的房间内,我能听得到他的心在跳动。
我说,我陪你上山,你没有这行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找个跳伞队,有教练,安全。他说,我不想那样,我也想过报名跳伞队,那是职业训练,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就想找人交流一下,多了解一下,纵身跳下的时候不摔死,体验一下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我说,你这个想法太疯狂了,还是不要这样,到悬崖边我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到你。
本来是不抱希望的,没想到那天张云生竟在悬崖边,看见我这次是两个人一起,看了我们一眼,目光又在我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我走了过去,跟他握了一下手,然后跟他介绍了小景,说我们是一起来的,新手,只是自己买了伞包,在悬崖边比划一下。
张云生说,新手没必要自己买伞包,加入我们的团队,学习的时候有专用的学生伞包,随后进阶,可以自己跳的时候,会帮你挑选适合自己的伞。你们自己买,什么也不知道,浪费钱不说,不是跟自己匹配的伞,跳下去也不安全。
小景说,我不想参加职业训练,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训练做了不平凡的事,那只是训练改变了他,而不是他生来就不平凡。
张云生说,兄弟,你这个作死的想法,很多新手都有。人在世上吧,平凡也好,不平凡也罢,踏实活着是最重要的。
小景说,我还是觉得要是经过训练才能跳伞,就失去了纵身一跳的意义。
张云生说,没有遇到我,你随便一跳是你的自由,遇到了我,你再随便一跳,就是我这种职业运动员的失职了,你可以到我的跳伞队里看一看,再决定要不要改变这个想法。
他几乎是扳着小景的肩头,把他从悬崖边拉走,然后手舞足蹈地跟他介绍着。
小景跟着他走了。我跟着他们下山,一路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直到分别的时候,我问张云生,你以前遇到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邀请我去你们的跳伞队?他说,我观察过你,你的伞包很旧,体积也小,里面的东西估计也不全。你平静地站在悬崖边,探探身子就走了,你从来没有打算跳,对吧?我说,不会的,不打算跳,我来做什么?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飞翔的渴望,有一种气场,想飞的人都能感受得到,你没有,我也不知道你来做什么。我说,来玩的。
他们两个一起点了点头。
两个月后,我在小景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要开始第一次试跳。他并没有邀请我,我也没有再询问。默默记下了日期,打破一年只去一次无顶山的惯例,再登一次无顶山。
从我所在的城市到无顶山,坐火车要一天一夜。一来一回,至少要请三天假。我的收入,还掉房贷车贷,再加上日用开销,基本上刚好够用。扣掉一个月的全勤奖,一个月的日子就会紧张很多,这是我不敢轻易请假的原因。
但我每年去一趟无顶山,是不用请假的。公司里的人,包括经理,一上任就听前任经理说了,我做了大家都不敢做的事情。我能在悬崖上面对围观的众人,轻松一笑,纵身一跳,在三千多米的高度里,鸟一样蹁跹自如,临接近地面的时候,不慌不忙拉开伞包,平稳落地。这份胆略,是做大事的人,在公司里做现在的事情,是简单轻松的。
而我在日常工作中,确实也没有出过岔子。我那超出一般人生活轨迹的举动,让很多人佩服。我在每年的8 月份请几天假去无顶山,只要我提前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这几天,经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事们也都睁一只闭一只眼,全当我在那,没有扣我的钱。
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情和爱。
这些年来我也从来没有打破这个惯例。
我还是放弃了11 月份的全勤奖,去了无顶山。山上的草木,比我上次来,色彩斑斓了很多,黄的红的紫的,揉在绿色里。明明是没有风的,那些颜色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走近了却又在那里纹丝不动。
小景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脸色有些苍白,比我上次见他,感觉老了些。
他站在张云生的背后,和他捆在一起。这是双人跳,老带新。我还以为短短的两个月,小景真的敢跳了呢。
我说,虽然是你带着他,但是他毕竟迈出了这一步,我在旁边,很感动。
小景的目光是畏缩的,他怯生生地扫过围观的众人,直到在人群中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他的眼睛开始有光亮闪出,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出笑容。
张云生对着围观的人,一脸成功者高高在上的笑。他的眼也在人群中扫过,目光和任何人都没有对视。我觉得他是在看人群背后那无垠的苍穹。
他朝人群挥挥手,背着小景在悬崖上转了个身,纵身跃下。他们的身子在空中翻腾着,我能想象得到,小景一定闭着眼睛。在一片尖叫声中,我看见他们两个成了小黑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后来张云生说,他从零基础学习到单独跳伞,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又用了一个月,学习了翼装飞行。我说,那你是天才,就是该吃这碗饭。人啊,有些看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在有些人那里就是很简单。他说,这行能有什么天赋,得有勇气,小景不行,他一直不敢向前迈出那一步,做再多的准备工作、做再多的训练也是没有用的。
我在那天,忽然想到,他们不过是成功地回到了地面。成功回到地面的小景,曾跟我躺在一个房间里,两张床近得能听得到对方的呼吸,他曾经想靠自己飞起来,终究还是参加了职业训练。
我们本来就在地面上,参加了训练,飞起来,落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不参加职业训练,又根本不敢飞,一样没意义。
我再也不愿到无顶山来,连续两年,一天假都不请。我埋头于工作中,然后是家庭和日常琐碎,每天也很忙,忙得隔天的事都能忘得干净。
直到有一天,经理又换任了,跟接任的经理介绍我说,这是王轩,咱们公司的老员工,年轻的时候喜欢跳伞,像鸟一样在悬崖上空飞翔过,这两年上了年纪,没有再跳了。
新经理跟我握了握手,轻声说了一句,向您学习。
我握了他的手,回去后看了看搁置在角落里的伞包,决定找张云生学习跳伞,哪怕是像小景一样,被他背着跳一次。
这一生过得匆匆忙忙的,我在所有人的印象里,都是一个很诚恳的人,而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诚恳,我想把唯一欺骗大家的事情变成真的。
我跟张云生也是约在我常住的那个旅馆里,老板娘的儿子已经毕业了,张云生进来的时候,老板娘的儿子敲门进来给我打来一壶开水,说是山上的泉水烧开的,一壶五十元。这次来,发现店里添置了许多新东西,费用也涨了。而在不远处,有几栋房子正盖着,老板娘说是他们的。
老板娘的儿子长得很英俊,我盯着他的脸看,才能勉强看出初见时的一些样子。他见我盯着他看,没有显得拘谨,很自然地笑了,放下水就准备出去。我叫住了他。
毕业后怎么不留在大城市?
我读大学只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留在大城市的。
我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孩子的人生起点呢。
喜欢这里,喜欢这样的人生,又哪里有什么起点终点的分别呢?
我想起了自己三十岁前,也是这样子想按自己的想法活,不想被困在工作生活里。我一度想离职,在下定决心前,来无顶山旅游,是因为听说这里的石头很好看,一块连着一块,层层叠叠,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哪里算是山顶。它只是在旅游爱好者中有口碑,还没有大面积开发,不收门票。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沿着曲折的路爬到了顶。顶部平坦,一群人围在悬崖边,我也好奇地凑了过去,一个人背着伞包,正在跟大家挥手,然后他跳了下去。旁边的闪光灯把我也拍了进去,并且拍得很清晰,我面色平静,站在悬崖边,背后背着一个双肩包。
这张照片后来登在了报纸上,在公司里竟然被传成了是去无顶山跳伞了,我最初是否认的,可是大家说,报纸都登出来了,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没必要不承认吧。
我感觉自己的身上有了光环,一旦高层被这个光环吸引,我在公司里的前景一定会很好,我就抱着这个幻想,在这家公司一直干到现在。
我可能真的就是张云生说的,从来都没打算跳,不管是跳伞还是跳槽,有风险的事情我都不敢做。
张云生跟我说,小景跟他学习的时候,说自己得了重病,时日无多,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太平淡了,只想在最后的日子里,体验一次飞翔的感觉。
我说,他跳了一次后,觉得幸福吗?张云生说,他没有说。我说,他不是不愿接受职业训练吗?张云生说,他到最后也抗拒这个,但是不这样,他无法完成心愿。回到地面后,他就默默地走开了,剩余的尾款都是家人代付的。我说,你后来也没有再见过他?张云生说,没有,换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腰部有一处长长的刀疤,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没有说。我说,刀疤跟重病是两回事吧。张云生,我也不知道,你知道点什么?我对他很好奇。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跳下去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小景,微信也被他删除了,也或者,别人实现了愿望,去过另一种生活了,不想再跟这种生活有瓜葛。
张云生说,也有这种可能,那么说说你吧,怎么忽然也想到要跳一次了?
那是在目睹了小景双人跳后的第三年,我实在忍不住年复一年的诱惑,也想着跳一次。我找到了张云生。他说,如果我愿意,我将是他带跳的最后一个人,随后他不准备再跳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或是为了兴趣,或是为了生活,我们都该为自己而活。
张云生自己说出了原因,跳了这么多年,一身都是病,经常签死亡合同,总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老得快,看起来和你的年纪一样,实际上我和小景年纪差不多。我笑了,你这也是打算叫我叔叔了?他说,你确实跟我爸的年纪差不多,你这个年纪,要是带跳,还得去医院检查一下心脏病高血压什么的,不是想跳就能跳的。万一身体有什么问题,在高空中出了事情,怎么办?我说,跳以前不都签合同吗?张云生说,最主要的,你不是小景,他有强烈的愿望,你是跳不跳都无所谓。
我觉得脸上一热,想出汗,还是强自镇静地笑了一下,端起了一杯茶。
他看着我说,你考虑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跳,联系我,我是做这行生意的,随时欢迎每一个人。
他说完就走了。我一个人在农家旅馆里喝光了那壶山泉水,坐到天黑。
出了农家乐的小院子,有一道清澈的山泉,几块石头围成了一个小潭。虽是秋天,但晚上也不是太凉,潭水里残留着白天的温热,人跳进水里,仰头满天繁星,耳边听着连绵的虫鸣,然后在淡淡的月光里,裸着身体,等着山风一点点吹走身上的水珠,很是惬意。
我每次来无顶山都要在那里泡一下,有时也会遇到别的旅客,只要不是异性,也不用顾忌什么。
天黑后我又去了小潭,我觉得是最后一次了,走得慢了些。那夜无月,只有淡淡几颗星,山间模糊的光线,似也不是从星光而来,倒像是有种光映照着,让我看见了那几颗星。山间无灯,不知道这模糊的光从何而来。天之神奇,大抵就是总会有些东西,让你猜不透来路。
借着模糊的光,看到潭边多了几块平整的石头,忍不住站在了上面,人一下子高出潭许多。风鼓吹着衣服,下面的潭陌生而带着寒意。我脱光了衣服,轻轻下跳,落入水中,心中竟然有飞了一次的感觉。
——丰子恺漫画作品欣赏
——趵突小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