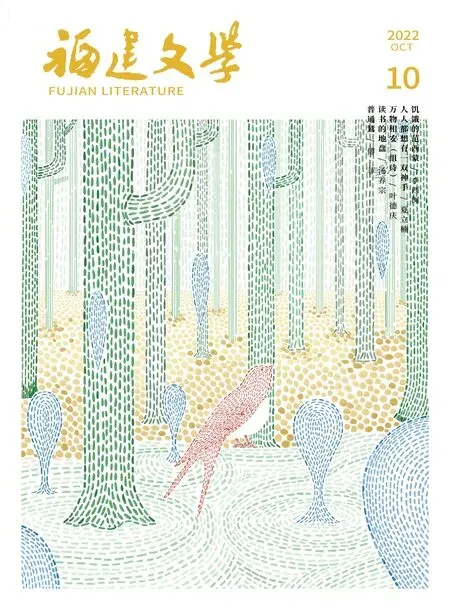窥心
濮 颖
殷陶要去四方城参加业务培训,第一时间告诉了唐宁。四方城有她的同学,这些年都少有交集。唐宁,算是她在那座城市里的故人。
正在浏览病历的唐宁看到信息后立即在键盘上一阵熟练地敲击:我休年假,正好陪你。唐宁没说谎,他确实在休年假,连续两周。即便是休年假,唐宁也没有别的去处。他早已习惯了医院廊道里来苏水的味道,白得有些耀眼的墙壁,以及窗外那株枝叶婆娑的法国梧桐。这棵梧桐树,正对着办公室的南窗,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它。春天的新叶,夏日的浓荫,秋冬的金黄,十几年来,这棵树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状态让唐宁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月光透过繁茂的枝叶,那些重叠变幻的影子就像一泓清波荡漾的流水。困顿的时候,唐宁经常站在窗前,凝望这片无声流淌的光影,心里总有一波清泉流过。这是四方城所有梧桐树里最美的一株。记得某天晚上他跟湘湘说起过这样的感受。从小到大就没有文学天赋,不善表达的唐宁居然会用诗一样的语言流畅地描述了这一切。这是一次超常的发挥,他为此兴奋得满脸通红,甚至想上前拥抱一下正在电脑前捣鼓博士论文的湘湘。可是湘湘连头都没抬。一股微微浑浊的气流从她有些肥厚的鼻孔里游了出来,嗤的一声,像小蛇一样瞬间游进唐宁的心里。
这些年,唐宁时常感到自己的心里有无数条小蛇在游动,它们在那颗红色的、搏动的器官上任意游走、纠缠,时而会用带着毒液的牙齿咬噬一口。唐宁缓缓闭上眼睛,用意念按下三角形的指纹锁,一台超清的显示屏立即出现在眼前。他的目光定死在那台唯有自己才看得见的屏幕上,一颗巨大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他用手去摸,是自己的心跳。那颗超强的器官已经坑坑洼洼,边缘不清。唐宁感到害怕,很多个夜晚他都会悄悄按下指纹锁反复地查看。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左心室的角落里有一颗类似草莓的器官。尽管隐藏很深,那么的渺小,但作为一名心外科专家,还是发现了它的存在。那颗草莓覆盖着丰富的血管,肉眼可以辨别出血管里有血液流动,肯定是一颗新心,唐宁松了口气。
他也曾试图去偷看湘湘的心脏,每次输入他为湘湘设定的密码后总是接收不到信号,就像小时候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从头到尾飘洒着密匝匝的雪花。家里的那台电视机至今还端坐在母亲的床头柜上,被一块洁白的带着流苏的针织台布盖住。这是父亲用自己发明的第一个专利的奖金买来的。缀着流苏的台布是母亲手织的。唐宁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父亲像一个凯旋的将士被一群人簇拥在客厅里。在大家的催促下,父亲看了一眼站在房门口的母亲,见母亲莞尔一笑,他就开始拆除这台机器外面厚重的包裹。唐宁站在他的身边,清晰地看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就在父亲将这台电视机稳稳地抱到那台荸荠色八仙桌上的时候,唐宁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了出来。那一夜,唐宁几乎没有睡,他知道父亲和母亲一样也没有睡。他们的浅笑与絮语被黑暗断断续续地切割,可是那些被竭力压低的声音还是零碎地从不太紧密的门缝中渗漏出来,唐宁竖起耳朵,这些声音又骤然消失在黑暗之中。那一夜屋角的秋虫也没睡,倒是那台黑白的机器在黑暗中睡得酣畅淋漓。第二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唐宁看见母亲坐在那只黄藤椅上,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捏着一把不锈钢针,小拇指上绕着几圈雪白的纱线,一块团花已经从左手上抖落下来,像一朵盛开的雪莲。
唐宁的父亲是第二年的夏天去世的。父亲走后,唐宁的母亲就将那台黑白电视机移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从此再也没有打开。有几回,唐宁偷偷摁下开关,屏幕上除了一团嚓嚓的雪花,还是一团嚓嚓的雪花。三十多年,那台电视机就一直端坐在母亲的床头,从来没有改变过位置。直到有一天湘湘回来,趁着他与母亲不在,把一个收废旧物品的人带回家。后来那台黑白电视机几经辗转,才重新回到了母亲的床头。也就是从那以后,唐宁的母亲坚决不肯再随他们去四方城。
很多时候,唐宁真想用手术刀剖开湘湘的胸膛,去看看这个千年修得共枕眠的人究竟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千年修得共枕眠”是湘湘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因为这句话,唐宁时常想起自己的父母。父亲走了三十年,母亲这三十年就一直待在老家,哪儿也不去。那个父亲和母亲曾经共同居住了十多年的小四合院,在周边装修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中显得格外破旧。尤其到了秋冬,屋脊上的蓬草、瓦松在风中乱舞,凄惶得很。唐宁好几次提出要把老屋修葺一下。母亲不说话,伏在父亲曾经坐过的那张老旧的办公桌边,不紧不慢地抄着赵孟頫的《寿春堂记》或是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到一句话写完后才停下手中的笔:等我走了,随你怎么弄。唐宁的眼睛立即酸涩起来,他抬头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父亲,父亲的眼睛在那层厚厚的玻璃镜片下好像也有些湿润。唐宁知道,那是屋里白炽灯泡的反光。毛毛这几年因为挂在墙上的爷爷,不肯随他回老家,她说她害怕。她还说这个房子旧旧的,院子里有股臭臭的味道,奶奶好老好老。房子确实很旧了;那股臭臭的味道是下水道的反味;而母亲因为父亲的离世,一直素食,长期脂肪与蛋白质摄取不够,导致皮肤干燥松弛,头发也变得灰白。这些年,母亲把带色的衣服全部处理了出去,家中看不见一丝亮丽的色彩。除了春节院门上的对联,家中能找到的红色,就是父亲与母亲的那张方方正正的结婚证。这张证书就压在床头柜的玻璃台板下面,红双喜下是并肩而坐的父母。唐宁时常在夜里醒来,总会想起母亲的床头柜,柜上的那台黑白电视机,以及压在玻璃台板下的那张红色的证书。他与湘湘也有这样的证书,只是形状不一,是两个小小的、红色的本子。
这些年,湘湘的脾气越来越大,床头柜上的药瓶也越堆越多。先是巢倍滋、大豆异黄酮,后来是补佳乐、雌二醇。药吃了不少,脾气却丝毫没有改善。湘湘说这是遗传。湘湘的母亲就是这样,一直到去世前,都没改掉爱发脾气的毛病。湘湘一样易激惹,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都会吵得脸红脖子粗,如机场一般平坦的胸口剧烈起伏,好像随时就会把人吞没。吵架的时候,她会把那个红本本从抽屉里翻出来,重重地摔在唐宁的脸上。有能耐,你去把红的换成绿的!每次,唐宁都会俯下身子把小红本拾起来,一声不吭地重新放到抽屉里,然后推开小房间的门,看一眼正在写字或是已经熟睡的毛毛。这几年毛毛去了寄宿学校,湘湘再摔红本本的时候,唐宁就去看床头柜上毛毛的照片。毛毛有一双好看的眼睛,随他。唐宁的姑妈说过,像爷爷。湘湘像被虫咬了一口:胡说!姑姑说:怎么胡说了?那是一根藤上的瓜。有几次,唐宁在湘湘扬起红本本,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床头的时候突然把她扑倒,强行行使了小红本内的义务。当他光着身体躺在床上,看着湘湘慢吞吞地套起内衣走向卫生间的时候,有些得意地笑了。夜里,他看到自己的心脏骤然变大了许多,心跳有些加速。他忍不住去偷看殷陶的心脏,那颗心在黑色的屏幕上有节律地起伏,他把自己的心慢慢重叠在殷陶的心上,满意地睡了。
毛毛越来越不愿意回高厦老家了。尽管唐宁一次次告诉毛毛,墙上的那个人是她的亲爷爷,是爸爸的爸爸,毛毛还是把扎满彩色毛球的头颅甩成一道七色光:那个人不是我爷爷,我爷爷在四方城。唐宁的心就像被马蜂蜇了,一连疼上好几天,这几天里,唐宁是沉默的,甚至不跟毛毛说话。湘湘说孩子说得一点没有错,她没见过墙上的那个人,她从小就是外公带大的。说外公是自己的亲爷爷一点也不为过。怎么可以跟自己的孩子过不去?真是小心眼。湘湘压根就不回高厦。那座破旧的小院,对于住惯了四方城繁华地段高档公寓的她来说,的确有着云泥之别。唐宁能理解,如果自己不是湘湘的丈夫,那个处于高厦县城南门外的破房子,以及这座房子里所有的东西,跟湘湘根本没有半点关系。以至于后来的春节,都是唐宁一个人回老家。他选择在除夕的傍晚回来,给父亲烧点纸钱,陪母亲吃个年夜晚,大年初一的早上给五服之内的长辈拜个年,下午就匆匆离开。他得赶回去跟湘湘、毛毛还有湘湘父母一起过年。湘湘说:大年初一一家人不在一起过,就等于没有团圆。唐宁在意这句话,抑或是更在意团圆这两个字眼。这些年,“团圆”就跟那个红色的小本本一样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以至于很多时候在湘湘与母亲之间,他违心地站在湘湘,也就是自己的小家庭这边。唐宁抬眼看了一下日历,9 日。明天又到了他向湘湘转账,也是湘湘主动尽义务的日子。只有这天,她才会早早洗漱,催促着唐宁上床,然后像母猴一样吊在唐宁的身上,又啃又摸。太贵了,一次两万。这句话,唐宁无数次在心里说过。
唐宁做过几百例心脏手术,所有病人的心脏都记录在他的电子病历里,唯独殷陶的心脏被他藏了起来。他至今还记得殷陶的心脏,记得上面的每一根血管和每一根神经。十多年前,在医院心超室,他亲自为她做的超声波检查,也是自己亲手给她写的病历。后来,又是他亲手操刀,为她修复了三十多年没有完全关闭的二尖瓣。这是他离开高厦县后,第一次与殷陶如此近距离、亲密地接触。他曾亲手触碰过殷陶白瓷一般的肌肤,触碰过她那颗滚烫的、跳动的心脏。想到这里,唐宁感觉身体迅速地发热,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那棵梧桐,急促地又打了一行字:梧桐叶落了,一片金黄。
唐宁生下来就具备一个理工男的超强大脑和非凡的动手能力。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问学生的话题就是长大了想干什么,唐宁跟大多数的男生回答一致:想当科学家。这么伟大的理想当然是极少人能够实现的,可是唐宁却实现了。若干年后,他不仅成为业内知名的心外科专家,还跟他的父亲一样发明申请了一些国家专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殷陶笑了。她笑唐宁这个标准的理科男居然会这么文艺。这算是唐宁与自己第一次约会。在此之前,殷陶是唐宁的病人,抑或是医患关系延伸出来的朋友。其实,这些都不正确。她与唐宁的确是故人。故人这个词,是殷陶左右考量之后的定义。不知道怎么形容唐宁,就像自己不知道唐宁将自己定义成什么一样。
唐宁立即开始梳理这几天的安排,这是结婚以来第一次单独陪湘湘以外的女人。有两个晚上,他失眠了。直到后来,他强迫自己服了一片艾司唑仑。当白色的药片随着温热的白水从舌根到咽喉,然后滑向食管,再慢慢进入胃部的时候,唐宁突然又从屏幕里看见了殷陶。殷陶的整个人是透明的,他看见她的上消化道里有两个小小的白色精灵,在一片粉红色的黏膜中游走,在翻腾的小气泡中跳舞,然后变得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殷陶和自己一样,唐宁做了一个深长的呼吸,随后倦意就像涨潮的海水将他包裹,显示屏上的图像也随之模糊起来。唐宁在有些混沌的意识中默念关机密码,屏幕上立即一片漆黑,就像此刻四方城的夜空。
就在出发前一天晚上,殷陶的部门领导约她乘专车同行。殷陶说已经订好了高铁票,并且与四方城的朋友约好了时间一起去看紫金山和章泽湖,抱歉不能同行。电话那边还没来得及掩藏好失落的语气,殷陶就将电话挂断了。她仰头看了一眼深蓝的夜空,尖削的下巴像极了天边的弯月。
唐宁选择了在湘湘上课的日子陪殷陶。湘湘是四方城里一所知名高校的教授,毛毛上的是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湘湘经常强调唐宁每个月转来的工资只能支付毛毛的生活费、学费、各种培训费和日杂费。自己不但没有花过一分,还要为这个家做兼职、理财。她嫁给唐宁这些年也没有妻以夫荣,而是像一只猎鹰,一直盘旋在四方城里的上空。她抱怨在四方城,太多像他们这样的高知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境外,都拥有两套甚至是多套住宅,各自驾驶着各种型号的BBA,而自己的女儿还在国内,银行卡上的钱也迟迟赶不上飞涨的房价。她开着那辆有些笨重的国产车,至今都不明白一个省内甚至国内知名的心外科专家每个月怎么就这么点收入,也想不明白唐宁为什么要捣鼓那些根本就不值钱的发明。她跟唐宁说过,有些红包是可以收的,有些讲座是可以去的,除了会诊,也可以走穴,那是周边区县市小医院以及病患求之不得的,是双赢的好事。她很不服气对面“绿地”住着的一个小外科主任,开锃亮的奔驰,而他那个颇有姿色的全职太太,连买菜都会挎着老花的敞口驴包。她说如果唐宁每周去周边城市走穴一到两次的话,她可以为他买一台宝马。她也暗地里摸过行情,不出一年,就可以稳稳地把宝马的成本收回。唐宁动过心,就是不敢行动。湘湘恨他没胆量,没魄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直到省中心医院骨科因为胆大出了事,湘湘才停止了这些理论。唐宁也总算松了一口气,也暗自为自己的胆小感到庆幸。
唐宁站在穿衣镜前,一边扣纽扣,一边规划行程安排。他得提前半小时起床,再洗澡,七点钟做早餐。湘湘上课的日子是不会给他留早餐的。他得自己热牛奶、煎鸡蛋、切牛肉、涂黄油面包、撬坚果、削苹果。在这之前,家里早餐都是湘湘母亲做的。那是标准的中国式早餐,稀饭、馒头加一只水煮蛋,一盘酸到倒牙的豆角。那时他们还挤在老城区的两居室。每天早晨,唐宁就会在各种声音中醒来。准确地说是在拖把来回捣鼓的声音中醒来。那是一只塑胶的拖把,很好用。湘湘母亲常常用它在地板上滚过一圈后,满意地扯下黏在拖把头上的细碎的毛发,长的、短的、黑的、黄的、粗的、细的,还有交织在一起、被压缩成线状的棉絮和布屑,然后再将它们扔进那只塑料的垃圾桶里。而后就是湘湘父亲介于咳嗽与呕吐之间的声音,那是慢性咽炎的他,正在卫生间用力地刷牙。早晨的二居室里永远慌乱而又杂乱。唐宁跟湘湘说过,拖地完全可以放在他们都上班以后,可是湘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她的母亲即便是一大早起床不拖地,也会有厨房的声响。这个家可以没有声音,可是请问家务谁来做,毛毛谁来带?话说到这个份上,唐宁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慢慢地,他习惯了在医院。直到后来毛毛住校,湘湘父母在小区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他还是习惯待在医院里。
唐宁边吃早饭边计算着时间,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殷陶住的酒店。唐宁还知道在那个酒店不远处有一家四季花店,他要买一束百合,半开,不要洒香水。因为殷陶身上的香气足以熏染这束百合。殷陶需要一个充足的睡眠,还需要一顿丰盛的早餐,当然,更需要有充裕的时间化妆。其时他会在酒店的大堂等上半个小时,那时正好是早晨九点。深秋的四方城气温不高,这个点正是一天中阳气上升的时候,唐宁好像看到了殷陶光洁的脸庞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两片酡红,就像第一次在老家的梧桐树下看到她一样。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是典型的二尖瓣脸。那是三十年前初夏的清晨,那天,唐宁刚从县医院下夜班回来,与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骑着红色轻骑的殷陶擦肩而过,风过处,一阵淡淡的香气。再后来,在心超室,在病床,甚至在手术台上,那股清香还在,混杂着来苏水的气味,一下子钻进唐宁的心里。
车从地下车库出来的时候,唐宁从后视镜里审视了一下自己,居然发现额前有一根白发,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招摇。他没由来地一阵慌乱,立即用手捋了一把发梢,原来不止一根。这一发现让唐宁有些猝不及防,他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的白发。湘湘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包括他的同事。这些年,在医院,他一直都是年轻有为的中青年专家的人设,是大家眼里永远不老的常青树。后面车子在摁喇叭,声音里透着焦躁,甚至是愤怒。这年头,人们好像有太多的怨气,等个红灯,避让一个慢腾腾地过斑马线的人,都会骂骂咧咧几句。就在前几天,湘湘因为绿灯亮的时候正接听一个重要的电话,只好等待下一个绿灯时,被后面的司机敲开窗户大骂了几句。当时的湘湘被骂蒙了,回家后气咻咻地向唐宁诉说。唐宁说可能人家真的是遇到了什么急事。湘湘气急脸红,一定要去找交警大队的同学调监控,然后去找做律师的朋友,发誓要跟那个敲窗骂人的司机讨个说法。这些年,湘湘在四方城积累了很多人脉资源,也善于利用这些资源。她很受用大家赞誉她的“长袖善舞”。她说资源就跟手中的权力一样,不用浪费,过期无效。喇叭声越来越急促,不止是后面的,还有再后面的。唐宁立即踩动脚下油门。
车在马路上行走,弯弯曲曲,像一条蜿蜒游走的长蛇。唐宁记得自己刚进省城的那会儿,母亲叮嘱他不要学开车。他知道母亲的意思,以至于考到驾照后很长时间都不开车。他也发现打车、坐地铁远比自己开车更方便,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节省汽油费,更多的是可以在车上眯上眼睛,哪怕就是那么一小会儿,下车后都会觉得神清气爽。他甚至觉得车上的小睡远比在家里大床上的一夜睡得更沉,也更轻松。
殷陶住的酒店在四方城的东郊,离市区比较远,虽然老旧了点,却是一处标准的园林式酒店,颇有民国风范。比起市区内的摩天大厦,快捷酒店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唐宁感觉自己应该提前半小时,哪怕是一小时,可是太早了又怕引起湘湘的怀疑。湘湘比一般女人敏感、大胆,也聪明,更是理财高手。这几年,她硬是将家中有限的资产通过理财手段慢慢扩大,从两居室到大平层,从老城区到市中心。可是她坚持咬着牙,不肯出售那套两居室。在四方城,像这样面积不大的二手房好出手,相对低廉的价格,很吸引像唐宁当年一样从外地挤进省城的年轻人。湘湘说现在正是房地产低迷期,卖涨不卖跌。唐宁好几次想把房子租出去,那个房子里只有发霉的家具、不能抽水的马桶,留着没有价值。湘湘不同意,那个房子里有她母亲镶着黑纱的照片,那是她父亲和母亲说话的地方。
湘湘母亲是在毛毛上中学后去世的,论她对唐家的功劳,说大过天一点都不为过。在这个家里,老太太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她顶着两个儿媳的压力,为女儿操持着家务。牺牲了酷爱麻辣的味蕾,跟着女儿一家吃着甜腻的淮扬小菜。湘湘喜欢拿唐宁的妈妈来做比对:姆妈,你皮肤白,穿花哨的衣服显年轻。不要学高厦的老太太,把自己弄得像修行的居士。姆妈,高厦的老太太吃素,你不能。你要带毛毛,做家务,消耗大。一定要多吃,每天的牛奶不能断。后来,连毛毛都称唐宁的妈妈是“高厦老太太”。
唐宁不想发声,确实,自己的母亲没有为他们的小家出过力。她总说她的家在高厦,不在四方城。湘湘母亲则说唐宁的母亲就是拉二胡的,自顾自。这句话是唐宁无意中听到的。那一夜,唐宁的心脏跳得极不规律,像是要蹦出胸膛。于是他在黑夜里再次打开DICOM 软件,看见了自己的心脏。那个器官上密布了无数条流动的血管,比多普勒清晰数倍的声效像万马奔腾,又像决堤的黄河水一般,似乎要将这个漫长而又寂静的长夜活活地撕裂。
今天的红灯好像特别多,他几次在等待的空隙想掏出手机给殷陶发条语音“路上拥堵,可能会迟到”,终究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其实在手术之后,他与殷陶根本没有见过,一切悄然无息。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无意中关注了一个叫作“眉峰碧”的公众号,他与她或许从此再无交集。这让唐宁更加相信,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偶然的。该遇见的,一定会遇见。他沉迷于殷陶的文字,就像沉迷于手术一样。他在殷陶的文字里有些恍惚,以致忘了世间还有惊涛骇浪、四季更迭,常常觉得桃红李白还没看够春天就谢幕了。殷陶笔下的山水风物,早已在他的心中提炼成一种审美符号,拷贝在自己的心上,慢慢地,竟成了身体力行的情感反哺,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血脉瓜葛,也成就了内心那种源源不断的驱动之源。这一切,使得他不甘于在虚拟的世界里与殷陶对话,他迫切地想要与殷陶在现实生活中交集。想到这里,唐宁的心跳加速,他知道是那颗小心脏的血流在高速运行。这颗小心脏已经迅速长大,并且从量变到质变。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副驾驶上的那只布包,里面是为殷陶配的中药饮片。殷陶说过因为创作睡眠一直不是很好,这些日子情绪也有点低落。这些药是他请本院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开的。老中医退休后归隐乡野,唐宁开车去拜访,还带了两瓶珍藏了十几年的美酒。湘湘也说过想看中医,唐宁却说补充雌性激素远比中药来得更直接。
唐宁远远看到了园林标识。不一会儿就驶进大门,沿着梧桐大道,随着指示牌,很快就来到了8 号楼——馥芳苑的主厅。唐宁知道这是酒店的景观楼。每个房间都有落地的门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户外的整片水景,梧桐树点缀其间。四围紫金山如屏障一般,真正的远山如黛,近水如烟。
挺拔的门童早已迎了上来,准备引导唐宁停泊在指定的车位。就在他摇下车窗的时候,一对银发的老人闯进他的视线。他们正挽着膀臂从酒店的大堂出来。玻璃门窗反射的阳光涂满了他们的面庞,金灿灿,暖融融。那个穿着得体、颇具绅士风范的男士正是湘湘的父亲。
那一霎,唐宁愣住了。他感觉到自己骤然停止了心跳。他眼看着一对老人向梅林方向走去,越走越远,直到走进一团和煦的光影之中。在门童的催促下,他下意识地将汽车倒进了车位。半晌,像还魂一样拿起手机给殷陶打电话,一次、两次。电话那头是接线生不急不慢的回复:sorry……唐宁下了车,到前台请服务生打了房间电话,依然没人接听。唐宁瞬间像被拧干了水分一般无力地瘫倒在沙发里。他有些吃力地举起手机,给殷陶发了两条信息。微信对话栏上的条框,像一座小小的城墙,将几段黯淡无光的文字包裹,一动不动。而殷陶的头像依旧在那,浅笑嫣然。
一个服务生说,昨晚送水果的时候房间就没人。另一个说一大早看见一位女士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出门,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先生要约见的人。唐宁无力地闭上眼睛,他又看见了殷陶的心脏。心率72 次/分钟的节奏,健康有力,一点看不出有二尖瓣修复过的痕迹。突然,他发现了另一颗跳动的心脏的影像,正慢慢地向这颗心脏靠近,似乎就快要重叠的时候,慢慢又拉开距离,而后再次聚拢……唐宁坐直了身体,就在他试图看清这一段影像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
唐宁抬起头,一眼瞥见大堂的电子日历:壬寅年九月十九。他有些怀疑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同样的时间。而这一年,却是辛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