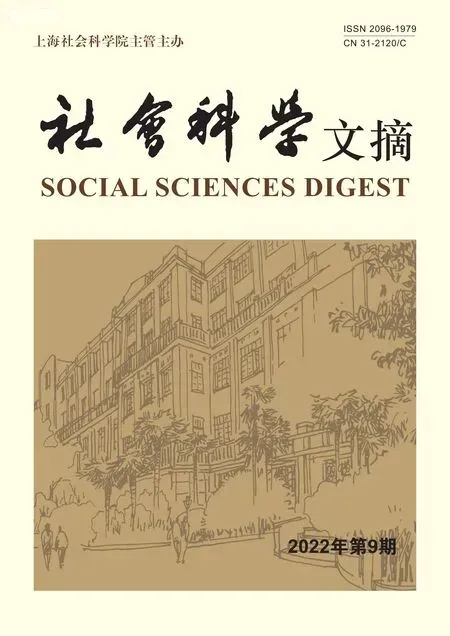工时视角下头部企业工资溢价及成因
文/刘元春 丁洋
引言
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失衡问题。就以后者为例,诸多研究证明,大企业工资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按劳动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超出部分即为工资的规模溢价,也称工资租。本文将重点关注头部企业工资溢价的成因问题。
对于工资的规模溢价,现有文献从不同维度寻找了原因,但均不甚理想。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五类。一是生产率优势论。工资的根本决定力量是劳动生产率,而相对小企业,大企业的生产率普遍更高。这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种解释,但它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按照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逻辑,当劳动力同质且可自由流动时,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不会持久地存在而应趋于收敛。相应地,工资也应趋同,除非劳动力不同质或不能自由流动。二是人力资本论。这对应于劳动力不同质的情形。此观点认为大企业的人力资本要高于小企业,这必将引致工资差异。但实践中大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未必高于其他企业。在国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量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特征的人却拿着迥异的工资。就以英国为例,1975—2000年工资差距扩大主要源于组内工资差距的扩大,而非组间差距。类似地,1989—2003年日本工资差距扩大也主要是由组内差距扩大引起的,组间差距反而缩小。三是利润分享论。大企业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能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它们有能力支付更高的薪酬,也愿意把一部分利润拿出来分享给员工。但大企业为什么要与员工分享利润呢?Brown &Medoff 将其归因为工会的作用。大企业的工会成员比例高,利润分享是受工会胁迫所致。这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情形。四是补偿论。有人认为,大企业的工作环境差,高工资是对负效用的补偿。但现实似乎正好相反,大企业的工作环境往往更好,办公场所更舒适、保障更健全、晋升空间更大。五是效率工资论。其核心观点是,大企业组织规模庞大,难以有效监督员工,为解决之,他们会按效率工资的思路,把工资设置得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以对工人形成震慑效应:如果偷懒,一旦被发现并开除将失去这份丰厚的薪酬。这个假说虽有思辨的启发意义,但实践中却难以检验。
如前述,解释企业间工资差距还有一把可能的钥匙,那就是劳动力流动受限。如果劳动力能充分流动,那么,不同企业间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特征的劳动者必将获得相同的工资;相反,如果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限制,那么,高工资企业就会像一个围城,外面的劳动者无法进入,工资溢价就会持续存在。但纵览劳动经济学各类文献,这种可能性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高工资企业是围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呢?它可能是制度藩篱,比如,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下,分配资源的权力阻止了次级部门的劳动者进入优先部门,并使后者丰厚的待遇得以维持。一些内生力量也可能会制约劳动力流动,比如,特殊的雇佣决策机制:如果一个大企业很保守,在产出扩张时不愿增加雇员,那么现有员工就能瓜分更多的工时而抬高工资。这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流动受限的情景,也是本文将要着力研究的一种情景。
要描述这个情景就要解剖企业劳动要素投入的行为黑箱。过去,人们一直将劳动要素投入与雇员人数简单地划等号,但在严格意义上,劳动投入是一个工时概念而不是人数概念,劳动投入等于雇员数乘以人均工时。当产出波动时,劳动要素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调节雇佣数来调整劳动投入,也可以通过调整人均工时来实现,或兼而有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从这种分离入手探究了企业行为,解释了很多以前解释不了的现象。这也将构成本文理论分析的切入点。
理论分析
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拟合小时工资曲线、求解生产者均衡发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调整劳动要素投入时有不同的偏好方式:对小企业来说,受限于每个岗位必须保有的最低人数限制,他们更偏好工时调整方式,雇佣量对产出的反应迟钝;中型企业偏好雇佣量调整方式,雇佣量对产出反应灵敏;大企业受组织成本的制约,更偏好工时调整方式,雇佣量对产出的反应也比较迟钝。其后果是,小企业人均工时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对应于均衡的时均生产率,其人均生产率和工资也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中型企业的人均工时维持市场均衡水平,人均生产率和工资也维持在市场均衡水平。大企业人均工时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人均生产率和工资也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由于大企业更偏好工时调节方式而非雇佣量调节方式,外面的劳动者将难以进入其中,工资不易被稀释。
实证分析
在实证层面,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构想进行了检验。将各年各企业的营业收入按行业分成五等,即25分位以下、25—50分位、50—75分位、75—90分位、90分位以上。90分位以上的可视为头部企业,25分位以下的更接近于小企业,中间的更接近于大中型企业。各统计指标显示,头部企业的工资中位值较全样本中位值高出近15%,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在人均劳动生产率上头部企业的中位值是全样本的2倍。但头部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占比均不存在明显优势,甚至低于平均水平。人均资本优势也无法完全解释人均生产率优势,头部企业的人均资本中位值为36.954万元,比全样本的23.229万元高59%,生产率则高出102%。
在计量策略上,本文利用fe-iv方法对样本进行回归。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工资的对数,解释变量为表征5类规模企业的哑元变量D(j=1-4),以25分位以下的企业为参照组。同时本文还引入了数个控制变量以及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引入后者的原因在于,工资可能会受到诸多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而呈现较大的连续性,并使当期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期。这是一个动态模型,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各地所属行业的平均工资滞后值ln mwage 作为其工具变量,因为地区性行业工资一般会对企业工资施加影响,但与影响单个企业工资的其他特定因素关联性不大。在回归过程中,本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如果引入某变量后发现原规模溢价变得不再显著甚至发生转向,那么工资的规模溢价就可能是通过它实现的。
回归结果显示,大企业的工资溢价不能从利润分享、人均资本优势、技术优势或人力资本优势等视角得到充分的解释,而应源自大企业更高的人均生产率。为继续检验头部企业人均生产率优势的来源,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人均生产率进行回归,人均资本存量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大企业的人均生产率优势并不能从人均资本的角度得到太多的解释。同时技术力量、人力资本等因素也不足以解释大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以上结果均通过了三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
基于雇佣量调整灵敏性的进一步检验
本文认为,大企业的人均生产率优势还可能源自其更长的工时优势,但工时不易直接度量。当产出波动时,大企业由于雇佣量调整迟钝,使人均工时维持在超额水平并推高人均工资。所以本文接下来通过比较各规模企业雇佣量对产出调整的灵敏性,间接检验了工时理论。利用与前述类似的计量策略,本文发现,雇佣量对产出变化的反应弹性呈现 “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进一步,本文认为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在于头部企业在扩张期和收缩期有不同雇佣策略。在产出扩张时不愿增招新员,以防组织成本进一步扩大,在收缩期不吝于裁员,借机降低组织成本。为检验这一构想,本文将样本分成两类进行回归,一是产出扩张时的;二是产出收缩时的。结果显示,在扩张期,90分位以上企业的雇佣量对产出的反应弹性为0.138,低于其他规模的企业。而在收缩期,90分位以上企业的反应弹性高达0.628,高于其他规模企业。这证明头部企业的雇佣量调节确实较为特殊:在产出扩张期雇员扩张幅度明显少于其他企业;但在收缩期,雇员收缩幅度并不逊色。扩张期吝于扩员、收缩期却不吝于裁员,保护了其工时优势和工资租。
本文贡献有三:其一,可以深化人们对工资规模溢价成因的理论认识。大企业工资高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如何解释它,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已有文献多止步于其生产率优势,或只是提出经验预判,而没有进一步深究后者的真正源泉。本文从雇佣量—工时调节的视角给出了一家之言的解读,是在理论层面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比较符合经验事实。其二,揭示了劳动力在雇佣谈判中仍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谈判势力提升,而是反映出头部企业较以往更强大的力量,使其在衰退时得以快速裁员,扩张时要求加班而不扩员。其三,具有独特的政策内涵。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打破不合理的工资溢价,就必须促进劳动力流动。哪些因素会限制劳动力流动?过去人们总是强调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有形藩篱的束缚,而忽视了以企业雇佣决策为代表的无形因素的潜在影响。大企业偏向于工时调节的要素调整模式已构成一堵无形的墙,让同质劳动者无法享受到均等化的工资。今天户籍制度改革的边际收益已有所递减,我们应将政策视角适时转向引导企业雇佣机制上。
结论及政策建议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这一长期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资本—劳动分配失衡这一主要矛盾,也不能忽略劳动—劳动分配失衡这一常见矛盾。本文特别关注为什么头部企业会支付更高工资的问题。若劳动力同质且流动不受限制,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对这一问题,传统解释是大企业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或人均资本或更先进的技术。但这些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与现实也不完全吻合。撇除上述因素,头部企业的工资溢价还可能源于另一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更长的人均工时。如果把劳动要素拆分为员工数和人均工时就会发现,当产出扩张时,大企业对劳动要素调整会更偏向工时调整方式而非雇佣量调整方式,因此更吝于扩员;相反,当产出收缩时,大企业更偏好雇佣量调整而非工时调整方式,因此又不吝于裁员。大企业就像一个围城,易出难进。员工凭此可以瓜分更多工时并将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维持在高于市场均衡的水平。现实中有三个经验事实可以佐证之:一是大企业加班现象很普遍;二是但凡遇到经济不景气,大企业裁员的力度都非常迅猛;三是扩张期大企业增员则相对谨慎,有的头部企业甚至以“非清北不要”等歧视性条件来提高进入门槛。
政策建议有两条:第一,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优化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结构,促进企业间工资公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分配制度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对于拥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来说,即便身处不同企业,只要创造的价值量相同,那么,就理应享受均等化的工资,而不应出现太大的差异。但本文揭示头部企业的工资要远超其他企业,而且这种优势并非源于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优势,而是源于工时优势。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机会不公平:头部企业垄断了行业产量的相当大份额,局外人却鲜有机会分享其中的工作量。按新古典理论的逻辑,要让同质劳动力分享均等化工资,就要完善企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机制,革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对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过去人们更多地强调户籍制度、市场分割等有形屏障的作用。殊不知,在微观层面企业特殊的雇佣决策机制更是一道无形藩篱,不仅难翻越,而且更普遍地存在。在今天户籍制度改革已经纵深推进,制度创新边际收益有所递减的情况下,政策应适当转向引导雇佣机制上,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构建起就业友好型的要素调节模式:在扩张期不要刻意压低扩员幅度;收缩期也不要肆意裁员。政府可根据扩张期的新聘员工规模、收缩期的稳岗保岗量对企业提供补贴,矫正市场失灵。另外,要引导企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来优化组织管理,降低组织成本,减少招员时的顾虑。
第二,进一步完善资本—劳动间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头部企业工资溢价主要源于工时优势而非时均工资优势,说明这些企业的劳动者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工资溢价,他们所获得的其实只是工时溢价。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得到提高。进一步,头部企业在扩张期加班强度大、收缩期却大张旗鼓地裁员,说明劳资关系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相较于其他规模的企业来说,劳方还居于更弱势的地位。资方的强势源于它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高工资则会进一步强化其强势地位,并像效率工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使劳方话语权进一步减弱。这显然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善资本—劳动间的分配格局。平衡劳资关系是一项长期任务,它不能光靠自治,还要引入第三方力量,比如强化工会的作用,或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在必要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通过专项的劳动规制政策来矫正资本—劳动间的博弈关系,让天平的砝码适当向后者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