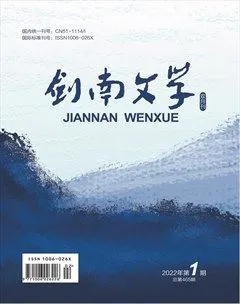回 家(组诗)
□ 老房子
回家
回家,以肉身吃肉,用真身喝酒
穿肠之物共朵颐,大快此时必定
天上人间
烟雾迷离
返乡在即
嘈杂之声内涌外寂
不同于麻雀、喜鹊以至乌鸦
田鸡吞噬蚯蚓,泥鳅和野生鱼逃逸
霭可作韵母
不会与貌似的它物合污。异味
灵魂何以戴着口罩飘荡,一个个
在墨镜后面
干瞪双眼
夜幕慢慢闭拢之时,用腹部
急急摸索归途。冷血。无血色的
萤火虫画出他乡的风向
蒲公英飘浮不定
沏壶茶,挟持记忆寥寥清谈
回家之途
隔着一条长长心路
23点以后。冬夜
23 点以后的冬
那些飞飞扬扬的亲吻,是他们脸庞
滑下的湿润
无限的若干的无可名状的……
环球同此凉热?
觅了一碗小面,大号“重庆”
有个崽儿说:
不辣!不麻!也不酸!
我只好心平气和劝自己:
总比孤家寡人热和多了
一碗小面
此时比天还大!
不信?
来试试
我就是年,以负禾之状行走
风从低处把眼疾的沙粒吹僵硬了
冷嗖嗖的。嚣声继续
北方汉子一张阔脸
千山万壑
笑话南方人细皮嫩肉。皴了
关于雪的若干想象
“这是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可是
连雨滴都藏匿
就像台历几年前就撕掉了最后几页
消失。彻彻底底
写字台
不再方便鬼画桃符
谁来签约,谁又来摔碎一把珍稀的
茶壶。他
就是一气之下的四散碎片
一处凹陷
弯不弯腰
无所谓可与不可
就像你听说的一句梦话:
“时间是祖先定下的规矩,规矩是
所有物是人非以后的祖先”
直起身,看雪
还是没有踪迹。它一旦来
便是新旧之间。尽管
这种划分很冷酷。可
我就是年,以负禾之状行走
就是那一只蟋蟀
到站,下车
Y 先生涉水来接你
两个清癯的形体在海岸
听一只蟋蟀:
到站下车是幸运的
过犹不及
前面后面很多很多的上下
不知道归宿
就是那一只蟋蟀
蹦出石头。还在想敲亮
自己的教科书
有难言之隐
药瓶
从书桌到书柜
又从书柜到电脑桌
猛地一天
傍晚的台灯昏黄了恍然
高矮粗细的厮们
稀拉杂乱立了一片
那架势
已不是上海滩在影视片里再现
冷汗。冷出了冷兵器的刃尖
肾上腺应急处置:
打,是不值的
杀人三千自伤八百
降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
进退失据
我抽出一本书又抽出一本书
我在电脑上敲打五笔: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
——我有夫子率领
我有文化自信
那些瘪三最多也就有知识无文化
我就在书桌一线布阵
来吧
别中了我的空城计
网球肘
一个运动型名称在
偶有阳光也只能斜着进来的狭窄空间
粘紧了胳膊。仅仅百日
就像出栏的猪被送到菜市场
关节被盖上了难以涂抹的检疫印章
阳台上不经意伸长的一茎草
抽出“嘶——嘶”风一样
生冷的欷歔
他已经记不清楚
曾经奋臂大呼过多少日
像将军抑或草莽。总之
不用登高
他的肘就挥高了无数潇洒
那些飞动的记忆
正在被窗外鸟声衔起的疼
一颗一颗吐出
昨晚和球友云对饮
眼里冒出的星星
没有丝毫替他缓解的善意
一个痛楚得漏了网的光阴
高挂西墙一壁
从早到晚
像是以拿捏他心结的把柄为乐:
来日你如果举得球拍
看我和谁对决
他平添嗫嚅,恐惧
健康一旦失分就不过是疼痛着
透风的更衣室
伤害是不可以任意冲刷的
热汗、球鞋
没有可以互赠的球拍
只有日光和月光
从看场子的临时工眼里
轮流斜视
老房子里面
一阵一阵龇牙咧嘴
而这也许
仅仅是与老房子痛点的一种相似
桂花酒
今夜,一滴
悬在草尖,欲圆未圆
星星无语
谁能点燃树梢
谁就把阴影戴在
草香引诱的风头上
瞅着远方
秋水在它的臂弯
讲述渐凉
再低沉
默念蛙声虫鸣
桂花酒
也滴在你草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