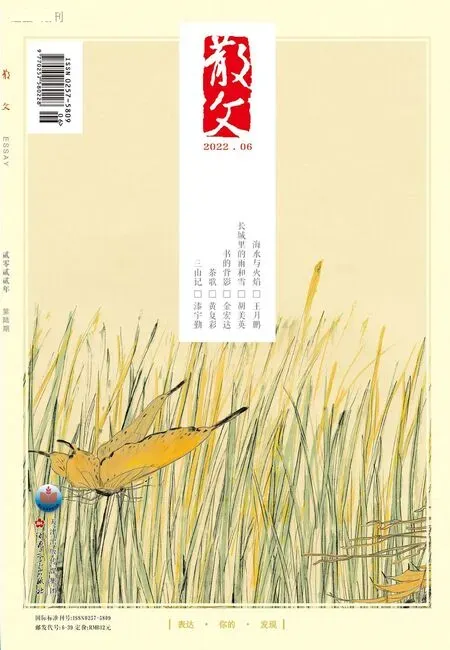长城里的雨和雪
胡美英
一
絮絮叨叨的雪,像人们絮絮叨叨的诉说——乌鞘岭是河西走廊东端的天然关隘。“汉霍去病率军出陇西,击匈奴,收河西,把河西纳入西汉版图,修筑令居(今永登县西北)以西长城,经庄浪河谷跨越乌鞘岭”。“明朝廷再次在这里修筑新长城,汉、明长城在乌鞘岭相会,蜿蜒西去……”《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五七七卷也载,乌鞘岭“盛夏风起,飞雪弥漫,寒气砭骨”。一些注说,从典籍里走出来,雪粒样地下在雪雾里,下在我的思绪里;修筑长城的人,也从雨雪里、从长城的纹络里走出来,走进我的想象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修筑长城的人是落在乌鞘岭上的雪吧,他们远远地来,又从远远的地方拉来黄土,筑起海拔最高的汉长城、明长城;风将黄土里草木的种子吹得到处都是,不长草的铁黑色山头,就披上了绒毛样的草植,给山体盖上了一层御寒的衣衫。他们和草木、和雨雪一起,得到了永生。
二
“1987年12月4日,我终于走到了山海关老龙头。”1987年4月,先前经历两次徒步考察失败的英国探险家威廉·林赛,又从嘉峪关出发了。那一年,坐在讨赖河畔长城第一墩下的威廉·林赛,年轻俊朗,意气风发。“能吃到馒头就算是赴宴了”,一路上经历着寒冷、焦虑、疲乏和心惊胆战,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他用一往无前的意志,寻觅着长城的身影。当进入山丹的时候,他被一农家狗疯狂地扑咬。“弄不好会被啃成一堆骨头!”在徒步两千四百七十公里的行程中,他用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这样一次又一次超乎想象的穿越。后来,在带领摄制组拍摄汉木长城的过程中,因为没有信号,他靠喝下自己的小便走出近五十摄氏度的酷热大戈壁,向120急救、文物、公安等部门发出求救信息,才得以脱险……威廉·林赛为了长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长城,他定居在中国;也是为了长城,他将在中国度过一生。长城,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两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跟随他们夫妇做保护长城的志愿活动。如今的他,已是霜染黑发,还在不遗余力地做着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他说:“长城有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效应。一看到长城,所有的疲劳都立马消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个文化的大陆……”(威廉·林赛《我的长城生活》)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已经打开,但是威廉·林赛的长城探险遇到的最大障碍仍旧是“不对外开放”政策,在之前的两次失败行程中,他九次被抓,一次被驱逐。在这一次孑然一人考察长城全线的过程中,他得到过长城沿线六十多位普通民众住宿和饮食上的帮助,他对他们心怀感激和敬畏,像敬畏长城一样。
在这些热爱长城的人的骨子里,都渐渐渗进了这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他们眼里,长城真的是活的,看长城,就能看见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保护长城的人们,来来去去,真真切切,像一场又一场的雪,轻轻地飘落在长城之上,让长城有了灵魂和温度。
细细密密的雪粒,落在将枯未枯的草棵上,我听见脉管里血液涌动的声音、水汽漫进每个毛孔的声音、雨滴落进胸膛的声音。雪水顺着这些北方山头汗毛样的草棵渗进土里,整个山头就漾动起蚕食桑叶般的吮吸声。等到粉状样的雪粒变成小朵小朵花瓣的时候,车窗跟前的山头像盖上一层灰白的棉麻布,草棵凸起的线条,织成一根根经络,坚强而有力量。这算是河西走廊的雪了吧?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童话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样的雪景,我就想起草垛、柴火、壁炉、炊烟、牛羊和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的母亲这些温暖的意象。白雾缭绕、天地相接的苍茫深处,是七个小矮人居住的地方吗?我那远逝的父母,一定正在那里和七个小矮人拉着家常。他们在雪盖的白房子里生着火炉,雪化成的白雾,就升上了天空,燃起白色的炊烟——咕嘟咕嘟地煮熟一锅雪做的粥,四溢而出,漫淌山河。
这世界,能超越地域和时间的,莫过于草木和雨雪。草木长进长城里,就长成了长城的筋骨:甘肃金塔附近的汉长城,泥土被两千多年的风雪荡去,露出一小扎一小扎红柳、芦苇硬刺刺的骨节,刺得风声都发麻,雪落在上面,却凸显出骨骼一样的纹路。雨雪长进长城里,就长成了长城的血脉:敦煌以西的木长城,露出一层一层芦苇穗的棱角,与风雪絮絮叨叨地唠着嗑,像那些风蚀的柴草垛;遇见阳光,又像岁月的火把,能被风携带的沙粒擦燃。
乌鞘岭好像总是与风雪有关。“长城进入焉支山的时候已经不太完整,脚踏在新下的雪上嚓嚓作响”,“大风骤起,接着是暴雨,随后又下起了大雪”,“狂风卷着干硬的雪粒迎面扑来,能见度不到十米”……威廉·林赛在《独步长城》里多次记下他进入焉支山往东走时的多雪天气,等他翻越乌鞘岭时,一定早已是风雪弥漫了。
风将雪粒吹成一道道白色的线条,斜织着,罩在空中。行走在乌鞘岭上望长城,感觉它如今更像是河西走廊东端的一道院围——河西走廊的人们,就在它的围护里放牧、种菜、侍弄庄稼,安然地生活……
三
落雪的河西走廊,就是一条在西北大地上奔流的白雪长河,一泻千里。落雪的河西,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河西,是开阔、沉默得让人的呼吸都能长出翅膀来飞翔的河西;而长城,则是这条长河里迎风跃起的巨龙,吟啸如雷。风雪中,一群群没日没夜修筑长城的人,可闻其声又可见其人。一条横贯东西的长城,变成一条横贯东西的人流,轰轰隆隆地在河西大地上涌动。
车过山丹,雪下得纷纷扬扬,车窗外隔一段就有一坨的长城身躯,像极了向西或者向东行进的驼队,似有迎风的咆哮,山呼海啸地涌进我的耳鼓。汉、明长城,就在这里汇聚在一起,极力想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北下的风雪,挡来挡去,就把自己挡成了这样一些思考的模样。
“一条高一截低一截的黄土残垣,像一匹上了年岁的骆驼卧在荒山坡上,向着焉支山方向延伸……”(威廉·林赛《我的长城生活》)在焉支山下,又有一个叫陈淮的人,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老陈当年辞去在兰州的工作,只身来到长城下,一住就是二十年,成为一个不带工资、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长城保护者、研究者。他写过五本关于长城的专著,卖书所得,就是他的生活费。”我一直想寻访马步升老师说的这个“老陈”,但又一直怕打破他在我心里的神圣形象。
跟随老陈《走过长城》的视野,我反反复复地探访着那些不同形状、不同神态的长城遗迹:甘肃的嘉峪关城、明沙窝、双井堡、草沟井堡、胭脂堡、骆驼城、许三湾堡、山丹长城、矗立在龙首山顶的汉烽燧、古定羌庙塘遗址、朱王堡、黄河岸边的松山新边……宁夏的固原秦长城、中卫四方墩、贺兰山麓西北最高大的城墙、营子山上石头垒砌的墙体与黄土长城并行、三关口长城、清水营兴武营的“二道边”长城、高沙窝的“头道边”长城、盐池县长城……陕西的定边县长城、砖井镇古城堡、郝滩乡长城、柳树涧堡、营儿峁、水路畔、新城堡、龙洲堡、靖边墩、黄草坬墩、统万城高大的城墙……
第一次在纸页上看见晋北山地长城的形状时,我对长城的想象被颠覆了。从山西偏关县北部老牛湾一座据黄河而立、与山河呼应的烽火台开始,一连串的堡子和烽火台,穿行在长城沿线的天地之间。“我开车绕行数十公里,终于在日暮时分站在了老牛湾堡遗址,其实出发地就是河汊对面的营盘岭村。”这个老牛湾堡,立于黄河岸上,黄稠的流水,绕过它的身旁,像流逝的时光,又像是与静立的墩台絮絮叨叨的诉说,回放在我的眼前,空蒙而真实……老陈说,有次遇到建筑队在长城底下挖土,他立马上前理论,并叫来了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加以制止。他见不得有人做有损长城的事情,每发朋友圈,必与长城有关。“站在滑石涧堡东望,酸枣洼村南边的山背上,长城蜿蜒穿过”,酸枣洼村南边山背上的长城,蜿蜒多少年了,长着厚厚的绿草,几乎快同庄稼同色,这算不算是长城的新生呢?
堪称晋蒙长城之经典的小元峁长城,把我看得如痴如醉:一座连一座的烽火台,像一排麦草垛,耸立于连绵的山头。最近的一个,伫立在一个圆形的山包上,山上长满细碎的草棵,壁立的山崖将它从底部的山地中凸立出来。墩与山包融为一体,远远望去,像肃北阿克塞华丽的蒙古包,伫立在天地之间,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多重蜿蜒于山岭间的黄土夯墙、间隔稠密的墩台,似天地之间的绝唱,令我震撼而神往。那些山地长城,俨然成为山川田园的生命体,坐落在城墙里的民居房舍,像是长城的子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六百多年前的黄土,覆上一层嫩绿的草,成为人们生活近侧的生命体。从它的身上,除了坚韧不拔,我还看到了生命倔强张扬的形状。
有别于一般人对于长城“高大古老”的刻板印象,在老陈的心里,长城,琐碎而生动,细微而温暖,是生活里的一部分。在附近生活的人们,在长城旁放牧、收割、扬场,他们扬起的麦粒,跟长城一个颜色。长城或穿过耕地,逶迤远去;或守在村头,成为村庄最凝重的表情。长城边,是散落的树,是醉人的野花,是红艳的丹霞,是清澈的碧水,是雪白的羊群,是缭绕着炊烟的村庄……在丹霞山上,长城甚至长成丹霞的一部分,印进了缤纷的色彩。
在辽阔的黄土地上,长城与大地是一个整体,与山河融为一体。那些黍子、青稞、土豆和荞似是从长城里生长出来的植物,长城看着它们一茬一茬地吐穗生长、收割归仓。目光落在纸页上河西走廊的长城上,一抹温暖自心底升起,我经常游走在长城边,已经熟悉它们的气息,就像我生活中的故人。那些“长”在麦田中、山冈上、河岸边、村庄里的土长城,仿佛不是人工修筑的,而是从那些地方长出来的,就是那些地方天然的一部分;它们身上新鲜的草棵,似乎有跟长城同龄的沧桑,给人无言而踏实的亲切之感。
四
河西走廊上的长城,多系黄土夯筑。大雪天的时候,长城内外所有生物都盖着白白的雪被,沉沉地睡着。而长城清醒得像个挥着长竿赶鸭子的老人,左一下,右一下,把雪花赶得里外都是。
我时常憧憬,像威廉·林赛那样,沿着长城做一次徒步行走,没有目的,只是想跟着长城前行;我生活在长城边,时常会去长城边走走,总觉得只要和长城说说话,长城就是活的,就有气息。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像我一样把长城当成自己的一个老朋友,慢慢地,他们的世界就离不开长城了。王金就是其中的代表。王金的人生经历就是拍长城、走长城、修长城。早在1982年,当时在共青团嘉峪关市委工作的王金、杨伟,带着修车工具、药品、地图、罗盘和简单的行装物品,于8月下旬骑自行车自费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开始艰苦的长城旅程。“我们从河北宣化出发,第一天冒雨行至八达岭。天快黑了,只好在桥洞下宿营……”
“9月中旬,我们艰难地行进在陕北高原上。这里的长城大部分已被南移的沙漠吞噬……”“当我们进入甘肃境内的时候,塞上已经很冷了。钱快用完了,炒面吃光了,脚下的凉鞋早已用绳子绑了好几遍,可前面还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但他们相互鼓励着,终于骑车完成了这段最艰苦的旅程,于10月1日胜利返回嘉峪关,途经七个省份四十多个市县。“古代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而长城正是这种智慧和才能的灿烂结晶。”这是他们用四十一天、三百二十多公里的行程换来的真切感受。他们沿途拍摄了四百八十张长城照片,写了七万多字的考察笔记。1983年3月27日,《中国青年报》以大篇幅的版面,对他们的这次考察进行了报道。也许正是骨子里融进了长城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曾是甘肃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探险》杂志编委的王金,穿越过罗布泊荒原、巴丹吉林沙漠,六次从五条不同线路进藏,足迹遍及珠峰北坡、可可西里、阿里等地区,出版过二十多本摄影画册,但他最爱拍的还是长城。他说他从二十多岁时就喜欢上了长城,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又被调到了文化局,主持嘉峪关关城的保护、修复和开发工作十几年。他的每一次行走,都打上了长城坚忍的烙印。现在,年近古稀的王金仍然精神矍铄,仍然经常在长城沿线拍摄,长城,已然融进了他的生命。
沿长城行走,我看到的是前仆后继的灵魂的接续和永生。他们也是落进长城里的雨雪,让长城不断地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