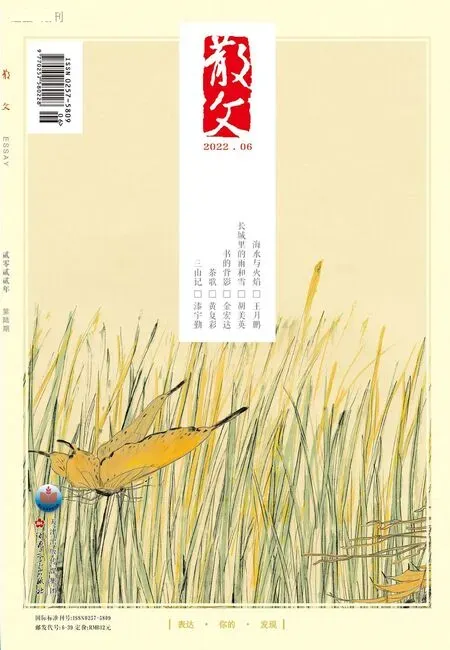海水与火焰
王月鹏
入海口
这是夹河入海口。站在桥上望去,河水与海水似乎并不在同一平面。夹河一路跋涉,沿途吸纳了太多支流,才奔波到这里。鸥鸟在风浪中穿行。滩涂时大时小,有人在挖蛤蜊。他们时而弯腰,时而抬头,像在耕种大海。某一天,大水突至,有人没来得及躲闪,就被冲进了海里。那些面向大海抒情的人,这才意识到,这个叫作“入海口”的地方竟然藏有如此险机。附近海域,若干年前曾发生过一起海难,船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缓缓沉没,那些落水的人,看得见岸边灯火,却无法也无力靠岸。
“入海口”,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他的文字中起初是模糊的,后来渐渐变得清晰,他试图赋予它一种品格,用以承载一些别处无法承载的东西。虽然,他并不确切地知道它能承载一些什么。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才不会干涸。人海之中,他是一滴出走的水。一滴水与另一滴水的相遇,是件难以说清的事。而他的所有努力,都在试图说清这件事,有时超越于意义之上,有时又深陷所谓的意义之中。
黄河路上车来车往。这条海边的路,却是以河命名的。这是入海口。距此百里之外,是黄海与渤海的分界线。能够隔开两个海的,该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那天下雨,他站在夹河桥上,看夹河远道而来,汇入浩荡的大海。雨一直在下,那些雨点落入海中,想必激起了若干涟漪,它们很快就被更大的水和更多的涟漪吞没。他站在桥上,俯瞰入海口,不知道是心中装下了这水,还是一颗心被这水淹没。时光变得恍惚。雨在不停地下,就像那些陈年往事。
他洞悉了入海口的秘密,却从未说出口。
给鱼留路
磨坊水坝,阻断了鱼群的路。
苏格兰于是颁布了一道法令,所有的磨坊水坝都必须留下足够大的开口,好让鱼通过。这道苏格兰法令是在1214年颁布的,距今已八百多年了。这期间,太多貌似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已烟消云散,“给鱼留路”这个细节却留了下来。我们常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其实海已经不是那个海,天也不是那个天了。不管海里还是天上,“网”无处不在。在海边,我经常看到有人在一条小河入海的地方撒网,想到那些向往大海的鱼,却在入海口扑入了网中,不禁心生悲悯。
那个撒网的人站在海边,像是一道峭壁。
这里的海岸极为平缓,没有峭壁,也见不到乱石,我总觉得这是一种遗憾。想象别处的峭壁巉岩,临海而立,海浪一次次涌来,然后被峭壁弹回,成为一道飞溅的风景。在阻与被阻之间,所谓的“美”出现了。浪涛把阻遏自己的巉岩分解成了若干石块,这些石块被海浪推着来回滚动,最终变为鹅卵石的形状。当我手摸光滑的鹅卵石,内心却是桀骜不驯。峭壁下的这方海域,曾经乱石滚动,犹似战争,海里的生物和鱼类不得安宁,要么消亡,要么逃离此地。我们所看到的,仅是宁静的海滩,洁净的鹅卵石,其间的过程都被略过了。那个黄昏,我从海边带回一块鹅卵石,摆在书桌上,伏案写作的时候,眼前常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幻觉。
有些时候,我把那幢临海的楼房视作所谓“峭壁”,想象乱石滚动,虚构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然后我到海滩上试着察看鹅卵石,却始终没有见到。海滩上,有人在徘徊,有人在用手电寻找沙蟹,一束光不时在海面晃动,把海浪分割成了千万份。
海中的“峭壁”随处可见,比如流网。这种网被置于水中,呈墙状,随水流漂移,把游动的鱼挂住或缠住。有专家认为,中世纪海洋渔业的兴起与“流网”的发明有关,这种网就像是浮在水中的一道墙,可以截获鱼群。
从网上摘鱼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网里的鱼再多,渔民也不会嫌麻烦,想想也是,还有比下海更麻烦的事吗?他起初从网上摘鱼时心里是有些急的,是那种按捺不住的急,后来就不急了。鱼进了网,上了船,一般就可以放心了。从网上摘下来的鱼,被丢在船舱,鱼尾击打船板的声音,白花花响作一片。
鱼缸是另一种墙。鱼在缸里游动,看上去自由无拘,整个家也有了动感。猫在鱼缸旁边玩耍,时常与缸里的鱼对视。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它们一定是说了些什么的。我时常喂猫一种精致的小鱼干,猫对此似乎并没有热情,甚至有些抵制。在渔村,人们会把吃不完的鱼晒成鱼干,挂到屋檐下,用网兜套住,显然是防备馋嘴的猫。猫瞅着网兜里的鱼干,目光温和,有些不解。很多时候,人是被自己编织的网所缚住的。
防护林
在这个城市与大海之间有一道防护林。许是因为树木长得参差不齐,我曾以为它们是野生的,后来才知,这是几代人种下的林子。这片盐碱地上散落着十四个村庄,风从海上来,时常卷起漫天黄沙。
他们种下的这些树,以槐树居多。每年到了五月,海浪声中弥漫着槐花的香气。养蜂人从远方赶来,率领万千蜜蜂,就像一个人指挥着千军万马,在防护林里奔突。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养蜂人。槐花依旧,开了一年又一年。大海依旧,海岸依然保持了平缓的样子。脚踩细沙,想到曾经的巉岩巨石,有一种时光感。抬头看海,海天一色,看不到彼岸。退潮后,海岸重新裸露出来,它已被大海赋予一些新的内容;也有一些东西,被大海遗落在了沙滩上。在海浪的巨大徘徊中,唯有海岸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有一天,我一个人在海边,看海天迷蒙处,突然就听出了海浪的节奏。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给大海把脉的人,从潮汐中辨出了来自彼岸的声音。这是大海的密语,它让我突然理解了身后的这座城市,理解了大海尽头那个看不见的地方,也理解了我自己。
想到那些记录于生死之间的航海日志,它们简洁、残缺,是最神秘的也是最珍贵的文字。正是那些亲身的经历、残缺的记载,拼接出了一份关于海的“认知”。他们的船,按照他们所发现的规律,在海上行驶。对于浩浩荡荡的波涛而言,岛屿、海岬,甚至也包括海岸,都是障碍。那些从山上跌落的水,因为急遽注入大海而产生的冲击力,让浪涛变得不再规则。船在其间穿行,很容易就被淹没。抑或,在人类所设定的航线里,一个浪头从侧面打来,船可能就沉没了。
海上看雨。海浪涌动,跟雨帘交织成了若干的“点”,我觉得我所在的船,恰与那些“点”是重合的。这不是发现,是想象。这样的想象让我心生恐惧,觉得大海更加变幻莫测了。
下雪时是另一种感觉。那个风雪之夜,我在楼上的窗口看到那海似乎要被雪填满了。海面与天空之间积满了来不及融化的雪,渐渐堆垒成一座山,向岸边移动。风卷动着浪,浪携带了风,固执地拍打岸边。往日那些面朝大海抒情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愤怒的海,还有拒绝融化的冰。天亮了,海边一片狼藉,浪把岸边的石头都拍碎了。而防护林依然保持了原来的样子,狂野的海风,没能彻底穿越它们。我似乎理解了这片防护林的意义。
更多的时候,临海的那扇窗是洁净的,大海看上去纤尘不染。一束花,插在窗前的花瓶里。金色阳光落在藤椅上。在花瓶里的花与大海的风浪之间,隔着一层玻璃。这个简单的场景,总让我想到那些更为复杂的人与事。可以不在意海上升起的一轮明月,最深刻的思念并不需要借助外在的事物来寄托;可以忽略海上的风与浪,淡忘风浪里的远航,一叶小舟停泊在心港,它惦念着别人看不到的那个彼岸;可以面向大海,忘记你的名字,忘记了来时的道路……只是,不该在窗口挂起帘子。这样的窗口,向着天空和大海敞开,不需要任何的遮掩。
窗户对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地图。我曾无数次站在地图前,目光随着手指越过千山万水,抵达一个又一个期待中的城市。然后,我累了,坐到藤椅上,背靠着窗口。窗外是海。这面阳光照不到的墙壁上挂满了涛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面墙,就像站立起来的海,那个难眠的人成为一枚被海遗忘了的贝壳。想象海上巨大的浮冰,宛若一座移动的岛屿,它的断裂和融化,在海上引起风暴。我们愿意把大海比作母亲,恰是因为无论怎样的风暴,都不可抵达和动摇大海的深处,很多生物是在那里孕育的。
风浪之下,是一方安宁的空间。
一片防护林,隔开了大海与村庄。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我的所谓阅读与书写,其实都是为了构筑这样的一道精神“防护林”。自我的主体性,倘若不能有效建构起来,就很难抵御外界的侵扰。那片防护林一直在,它已超越了功能与审美的意义。
与一艘老船合影
沙滩上有一艘老船。我走过去,请朋友为我和老船合影。
人来人往。他们只是看到了大海。不曾亲历海上风浪的人,不要说懂得大海。这艘被废弃的老船,它沉默着。透过破漏的船体,我试着去看不远处的城市,那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一个变得有些模糊了的所在。我从那里走出,终将回归那里。就像这艘残船,正在一点点把自己归还大海,它是海的一部分,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这艘老船,成为海边的一道风景。我没有觉得它是风景,我只是觉得自己遇到了另一个自己。海还是那个海,是我们共同的背景。一些风浪从破损的船体中释放出来。这艘船走过的路,写在风浪里,也被风浪抹去。风浪是一只神奇的手,它挽留一些东西,也拒绝一些东西。在大海面前,人们往往只愿理解一朵浪花、一个贝壳、一只飞翔的海鸥。海成为这些事物的背景。作为背景的海,是被真正理解了的海吗?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浪花,不见大海。想到那些写作的人,他们笔下倘若缺少了一种作为背景的“整体感”,那些碎片,也就只能是碎片了。
一棵树,在山中成长,然后被砍伐做船,行于水上。船体在风浪中日渐朽掉,最后在火中化为灰烬,成为土的一部分,成为另一些树的养分。一艘又一艘的船,驶向大海。波浪与波浪之间闪烁的光,犹似利斧的锋刃。一棵树的不同的生命形态,在某个时刻交织到了一起,并且被我发现。
海是包容一切的,包容它所喜欢的,也包容它所不喜欢的。这世间的所有困惑,海都以自己的方式给出了解答。懂了的人,自然是懂的;不懂的人,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
这艘废弃的老船,其实一直在讲述。而他们以为它是沉默着的。
船已老去,而海仍年轻。一艘老船的孤独,不在于海浪的巨大徘徊,而在于一个人的渐行渐远。那个人的背影,带走了那些风浪里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