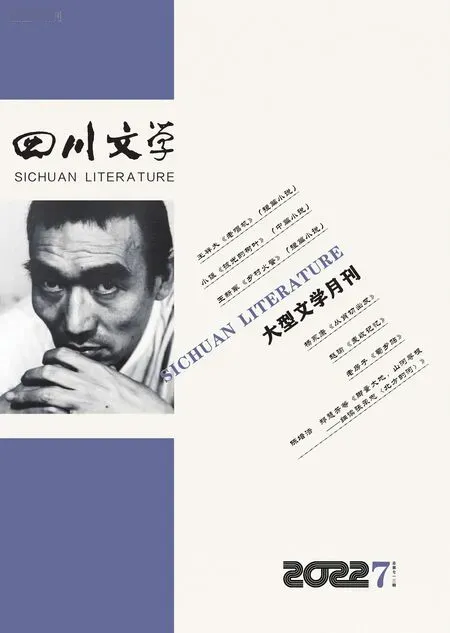锦城夜雨
□文/杜阳林
成都的雨夜,适合思接千载心游万仞,酣眠似乎成为一种浪费。而我对这座常有夜雨的城市,更喜欢她另一个别名——锦城。
锦城自古养蚕业发达,古蜀王名为“蚕丛”,西汉扬雄在《成都赋》中也称成都为“锦官城”。东汉时期,蜀锦是当时成都的支柱产业,朝廷在这里配置了专门管理这一产业的锦官。蜀锦畅销全国,成为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于是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或“锦城”。
锦,意识中与之成词的大多是让人沉醉的美好事物,比如锦缎、锦绣、锦书、锦心,锦上添花、繁花似锦、锦囊妙计、锦绣前程……念及这个锦字,我的舌尖便仿佛噙着一片桑叶,暗自生香,绸般丝滑,清新怡人。但向来的认知,“锦”既是娇嫩华贵的,也是柔弱至极的,它不是勇猛大汉手中挥舞的流星锤,而是二八佳人纤手轻执的檀香扇。成都既然自古被称为“锦城”,她是如何从内里生长出这种风流婉约气质,来堪堪匹配这个“锦”字的呢?
地理上看,成都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适于种桑养蚕。早在商周之时,古蜀先民就在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丝绸文明,并由此开拓了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通道南方丝绸之路,使绚丽多彩的丝绸享誉中外。汉唐以蜀锦、蜀绣为代表的成都纺织业,号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旅行来到成都,赞叹这里是“锦绣之都”。遥想那历史气象,锦之城,丽之都,顿觉熠熠生辉。
李白曾歌咏“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读此瞬间觉得满目锦绣,纯真自然,尤其这个“锦”字,立时仿佛整个成都都流光溢彩,随处都是风景。而若深究“九天”是如何“开出一成都”,就会发现,成都的出现,是造物主的恩赐,是大自然的杰作,似险峭悬崖上开出的一朵绝世雪莲。
当沧海变成桑田,大海退去波涛,成都平原周围的大山渐渐隆地而起。放逐于漫漫历史长河去追寻,海山之变,有多么惊心动魄,就有多少爱恨纠葛。当成都所有的创痛随风而去,她用崭新的形貌,来默默承载当下的褒贬。
我瞬间明白,锦城的夜雨,其实来源于一场天际的奔赴和邂逅。
白天的锦城,空气潮湿,云层挡住了部分太阳的辐射,云上和云下的气温不会相差太多。到了夜里,云层以逆辐射的方式,给地面输送热量,云层出现上冷下暖的现象。偏热的潮湿空气上升,遇到冷空气,冷凝成小水滴,但小水滴聚集成大水滴,就会从云层中掉落地面,便形成了雨水。
如果以浪漫之心来解读,锦城上空的云,既矜持又热情。白天她文静安然,宠辱不惊,一派平和,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揣着热切而雀跃的念头上升,再上升,仿佛要将一腔话语向星星和月亮倾诉,让心思变成欢愉的雨水,抛洒人间。夜雨洗尘,花木皆精神,给锦城带来了空灵之气,芬芳有加,娇颜顾盼,似乎经历了一场大自然的约会。
杜甫在《水槛遣心》中写道:“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一句“蜀天常夜雨”,代表着久久不歇,淅淅沥沥,多少缠绵悱恻,多少此情此景,都在这短短一句话里,有了景的动态,也有了情的波澜。杜甫抒发这样的情感,将空间和时间融为一体,将所见和所思熔于一炉,皆因蜀雨一落就是数日连绵,弦歌不断,在成都的天空之下,“雨夜”成为一种“常见之态”。
成都平原地势平坦,越是往西,海拔越高。由于地势起伏颇大,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携带暖湿气流,与来自西部高原上的冷空气在此交汇相遇。落差极大的地形,阻挡了暖湿气流前进的步伐,水汽被迫抬升,使得成都平原降水量十分丰富,被称为独特的“华西雨屏带”。
“交汇”二字,无论天文还是地理,抑或几千年来锦城这座城市的人文气质,都格外看重。它是气流的交汇、空气的交汇,同样也是人与锦城的交汇。相逢相依,尔后汇融,无数传奇在锦城上演,历史的笔触在云淡风轻之间,已汇就了传世的名章和诗篇。
我喜欢锦城夜雨落地的声响。窗外雨水无尽,夜空格外缠绵轻柔,雨雾和灯光相裹。房前的芙蓉和紫薇,银杏和梧桐,洋槐和香樟,水杉和雪松,罗汉松和黄葛树,广玉兰和悬铃木,无分你我,都会浸润在朦胧的雨夜。雨丝从天而降,从枝叶树茎,流淌历朝历代的文人佳句。苍苍莽莽的世界,古与今不再重要,当下和往昔一舟飞渡。
一滴水来自天上,一滴水坠向人间,一场雨浇湿唐砖汉瓦,一场雨冲淋高楼大厦。夜雨,锦城四季轮换,春秋交替,时光笃定了性子,稳稳朝前行走,绵绵雨丝或烈烈雨柱,也循了自然的规律,该洒时洒,该落时落。我不禁揣测,倘若没了这从古到今的夜雨,锦城还是那个锦城吗?带着湿漉漉的深情,浸着三千年的诗意,在砖瓦木石之中,成都还能生长出另一种灵秀出尘的轮廓和肌理吗?
一场春雨在夜间飘散,清晨才止歇脚步,在那个乍暖还寒时分,我走进了浣花溪的杜甫草堂。脚下的石板像吸饱了墨汁的宣纸,湿得恰到好处,黑的路白的天,终究不是寡淡的水墨画,竹篱笆的迎春兀自金黄,月季也依旧嫣红。靠近这里的茅屋,我眼前仿佛浮现了杜甫的背影,他就在蒙蒙雨雾中穿行,灰衫旧袍,踽踽独行。踏着春雨的湿痕而来,我就是为赴一场隔世的崇敬之约。
沐浴过夜雨的草堂,薄薄的水气,氤氲出一个久远荡而动的时代。顶戴雨珠的小草摇摇摆摆,大唐的高楼倾了,庙堂散了,宝座上的巍巍帝君早已剩下一把白骨,而诗句还在流淌,还在生长,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一种顽强而永恒的存在。我踏着昨晚的雨痕,萦绕于心的却是大唐千年不散的诗篇。
当诗圣杜甫辗转入川时,已人到中年。可他笔下所书写的锦城夜雨,却大有青春气息,诗作诞生的奥秘,和实际年龄无关,与心理年龄有关。此时的杜甫,多年漂泊,四下流徙,终究一家大小能在成都团聚,妻儿绕膝,家人有了一处安身立命的草堂,无论富贵或贫瘠,那都是杜甫珍爱的家。睡在自己家中,夜雨落下的感觉真好,有屋檐遮头,有寒室栖身,曾经的浪漫因子,在悲苦吟哦的诗人心中复活。他并非不懂得浪漫,不懂得审美,而是生活极少为他创造相宜的机会。感谢成都,容留了一个风尘仆仆的诗人,也用一场春天的夜雨,滋润出一派天真纯粹的喜意。锦城夜雨,是杜甫安定生活的鲜明注脚,每个毛孔都书写着他对当下的满足和惬意。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勾起杜甫喜悦之情的夜雨,她更像是梦之精灵,周身澄澈通透,只闪烁一点鱼鳞般的水光,在锦城的街巷游走,洗琉璃瓦之尘,拂青石路之灰。即使侧耳去听,也难以捕捉她洒向地面的声音,她灵动活泼,脚步轻巧细碎,一个“潜”,一个“润”,实在是神来之笔。
在杜甫离开一千多年后,我离川读书,又回川工作,如今在成都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刚到成都,惊讶于这里春雨的“含蓄”与“体贴”,像是含羞带怯的深闺女子,轻易不肯见人,非要等到夜里,雨丝才如绣花针一般,轻轻飘静静舞,在清寂寥廓的空间,尽情抒发自己的喜悦。加班晚归的路上,遇到这样的雨,都不用打伞,任由她清凉多情地柔抚,抚过夜行人的衣衫,在发梢缀上晶莹的雨珠。橘色路灯的光,映亮了纷飞的细雨,如同细末盐粒,没有雨的凌厉,只见水的温柔。
那一刻,我骤然懂得了千年前的杜甫,懂得了他的欢喜,也懂得他清晨望见“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盛大喜悦。若没有这漫不经心的春雨细抚,又哪有“红湿处”,引人看雨后之花,花瓣洁净无尘,草叶精神抖擞,更显千娇百媚。不用说,待到晨曦微露,“晓看”之时,千年前和千年后的夜雨都不见踪迹,空气如洗,天地间到处都有“好雨”来过的痕迹,却难以见到她的真容实貌。
锦城春天的夜雨,我感觉总有一种滞后与延宕的戏剧效果,她的出现和别离、到来和散场,都是寂静的。恰恰是这份静,让人魂牵梦萦,让人心生怜爱,更加认定她是锦城春季缺不了的“女角”,唱着一首无字的歌,也能激发诗人无限的情愫。
夜雨和杜甫相逢,将年轻还给他,将欣喜还给他,让他在一夜好梦之后,惊讶于花叶清雅的眼前盛景。雨虽停了,薄雾未散,万物得以沐洗滋养,蓬勃生机,诗人也在刹那感受到了内心欢愉的力量。这力量和他泣血摧肝地吟老兵、唱征夫、哀流民不太一样,这是另一种美,自然而纯粹,剔透而纯真,让他暂时忘记了世间的苦难深重、哀鸿遍野。夜雨似乎是无情的,她并没有与百姓血泪混流一处,也没有故作时代的大悲之音,她就这样安静地出场,淡然地落幕。她的清淡内敛,却又是最大的怜悯,帮助一个诗人找回内心蛰伏的浪漫温柔,也用亘古不变的从容,夜夜叩访,将锦城浴洗一新。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这句出自汉代《说苑》的成语,背后藏着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的深刻喟叹:如果我不能像春风一样温暖人,像夏雨一样滋润人,那么处于困境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了。
倘若“天街小雨润如酥”说的是“春雨贵如油”,到了夏雨,便是一种“重”。是重要,亦是浑厚,象征着生命必不可少的“滋润”。
锦城不是火炉,但一到夏季依然酷热,如果在备受烈日炙烤的绿色植物上扔一根火柴,可能就会噼噼剥剥地燃烧起来。日头挤干了植物身体的水分,它们的生命,压迫成一张张苍白的纸。
人们汗水淋漓,就像一丛焦虑的灌木,渴望一场雨。甘霖的滋养,成为一切生命迫切的等待。
锦城夏日的夜雨,在人们的期盼中,伴随闪电撕裂黑色幕布,不打招呼说来就来,让凉爽的夏风吹拂人间。
在雨声中安静躺卧,我需要的正是这种酣畅的痛快。窗外雨水尽情倾泻洒落,闷热压抑之感顿觉消失。苏轼写夏季暴雨,声势浩大,磅礴如斯:“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回味东坡诗词,仿佛目见其景。即便此刻我躺在夜色之中,也能与诗人眼中的浩荡暴雨达到共鸣。
锦城夏季的夜雨到来之前,闪电雷声在天际爆开,雨柱银白,雨雾缭绕,挥散不开。狂风骤雨如万马奔驰,铁蹄踏踏,对饱受酷热折磨的人而言,仿若天外佳音,送来平和静怡。
夏日夜雨不是都会挟裹雷霆万钧而来,也有缓缓而至的时候。欧阳修也曾写过轻柔之夏雨:“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柳林外,传来轻响的雷声,池塘上细雨绵绵,雨水滴落,在荷叶上发出细碎的声音。锦城夏日的夜雨,也有欧阳修笔下珠落玉盘的意境,清扫炎夏燥热烦忧,格外惹人怜惜。此情此景,颇似江南梅子雨,搅动人们的柔肠万缕,正如赵师秀诗中所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夏雨的体内,蕴藏的不仅仅是电闪雷鸣,是恣肆磅礴,亦有绵绵不绝的诗意,生生不息,屋外雨滴叩击池塘,蛙声一片,屋内走棋轻震灯花,子落棋盘的声响与雨声相呼相应。
锦城的夜如帷幕,落下的雨滴不再是雨水,而是永恒的思绪。嬗变的时光行走雨帘之中,渐渐褪去外壳,袒露出柔软的底色,千年光阴自在流淌,好像手中持了雨的密信,大可一朝飞渡,去感知大宋年间的“天外黑风”或者“柳外轻雷”。摇曳多姿的雨,惊艳了泛黄的卷册,一场文学与审美的雨,下得缱绻多姿,为历史留下一页微凉而潮湿的痕迹。
锦城夜雨百变多面,热情如她,矜持亦如她。可不管它是气壮山河而来,还是轻叩屋檐而至,都能带给人间滋养和润泽,洗去尘埃碎屑,应和人们的期望,带来一个清爽的世界。
一层秋雨一层凉,锦城秋雨缠绵,人们忍不住添加衣服。道路旁边种植的芙蓉树,经过秋雨清洗,花瓣琉璃薄脆,如美玉明净,坠留的雨滴,带着惆怅的情思,将落未落。
入夜时分,夜雨如倾如诉再度飘零。
雨点落在屋瓦、窗棂、台阶,也落向草尖、树叶、花瓣。夜雨如同身形苗条的舞姬,踮着足尖翩翩起舞。她与春雨既相似,又不同,都一样纤细清丽,柔若无骨,润物无声。若春雨是丝缕流苏,秋雨就是拂尘无色,安静与安静之间,清瘦与清瘦之间,有微末的差异,有情绪的起伏,都是蜿蜒荡开了一个季节的序曲。秋天的夜雨以落叶为背景,以枯枝为基调,是一种略显粗莽的抚摸,是一声略带哀婉的喟叹,也会带来生命深处的战栗和疼痛。但唯有痛,才让人更加感知四季变换,更迭不休,这时的夜雨也就有了铮铮铁骨,有了一番倔强意气。
夜里雨声叩窗,我从书房望向窗外。夜色深沉,淅沥有声,而我检视飘落锦城的秋雨,手中握住的这点苍凉与温暖,心中惊起的微微涟漪,已跨越了诗词的荏苒时光,在美学的时空浮荡。
清朝著名的佳公子纳兰性德曾写《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锦城这个季节的芙蓉,于秋雨中早已舒展,娇肢弱躯,仿佛无力承受冷雨凉风,一夜连着一夜,秋雨不歇,仿佛没个尽处,漫不经心之间,赋芙蓉冰肌雪骨。我不知道花朵是否也曾在雨中暗泣,怨恨世上所谓的怜香惜玉,不过是说说而已。夜雨并不因为怜悯自己而少落一滴,却又因为雨的洗涤,芙蓉才会变得焕然一新,娇俏动人,幽幽花香与雨水微寒交织一处,明早不知是怎样一种冰清玉洁的景象。它盛开凋落,正如我们的生活,总要历经过曲曲折折的漫长道路,总要体味过寒凉加身的刻骨铭心,才叫一个完整。
别人都道秋雨无情,而我却认为,秋雨和秋芙蓉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在夜里让清冷遇见了清冷,寂寞叠加了寂寞。如此想来,真让人心生怜惜,又不乏敬畏,仿佛是从一派冷意中生长出来的禅意,铺排了倔强的风景。窗外雨丝成线,是金钩铁画一般的瘦骨嶙峋,好像行草的流利,在锦城平平仄仄的夜里,更添一份书香墨韵。我久久凝望,舍不得动弹半分,真想将那些愁情别绪,敲打成潇洒的走笔。
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曾在《九月末风雨初寒二首》中写道:“老肌畏寒苦,幸此手足温”。秋雨淅沥,我想,是谁最先有所感应呢?也许是触动了“老怀”之人,已经在世间走过半生,有所过往和阅历,才会为清冷秋季的夜雨着迷,身体长出敏锐的触须,看过春雨的绵绵多情,听过夏雨的雷霆万钧。现在,愿意一边忍受“秋雨生凉,老肌畏寒”的苦楚,一边打捞生活中的点滴诗意。
我忽然明白,真的要走过这漫漫岁月,才会懂得夜雨之美,看昏黄路灯,构建一个寒素的舞台,简朴却不失诗意。院内的灯光,映衬得雨丝纷飞,从光亮中伸出无数双手,抚摸锦城千百年的容颜,温柔而执着,要将时间滞留的尘灰全都抹去。锦城夜雨,才能敲打窗棂,这份清脆的声响,也就成了我行至中年的淡淡梵音。
锦城秋日的夜雨初歇,早晨的路面铺上金黄的银杏落叶,像一枚枚岁月遗落的书签,像一行行妙笔写就的诗句。她们曾在雨中如何蹁跹如何旋舞,如何灿烂如何凋零,终究成为不可考的秘密,但一个季节的背影,就这样被时光的变迁遗忘。
曾经宦居锦城的陆游,听过无数次冬雨绵密。他熟悉那样的声响、那样的节奏,在雨夜做梦,也许还握着一柄宝刀,踌躇满志,豪情万顷。“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此刻,诗人是宝刀,犹如夜雨是战曲,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刀锋刺穿雨帘,珠玉溅落,好一个快意人间。
到了“僵卧孤村”的晚年,陆游在风雨冬夜中勉强睡着了,梦却不是美梦,是自己孤身一人,骑着铁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
我暗自思忖,“孤村”不是锦城,如果能让晚年的陆游自行选择,他也许更愿意在锦城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夜空在我的记忆中撕开一道道口子,雨线带着冰雪凛然的寒意,飘飘洒洒,如清亮的钉子,无悔无怨地锲入大地。夜雨不疾不徐,不像春雨那般细柔,不似夏雨那么暴烈,没有秋雨那么凄寒,带着一点看过季节变换、如今已有宠辱不惊的念头。冬日夜雨平静而从容,犹如一个老人,腿脚不如年轻时轻便,但拄着拐杖,依旧能将脚下每一步走得扎实稳妥。
更何况,成都的冬天,还有让放翁迷恋不已的梅花。陆游曾说:疏梅已报先春信,小雨初成十月寒。
就因这一场场雨水的滋养,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对锦城流连忘返,沉醉抒怀。
我想,下雨怕什么,岁暮始寒又怕什么呢?稀稀疏疏的梅花已在枝头绽放,梅已开,春天还会远吗?陆游是乐观的、积极的、豁达的,纵然受多少打击和挫败,但内心始终拥有一种打不垮压不弯的力量。夜雨簌簌而落,恐怕还会给梅花添了别样的冷香。
前几天的一个傍晚,锦城依然细雨翻飞。我坐车回家途中,视线透过车窗,与夜雨中傲然挺立的梅树相触相接。那些从枝头从花瓣不紧不慢坠落的雨滴,是轻盈的,自有一种内在的活泼音韵,并不一味堕入哀痛沉沦不起。锦城冬日的夜雨,是一首舒缓慢板的歌,像是给一生的奔波劳碌写下注解,不是为了让人心酸,恰恰相反,是教人释然。雨脚慢慢行,我就缓缓听,屈起指头,为这乐音配一点伴奏,内心绷紧的弦线,渐渐放松。
我躺在床上,俗世烦事,沉沉如铅,依然难以入眠。窗外夜雨飘散,冬日树枝清瘦,没有初夏雨打芭蕉的声音,没有你来我往热切交流的接纳,冬雨也就遇不见宽阔肥沉的枝叶,但却敲击出了空旷的骨感回音。
我翻身起床,在书房打开电脑,翻看还未结束的文稿。窗外的冬雨正以透明之身,与树上枯枝反复缠斗,瞬间坠地散弭。我忽然生发一份悲凉,夜雨在清冷之中,多了一份命运的无可奈何。纵然是这样,雨还是依着自己节奏落下,不曾抢一步,也不曾快一秒。
我点上一支香烟来到窗边。此时的夜雨通透而敞亮地拥抱人间万物,张开的双臂,收获的都是空空怀抱,但雨还是要落下,还是要一次次去面对新的相遇和接触,无奈和消逝。夜雨将心中结冰的泪化成了水,在自然的宿命中,谁都是过客,无力挽住光阴,不能改写既定的命运。也许,守护内心的温暖,放开那份伤感,是我最好的选择。
这个雨夜,让我眼角逐渐潮湿。
到底是谁在天上操控了雨,我不再去思考。但命运的巨手,让人世的这场雨,从诗意走到了哲理,从白霜覆瓦走到了桃红柳绿,又从三月景明走到了料峭寒冬。经历甘苦聚散,见证繁华沧桑,让夜雨和岁月一并去积淀和打磨,化为我与锦城深刻的血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