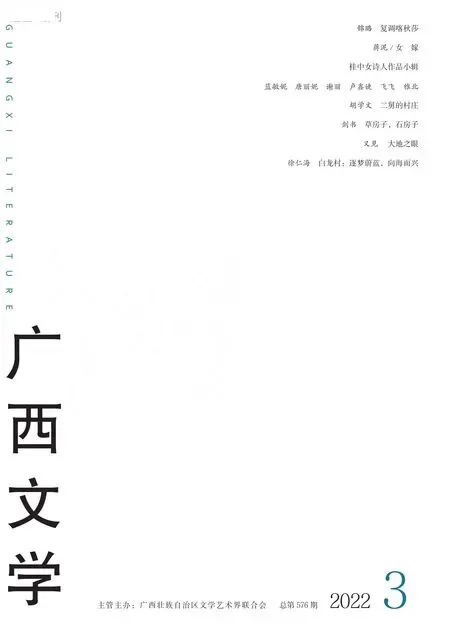曹铁山小小说二题
曹铁山
二舅是一盏灯
记得小时候,有天晚上在家门口玩耍时,忽然看见一只会行走的灯笼向我晃悠晃悠走来。
灯笼不大,桶状,好像一个西葫芦。灯笼离地面一尺多高,忽忽悠悠,不紧不慢。我知道灯笼自己是不会行走的,定是有人提着灯笼在行走。待灯笼到近前时,才发现原来是二舅一手点着盲杖,一手提着灯笼朝我家走来。我停止了玩耍,接过二舅手中的灯笼,牵着二舅手中的盲杖把二舅领到家里。
二舅可忙了,整天走东串西,靠一把三弦说书,靠一根笛子算命,据说收入颇丰,比心明眼亮的父亲还能挣钱。
二舅每次来我家都会住几天,不是他要住,是别人留他住。白天,常有人来找二舅偷偷算命,算一命五毛钱,谁都算得起。二舅算命有个特点,最后总会让人看到一线希望。有时也有人找二舅查订婚结婚的日子,查日子虽然不收钱,却要讨喜钱,喜钱多少没定数,所以来我家找二舅的人就多。到了晚上,二舅则更忙了,会被这个生产队请走,会被那个生产队请走,让二舅给说书。二舅消瘦,肚子不大,肚里却装着很多很多书。像岳飞的书、老杨家的书、老包的书,估计有一车书吧,好像一生都说不完。二舅说书当然不是白说,是包场,一晚上两块钱,由生产队支付。那时没有文化娱乐活动,除了那几部翻来覆去的电影,再无其他热闹。生产队长说说书是寓教于乐,名正言顺就能下账。还轮流管饭,把二舅最主要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了。
虽然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孩童,却也是生产队半个劳动力了。我给生产队放牛,大人挣十分工,我挣七分工。因为有我挣工分了,我家从此也成余钱户了。可母亲却还是忧愁,忧愁我该是上学读书的年纪,却劳动了。
一天中午吃完饭,趁着没人来找二舅算命,母亲说二舅,给你外甥也算算吧,看看他将来命运如何。
因为二舅常上我家来,我辍学的事情和放牛挣工分的事情,还有平时喜欢看书的习惯二舅都有所耳闻。二舅向母亲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双手十个指头一阵乱动,滴哩得嘞说了一大串子丑卯酉我听不懂的算命术语后,二舅说,从卦象上看,外甥的命运不赖呢,有官命呢。母亲就笑笑,你外甥是有官命,现在放牛呢,是牛倌儿。二舅就让母亲别打岔,说从卦象上看,外甥真的有官运呢。母亲说,将来那是当生产队长了?二舅说,生产队长不是官。母亲说,那是大队民兵连长啥的了?二舅龇牙笑了下说,比大队民兵连长官还大。母亲就惊讶,那就是公社干部啦,那就是吃“皇粮”啦?二舅说,从卦象上看,外甥将来就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母亲就苦笑,若是将来能当公社干部,那敢情好,可是,公社一级干部都是有文化的,你外甥才小学四年级呀!二舅说,所以得继续念书呀!母亲叹息一声说,念不起呀!二舅说,念不起就自学,过去也有很多自学成才后来奔大前途的人呢,像凿壁偷光看书的,像囊萤映雪学文化的,最后都成了有才之人。二舅又把脸转向我说,外甥,你一定要争气呀!
二舅的话我记在了心里,我虽然退学了,虽然当牛倌儿放牛了,每天放牛时,却仍然背着书包,书包里装着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语文课本,牛啃草时,我就啃书。我拼音基础好,课文课本里的生字都标有拼音。我记忆力也好,拼过两遍,就记在了心里。四年的放牛生涯中,我不但自学了初小、高小的语文课,还阅读了当时热门的《金光大道》《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几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再后来,一些禁书也逐渐开放了,我通读了《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战争题材的长篇巨著。其间,还借着“批《水浒》运动”,通读了《水浒传》。再后来,把《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都通读了个遍。当然是磕磕绊绊地读,老书都是竖排版、繁体字,我是借助字典读完的。
有了读书的基础,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小说来,写起散文和通讯报道来,还花八分钱的邮票寄了出去。有的短小说和通讯报道在地市报纸上登了出来,新闻稿在电台上播了出来,我竟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
1983年,全国各公社都成立文化站,我很荣幸被招入了,真的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公社干部了。
一天晚上,二舅又提着灯笼来到我家,母亲把我参加工作的消息当作喜讯说给了二舅,说二舅算卦算得真准!二舅高兴地说,不是他算得准,是外甥努力自学的结果。
我是很感激二舅的,是二舅给我心里点了一盏灯,我才暗下决心自学文化,自学成才参加了工作,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
二舅在我家待了几天,走时我送二舅到村口。我把灯笼递到二舅手上时,向二舅问了一个问题,二舅,您走夜路打灯笼,您也看不到光亮呀。二舅笑笑说,我是看不见光亮,可是别人能看见光亮呀!我还是不解,别人看见光亮,对您有作用吗?二舅并不直接回答我,说,你已是个文化干部了,其中的奥妙,你自己慢慢琢磨吧。
二舅走远了。夜幕里,二舅提着一盏灯笼在夜路上闪烁。
看灯火
1975年的腊月二十八这天下午,我们滦河湾公社半山腰生产队迎来了两件大喜事,一件是生产队开支了,一件是生产队分肉了。上午,我们半山腰生产队的社员们还在愁眉苦脸,心想着这个年咋个过法,下午人们的脸上就彩旗一样挂上了喜色。
开支、分肉同步进行,应了喜事成双那句吉祥话。开支是在生产队队部的炕上,放着那张生产队会计专用的小方桌。小方桌周边,盘腿坐着生产队会计、现金保管、信用社主任三位“财神”。会计眼睛盯着名册念花名,念到谁,谁就侧棱着肩膀挤到前面,在名册上签字、摁手印。信用社主任就按照签字按手印的金额手指蘸着唾沫数钱,然后再交给现金保管。现金保管再数一遍,转手交给名册上刚才应声签字摁手印领钱的那个人。
开支之所以要信用社主任到场,是因为开支的钱是从信用社贷的款,钱是由信用社主任胳肢窝夹着黑皮革兜子送来的。还有,信用社主任有动员社员存钱的任务,每年都是这样,现场办公开存折。
今年,信用社主任却是白费唾沫了。信用社主任还算有自知之明,也没有一而再动员,只是例行公事问上一句,存钱不?却招来社员一眼一眼的白眼。现金保管没心没肺爱逗吸溜,把钱递到社员手上时,会面带笑容宽慰一句,困难是暂时的,以后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开支,实际上是借支。今年大旱,粮食歉收,果园的苹果先是着了虫,后又遭了雹,等于有支出没收入。抗旱时用工多了,粮食又减产,劳动日值险些成了负数,秋后一结算,家家都成了缺钱户。大河无水小河干,过年了,社员们都大眼儿瞪着小眼儿瞅队长,盼望着队长想办法弄钱过年。
多亏上级体恤社员,给生产队长下了严指示,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得想办法给社员开钱过年,也得想办法让社员吃上肉。无可奈何,生产队长就从信用社贷了款,每户每人借支一元钱。一人一元钱好干啥呀?队长又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把磨道上拉磨的一头老驴杀了,给社员每人分了一斤驴肉。
我家四口人,生产队给借支四元钱,分了四斤驴肉。晚上吃完饭,父亲母亲开始安排过年一应事项。因为我是家中唯一有文化的人,已经十二岁了,上小学三年级,父亲母亲就也让我参与,他们说,我拿铅笔记。虽然父亲是一家之主,家里内务事情却是母亲做主,父亲只管点头和补充。
母亲一项一项说,我一项一项记:窗户纸六张,三毛钱;写对子大红纸一张,一毛钱;火柴半包,一毛钱;盐两斤,三毛钱;酱油醋各一斤,两毛五;灯油一斤,一毛五;粉条一斤,六毛;年瞎(年瞎就是鞭炮)五毛;给妹妹买发带儿二尺,一毛钱;给父亲打酒一壶,两毛钱;给妹妹和我压兜钱,四毛。还剩一块钱,母亲说就不动了,留着家里遇到事时应急。
四斤驴肉怎么安排,父亲母亲意见有了分歧。父亲的意思是年三十晚上、大年初一两顿都给炖了得了,也好解馋。母亲则坚持细水长流,二斤驴肉年三十晚上焖着吃;一斤驴肉大年初一包饺子;还有一斤驴肉大年初三初五晚上吃,大年初五之前都要有荤腥。母亲的话吐口唾沫就是钉,父亲只得依了。
父亲在炕沿帮上磕了烟灰,对母亲说,我和孩子都沾着钱边了,你买点啥呢?要不你买双袜子吧。母亲凄苦地笑一下,袜子补一补还能穿,年好过,节好过,平常日子难过,那一块钱还是留着应急吧。
年三十晚上,我家的年饭是丰盛的,饭是大米饭,大米是母亲拿黏米去职工家换的。焖的驴肉搁了一斤粉条,又多搁了冻豆腐,盛了满满一大盔子。由于很长时间没吃到荤腥了,我们一家四张嘴吧唧吧唧吃得山响。虽然是寒冬腊月天气,我们却都吃出了汗津,嘴唇上都挂满了油花。
年夜文化大餐也是丰盛的,小喇叭广播着越剧、豫剧、京剧、评剧唱段,还有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还有郭兰英、王坤等人的歌曲,小喇叭广播一直播到子夜十二点才结束。
欢快的鞭炮声从一擦黑儿就断断续续响起,一会儿叭一声响,一会儿咚一声响,像电影战斗片里打的冷枪冷炮。接近子夜时分鞭炮声密集起来,鞭多是二百一挂的短鞭,嘎巴几声就没了声息。二踢脚的声响地上一声天上一声,声声崩着穷气。
大年夜掌灯都比较早,虽然穷,家家户户还是大方了一回,把灯捻挑长些,家家都点燃两盏油灯,里间屋一盏,外间屋一盏,让灯火彻夜长明。
我们生产队坐落在半山腰间,东一家西一家像散落的羊屎蛋儿。过了子时就是辞旧迎新了,人们不知何年何月养成的习俗,此刻都要走出屋门居高临下定定地看一眼山下人庄中的灯火。
冻得瑟瑟发抖时,我问母亲为何要看一眼山下人庄中的灯火,母亲告诉我,管新的一年心里亮堂的,管新的一年日子红火的。
我家比别的家日子更艰难,每年站在房前高岗上看山下灯火时,母亲都要我们一家多站一会儿,比别家多看几眼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