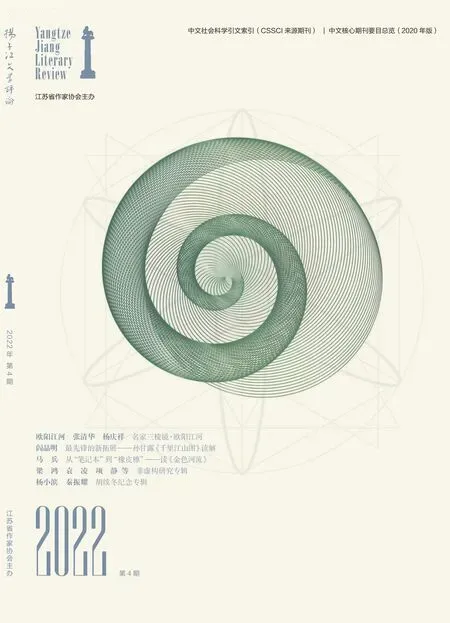诗性、现实、文体及其他
——论陈年喜的散文创作
宋宁刚
作为一个写作者,陈年喜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5年。该年年初,由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上映。随后,由吴晓波策划、秦晓宇选编的同名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也出版面世(虽然实际上是诗集选编的计划在前,纪录片电影的拍摄在后)。在影片上映后不久的2015年2月2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与诗人导演秦晓宇以及杨炼等人,共同发起一场“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正是在这场据说有“千人现场,千万人收看直播”(吴晓波频道)的诗歌朗诵会上,“矿工诗人”陈年喜(和影片中出现过的其他五位诗人一样)与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的杨炼同台,站在了聚光灯下。也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陈年喜得到了媒体的又一次关注。
而在纪录片电影中出现过的六位诗人中,陈年喜受到的关注最多。其中原因很多,比如他和其他诗人(如乌鸟鸟、邬霞、郭金牛等)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是打工诗人,更是“矿工诗人”;不仅是“矿工诗人”,而且是采金矿(而不是铁矿、煤矿等)的“矿工诗人”;不是一般的矿工,而是集刺激性与危险性于一身的爆破工……于是,打工诗人/矿工诗人/爆破工诗人等多重身份,将陈年喜与其他许多打工诗人区别开来。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格外吸引媒体;而媒体的关注,又反过来使他备受大众瞩目。
也是在2015年,陈年喜由于颈椎病恶化,不得不告别了十六年的矿山生涯,寻求新的出路。在艰难的处境下,由于影片的上映以及与诗人朋友们的相识,他获得了新的机会,于2016年应邀访美进行诗歌交流,在哈佛大学、耶鲁等大学做演讲,并于这一年12月获得首届桂冠工人诗人奖。此后,陈年喜开始比较密集地写作散文与非虚构作品,并及时地发表于网络平台或传统刊物。通过书写衰败的乡村和农民,书写此前几乎没有人写过的采金矿的群体,陈年喜成为时下文学写作中火热了十余年的“非虚构写作”中别具风貌的一员,大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写作版图。
正如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中所说:“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真实生活的十分之一。其余的一切通常为黑暗所掩埋……”通过散文创作,陈年喜不仅照亮了诗歌写作中“为黑暗中所掩埋”的部分,也与自身的诗歌创作之间建立起了某种互文和补充的关系。这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从2015年通过电影走向公众之后,除了《鲁豫有约》,陈年喜还被《南方周末》 《智族GQ》 《南方人物周刊》等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采访报道,并入选《南方人物周刊》2021魅力人物“100张中国脸”。矿工诗人、非虚构写作者、尘肺病患者、公益事业参与者(在2021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的腰封上,赫然印有“你买1本书,我捐1块钱给尘肺病家庭孩子”的字样)等多重身份,使陈年喜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更使他成为拥有大量粉丝的“大V”式的公众人物。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陈年喜的个人作品也得以比较顺利地出版(对于出版方来说,陈年喜本身就是一个卖点,甚至一个自带光环、大有开发潜力的IP)。2019年,作为“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歌精选”丛书六种中的一种,陈年喜个人诗集《炸裂志》出版。2021年,他又推出两部散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与《微尘》。2022年初,他几乎同时推出全新的散文集《一地霜白》和诗集《陈年喜的诗》。
由此不难看出,从通过纪录片进入大众视野开始,陈年喜的写作和作品出版本身,在相当程度上都离不开媒体的加持。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年喜的写作与出版,可被视为媒体、网络和出版商深度参与和介入的社会媒介现象。
本文无意过多停留于这个现象本身,而是希望在勾勒出陈年喜及其作品出现至今的背景与轮廓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陈年喜的“非虚构散文”作品的质地、特点以及由之所生发的问题。
按照陈年喜的三部散文作品集的介绍,《微尘》被称为“散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被称为“非虚构作品集”,《一地霜白》被称为是“非虚构散文集”。无论是(狭义的)“散文集”,还是“非虚构作品集”和“非虚构散文集”,从文体上,都可归在广义的散文门类之下。
阅读陈年喜,我们不免有些恍惚,仿佛这样的写作者是从《平凡的世界》里走出来的,和矿工孙少平是同龄人、同路人。虽然这样说显得有些怪诞,因为孙少平是虚构的小说人物,陈年喜则来自现实生活;孙少平出自陕北农村,陈年喜出自陕南山区;但他们同样经历过贫穷、闭塞、生的艰难……虽则如此,他和孙少平还是有很多不同——最显著的一点是,在孙少平身上有独属于1980年代的理想气质,甚至可以称作“励志”的气息,而在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三十余年社会生活的陈年喜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更多是更具当下性的、带着个体之卑微的清醒气质。在后者这里,有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受挫后的卑微,以及在卑微中保持着高度的自省与直面的勇气。
读陈年喜的诗,不难了解,他笔下的诗行内容深沉、情感悠远,诗行的节奏或舒缓或紧凑,分行与分节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诗人出色的语言意识。读他的不分行的文字,我们同样能够清楚地看到,作者不时在散文中楔入自己或他人的诗行,让诗文之间彼此提携、照应、互文、补充,处处闪烁着诗的光芒。与此同时,文中如碎金一样闪耀的诗性语言也格外惹眼:
虽然还是初春,河水已开始上涨,它裹挟着泥沙、败草、冷气以及上游的消息,莽莽苍苍,横无际涯,在河床上铺展得极其肆意。
这是他眼中的叶尔羌河。
他的耳朵很薄,阳光穿过耳轮,照见弯弯曲曲的毛细血管,粉红又老旧。
这是他看到的村里的准职业媒人(自称“媒婆”)。
出门下台阶时,他摔倒了。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扶杖行走。
此后,他再也不需要拐杖了。
这是他写父亲的散文结尾。
以上几段文字,无论是前两者的描述,还是最后的省略叙述,都具有高度的诗性。诗之于散文的反哺作用,以及陈年喜作为诗人的本色,都于此可见。更不用说,如前所提及的,作者常会将诗行嵌入叙述,让诗与文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除了上述所写,作者对自然景物以及季候风物的描绘,也颇见诗心:
包头的春天来得特别慢,特别晚,老家陕南已是莺飞草长,这里还是一片寒彻,广野千里,苍黄枯萎。它像一位迟到的学生,迟疑着躲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往教室进。
如果说这是诗人之敏感的见证,那么,他对通常看来缺乏诗意的事物充满诗性的描述,就更可见出他的诗性直觉和想象力:
我想,我的义务是催促他像对待诗歌一样善待小张,给她一个好的归宿。……但哪怕是在偶尔的电话里,我也会常常听到他们的争吵声,那是一把刀在一朵花上摩擦的声音。
张则成的生活简单、狭窄得像一张纸条……
最可贵的,是作者能将景物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书写——不仅书写,而且在自然与人事之间形成巨大张力。比如,说一个底层人的生活及其可能性,“狭窄得像一张纸条”,不仅贴切,而且读来令人心惊、心碎。类似更为出色的例子还有很多。
此外,在总体克制的笔触中,陈年喜还借助谚语、古诗,不仅提升了文字的诗意与活力,而且让他的叙述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地”特征:
“穷人莫听富人哄,梨子花开正下种。”古老的农谚里,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开始种早玉米了。地丁、黄花丁都钻出了地皮,东一片西一片,努力地要抱成一团。潮湿的春光里,喜鹊在枝头搭出新窝。
仿佛作者是在有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回归一种古老的常识,不只向那种古老的诗意致敬,也同样将之导向大地,导向大地上的生活,导向真切、饱满的现实。后者既是他写作素材的来源、他的写作对象,也是他写作的道义之所在。
的确,除了总体流畅的文字表述,阅读陈年喜散文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透过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结实而饱满的现实。这里的结实与饱满,既是审美意义上的,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那是一个人、一群人、进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强大而鲜活的生活现实,包括他们的生、老、病、死。它们的厚度与重量,远远超出了三本书的分量。
作者以记录的手法和旁观的视角,书写了一群微尘与草芥般的人的生:
我曾见过年轻的陪读母亲,从(县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无数遍地比对土豆的价格和品质,用半天时间,最后买二斤土豆。对于穷人,时间有的是,而钱怎么精打细算都没有多余的。
那天石头非常硬,掌子面特别光滑,钻头在岩石上找不到着力点,碰撞、弹跳了好长时间才形成了一个浅洞。钻头与岩石碰出的火花落在了他的衣领里,很烫。钻孔流出的水沿着安全帽,一直流到了嘴里,含了重银的水在嘴里有一丝丝说不出的甜味。
他们的伤与病:
路亮最怕听父亲(一个多年的矿工,一个矽肺病患者)的咳嗽声,像秋后垂死的蝉声,声嘶力竭,那比自己咳嗽还难受。
以及,他们必然或意外的死:
再见到大明时,他整个人已经不行了……他瘦得皮包骨头,身体显得又高又弯。长期的浸化冶炼提金,氰化物与汞的毒性浸入他的身体,像一棵再也拔不出来的芦苇,根须扎满塘底。这是大多数炼金人无可逃避的一天……
这些近乎无名的死者,无论人名、还是死的方式,都可以列很长:被铁钎穿透胸背的阿全 (《那场旷日持久的矿事》),开着车从山崖上坠落下去的赵大头(《那一年,在秦岭黑山》),死在矿上的大牙、朝海、赵大成(《父亲这辈子》 《小城里的文人们》)、死在建筑工地上的陈族(《用平板电脑写诗的人》)、死于氰化物与汞中毒的周大明(《我的朋友周大明》)、死于矽肺病(硅肺病)或尘肺病的余海及其他工友们(《表弟余海》)……
他们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吃苦力、求生存的人,也是这世上遭罪受难的人,他们是无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是不幸的,又由于陈年喜的书写而有幸被人短暂地记忆。也因此,可以说陈年喜的写作,为在大众视野中一直缺席的群体绘制了群像,同时也拓展了纪实(或非虚构)写作的版图。
除了直接书写底层社会的人与事,陈年喜几乎怀着某种兴致,耐心细致地写下了很多地方:
我们翻过高高的山梁,到了黄县。黄县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地图上叫龙口市,属烟台管,它与玲珑矿就隔着一道山梁。我们站在山梁上回看,渤海似乎更近了……
我曾在北京稀稀疏疏地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顺义区李天路,在朝阳区管庄至金盏乡温榆河的漫长城郊线上,度过了两个秋天。
像皮村、金盏乡、玲珑镇、黑山这些地名,与我们通常熟悉的北京、西安、烟台不同,它们带给读者的是对陌生之地的了解,对更为具体和微观的地方之感知,哪怕这些感知仍然有些抽象。在陈年喜笔下,无论北京、西安,还是别的城市,都更具体、更微观,微观到一个城市的某个区某个乡(镇),甚至某个村。它所展现的是“去掉了金光”的具体而微的地理,是日常和现实——更具纹理的现实。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去掉了大城市那令人炫目的光环和抽象宏大的具体地点。它们带着日常的现实性,不仅有“去蔽”的作用,更有“祛魅”的作用——当作者说,“在巨大的北京,皮村是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村子”,他呈示给读者的,不仅是与“巨大的北京”相比,卑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村子”,也是在那里求生的卑微的生命。正因此,他的书写不仅是真实的,在姿态上也是极为低微的,一如他所写的对象。
站在这些地名背后的,是人,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乃至从黑暗、危险的地心讨生活的艰辛而卑微的人。也因此,陈年喜的这些文字,既有鲜明的记录意味,也不无为社会底层弱势的无名者立传的意味。他的写作因此是现实而具有道义力量的。
本文开头提到,从文体上说,韵文之外,都是(广义的)散文。其中包括一切不分行的文字,甚至包括小说,自然,也包括“非虚构作品”。
如果我们认为散文与小说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真实、不能虚构的,那么散文与非虚构之间可以共享的内容就更多。不过,从狭义来说,散文与非虚构作品还是存在一些区别。比如,后者更强调叙事和故事;在叙事时更注意语气的节制,而非抒情的释放;更强调眼睛看到或身体感受到的,而非内心感想。在写作的题材上,非虚构写作更强调关注“我”之外的更广阔的现实,强调“他者”(人或物),而非“我”;即使写到“我”,也更多是写作为社会角色的“我”,以及“我”作为社会中的某种存在类型的样本,或者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非过于聚焦自身抒情和敏感的个体之“我”——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可以从旁观的角度去写他人的敏感和独特。
以此来衡量《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和《微尘》,虽然前者被称为是“非虚构作品集”,后者被称为是“散文集”,其实两者都更像是“非虚构作品集与散文集”的合集;而《一地霜白》被称为“非虚构散文集”,实际上更像是纯粹的散文集。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诸篇,以非虚构作品为主,第二和第四部分则更像是散文。如果说第一部分中的篇什,大多是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中心,向外延伸所写,那么第三部分中的文章,像《媒事》 《洞穴三十年》 《填埋垃圾的人》 《断链的种菇户》等,就是作者跳出“我”之外,通过有意识地“采访”、了解他人的生活,所写的非虚构作品。其中以《媒事》最为突出。它是作者有意识地邀约乡村媒人讲述他的“工作”,听他讲,记录他所讲,然后将之整理后形成的文字,因此连口吻、语气都保留着讲述者鲜明的痕迹。
在《微尘》一书中,作者也多次显示,他是经过有意识的采访、了解,搜寻素材才形成文章的:“结束这段长长的电话采访时,已经是晚上十点。电话那头的路亮似乎意犹未尽。他的房间响起了吉他的旋律……”;“我和张亮坐在他家的堂屋里。屋子有些年代了,墙皮脱落,一口水缸笨重地立在墙角……递他一支烟,我说,开始吧。几天前,我就和张亮约好听他讲讲一年的异国矿山生活。”
有意识的记录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它是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件:对他人的生活与故事永远葆有热情与好奇,对他人的存在永不漠然或忽视。这也是非虚构作品的价值之所在:记录、呈现、去蔽、祛魅,让生存的褶皱与细节更多绽露,让更多生命的幽微的存在真相展现于世人面前,让沉默的大多数获得它在这世间应有的“光照”。陈年喜的第一篇非虚构作品《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之所以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也由此可见,非虚构作品的向外延展性和纵深性越大,就越有意义,至少从题材方面来说是如此。
在《微尘》这部“散文集”中,除了写父亲(《父亲这辈子》)、母亲(《不曾远游的母亲》)、儿子(《陪读的日子》)和“我”自己做手术(《手术》)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其他十几篇文章(全书共21篇),绝大多数都可以看作是“非虚构作品”。如该书开篇的《我的朋友周大明》:
周大明家有三台生铁碾子,一台三十吨,另外两台各十五吨。……三台机器同时转动起来,惊天动地,房屋颤抖,面对面说话得用手势帮忙。三个浸化池,在后院里一字排开。碾子、池子一年四季不闲着……因为用水量很大,整个院子总是湿汪汪的,混合着药剂的水流出院子,顺着排水沟泛着白沫一直流到村前的小河里,然后汇入洛河,最后混迹于滚滚黄河的波涛和流沙。
这里有散文式的细致描述,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场景记录式的客观描述。
院子里的空气里总是弥漫着重重的药剂味。一种淡淡的、苦杏仁味的暗香在其中弥散,仿佛北风里的一股细柔轻风,有点儿刺鼻,有些沁心。这是氰化物的味道。
看似带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刺鼻”“沁心”),实则来自“我”这个旁观者、叙述者、“记(录)者”的嗅觉,属于基本的感知层面,不夸张、不抒情。最后的那句科学式的说明句(“这是氰化物的味道”),更为这段叙述“定音”。
《微尘》中的有些篇章,无论作为(狭义的)散文,还是作为非虚构文学,似乎都不那么纯粹,也即在写法上杂糅散文与非虚构的写法。比如在《不曾远游的母亲》这篇总体上更像是(狭义的)散文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生活像一口锅,她(指母亲——引者)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锅有时是冷的,有时是热的,只有锅里的人,冷热自知。
这是典型的散文写法,不那么具体(对于散文,具体是一种选择;对于非虚构,则是必须),带着个人的感慨(非虚构则要尽可能地去感慨、去抒情)。
在《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部“非虚构作品集”中,有篇文章叫《在玲珑》,开头是这样的:
想起这段故事时,突然想起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一句话: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是的,不觉间,那个冰天雪地的玲珑一夜,已经过去二十一年了。
显然,这是典型的回忆散文的写法。无论是回顾式的写法,还是感慨的笔调,都是如此。
此外,在写法上,作者在很多文章的开头(包括不同部分的开头),都有意识地用简短的句子开篇,或者,先行将一件事情的结果告知读者(如某某人死了),向读者打开一个相对开阔、陌生的世界,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将笔触伸向“我”之外的世界及其他人,都更像是非虚构作品的样式(虽然倒叙是一种普遍的写作手法,但在非虚构作品中,先以简单的叙述讲述结果,然后展开一个故事,几乎已成为最常见的叙述策略之一)。
作为诗人,陈年喜有自己天然的优势。他默默写诗多年,对这门手艺足够熟悉。作为非虚构写作者,陈年喜也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他有许多写作者都难以比拟的独特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读《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感觉其可进一步提升之处在于,相比诗,非虚构写作对陈年喜(对国内绝大多数文学写作者也一样)来说,是一个新文体、新事物,对于这种文体及其特点,尚需在写作中继续熟稔。如他所言,“我是完全凭感觉写的”。对于一种文体,凭感觉写当然可以,但仅凭感觉写,要走得远,显然不够。
陈年喜的陕南老乡、国内著名的非虚构作家、前《南方周末》记者袁凌说得没错,陈年喜文笔不错,“但是写故事很弱”。所谓故事,需要叙事,也需要细节,需要叙述,也需要描写,仿佛不同的景深,打开写作的内在层次。在这些方面,陈年喜还需更多操练。
比如《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第一部分的有些故事,叙述可以更清晰、甚至更简单一些。在个别地方,则需要再详细一些:
他是我的同学,他后来成为打遍天下的矿业主,沉浮胜败,兴荣亡辱,有无数后话。……
矿洞内部四通八达,结构诡谲复杂,天井、下采、空采、矿仓星罗棋布如同迷宫。
在这样的叙述中,用了太多成语类的词(“沉浮胜败”“兴荣亡辱”“诡谲复杂”“星罗棋布”……),显得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内容。笔者在多个场合讲过,在真正的文学创作中,成语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因为成语是已完成的话语,也是“陈(旧之)语”,它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生动的场景或故事,而从第二次使用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板结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话语,不再鲜活地表现具象。也因此,作家们很少使用。偶有使用,也多是反讽的,也即创造性地用。他们知道,严肃的文学写作,从本质上讲,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词,从而为这个世界贡献词,而不只是袭用。
非虚构作品,如果说它需要概括,也要非常审慎。更不用说,它需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在上述叙述中,什么叫“打遍天下的矿业主”?多大的“天下”?所谓“沉浮胜败”“兴荣亡辱”又是什么意思?它们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故事?无论是从散文的角度,还是非虚构的角度,宁可不写,也最好不要笼统带过。
在陈年喜的叙述中,也有一些特别吸引人的细节。比如“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借助蜡烛的弱光发现矿石上偶尔的纯金颗粒,大如麦粒,小如针尖。这些矿块带到洞外的某些小店铺,可以换取一双袜子或一瓶高粱大曲”。这才是宝贵的,令读者眼前一亮的。
前文曾论及,非虚构写作需要作者尤其注意自身情感的节制。比如:


上引句中,“令人惊奇”不必说出来,留给读者去感受即可。“夜长风烈”也不必有,因为后面已经说明是“半夜”,至于风的大小,自有后文“彩条布常被从某一面揭起来”去说明。
此外,叙述的句式和逻辑问题也需注意。陈年喜似乎比较喜欢用长句,尤其在《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中,几乎有点像是他的个人叙述风格的展演。常见的非虚构作品,因为其所刊发的媒介(如报刊和网络平台),以及其所面对的读者(普通大众)的缘故,一般都比较好读。而陈年喜的非虚构作品,从行文叙述的角度看,有一些涩味。相比之下,《微尘》在表述上要顺畅得多。
陈年喜“凭感觉写的”非虚构作品,一方面让我们反思,常见的非虚构这样写下去,似乎难逃同质化的倾向;就此来说,他的这些显得不那么圆熟的非虚构作品,未尝不是一种矫正,至少是必要的提醒;而对陈年喜个人来说,则需要反向的自我改进,也即注意在保持个人特点的同时,有对文体和写作通则尽可能充分的自觉。
总体来说,非虚构作品为了表达的灵活和阅读的简便,不能不考虑读者。这就要控制长句,多用标点,尽可能地化繁为简。




总体来说,在长达数年的写作锻炼中,无论对于诗,还是对于非虚构写作,陈年喜越来越有“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近十年离开矿洞的生活,更是使得他在文字上有更多的投入。正如“他把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相信他也完全有可能将之带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将底层人的生活定格在文字中,不使之湮没。即便有些内容不是第一次被书写,它们也值得被不同的写作者一再书写,因为那是中国大地上沉默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大多数,他们艰辛地生活于世,却一直身处背光之处。无论对于何种写作,那里都是优良的矿脉,也是能够为写作赢获价值和尊严的地方。
【注释】
①[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②“炸裂志”这三个字,最早被作家阎连科用来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2013),随后被陈年喜借来当做一首诗的题目,此后又被秦晓宇借来命名有关陈年喜的纪录片,并且成为陈年喜的首部诗集的书名。可以说,这三个字在陈年喜这个爆破工诗人这里,获得了新的、更为恰切和更具生命张力的意义。


⑯或许因为“散文集”听上去不如“非虚构集”那么有卖点,出版者或作者才称《一地霜白》为“非虚构散文集”。在一般理解中,散文本身就是真实的、不虚构的。也有可能在出版者或作者看来,这部散文集更具有“非虚构作品集”所具备的打开底层现实的质地,所以才这么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