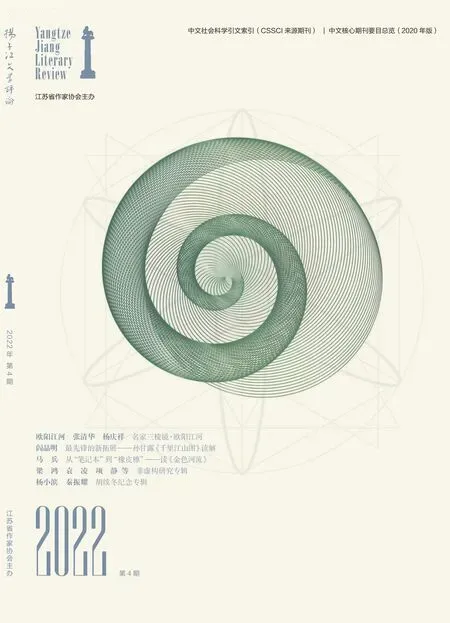幸存者、当代性和文明的眼泪
——欧阳江河长诗阅读札记
杨庆祥
我试图以一种非整体的形式来应对欧阳江河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从研究的角度看,欧阳江河属于那种需要“研究资料汇编”同时又反对“资料汇编”的作者——注意,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一个书法家、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者、一个对音乐、美术、威士忌和红酒都有见解的鉴赏家。一个碎碎念的“老男孩”、一个头发漆黑同时目光狡黠的“火星人”。需要“资料汇编”的意思是,他必将在当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留下他的“令名”,传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他的传记、文本、访谈、评论,甚至是八卦绯闻的基础之上。反对“资料汇编”的意思是,那些整齐的分类法和貌似严密实则空洞的概念定义会将创造之门焊死,留给我们一具文学史的僵尸标本。所以我寻求灵动的对位法,能够将欧阳江河重新塑形,吹一口气,在他的分身和幻影里不是手足无措,而是能够一起蹁跹遨游,在多重的目光里看到“成千吨的自由落体,/以及垃圾的天女散花”。
幸存者。这是理解欧阳江河长诗的一个起始之词。在长诗《悬棺》里,“幸存者”是反复被质询和拷问的对象。《悬棺》完成于1984年,其时中国当代思想和美学领域最重要的潮流“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寻根文学”的实践者如韩少功、李杭育、贾平凹等等,他们的作品里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最后一个”的形象,这“最后一个”往往代表着某种即将消失的传统技艺或者文化,在一些缺乏深刻反思和自省的作品中,文化缅怀的意味大于文化重建的意味。如果将欧阳江河长诗中的“幸存者”与“最后一个”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幸存者”这一形象是非哀婉的、非叹息的、非牧歌式的。也就是说,虽然《悬棺》开篇也从“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术”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开始其叙事,但是,诗人没有迷恋这些元素所代表的那种政教秩序和文明形态,恰好相反,他汲汲于拆解和重构。所以书写的景象不过是“无字天书”,而“五行遁术”的目的是“走吧,离开此时此地。离开他人,也离开自身”。幸存者只是对“死亡”的一种延续。1984年欧阳江河应该没有读过列维纳斯,不太可能了解其“面对死亡我们一无所能”的观点,但是他却在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列维纳斯的反题:幸存者在死亡的延续中并非一无所能,至少,他可以通过对词和文字的重组和拆解来展示一种启示:“这个启示将是唯一的启示……/这唯一的启示与诞辰俱来,留末日独去。”
让我们在“幸存者”这里稍微停留。幸存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原型,中国的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将自己牢牢地锚定在幸存者的位置。他在幻灯片事件中觉知到了幸存者的使命,虽然他一再犹豫“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也许还有罢”“仿佛内心里有鬼似的”。幸存者由此变成了一个历史结构的产物,并被这一历史结构反复塑造出来。如果说鲁迅表达的是“辛亥一代”幸存者的历史知觉,那么,北岛表达的就是1970年代幸存者的历史知觉。在北岛的代表作《回答》中,幸存者作为充满了希望的延续——恰恰不是欧阳江河的死亡的延续——成为一种进步论和未来想象的注脚。在这里,欧阳江河第一次将自己与北岛这一代区隔开来,他不抱有这种乐观——虽然在1980年代这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但欧阳江河对历史的“反复性”——这一“反复性”不仅仅是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司马迁和鲁迅意义上的——的体认让他意识到了一种延续性的恐怖——“你,幸存者,除了谎言还能说出些什么”。对这一“谎言谱系”的切肤之痛也许构成了欧阳江河诗歌词源学的起源:他必须不断地使用反词。“反词”在这里不仅仅指向一种词汇表,同时也指向一种结构诗歌甚至是思想的方式。幸存者不能成为一代人的雕像,这依然是集体主义的癔症,是一种纪念碑式的自我感动,欧阳江河要进行一次清洁仪式,才能完成幸存者的蝉蜕。这一仪式在《傍晚穿过广场》里得以完成,历史再次反复,而幸存者从这一反复的铁网中“漏”了出来:
我没想到这么多的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
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
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傍晚离去
或倒下。
他决定“一个人走过广场”,巨大与渺小构成了一种反讽的画面,但是却有撼人的力量。幸存者真正成了一个亡灵,正如那复活的恐怖又亲密的场景:“在他死后三天,或从死的那一刻开始——他穿着编织精良,缠绕包裹的衣服,维持着最最优雅的习俗,在我们内心深处答复着我们。”幸存者现在半生半死?他要去哪里重新获得“答复”和“交谈”的能力/权利?
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路标。幸存者沿着这个路标将进入一个新的当下。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市场经济几乎构成了全部书写的背景和历史生发的地基。但显然,如果从《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诗作来看,欧阳江河并不愿意将“市场经济”处理为一个若隐若现的幕布式的存在,相反,他直接将其设置为“主题”,不是“人”在市场经济的舞台或者幕布前活动,而是市场经济取代“人”,并活跃在舞台的中央和幕布的前台,“人”退而成为布景和烘托,传统的主客关系几乎全部被倒置或者拆解了:
在口号反面的
广告节目里,政治家走向沿街叫卖的
银行家的封面肖像,手中的望远镜
颠倒过来。他看到的是更为遥远的公众。
市场经济作为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重申其合法性的关键性配置,在其时的历史语境里已经面目暧昧。1990年代的知识者虽然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开放自由”抱有期待,另外一方面又因为思维惯性和既有意识形态规训的延续,对市场经济抱有道德上的怀疑甚至恐惧。欧阳江河也许是第一个将“市场经济”作为诗歌主体进行书写的诗人,并且使用的是带有战略建构意味的长诗形式。这是欧阳江河的一次“正面强攻”,这一强攻摆脱了立场和派别可能带来的道德预设和意识形态偏见,而是将市场经济视为一个历史的活体。现在,它被召唤出来了,“省吃俭用的计划经济的政治美德”也许会第一时间被“银行家举手反对”。更核心的是,“花光了挣来的钱,就花欠下的。如果你把已经花掉的钱/再花一遍,就会变得比存进银行的更多/也更可靠”。这是我读过的对“市场经济”和“债务定律”最精彩的诗歌表达。我们在此无法判断欧阳江河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原则,也许他唯一的立场和原则就是如艾略特所言的“文学必须不断地跟随当代世界一起改变”。也就是说,“当代性”构成了欧阳江河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仅是政治的,更是历史和美学的。在“当代性”中,需要注意的不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陈述”,而是斩断“词”与“真”之间的固定语法联系,在“虚构”的意义上来将“当代性”表征为一种新的词语排列和语法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具有方法论的提示。
将当代性推向极致的,是完成于2012年的长诗《凤凰》。《凤凰》是当代诗歌史上少有的现象级诗歌文本之一。这一现象级不仅仅是在阅读和阐释的意义上,尽管《凤凰》确实引起了评论界一股解读的热潮。这一现象级更是由这一长诗写作在发生学和文本阐释学意义上所具有的“可写性”来决定的。就发生学来说,长诗《凤凰》起源于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凤凰》,而徐冰的《凤凰》则来自资本的一次试图为自己寻找解释并在此解释的基础上建构自我公共形象的冲动——中国的市场经济经过近30年的“炸裂式”发展后正在渴望建立它的美学和思想——在此,市场经济获得了其作为当代资本/资本家的赋形。力量、冲动、生命意志构成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写作的内在驱动力,这里可以参考的范例是莫言小说中的语言狂欢和徐冰版画“复数”系列中的蝌蚪繁殖——也正是莫言,在其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蛙》 中最终将这种生命意志予以阉割。
徐冰的《凤凰》采用了另外一种路径,他以工业的“废弃品”结构其凤凰的躯体,但呈现的内在精神却难以名状。在这个意义上,徐冰的《凤凰》确实是一个未完成的“天问”,装置的语言无法准确全面地揭示当代性——这一当代性需要诗歌语言:声音、词语、语法以及由此刺激而生的意识形态想象力。这就是欧阳江河的创造,长诗《凤凰》不是对艺术品《凤凰》的简单的延续或者注脚,而是一个对位的文本,他们共时性地发生于中国当代性的内部,带有某种“易”的神秘,但是,他们都指向世界性——在这一点上,装置性作品《凤凰》是中国当代性的一次“模具化”——“凤凰彻悟了飞的真谛,却不飞了”,而长诗《凤凰》则将这一模具重新熔化,形成了一种如鲍曼所谓的新的“流动性”——“如果这样的鸟儿都不飞,还要天空做什么?”
但凤凰的飞却不仅仅是飞在肉眼可见的天空中。因此,在长诗《凤凰》里,飞的物质条件不仅仅是翅膀,也不仅仅是物理要求的平衡术,而首先在于“目光”。也就是说这一“飞”更是思想意义上的,是对文明史的一种观察、考量和激活。在文明史的框架里,凤凰属于东方的“奥义”大鸟,所以不是鹤,也非龙,而只能是凤凰代表了东方。在对这一“文明大鸟”(它是动物学分类中的鸟吗?)的注视中,多重的文本带来了多种的奥义。长诗的10、11、12节集中于这样一种建构。庄子、李贺、贾谊、李白、郭沫若、列宁、毛泽东……这些人都成了凤凰的化身和幻影,而革命、改造、资本、消费也都成了凤凰一次次涅槃的燃料。长诗本身的结构成了“丹炉”一般的存在,在这一“丹炉”中,各种词语的原材料在思想之火的煅烧中发生着转化(transfer):
郭沫若把凤凰看作火的邀请
大清的绝症,从鸦片递向火,
从词递给枪:在武昌,凤凰被扣响。
这一身烈火的不死鸟,
给词章之美穿上军装,
以迷彩之美,步入天空。
但是这一“丹炉”的产出却也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出炉的可能并非文明的内丹,而是一炉不明所以的碎屑。即使在那文明的内丹里面,也有“在黑暗中,越是黑到深处,越是不够黑”的负累。但是所谓的当代性或许在此呈现出了其诡异的辩证法:它仅仅意味着一种运动的趋向,而运动指向的目的,却完全无法把握。当代性再一次抽空了它本身的现实所指,与尼采的“永恒轮回”发生着意义的勾连。在欧阳江河这里,当代性是多重维度的(思想)运动:历史的,现实的,想象的;同时也是悼念的,反讽的,内省的。
在历史中,唯一不朽的只有当代性。
让我们折返回2009年的长诗《泰姬陵之泪》。《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的最后一句诗是“你知道自己不是新一代人/‘忘记我在这里’”。作为幽灵一般的幸存者再次不无痛苦地体认到了“错置”和“错位”,他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他属于一场看起来无端涌现的“当代性”——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一次小小反刍吗?长诗中反复出现的句子是“2009年,我拍下了1632年的/我非我”“2009年,镜像回头一瞥,递过1632年的/隔世之约”。2009年是诗人身处的此时此刻,1632年对诗人来说是彼时彼刻,但是对“泰姬陵”里的“泰姬”来说却是她的此时此刻,“彼时彼刻”和“此时此刻”在长诗里被反复纠缠在一起,时间的刻度已经变得模糊,一种历史的“通感”和心灵的“共情”突破了物理的局限,当代性的涌现让一切都变成了此时此刻的活体。
在这涌现的世界之源中,最重要的是“泪水”。长诗《泰姬陵之泪》以“泪”为题,长诗《凤凰》中也数次出现了“泪水”。这在欧阳江河的诗歌中很是罕见,早在1980年代的起步阶段,他就将抒情之泪深埋在经验和智性之下,但这一次,他无所顾忌地亮出了“泪水”——不仅仅是抒情之泪,而是经过熔化和锻造之后的文明之泪:
根,枝,叶,三种无明对位而流。
日心,地心,人心,三种无言
因泪滴
而缩小,小到寸心那么小,比自我
委身于忘我和无我还要小。
一个琥珀般的夜空安放在泪滴里,
泪滴:这颗寸心的天下心。
齐奥朗曾经用诗一般的散文语言探讨过“眼泪”的起源:“当我探寻眼泪的起源,就想到圣徒,他们会是眼泪那苦涩之光的源头吗?有谁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泪水是他们的踪迹。”这是基于基督教文化对“神圣眼泪”的追溯,圣徒与眼泪的关系成为起源。但是在欧阳江河的诗歌中,却并没有那样一种严格宗教意义上的“圣徒”,在中国古典的世俗文化和现代的革命文化的融合中,“圣徒”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但是对“神圣”的追求并没有因此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以“文明”代替“神圣”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幸存者不是圣徒,但幸存者却可以是“文明之子”——即使如布罗茨基这样生活在东正教语境中的诗人,最后也不得不选择文明而不是宗教为其庇护所。欧阳江河的泪水不是抒情之泪,同样也不是忏悔之泪、救赎之泪,甚至也不是“爱的眼泪”——因为文明本身并非一种恩典。文明是一种历史叙述,或者说,文明也许不过是一种“诗(思)写”或“诗(思)想”,因此,无论是在《泰姬陵之泪》还是在《凤凰》中,救赎都被“搁置”了,欧阳江河无意去追求那种带有“未来学”和“末世论”的救赎——这两者不过是硬币的两面。对欧阳江河来说,文明之泪并非神圣之泪,它甚至反对那种神圣之泪:
但那些不洁的黑暗的泪水能不让它流吗?
那些泪水里的白垩和铁,那些矿层,那些泥沙俱下,
那些元气茫茫,生死茫茫,歌哭茫茫,
年轻时泪流,
老了,厌倦了,也流。
文明的眼泪也是野蛮的眼泪,正如文明的文献也同时是野蛮的文献。在这里欧阳江河也许遇到了“书写”与“文明”的辩证:书写并非是一个从“无字天书”到“有字符号”的物理记载过程,同时也是将人类的爱欲与意志、善与恶书写为历史并转化为“文明”的主体行为。欧阳江河的长诗写作因此具有了至少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长诗作为一种书写行为,它必然是一个物理过程,这一物理书写的过程包括基于心脑的智力、词语的修辞以及结构的能力;在第二个层次上,长诗的写作包含着将人类的“历史实践”转化为“文明形态”的维度,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真正的长诗写作呈现了文明内部的“野蛮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长诗写作本身也应该是一种“野蛮”行为;在第三个层次上,长诗的写作指向的是一种“个人内在的真理性” ,以“个人内在的真理性”去平衡文明的“野蛮性”,并由此获得其与人类生活世界的互动。这三个层次“三位一体”,形成一个旋转开放的圆环,圆周上任何一个点都召唤着一首长诗的加入。
在这一形而上的意义上,长诗无法完成,也不需要完成。对长诗的阐释无法完成,也不需要完成。
2022-05-27,北京
【注释】
①欧阳江河:《老男孩之歌》,这里的“老男孩”可视作一个自喻。收入欧阳江河《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
②参见欧阳江河:《火星人手记:关于长诗手卷》,《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页。
③欧阳江河:《凤凰》,《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
④这一类作品众多,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义的《老井》、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等。
⑤参见[法]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⑥⑧欧阳江河:《悬棺》,《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6页。
⑦参见[日]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柄谷行人借用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理论,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性反复。
⑨Blanchot,Maurice.,trans.Ann Smock.Lincoln,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sess,1982.
⑩艾略特的原话是:“文学批评必须不断地跟随当代世界一起改变。”见[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⑪参见李陀:《序 凤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杨庆祥:《“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凤凰〉的风景发现和历史辩证法》,《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吴晓东:《后工业时代的全景式文化表征——评欧阳江河的〈凤凰〉》,《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姜涛:《为“天问”搭一个词的脚手架?——欧阳江河〈凤凰〉读后》,《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等等。
⑫2019年,北京筑中美术馆举办了徐冰等5人的版画展,我为该展撰写的序言中亦提到了这种“生命意志”的互动性:“徐冰在1980年代创作木刻‘复数’系列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击中了一个时代的症候,这一症候并不仅仅是来自本雅明所断言的‘技术复制’,而更是来自一种深刻的同时代性。在同时期莫言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汪洋恣肆的欲望。莫言的语言狂欢和徐冰的复数重叠见证了1980年代因为社会转型而激活的生命意志。在所有权被重新分配后——这在标志有赵钱孙李的《庄稼地》里有直接的体现——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都以倾泻的姿态喷薄而出,而用木刻这一相对冷峻的形式来展示这一短暂的心灵浪漫史,是徐冰奇特的辩证法。”参见杨庆祥:《意志的形变》,筑中美术馆徐冰等5人版画展序。
⑬荣格认为中国《易经》的时间特点在于其“同时性”:“事实上,时间仿佛远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包含着性质或基本条件的具体连续体,这些性质或基本条件能以一种无法作因果解释的平行性在不同的地方相对同时地显现出来。比如相同的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的巧合出现。”见荣格1930年5月10日在慕尼黑纪念卫礼贤的演讲词。
⑭[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⑮[法]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沙湄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页。
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欧阳江河在2022年发表的长诗《圣僧八思巴》和正在进行写作的长诗《鸠摩罗什》,都是以佛教的重要人物为主题,这意味着欧阳江河又尝试一种新变,这两首诗本文暂不讨论,也许应该放在欧阳江河界定的“60岁以后写作”的框架中理解更为合适,当然,这里面毫无疑问地具有文明论的指向。
⑰参见[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唐烈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⑱欧阳江河《火星人手记:关于长诗手卷》第117节:“以他人作为言说对象的元诗立场,赋予长诗写作超乎个人抒情之外的写作主体性,借此,写者本人终得以放弃自己思想的纯洁性,终得以对读者说: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欧阳江河:《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20页。)我个人认为,“脏”已经触及到了长诗写作的芜杂性,但“野蛮”更能揭示其本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