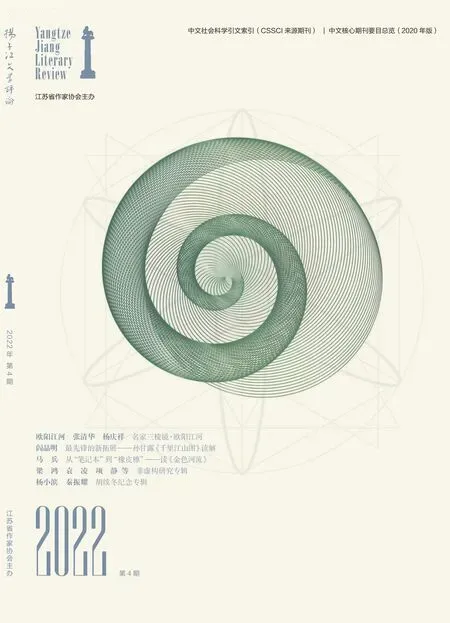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有一个引领者
——欧阳江河印象
张清华
某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我行走在威尼斯的街道上。我必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城市,蓝色的亚得里亚海在不远处起伏,这在水里浸泡了千年的城郭,就在她的水边,在那些原本可能是草莽覆盖的河岔中。我无法描述这城市,我意识到,我正处在哑口无言和目瞪口呆的反应中。
更可能的是,我正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那一刻,我意识到这点,一句古老的格言攫住了我。
为什么呢,眼前有景道不得,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描述它。我在这途中停下来了,一任时间随风而逝,犹如过去两千年中早已灰飞烟灭的历史。
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选择哑口,因为这样的建筑和栖居原本就是诗,还要怎样搜罗张致,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超过这些画面本身的诗意?
整整十年后,又一个春末夏初,疫情时期,我行走在离家不远的街道上。黄昏降临,天边的一抹晚霞,像一片末日的火焰,忽地将我带入到遥远的往事之中,让我的记忆如此虚无而又荒诞地燃烧着。我为什么会想起多年前的威尼斯,想起那座城市的黄昏,那带着清凉和温柔火焰的向晚?眼下,这偌大城市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恍惚感,不知道这一刻是谁,何人行走在现实和记忆中,行走在那依稀蜿蜒的通向语言的途中,然后又迷失。
但是有了。我耳边忽然想起了一个短语,一个无厘头,但又确有来头的词组,或是一个遥远的叹息——“那么,威尼斯呢?”
是的,威尼斯呢?它和谁有关?
我在文字的开头,抑制不住地写下了这些句子,当然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这一刻真实的幻觉。在这疫病的时代,不惟抒情是不道德的,甚至过于沉迷流畅的语调和漂亮的句子本身也不道德。我只是想用自己来反衬——不,是想用他,来激励常常失去语言的自己。
他是谁?当然是欧阳江河。他随时随地,都游走在语言的巨大光晕之中,仿佛核聚变,他的语言会随时生出难以想象的,输出巨大能量的链式反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我一直在琢磨着老海德格尔的这句话,难道语言不是应声即到脱口而出的么,为何还要在通向它的途中盘桓?是的,我意识到,这是“在”与“思”所共同决定的,“言”是“思”的结果,也是“在”的证明。这里有一条形而上学的小径,蜿蜒在精神的山巅和生命的云端,当那言和思共同出现且最终汇合的时候,就是人感受并印证了“在”——此在、存在——的时候。
所以,不惟“我思,我在”,这一路途的终点还必须有“言”,言尽出,而意方现。可我通常却在通向这境地的途中迷失。这让我常常停留在生命的恍惚与迷惘之中,不知道那一刻的我,是“在”也“不在”。
所以十年前的我,不曾为威尼斯写下一个字,十年后的这个黄昏也是。我依然只有记忆的混沌和无言的怅惘。尽管那一刻中威尼斯的美景似乎蜂拥而至,我依然不知道说些或记下些什么。但那一刻,我忽然记起了他的诗句,那些句子如同黄昏时分的晚霞,倏然以盛大的气势,覆盖了我的世界。
你一夜之间喝光了威尼斯的啤酒,
却没有力气拔出香槟酒的塞子。
早晨在你看来要么被酒精提炼过,
要么已经风格化。文艺复兴的荒凉,
因肉身的荒凉而恢复了无力感,
说完一切的词,被一笔欠款挪用了。
拜占庭只是一个登记过的景点,其出口
两面都带粘胶。一种透明的虚无性
如鸟笼般悬挂着,赋予现实以能见度。
每个人进去后,都变得像呵气那么稀薄。
这只是一首诗的约二十分之一,但它是如此灵验地打开了我关于威尼斯的一切,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关于这城市的风景、历史、传说,还有这游历者或过客,所能够背负的一切。但这一切只在他的“思与在”中存活,而在我的语言世界里,就仿佛是那座古老的通向密闭牢狱的“叹息桥”一样,压抑、兴奋、晦暗,只剩一声短促而缥缈的叹息。
“那么,威尼斯呢”?
是的,它在语言中醒来,然后又在风中逝去,最后留驻在了欧阳江河式的黄昏里。
在诗歌中的欧阳江河,即使不是一个圣者,也是一个十足的智者,他用全部的诗歌写作,实现了一个智者的形象,一个具有“玄学气质”的思想者的范儿;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却一直努力成为一个俗人。你要是请他吃饭,他会说今天的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你要请他喝酒,他会说这酒真不亚于茅台;你要请他喝茶,他会把你的茶赞美成一朵花,味道堪比舒伯特、瓦格纳晚期的音乐。
所以你没有办法不在敬重的同时,喜欢他这个人。生活中的欧阳江河常常会让人产生错乱感,这就是那个写出了《玻璃工厂》 《傍晚穿过广场》 《凤凰》乃至于《苏武牧羊》的欧阳江河吗?他什么时候只要愿意,都会欣然走下云中的神坛,笑嘻嘻地和你站在一起,手里端着酒杯,与你称兄道弟,甚至口占俗词儿,顷刻间万丈红尘。
所以欧阳江河的酒局多、活动多,缘何?因为他从不掀桌子,砸场子,请他吃饭的人除了仰慕他的诗名和才华,还会欣然于他满满的“正能量”——会把你的菜和酒夸到天上,会带给你一整晚的快乐,把你阴郁的情绪一扫而光。还有开会,任何场合只要他在,就不会冷场,任何话题只要到了他那里,就不用担心不会升腾到云的高度。
当然,一旦把话筒交给了他,那也就意味着你甭想按点儿开饭了。因为只要他打开了话匣子,就没有别人什么事儿了。
我一下子把话题又拉这么低,是想让读者知道,诗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当年李白和苏东坡也是这样,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好酒喝到哪儿,偶尔还会写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类的俗句,来支应朋友。《赠汪伦》那么有名的一首诗,可是你打听一下汪伦是谁,谁会知道,不过就是喜欢做东的酒友而已。
可是你会觉得他们俗么,当然不会。所以我会和他说,江河兄,我是会允许你“俗”的,你怎么俗都可以,因为只有大诗人才有俗的资本——在别人那儿是恶俗,在你这儿便是大雅。
自然是玩笑,他也就高兴地哈哈大笑一番。
但也有话不投机的时候,这时欧阳江河也是个十足的“暴脾气”,也会马上翻脸,光是我亲自见过的就有几次。但是和山东人不一样,他不会上拳头,四川人虽然脾气暴,但不会真的像山东人那样,动辄拼老命,出手没轻重。他们无非是语言上使劲,声音大,嗓门儿突然高上去罢了。江河也是这样,吵起来嗓门大到顶破屋子,事后却不记仇,再见面时还跟没事儿人一样,这就很可爱。诗人嘛,没点儿率性也不好玩,而没点儿赤子心胸也不可敬。
江河随时会穿越,从红尘到殿堂,从古人到今人,从纸上到现实,也就是一秒钟的事儿。顷刻间他摇身又变回智者的肉身。
西川曾说,没有欧阳江河不能谈的话题,只要你有题目。大部分时候他都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只要开口就如悬河。有时话题离他的惯常稍远,他会在前几分钟里有些许犹疑,“开始他自己也确实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几分钟以后,他会突然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高级的、玄学的、世界性的话题,然后从老子到康德,从本雅明到德里达,从苏格拉底一直到齐泽克……直到把这问题变成一贯通古今、纵横八荒、上天入地的题目。
所以,欧阳江河既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人,也不是奥林波斯或昆仑山上的仙人,而就是一个现实中的智者。他的思想本身你也许不一定赞同,但你无法否认,他是当代中国诗人中“最具思想能力”的一位。“思”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动词,在他这儿是永动词,“诗学”仅仅是他庞大思想场中的一个小界面。不过由他所生产的“中年写作”“减速诗学”“异质混成”“作为幽灵的写作”等等概念,至今依然是当代诗歌最具原创性和引领性、也最敏感地回应着当代历史的概念。
再说说欧阳江河的俗故事——我常想,现如今人们对李白的了解,也就是限于“酒中仙”“谪仙人”那点事儿,很少有真实的故事,为何,就是缘于当世友人的手懒,没把他那些靠谱的不靠谱的事迹,都一一记录下来,所以才使得研究者倍感材料的贫乏。作为与他混迹多年的“老盆友”,自然应该照实了说,绝不为贤者讳。
欧阳江河“喜欢丢东西”——这么说是因为他太容易兴奋,一兴奋就会魂不守舍,与现实就会发生脱节,然后就开始丢三落四。当然,他肯定不会把自己也丢了,甚至也会把别人也“拐”了来,但他的手机却换得特别勤。
我与他同行的出游经历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次数,关于他的手机都出现了离奇的故事。一次是手机掉入了公厕的马桶里,找人捞上来,发现主板已烧坏了,找人去修,致使行程耽误了半天;有两次手机丢到了高铁上,其中一次我拜托了铁路公安的诗人朋友,追踪数千公里,硬是帮他找回来了;还有一次,是他从外地回来,发现手机又不见了,我再次找到铁路公安的朋友,这次人家调动了多处同行,协力找了一个星期,最后表示非常沮丧,觉得失了铁路公安的面子,因为他们多年来几乎从没有失手过。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欧阳江河突然从自己的行李箱中找到了。连他自己都纳闷:自己一路都在刷手机,出站时也要用它打车,而行李箱锁得好好的,从行李架上回到家中,是何时,又因何,这手机竟然钻到了箱子里?
还没完,还有一次,是欧阳江河到学校来参加活动,他一脸春风来到我的办公室,还没落座就接到一个电话,人家问他是不是把别人的手机拿走了,他说,不可能啊!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部一模一样的——原来,他把别人的手机当成自己的给“顺”来了。人家那边本已准备报案,我赶紧抢过手机对人家解释,说我是他同事,我保证我们的这位先生是良民,确乎是不小心拿错了。原来是他刚刚在咖啡馆买单时,误把桌子上的一位女士的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出这些奇葩“娄子”,我相信江河兄绝然不是撒娇,虽然我们都开他的玩笑,说他是被亚娅——他的年轻太太“惯”出来的,但也委实有点冤枉别人了。不是别人惯他,而是他自己“惯着”自己。而且是有选择的,因为他关于旅行方面实在是十足的“老江湖”,一旦出国,他便细心得毫发无误,从没出过什么问题。那一次,在开罗不远的胡夫大金字塔下,我被一群居心不良的当地小贩给困住了,他却轻松地躲了过去,且又回来帮我解围,不然可真要麻烦了。他用英语大声地说着,“No,you must be stop!”那些仿佛从电影《木乃伊》中钻出来的长衫贩们,在一个东方面孔的小个子面前,居然一哄而散了。
那一刻我顿然觉得江河兄变得十分高大。
说到他的英语,他自己经常说自己会一点,但是很“烂”,可他喜欢用烂英语交流,一旦喝到三两以后,那英文水平会突然好出若干个量级。西川说,“江河是可以用100个英语单词讨论哲学问题的”,西川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跑遍了全世界,英语自然属殿堂正宗,别人的那点儿货,在他那里都不叫事儿。但他这么说,可不纯然是调笑江河,而是在夸赞他的交流能力。
诚哉斯言,我多次领教过江河兄英文的厉害——他确乎用最少的英文词汇,实现了最大的交流效果。这在中国的诗人和作家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大都羞涩,不太擅长与外国人当面交流,尤其更不愿意“拽”外文,即便是有的人英文稍好点,和老外在一起也都是寡言少语,打完招呼就哑火了。但江河却不会,他会一直借着酒劲儿飚英文,仿佛武松的醉拳,喝一分酒就有一分的力气,他是喝一分酒就有一分的熟练度。
而且到最后,那些个老外,无不与他勾肩搭背,成了哥们儿。
1987年,我在《诗刊》上读到了欧阳江河的一首《玻璃工厂》,这是他在继长诗《悬棺》之后又一次惊到我。1990年代初,我在一本诗选中读到了博尔赫斯的那首著名的《镜子》,感觉到这首诗与《玻璃工厂》似乎存在着某种奇怪的“互文”。很多年后,我越来越觉得这两首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可对读性”,但我确信,江河在写《玻璃工厂》的时候,并没有读到博尔赫斯的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所见略同”,是因为他们都是智者,他们的写作属于接近的类型——即“元诗型写作”,喜欢将事物穷究极问,作追根刨底的分析,以及“关于分析的分析”。
博尔赫斯写的是“镜子”,欧阳江河写的是“玻璃”,镜子当然是玻璃做的——在现代的意义上,而玻璃本身也有镜子的性质;但镜子是单面的,玻璃是透明的,更加有虚无感。所以,两首诗都充满挑战,须直接面对“镜像”“幻影”“虚无”“悖反”这类哲学性的元命题。这使得它们都没有办法不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元诗”。而且通过不断的对读,我发现,它们在结构上也有着共同的“流转的分析性”,大量使用流动的“转喻”,不断地展开关于镜像与存在的讨论与分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诗人之间,确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老博尔赫斯从镜子说到了水面,又说到了大理石的桌面,再回到手中一面具体的镜子,再到“照妖的镜子”,“上帝的反影”一般的镜子,或者镜子一般的造物主的反影;而欧阳江河则是由玻璃延展到“工厂附近是大海”,再到火焰中的石头、流动的液体……他们都是在说镜像或者诗歌的诞生、语言与思想的诞生、人的主体性的诞生,还有这一切本身的虚无与虚幻,等等。
我知道不能把“印象记”弄成诗学分析——我的意思是,欧阳江河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诗人,他的解构性、当代性与综合性,其实已超出了博尔赫斯。他从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具有了这种气质,不止《玻璃工厂》,短诗《手枪》 《汉英之间》,长诗《那么,威尼斯呢》 《凤凰》,以及近年的《埃及行星》 《圣僧八思巴》《苏武牧羊》也都是类似的作品。
欧阳江河的方法论意义,在我看来大概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第三代诗人”中最早具有“语言的分析性”的诗人,因此我以为他是可以称为中国式的“玄学派”或“玄言派”的诗人。玄学意味着对于所使用的语言本身,要进行反思性的分析,即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这使得欧阳江河在最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反抒情的诗人”,或者说他对于前人不假思索就使用的抒情语言,进行了当代性的“分拆”,一下将这些语言在敞开的同时,也都尽行“废黜”了——当然,他废黜的是语言中旧的无意识,打开的则是其可能的“元意义”与更多意义。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第二点,即他是有“总体性能力”的诗人。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因为有欧阳江河的诗,所谓的“时代”或“历史”,在诗歌中才会有断代和延续。当然,有这类抱负的诗人可能还有很多,但在海子之后,能够处理“文明主题”的诗人已经没有了,能够真正处理“时代主题”的诗人也已少之又少。而且武断一点说,可以“正面强攻”式地处理时代的诗人,惟欧阳江河而已。当然对他来说,哲学化是一个途经,如《汉英之间》和《玻璃工厂》一类,但这也会导致写作的“非历史化”,或者“无风险的中性写作”。但毕竟欧阳江河也写了《傍晚穿过广场》这样的诗,也啃过《凤凰》那样的硬骨头。我总在想,因为有了这样的诗篇,中国诗人在巨大的历史转折中,才可以说没有缺席。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异质混成”的构想,正因为这一主张,汉语诗歌的语义容量和表现力,才有了质的飞跃。当然完成这一实践的不只是他个人,但在诗学的意义上给出命名的,却不是别人。欧阳江河和“第三代”中其他最杰出的诗人一起,实现了汉语诗歌的当代性变革,赋予了汉语以更大的弹性,更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的载力,以及更具有分析性、自我悖反意味的质地。
我好像没有办法只谈一个日常生活的欧阳江河,而必须顺道儿谈一谈他的诗,这个“印象记”才称得上完整。现在,我必须适时回来,再来说说作为朋友的欧阳江河。与欧阳江河这样的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场域是幸运的,因为可以随时从他那儿得到启发,得到看问题的不一样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不幸的,因为大诗人通常都具有强大的精神吞噬力,会让你的存在变得更加可疑和渺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2015年的盛夏,我和欧阳江河,作家艾伟,还有北师大出版社的两位同事,应邀到约旦参加中国主题书展。那一趟旅行,让我见识了江河的另一面。在主活动结束后,我们去参观了约旦南方沙漠深处的“佩特拉古城”。这古城是东罗马时期的建筑,非常壮观,也是好莱坞大片《夺宝奇兵》的外景地。古城隐藏在一座巨大的山中,令人畏惧而又向往。盛夏时的阿拉伯世界如同火星一般,举目望去寸草不见,亦看不到一滴地表水,只有茫茫的赭色沙漠。我们乘坐着一辆奔驰牌的商务车,如同坐在一艘探险船上,一路设想着会随时变成掉入烤箱的咸鱼,既兴奋又感慨着,来到了那座如同铁锈包裹的赭红色的山前。
车子只能抵达距古城遗址一公里附近的停车场,我们要在近五十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步行前往。我自来身体状况一般,举着伞,一路蹒跚着,往山谷中的古城方向走着。其他的几位也都举着阳伞,奋力走在碎石路上。只有欧阳江河,根本不打伞,闲庭信步般走在烈日下,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说来也奇了,那山外表荒蛮,山谷中却别有洞天,居然有了植物,路边不时能看到一小簇的芦苇,偶尔会有一两棵小树在骄阳下摇曳。穿过山谷的小路,里面陡然出现了一座浩大的罗马古城,在山壁上,开凿了无数巨形的岩窟、宫殿、以及罗马式建筑,据说那时此处可以居住十万人,城中有半圆的下沉式罗马剧场,有市政厅、法院、浴场、甚至还有监狱,简直匪夷所思。
关键是,在最初的兴奋之后,我很快就走不动了,在路边一个凉棚下坐下来喘息,那几位同行的朋友虽然走得远一些,但也都渐渐少了精神头,依次在路边阴凉里休息。惟有不打伞的欧阳江河,一直走到了古城的尽头,然后又大踏步地回转,来到我们的跟前,兴致勃勃地介绍前面他看到的风景。
我吃惊的是,这位江河兄平时从不锻炼,哪来的体能和精力,致使他永远像一架机器那样高速运转,从不知疲倦?
回程中,在古城附近的另一座有居民的小镇上,我们来到一家羊肉馆,约旦方面的朋友给我们点了一大锅羊肉,少说也有四十斤,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吃羊肉的阵势,足见阿拉伯兄弟的真诚和厚道,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了一生中最饕餮的一顿大餐。最后离开前,陪同我们的安曼文化局官员萨米尔,也是一位作家,他建议我们每人吃掉自己盘子里的那一份,我看到只有江河兄,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任务。
回程中的江河,依然志得意满,不见半点倦容。
后来我曾专门与他探讨,为什么他从不锻炼身体,却总有着过人精力。他的回答是,年轻时当兵养成了好身体,而我的结论是,他直到逼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才步入了体制,从没有受到过“单位的蹂躏”。
当然,这一切都属于玩笑,一个人的身体,从根本上还是爹妈给的,又是自己的性格与心态所塑造的,江河是一个永远乐天的“达人”,所以身体感受会比常人好。而且这些年他愈发从容潇洒,放诞无忌,即使血糖高也几乎从不忌口,他自称是“作为幽灵活着的人”,所以也就不会老去。
欧阳江河改变了我们关于诗人的定义,比如说,从屈原到杜甫,再到李煜,那种冤屈的、苦命的或颓废者的形象。他是一个智者,比苏东坡还洒脱,比黄山谷还通达,从他那儿看不到愁眉苦脸和顾影自怜,看到的永远是对人生的恣意享受,对事物的敏捷好奇。仿佛一架诗歌的永动机,欧阳江河在不停歇地、不知疲倦地奔涌着,飞速转动着。他骄傲地、愉悦地享受着命运给予这一切。
“我是老男孩欧阳江河。”他毫不含糊地说,然后就是他那特有的放声朗笑。
如果欧阳江河有一个前世,那么此人是谁呢?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是庄周,那个有几分撒娇、又百分百执着的庄子,那个梦蝶之后,发出了迷惑他人又迷惑自己的天真追问的庄子。
蝴蝶,与我们无关的自怜之火。
庞大的空虚来自如此娇小的身段,
无助的哀告,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梦想从蝴蝶脱身出来,
但蝴蝶本身也是梦,比你的梦更深。
我一直认为庄子是语言的大师,也是最早对语言本身保有警惕和反思的哲人,但他也有“知止”难言的时候。比如在这只于梦中蹁跹的蝴蝶面前,他就犹疑了,他感到无法描述,而只能作出一个含糊其词和故作高深的追问。可是欧阳江河并不畏惧,他越过表达与言说,而直指可疑的叙述与犹疑的话语本身,铺开并且剥离了那只蝴蝶的翅膀,将之拍死为一枚蝴蝶状的“胸针”,在对这一古老的追问作出了现代式解释的同时,也给出了反讽。
这就是欧阳江河,乘着他自制的“凤凰”,或是干脆化身为一只“蝴蝶”,在通向语言的荆棘之路上,在词语的陷阱旁边,在堆积成山的词的废墟之上,在这一切构成的幻象与梦境之中,闪转腾挪,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