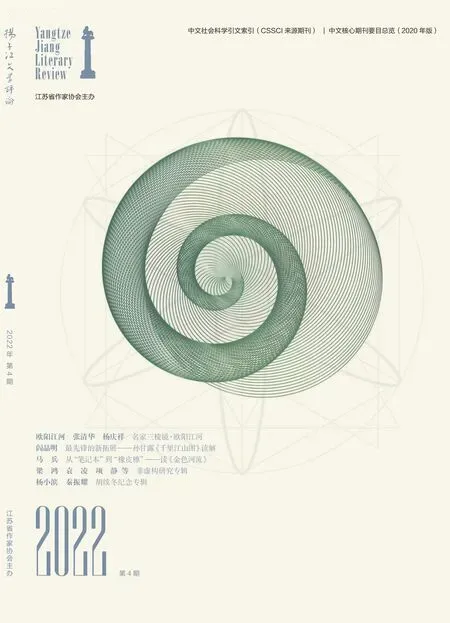借由个体书写,寻找通往存在“本真”的路径
——关于“三明治”平台11年个体生活书写实践的探讨
李依蔓
一个问题,写作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日常吗?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发出“娱乐至死”的呼鸣至今的当下,可以想象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本就以写作作为创作方式或谋生职业的作家或文字工作者,把书写当作每日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就像吃饭、饮水、睡眠、工作一样不可缺少吗?
当下的社交媒体内容生态堪称光怪陆离,娱乐形态不断推陈出新,日常言谈的间隙出现频率更高的词汇是电影、电视剧、音乐,在年轻人中时下流行的聚会项目是剧本杀。今天的人们谈论这些,如同距离我们最近的1980年代“文学热”中的年轻人谈论米兰·昆德拉、萨特,讨论伤痕文学和知青小说。他们写诗、散文、评论,相互通信。如今一个人更有可能收到“一起去看最近上映的那部电影”的邀请,而不是“最近你在读什么书/写什么”的询问。很少人会在日常中谈论写作,或者自己的写作,哪怕是与还算熟悉的朋友。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变化的原因一部分归于最近几十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职业分工趋于更精细的分化,也见于高等教育系统内学科划分以及研究领域更细分的发展。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效率与效用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有着更大声量的环境之中,一个人说自己写作,更有可能被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或能够带来某种实际的用处。不以写作为职业的人群之中,有多少人会将“写作”作为自己生活日常的一部分?真的有这样一群人吗?
至少在成立于2011年的写作平台“三明治”上,每个月有200-300位写作者,每天会花30分钟至2个小时不等的时间用于写作。他们书写的内容大部分可以被认为是“个体生活书写实践”,可能是此刻、当下对生活的观察和记录,可能是对过往某一段经历的回溯和梳理。
这些写作者的职业大部分与写作无关,公务员、医生、教师、品牌策划、公关、会计师、保险代理人、留学规划顾问、创业合伙人、咖啡店主、程序员等等。他们所在的地区也非常多元,既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贵阳、拉萨、乌鲁木齐等国内不同城市,也有英国、土耳其、南非、美国、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城市。过去十一年中,有超过20000位写作者在三明治的平台上通过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主题的“生活写作”,平均每人每天书写的文字量至少为300字,每月书写文字量在10000字左右。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写作”确实是他们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日常。
“三明治”作为一个非官方、自发运营的文化组织,在过去十一年是如何推进个体生活书写实践的?为什么“三明治”要倡导普通人的个体书写,将“生活写作”纳入生活日常?这是本文想要介绍和探讨的内容。希望通过对过往十一年“三明治”积累的当代中国个体生活书写实践经验的梳理,能够为个体书写之于普通个体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这一问题,提供一些主流视角之外的角度和信息。
一、两个项目:“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
目前“三明治”常规的个体生活书写实践,主要有“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两个项目,每个月都会进行公开招募,为参与者提供不同需求的个体书写系统支持,在此先做简要介绍。
“每日书”项目发起于2016年,运行机制是每50-80位参与者组成一个半公开的写作群组,每个人拥有独立的写作页面,每天完成至少300字的写作,每个自然月为一个周期,每月的第一天开始书写,至第30天结束(2月为28或29天)。目前“每日书”参与时间最长的写作者已经书写了超过四年,累计超过50个月。写作内容全部基于参与者的主观自由选择,但大部分参与者的创作内容都和个人生活有关。比如一位深圳的纪录片导演写自己曾经拿着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在南半球“流浪”的生活,那时她刚本科毕业,澳大利亚也刚对中国大陆开放“打工度假签证”申请,这对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来说都是新鲜事。一位在北京的全职妈妈,写下自己在38岁这一年终于学会游泳的经历。一位在日本东京生活了10年的国际投行交易员,写下自己和同事朋友的采访聊天,记录一位华尔街交易员离开金融圈后的状态。一位生活在上海自称“金融民工”的女孩,写下自己在母亲去世一年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装修了一套房子、通过了司法考试客观题部分、进了三次手术室,她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陆续书写。除了这些对个体有特殊意义的阶段或经历的生活书写,还有很多参与者在“每日书”中书写的是看似琐碎的生活日常,他们在写作页面上“这个月我想写什么”的区域中写道:“我的网课教学生活”“发现笔下的自己”“生活絮叨”“没有主题,就先自由自在地书写吧”“凌乱、无序、散漫的思想记录”“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记录自己的小时代”“生活的意识流”。
在“每日书”中的书写是半公开性质的,参与者的书写内容仅对写作社群内的其他参与者开放,参与者可以浏览其他人的写作并进行评论和互动。“每日书”项目不会对参与者的写作内容进行“好”或“不好”的评判,仅在创作上提供灵感启发的支持,比如设置“女性主题” “食物记忆” “世界公民” “城市漫步”等不同主题,并提供可以参考并尝试的思考及书写角度。以连续四年都在三月进行的“女性主题每日书”为例,我们在2020年向参与者们提供了30个问题,比如“你曾被要求剪短头发吗?”“你对年龄有焦虑吗?”“你提到月经或卫生巾会感到尴尬吗?”“你晚上独自出门会害怕吗?”“如果对调性别,你最想以另一种性别的身份体验什么事情?”参与者可以在这30个问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
“短故事学院”项目则发起于2017年,参与者们可以在编辑一对一的陪伴下,在14天内完成一篇5000-12000字左右的非虚构个体生命故事作品。对于缺乏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来说,从“想写一篇故事”到“完成一篇生命故事作品”之间是存在距离的。非职业的写作者有珍贵的写作意愿和写作冲动,同时也需要必要的写作技巧指导,以及往往只存在于职业环境中的作者与编辑的支持关系。因为写作终究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创作,纵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诸如《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非虚构的艺术》等关于如何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出版物,但所有的写作技法的知识都必须落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才能被理解,才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在“短故事学院”的项目中,我们将完成一篇生命故事的过程从写作技巧层面进行拆解,以在线分享的形式向参与者提供“写作工具包”,让没有经过写作专业训练的参与者可以循序渐进地了解写作的不同环节,比如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选题、如何为主题寻找合适的素材资料、如何开一个好头、如何搭建文章的框架结构、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如何为故事收尾、如何修改调整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每天根据建议的任务目标进行写作,再由编辑一对一给予有针对性的反馈,写作者可以根据编辑的反馈再继续推进写作,直至14天左右整个作品最终完成。
专业的作家、媒体从业者或者其他文字工作者通常具备独立完稿的能力,编辑仅在确定选题及修改阶段介入,与写作者进行讨论,视情况而定是否需要修改调整以至定稿。但对于非专业的写作者而言,在整个书写过程中与编辑建立紧密联系是必要的,这种紧密的联系不仅仅提供了写作技巧上的支持,往往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陪伴。
二、个体时代降临:从“他者记述”到“自我表达”
自“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这两个项目发起至今,事实上我们能够观察到过去十余年中国社会中个体表达的变化趋势,即从“他者记述”到“自我表达”的转变。
在三明治创办的2011年,个体在公共平台的表达渠道虽然仍十分有限,但技术对社交媒体的革命性影响已经汹涌而至。2009年,新浪微博的出现让一部分用户从博客的长文本转向140字以内更轻量、更即时性的表达。在更早一些的博客时代,有一定长度的完整文字表达对表达者的逻辑能力、写作技巧甚至文学素养都有很高要求,而微博的出现似乎打开了一个更容易进入的表达通道,也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通个体发出邀请:发出你的声音,说出你想说的话。普通个体在这种更轻型、更无压力的表达媒介中,无意识地练习着“小声说话”,哪怕只是喃喃自语。2011年也是微信正式面世的一年,微信最开始只是一个通讯工具,随着2012年“朋友圈”功能上线、“微信公众平台”被推出,微信为个体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小声说话”不再是对着空旷的广场,而是在更私密的熟人朋友圈子内的半公开表达。此外,摄影、视频等领域的开放也为普通个体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空间,比如2011年面世的Lofter等摄影图片分享平台,2013年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开始扶持“UP主创作者”,即普通个体被鼓励用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或任何想对外分享的知识主题。
麦克卢汉在1967年提出的洞见“媒介即信息”,仍然可以与当下中国彼此映照。媒介平台技术手段和呈现形式在新一轮创业投资的浪潮下飞速迭代,在此先暂且搁置“新媒介”对表达的限制和冲击,我们必须看到,从文字到摄影、视频,2000年代这最初的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普通个体表达启蒙的蓄势阶段:显现出从“看别人表达”到“我表达”的转变趋势。虽然在这个阶段,普通个体的表达更多是碎片化的,社交媒体的传播属性也更侧重于即刻的情绪和观点。
2011年“三明治”成立之初,我们观察和感知到了更蓬勃的对“普通个体”的关注,也从那时开始征集记录普通个体的故事,并发表在“三明治”的官方网站上。最初我们关注到的是“三明治一代”,即出生于1975-1985年之间、正处于30岁上下阶段的人群,这一代“中国三明治”的成长伴随着独生子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为这些个体带来相较于父辈更优渥的物质条件、更充沛的自我发展的机会,比如更多的受教育可能,更多的国际交流和留学机会,更多元的职业道路选择。但同时,这一批人群也面对着几乎没有过往经验可参考的焦虑,像一块“三明治”一样处于职场、家庭、个人发展的夹层之中:父母和孩子如何同时兼顾?上司和下属之间如何相处?城市和故乡之间如何选择?按部就班的稳定工作和追求理想的个人事业之间如何选择?一位“三明治人”在九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2011年一整年,都在提醒自己进入了‘三明治’的状态。这一年我自己的工作开始进入瓶颈期,对按部就班的工作越来越疲惫,对生活的好奇感越来越强烈,渴望成长,渴望尝试新鲜的事物。我每天脑袋里面轰轰隆隆地过小电影,却没有任何创造和输出,这让我开始对自己不满。我一边被捆绑在生活的大板子上,动弹不得;一边想要‘做好自己’的念头越来越清晰。一边拒绝所谓‘成熟’,一边跟着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这一年有很大很大的迷茫,和很大很大的冲突,也有很大的动力和希望。”
这些中国青年人不得不面对的诸多“如何选择”,事实上也是一个个关乎本质的发问: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生活?我要为我的生活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将从这个选择中获得什么?又将要为这个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
十一年前被记录下的许多故事,在今日看来仍然会让人触动。一位叫千寻的女孩离开稳定国企,降薪2/3去做基层公务员,想要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位摇滚青年实验他的“互联网人类学”;一对夫妇辞去令人羡慕的投行以及建筑工程顾问工作,走遍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数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一年的Gap Year,并全程记录直播;一位前奥美广告人决定回到家乡养蚕,复兴浙江桐乡传统的手工蚕丝被制作技艺。2014年,部分普通个体的故事被集结成作品集《30岁后,为梦想寻找现实的出口》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当年这些主人公的故事如今仍然在继续发展变化,我们也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络,对他们生命状态的新进展进行持续记录,或邀请他们自己用文字的方式记刻自己的不同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普通个体的经历和故事更容易被当作媒体某个特定选题报道的“素材”,由报道者对相关的普通个体进行采访,再进行第三人称的记叙,只有部分第一人称的个体声音在直接引语中体现。如果没有媒体的公开报道或者发表,没有来自有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权威他者”的“看见”,普通个体的经历和故事有书写和讲述的意义和价值吗?起码在2011年左右,普通个体也没有这样的普遍意识,少有进行相较于社交媒体上被切割成碎片的表达而言更完整的自我表达的欲望和尝试。因此在2011年“三明治”创立时,我们观察并记录的个体故事大多由三明治的编辑团队或志愿者对故事主人公进行采访并写作而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他者记述”。但这种记录又区别于传统的媒体报道,写作者和讲述者之间是一种有机联结的合作关系,而非有更强目的性的选择和采样。
在2016年“每日书”项目发起之前,我们还尝试建立“三明治同行者”社群,召集认同反思的价值、在具体生活中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的价值的青年人,不定期邀请对一些特定话题感兴趣的“三明治人”进行自我经历的分享并书写,比如“从谋生到工作,你的工作观是怎么样的?”“股市火爆的年代,你如何进行理财?”“你和父母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中是否有变化?”这些回答经过基本编辑后,被归至“Humans of China(人在中国)”的专题在“三明治”的对外平台进行发表,这个专题名称的灵感来源于摄影师布兰登·斯坦顿,他从2010年起为纽约街头的上万名普通人拍摄影像并记录他们的故事,并出版了作品集《》 (人在纽约)。这也是受到从“他者记述”到“自我表达”转向的鼓励和启发,一种新型的新闻和内容创作实践。
直至2016、2017年“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项目发起,三明治的内容创作基本上完成从“他者记述”到“自我表达”的转向,更多的普通个体开始在这两个项目中进行更常规、更集中的生活写作和个体表达,在这些书写尝试中去寻找并确认自己的特质和声音。
我们将这种转向视为一种对时代精神和文化趋势的捕捉,而不是单方面人为构造的结果。
三、更深刻地面对“自我”议题,将书写当作日常
在一个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也有更多动荡和变化的时代,曾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大厂、大院给人带来的集体性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不再是“理所应当”的存在。200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局面,并具体地体现在每个个体细微的生活状态之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曾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谈到“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他用一种流动性的方式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尚未沉淀或凝固为明显可见的人类社会文化状态与个体私人经验的关系,“我们正在界定的也是一种社会经验……这种经验又常常不被认为是社会性的,而只被当作私人性的、个人特癖的甚至是孤立的经验。但通过分析,这种经验(虽然它另外不同的方面很少见)总显示出它的新兴性、联结性和主导性等特征,它的确也显示出其特定的层系组织”。显而易见地,无论主动选择与否,这一代中国青年不得不开始更深刻地面对“自我”的议题。
何为“自我”?从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殿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到16世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借由理性主义的“我思”导出“我”之存在的必然,如今“自我价值”成为现代社会中无须证明其合法性的个体追求之目标。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杰罗德·塞格尔(Jerrold Seigel)在:(《自我的观念:17世纪以来西欧世界的思想与经验》)中,对笛卡尔(Descartes)和洛克(Locke)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中已然形成的、关于“自我”的三个维度进行了阐释——身体或物质层面的自我(bodily or material)、处在关系中的自我(the relational)以及反思性的自我(the reflective)。
第一个维度的自我,即“身体或物质层面的自我”比较直观,即“我”在这个世界中的物理性和物质性存在。第二个维度的自我,即“处在关系中的自我”,指的是一个个体被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所塑造或影响的自我,这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自我”,体现于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方面。
第三个维度的自我,也就是反思性的自我,在这本书的导论部分杰罗德·塞格尔是如此描述的:“第三个维度(的自我)……源于一种人之为人的能力,即同时把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存在当作积极关注的对象,不仅将‘反思之镜’面向世界之中的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且也面向我们的意识。反思性的自我让我们与自己的存在保持距离,以便能对自我进行检视、判断,有时还会指导或修正它。在这个层面上,反思性的自我是‘自我实现’的积极的行动者,在观念和信仰之间建立秩序,并为行为提供指导。它某种程度上似乎是自我构成或自我创造的:我们如何关注自身,我们就将成为什么样子。”这三种不同的“自我”维度中,前两者体现着个体日常生活的基本层面。而普通个体对自我的反思和书写,正是“反思性的自我”这一维度的体现。
柏拉图在《申辩篇》中整理重述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诉,苏格拉底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每一天都讨论善和所有其他你们听我谈论的题目,以及检讨我自己和别人确实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以及一个不能做这种检讨工作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你们更不会相信我。先生们,无论如何,我强调,我说的都是事实;虽然用它来说服你们很不容易。”苏格拉底所说的“检讨”,或者说也可以被翻译成“反省” “反思” “审视”,即通过“助产术”式的辩论和谈话,对许多看似不言自明的概念或事情进行追问。比如在《美诺篇》中追问德性是否可以被教授,在《理想国》中追问什么是正义,在《会饮篇》中追问什么是爱、什么是美。苏格拉底的追问惹恼了许多雅典公民,但也完成了西方哲学重要的转向,即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向对人,对现实的关注。
由于书写这一表达形式天然包含的、对于人类逻辑和理智的心性层面的运用,尤其是当个体进行关于自我的书写时,必然伴随着对“我”的重新检视,对过往经验的梳理,向内进行关于“是何” “何以是”的发问。这是一个不断向内返回自身的自省的过程,亦是不断描绘自我样态和边界的过程。关于自我的未来可能也在这样的日常反思和日常书写中得以展开。
在今年三明治对参与“每日书”项目的写作者进行“个体书写日常”问卷调研中,82%的写作者表示将书写作为生活日常的理由之一是“通过梳理和反思,更了解自我”,排名第二的理由是“享受创作的快乐”,第三、第四是“放松情绪、舒缓压力”和“在小型社群中结识有趣的朋友”。在接受调研的写作者中,51%的写作者表示每天有30-60分钟用于生活写作,22%的写作者表示写作时长在1-2小时甚至更多。我们还邀请这些身在福州、广州、上海、乌鲁木齐、烟台、香港、波士顿、西雅图等等不同地方,职业身份分属咖啡师、外企职员、事业单位职员、IT项目经理、咨询师、建筑设计师、教师、HR等不同类型的写作者们分享,他们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或者环境下,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书写。
“可能随时随地写,上下班路上,甚至上厕所的马桶上,陪老人看病在医院等叫号,路边马路牙子等人,半夜醒来床头,都有可能写一阵子。这些碎片时间一般都是用手机书写。用电脑的时候可能是晚上孩子们睡着以后,或者下班后在单位多待那么一会儿,才能安静地书写。更喜欢用电脑,可以更多地思考。但是迫于现实,用手机更多,因为便捷。”“大概是凌晨两点到四点,在寝室里用电脑写作。”“上下班地铁途中、睡前半小时、凌晨失眠时、清晨被鸟叫醒时、办公室躲厕所划水时、开会听无聊的PPT时,医院排队做CT时写。”“早晨起来做早饭的间隙或者晚上,在家里厨房、客厅沙发,在手机上写。”“一般在书房用电脑写,这样更能专注可以理清思路,忙了就随时随地碎片化写,记录一些当下的瞬间。”“一般是在晚饭后五六点左右写,如果一天很忙的话,就会在九点左右洗完澡写,都是一些人比较舒服,比较放松的状态。会在自己房间的电脑上独立写作。”
通过这些写作者们描绘的情境,我们可以尝试更具体地想象,他们的日常个体书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四、对存在“本真性”的寻求与个体生活书写实践
在西方文论中有生命写作(life writing)的概念,中国学者贺秀明曾在论文《西方文论关键词:生命写作》中梳理了“生命写作”的缘起和发展,我们可以将“生命写作”理解为“捕捉叙事结构和具体图像中的短暂瞬间和生命进化阶段”,包括所有自传或传记性的写作形式和表现行为,例如自传、传记、回忆录、忏悔录、对话叙事、日记、书信、口述历史、监狱叙事、自我肖像、旅游叙事、战争回忆录、行为艺术,以及脸书、推特、微信、微博、博客等数字媒体平台上的各种自我展现形式。伦敦国王学院、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也分别在2017年、2011年成立了和生命写作相关的研究中心,对不同形式的个体非虚构书写实践进行系统研究。
“三明治”所倡导的非虚构个体书写实践,亦可归入“生命写作”的范畴。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这种生命书写不断向“自我”复归的途中,是否还有对个体而言更深的意义寻求?为什么过去十一年中,有超过20000位写作者愿意如行为艺术一般,在“每日书”“短故事学院”以及其他“三明治”倡导和发起的生活写作项目中聚合为社群,并长时间进行生活书写的共同实践?
在这些写作者的书写实践中,我们观察到了一种寻求自我“本真性”的价值理想。以“短故事学院”中的作品为例,写作者们在“短故事学院”中选择碰触、直面、梳理并最终决定书写成完整作品的主题,往往是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或者有特别意义的人生经历。一位生活在上海的人力资源总监写下父亲在去世前主动选择捐赠遗体,并在去世后成为“大体老师”的故事;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大学教师,写下他大学毕业后仍然修了二十多个学位的故事,他在书写过程中尝试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一路追寻“无尽学业”;一位生活在广州的咖啡店主,写下自己作为一名听力障碍者在成长过程中曾经经历过什么,她用一种非常浪漫的方式形容在他人看来也许是“缺陷”的听障——“我的耳朵里有一片旷野”;一位广州的“新手妈妈”写她有一个不敢告诉孩子秘密,她觉得自己“不爱”自己的孩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完全让渡和牺牲自我的“理想母亲”,然而一个母亲一定天然地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并且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去爱吗?
从这些主题可以看到,写作者们在“短故事学院”的生命写作是一种向内的探索,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心理咨询或精神分析的过程。但无论在温暖舒适的心理咨询或精神分析房间内,还是在一个等待填满的空白文档上,坦诚地直面自我并向外表达,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遑论要将这种表达以创作的标准进行打磨,并以完整文字作品的形式予以呈现。
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本真性的伦理》中论述的那样,“自我实现背后的道德理想是对自己真实……我用道德理想指的是什么东西?我指的是一个概念,关于什么是一种较好的或较高的生活模式,在这里,‘较好的’和‘较高的’,不是依照我们之碰巧所欲或所需来定义的,而是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应该欲求什么的标准”。
在《本真性的伦理》中,查尔斯·泰勒还论述了“本真性”的起源和发展。本真性体现了现代个人主义向内发展的主观转向,我们的感受与判断对错的标准不再依从宗教或神,而是我们自身。“存在着某种做人的方式,它是我的方式。我被号召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别的任何人的方式,过我的生活。而这就将新的重要性给予了对我自己真实(being true to myself)。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没有领会生活的目的,我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什么是做人。”
“它将一种无比的道德重要性赋予一种与我自己、与我自己的内部本性的接触……通过引入原发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ity),这个理想极大地增强了这种自我接触的重要性:我们的每个声音都有其自己的东西要说出来。我不但不应该让我的生活符合外部一致的要求;在我之外我甚至不可能找到我据以生活的模型。我只能从内部找到它。”
“对我自己真实意味着对我自己的原发性真实,而这是某个只有我才能够阐明和发现的东西。在阐明它的过程中,我也在定义我自己。”
查尔斯·泰勒关于“本真性”的阐释,与一位“短故事学院”写作者在其写作后记中的分享在内核上发生了遥远共鸣。这位作者说:“有很多事情想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大家好像都习惯了在社交媒体上去展示那些生活中的自以为的高光时刻......但生活从来都是以真实的面目待你,而去尽可能诚实地记录下来,是对自身生活的一种真诚态度。”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曾向我们展示人类作为存在在世的虚无和荒诞,但当如同孤岛一般的个体开始书写自己看似微不足道的生命经验,这种个体生活书写实践就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实践,不加评判地面向自我的存在本身,进行直观的描绘,意义通常就在这种看似“无为”的面对和描绘中自然显现。并且,当我们通过书写抵达对自我的真实,确认并寻回自己的存在经验与感受,无数个隐秘的私人情感将连接成为更宽广的共同整体。
而这种珍贵的个体生活书写实践,也如精神档案一般实时记录着当下中国青年的心灵图景。
【注释】
①[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2页。
②参见 Jerrold Seig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④⑤⑥[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页、37页、37-38页、38页。